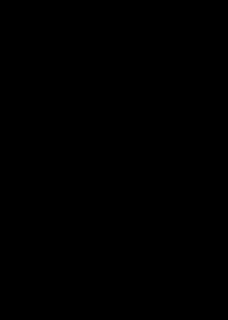
1谢知柔跪在我面前。她那张艳绝京城的脸上,挂着两行泪。水晶一样,说掉就掉。“鸢儿,
再帮姐姐一次。”她的声音发着颤,手死死抓着我的裙角。裙角是粗布的,洗得发白。
她的手指却很白,像玉。我没动。我看着她。她今天穿了身藕荷色的新衣,
裙摆上绣着合欢花。是我娘熬瞎了眼,一针一线给她绣的。她说她要去参加诗会,
不能穿得寒酸。现在,这身漂亮的衣服,跪在地上,沾了灰。“圣旨下来了。
”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陛下他……他点名要我入宫。”她口中的陛下,是裴烬。
那个杀兄弑父上位的暴君。京城里三岁的小孩听到他的名字,都会立刻停止哭泣。
我当然知道圣旨下来了。我死的时候,就是接了这道圣旨之后的事。“姐姐是京城第一美人,
陛下倾心,是福气。”我开口,声音很平。像一汪死水。重生三天,我第一次跟她说话。
她愣了一下。可能没料到我会这么说。她抬起头,那双漂亮的杏眼,此刻全是惊恐。“福气?
那是个疯子!他……他会杀了我的!”她抓我裙角的手更用力了。“鸢儿,
你和我长得这么像。求求你,你替我进宫。爹爹已经答应了,只要你点头……”我笑了。
很轻的一声。谢知柔的哭声停了。她看着我,眼神里除了哀求,还有一丝被冒犯的恼怒。
一个庶女,怎么敢笑她这个嫡女?上辈子,我就是被她这副样子骗了。
她也是这样跪在我面前,哭得梨花带雨。说她有了心上人,宁死不入宫墙。
说我是她唯一的妹妹,只有我能救她。她说,等她的心上人高中状元,一定会来接我出去。
我信了。我一个庶女,娘亲是罪臣之女,在府里活得像条狗。她偶尔的一点好,
就像冬天里的一块炭,暖得我心甘情愿为她去死。我替她上了花轿。嫁给了裴烬。
裴烬是个疯子。但他没有碰我。他只是把我关在长信宫,每天来坐一会儿,看着我,不说话。
他的眼神很冷,像在看一个死物。后来,谢知柔的心上人真的高中了状元。他来接的,
却是谢知柔。他们风风光光地成婚,十里红妆。而我,在他们大婚那天,
被安上了一个“祸国妖妃”的罪名。裴烬亲自下令,将我凌迟处死。三百六十刀。
我死在刑场上。围观的人很多。我看见了谢知柔。她挽着她的状元郎,站在人群里,
笑得一脸幸福。她的嘴唇动了动。我读懂了。她说:“庶女,就该有庶女的命。”刀很冷。
一刀一刀,割在我身上。血流干的时候,我听见裴烬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他说:“骗我,
该死。”现在,谢知柔又跪在我面前。求我再替她死一次。“姐姐,”我蹲下身,
扶住她的胳膊。她的胳膊很软,很滑。不像我的,又干又瘦。“你知道的,我替你,
心甘情愿。”我说。她眼睛一亮。“但是,我有个条件。”“你说,别说一个,
十个我都答应你!”她急切地抓住我的手。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把你这身衣服,
脱给我。”她脸上的喜悦僵住了。“还有,你房间里那套赤金头面,那支西域进贡的琉璃簪,
还有……”我每说一样,她的脸色就白一分。那些,都是她最宝贝的东西。“鸢儿,
你……你要这些做什么?”她声音里带着戒备。“姐姐嫁的是状元郎,以后是状元夫人,
自然有更好的。我嫁的是陛下,总不能太寒酸,丢了相府的脸,对不对?”我的手,
抚上她鬓边那朵珠花。“这朵,也很好看。”她的身体在发抖。是气的。一个庶女,
竟然敢肖想她的东西。我看着她,等着她的答案。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要反悔了。
她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给你。”我笑了。“好姐姐,真疼我。”我扶她起来,
帮她拍了拍裙子上的灰。“你放心,这福气,我替你接了。”我一定,会好好“享”的。
2大婚那天,天是红的。喜帕盖下来,眼前也是一片红。我坐在婚床上,像上辈子一样。
手心全是冷汗。耳边是吹吹打打的喜乐,很吵。但我什么都听不见。脑子里,
只有刀锋划过皮肤的声音。嘶。嘶。一声又一声。我掐住自己的掌心,剧痛让我清醒了一点。
不能怕。谢知鸢,你不能怕。这是你选的路。吱呀一声,门被推开了。喜乐声远了。
房间里很安静。静得能听到我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像在敲丧钟。
一双黑色的靴子停在我面前。靴面上绣着金色的龙纹。是他来了。裴烬。
我闻到一股淡淡的龙涎香,混着一丝血腥味。他刚从刑场回来?还是杀了哪个不听话的大臣?
喜帕被人用一杆玉如意挑开。光线刺进来,我眯了眯眼。我看清了他的脸。很年轻,很英俊。
剑眉星目,鼻梁高挺。只是嘴唇很薄,没什么血色。和他杀人时的样子,判若两人。上辈子,
我到死,都没这么清楚地看过他。他也在看我。眼神很深,像不见底的寒潭。他伸出手,
朝我的脸探过来。我身体一僵。整个人像被冻住了。他的手,修长,骨节分明。
很好看的一双手。可我只记得,就是这双手,握着朱笔,批下了将我凌迟的旨意。他的指尖,
冰冷,像上辈子那把刀。我控制不住地发抖。牙齿咯咯作响。他的手停在半空中。
“你叫什么?”他开口。声音也冷,像冰块撞在一起。“臣女……谢知柔。”我低着头,
说出那个我憎恨了半生的名字。“谢知柔。”他重复了一遍,尾音拖得很长,
带着一丝说不清的意味。“抬起头来。”我顺从地抬起头。他凑得很近。
我能看到他漆黑的瞳孔里,映出我自己的脸。一张苍白、惊恐的脸。“你怕我?”他问。
废话。谁不怕疯子。但我不能说。我摇摇头,努力挤出一个笑。比哭还难看。
“臣女……是太欢喜了。”他盯着我,没说话。房间里的空气好像凝固了。压得我喘不过气。
他突然捏住我的下巴。力气很大,像是要把我的骨头捏碎。“欢喜?”他扯了扯嘴角,
那不是笑。“朕怎么看着,你像要哭出来。”“没有。”我忍着痛,吐出两个字。“是吗?
”他的另一只手,抚上我的脖子。大片的皮肤,暴露在冰冷的空气里。他的指腹,
在我脖颈的动脉上,轻轻摩挲。一下。又一下。我浑身的血都凉了。他想杀我。现在就想。
“你和传闻里,不太一样。”他说。“传闻里……臣女是什么样?”我用尽全力,
才让自己的声音不发抖。“传闻里,相府嫡女谢知柔,骄纵跋扈,明艳张扬。”他的手,
顺着我的脖子,往下滑。停在我的锁骨上。“可你,像一只受了惊的兔子。”他吐出的气,
喷在我的耳廓上。又热又痒。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兔子?”他轻笑一声。“朕最喜欢,
捏断兔子的脖子了。”他的手,猛地收紧。我呼吸一滞。眼前发黑。死亡的恐惧,
瞬间攫住了我。上辈子的痛,好像又回来了。就在我以为自己又要死一次的时候,
他松开了手。我跌回床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喉咙里全是血腥味。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像在看一只蝼蚁。“记住你的身份。”“你是朕的皇后,不是一只随时能被捏死的兔子。
”他丢下这句话,转身就走。走到门口,他停下脚步。没有回头。“还有,
朕不喜欢你身上的味道。”“换掉。”门被关上。我瘫在床上,浑身都被冷汗浸湿了。
我摸了摸脖子。**辣地疼。他不喜欢我身上的味道。当然。谢知柔最爱的,
是清雅的兰花香。而我今天,为了恶心她,特意用了她送我的,最廉价的桂花香膏。我低头,
闻了闻自己的袖子。一股甜腻的、廉价的味道。我突然想笑。裴烬。你上一世,
闻了整整一年。怎么现在,就不喜欢了?3我在长信宫住了下来。和上辈子一样。这里很大,
也很冷清。除了几个不会说话的哑巴宫女,再没有活人。裴烬没有再来过。他好像把我忘了。
每天,都有人送来饭菜,汤药。饭菜很精致,但我一口都吃不下。汤药是补身子的。
我每次都倒掉。我不需要补身子。我需要一把刀。第三天,管事太监李德全来了。
他捧着一个托盘,上面盖着黄布。“娘娘,陛下赏赐。”他尖着嗓子说,脸上堆满了笑。
但那笑意,不达眼底。上辈子,他也来过。送来的是一匹蜀锦。我当时还很高兴,
以为裴烬对我,有那么一点不一样。我真是蠢。“什么东西?”我问。李德全掀开黄布。
托盘里,是一只白玉碗。碗里,盛着黑乎乎的东西。一股浓重的人参味,混着别的什么药材,
冲进我的鼻子。“这是陛下特地吩咐太医院,为娘娘熬的补药。说是……最补女子的身子。
”李德全的腰弯得更低了。我看着那碗药。黑色的药汁,映不出我的脸。我端起来,
凑到鼻尖闻了闻。人参,鹿茸,还有……红花。分量很足的红花。好一碗“大补”的药。
女子喝了,这辈子都别想有孩子了。“陛下有心了。”我端着碗,对他笑了笑。
李德全的表情有些意外。他可能以为我会哭,会闹,会把药碗砸了。
就像所有被打入冷宫的女人一样。我没有。我当着他的面,把那碗药,一饮而尽。药很苦,
很烫。像火一样,从喉咙烧到胃里。我面不改色地把空碗递给他。“替我谢谢陛下。
”李德un全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异。他接过碗,什么也没说,退了出去。他走后,
我立刻冲到墙角,把手指伸进喉咙里。抠。使劲抠。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我把刚才喝下去的东西,全都吐了出来。吐得天昏地地。眼泪鼻涕流了一脸。我瘫在地上,
像一条缺水的鱼。胃里**辣地疼。但我心里,却很痛快。裴烬。你以为一碗绝子汤,
就能困住我?上辈子,你让我死。这辈子,我偏要好好活着。活到你后悔的那一天。
我擦干眼泪,扶着墙站起来。走到梳妆台前。镜子里的人,脸色惨白,头发凌乱。
眼睛却很亮。亮得像有火在烧。我从妆奁的夹层里,摸出一个小小的纸包。打开。
里面是一些黑色的粉末。这是我入宫前,特意准备的。是从一个走方的郎中那里买来的。
不是毒药。而是一种能让人“假孕”的药。只要连续服用七天,脉象就会和有孕一模一样。
我倒了一点粉末在手心,用水和着,吞了下去。很苦。比刚才那碗绝子汤,还苦。
但这是我的希望。裴烬,你不是想让我断子绝孙吗?我偏要给你一个“惊喜”。
我要让你亲手捧上一个不存在的皇子。再亲手,把他摔碎。我要让你也尝尝,
从云端跌落的滋味。4我“怀孕”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后宫。是我自己传出去的。
我让一个哑巴宫女,故意“打碎”了一只给我安胎用的药碗。碎片被一个洒扫的太监捡到,
送去了皇后那里。皇后是太后的侄女,一向看我不顺眼。不出半天,整个皇宫都知道,
我这个被陛下厌弃的“谢知柔”,有了龙种。那天下午,谢知柔来了。
她穿了一身水蓝色的宫装,打扮得很素净。脸上却带着藏不住的得意。
她现在是宫里的柔贵人。听说,很得太后喜欢。“姐姐。”她走进来,柔柔地叫了一声。
眼睛,却直直地盯着我的肚子。“听说姐姐有喜了,妹妹特地来看看。”她身后跟着的宫女,
捧着一个食盒。“这是太后赏的上好血燕,最是安胎。妹妹亲手炖了,给姐姐送来。
”她笑得很甜。和上辈子一样。上辈子,我也有过一个孩子。在我被打入冷宫之后,
才发现的。我当时害怕极了。是谢知柔,每天偷偷来看我,给我送吃的,安慰我。
她说她会保护我和孩子。她也给我送来一碗燕窝。她说,这是她求了太后好久,才得来的。
我喝了。当天晚上,我就流产了。血流了一地。孩子没了。裴烬来看过我一次。他站在床边,
看了我很久。眼神很复杂。我看不懂。他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来过。
直到我死。现在,又是一碗燕窝。一模一样的场景。“姐姐怎么不喝?
”谢知柔把燕窝推到我面前,“难道是怕妹妹下毒?”她说着,自己先用银勺舀了一口,
吃了下去。“你看,没毒的。”她笑得天真无邪。“妹妹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端起燕窝,
放在鼻尖闻了闻。是血燕的味道。很纯。没有加别的东西。我看着她。“只是我现在,
没什么胃口。不如,这碗燕窝,妹妹替我喝了吧。也算沾沾龙气的福分。”我把碗,
推回到她面前。谢知柔的脸色变了。“姐姐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给你的,我怎么能喝?
”“有什么不能的?”我拿起勺子,舀了一勺,递到她嘴边。“你我姐妹情深,
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自然也是你的。来,张嘴。”我的动作很慢。勺子里的燕窝,
晶莹剔ટું,还在冒着热气。谢知柔的身体往后缩。眼睛里全是抗拒。“姐姐,
我……我不能喝。”“为什么不能?”我追问。我的手,很稳。勺子,离她的嘴唇,
只有一寸。“这燕窝,太补了。我……我身子虚,受不住。”她找了一个蹩脚的理由。
“是吗?”我笑了。“我怎么听说,这血燕性平,最是温补。怎么到了妹妹这里,
就成了虎狼之药了?”我的目光,落在她平坦的小腹上。“还是说,妹妹这肚子里,
也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怕被这碗燕窝给‘补’出来?”谢知柔的脸,“唰”地一下,
白了。她猛地站起来,打翻了桌上的碗。啪!碗摔在地上,四分五裂。燕窝洒了一地。
“谢知鸢,你胡说什么!”她失态地尖叫。她从不叫我谢知鸢。她总是“鸢儿、鸢儿”地叫。
亲热得像亲姐妹。只有在气急败坏的时候,才会连名带姓。我慢慢站起来。走到她面前。
比她高了半个头。我低头看着她。“我胡说?”“那你告诉我,你和你的状元郎,
暗中来往了多久?”“你以为,你做的事情,都无人知晓吗?”我每说一句,
她的脸色就更白一分。她踉跄着后退一步。“你……你怎么知道?”“我知道的,多着呢。
”我逼近她,在她耳边,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我还知道,
你送来的这碗燕窝里,什么都没加。”“因为真正有问题的,是盛燕窝的这个碗。
”“碗的内壁,涂了一层‘化胎散’。无色无味,遇热则化。只要我喝了这碗燕窝,
不出一个时辰,我的孩子,就没了。”我说完,直起身子,看着她。她已经完全呆住了。
嘴唇发白,浑身发抖。像见了鬼一样。“你……你到底是谁?”她颤声问。我笑了。
“我是你姐姐啊。”“一个,从地狱里爬回来,找你索命的姐姐。”5事情闹大了。
谢知柔在我宫里“失足”摔碎了太后赏的燕窝,还“冲撞”了我这个有孕的贵妃。
裴烬来的时候,她正跪在地上哭。哭声凄惨,闻者伤心。我坐在椅子上,慢悠悠地喝着茶。
一口,一口。好像眼前这出戏,与我无关。裴烬一进门,屋子里的气压瞬间就低了。
他今天穿了一身黑色的常服,上面用银线绣着暗纹。让他整个人,看起来更冷了。“陛下!
”谢知柔像是看到了救星,连滚带爬地扑过去,抱住他的腿。“陛下,你要为臣妾做主啊!
姐姐她……她污蔑我!”裴烬低头,看着她。面无表情。他没让她起来,也没把她推开。
他的目光,越过谢知柔,落在我身上。“怎么回事?”他问。是问我。我放下茶杯,站起来,
对他行了个礼。“回陛下,妹妹来看我,一时手滑,打碎了碗。”我说得轻描淡写。
“不是的!”谢知柔尖叫起来,“是她!是她故意把碗推到我面前,逼我喝!
她还说……她还说我肚子里有野种!”她这话一出口,空气都凝固了。裴烬的眼睛,
危险地眯了起来。他一脚踢开谢知柔。动作很轻,但谢知柔还是滚了两圈,撞在桌角上。
她痛得闷哼一声,不敢再哭了。“野种?”裴烬走到我面前。他身上那股龙涎香,更浓了。
我闻着,有点想吐。“你说的?”他问。“是。”我点头。我以为他会发怒。
会像上辈子一样,不问青红皂白,就给我定罪。但他没有。他只是看着我。看了很久。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妹妹她,一来就说身子不适,闻不得补药。
可臣妾听府里的老人说,只有刚怀上孩子的人,才会对这些东西如此敏感。”我顿了顿,
抬眼看他。“陛下若是不信,可召太医前来。一问便知。”裴烬的目光,
转向趴在地上的谢知柔。谢知柔的身体,筛糠一样抖了起来。“不……不要……陛下,
臣妾没有,臣妾是冤枉的……”她的声音,已经带上了哭腔和绝望。裴烬没理她。
他对身后的李德全说:“传太医。”李德全躬身退下。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
死一样的寂静。我能听到谢知柔压抑的、崩溃的抽泣声。裴烬一直看着我。他突然伸出手,
挑起我的一缕头发。放在鼻尖,闻了闻。“你换了熏香。”他说。是陈述句。“是。”我答,
“陛下不是说,不喜欢之前的味道吗?”我换了最清淡的檀香。很淡,几乎闻不到。
“这个味道……”他凑得更近了。呼吸,喷在我的脸上。“朕喜欢。”他的指尖,
擦过我的脸颊。很烫。和上辈C子的冰冷,完全不同。我心头一跳。下意识地想躲开。
他却捏住了我的下巴。力道不大,带着一种不容抗拒的强势。“告诉朕,你到底是谁?
”他的声音很低,只有我们俩能听见。“你不是谢知柔。”我的心,漏跳了一拍。
全身的血液,好像都冲上了头顶。他知道了。他怎么会知道?我强作镇定。“陛下在说什么,
臣妾听不懂。”“听不懂?”他冷笑一声,“谢家的嫡女,是京城里出了名的草包美人。
胸大无脑,一根肠子通到底。她绝说不出刚才那番话,也绝没有你这样的眼神。”他的拇指,
在我下唇上,轻轻摩挲。“你的眼睛里,有东西。”“有恨,有火,还有……”他顿住了。
好像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词。“还有,朕。”我的瞳孔,猛地收缩。“所以,你是谁?
”他盯着我的眼睛,再一次问。“是谢知鸢派你来的?”谢知鸢。他念出我的名字。
我上辈子,真正的名字。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他为什么会知道我?
一个养在深闺,从未出过门,死了都没人记得的庶女。他怎么会知道?
太医就在这个时候来了。打断了我们的对峙。裴烬松开我,退后一步。好像刚才的一切,
都只是我的幻觉。“去,给她看看。”他指着地上的谢知柔,对太医说。
太医战战兢兢地走过去,跪下,开始给谢知柔诊脉。谢知柔已经面如死灰。我的手,
藏在袖子里,死死地握着。指甲,陷进了肉里。裴烬。你到底,是谁?6太医诊脉的结果,
不出所料。谢知柔,有了一个月的身孕。裴烬的脸,当场就黑了。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
他一句话没说。只是看着谢知柔。那眼神,像在看一个死人。谢知柔瘫在地上,
连求饶的话都说不出来了。“拖下去。”裴烬开口,声音没有一丝温度。“打入冷宫,
没有朕的旨意,不许任何人探视。”两个侍卫走进来,像拖一条死狗一样,
把谢知柔拖了出去。她没有挣扎。好像已经认命了。屋子里,又只剩下我和裴烬。还有一股,
若有若无的血腥味。是谢知柔撞在桌角上,流的血。“满意了?”裴烬走到我面前,问。
“陛下为臣妾做主,臣妾感激不尽。”我低下头。不敢看他的眼睛。我怕他再问,我是谁。
我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回答。“你倒是聪明。”他冷笑一声,“借朕的手,除掉她。
一石二鸟。”“臣妾不敢。”“你有什么不敢的?”他抬起我的下巴,强迫我看着他。
“你连‘假孕’都敢,还有什么不敢的?”我的心,沉到了底。他知道了。
他连我假孕的事情,也知道了。“你怎么……”“想问朕怎么知道的?
”他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你那点小把戏,能瞒得过太医,瞒不过朕。”他松开我,
走到窗边。负手而立。“朕身边,有个擅长用药的高手。你那点东西,在他面前,
就是班门弄斧。”我沉默了。原来,我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在他眼里,只是一个笑话。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跳梁小丑。被人看穿了所有底牌。“为什么?”他问,没有回头。
“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了……报复她。”我选择了说实话。在他面前,撒谎没有意义。
“她抢走了我的心上人,害我替嫁入宫。我恨她。”我说的是上辈子的事。但我赌他会信。
因为,这是最合理的解释。果然,他没有怀疑。“心上人?”他转过身,
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就是那个新科状元,林萧然?”我没说话。“为了一个男人,
值得吗?”他问。“不值得。”我说,“所以,我后悔了。”“后悔了?”“是。
”我看着他,迎上他的目光。“我现在,只想好好地活着,当陛下的女人,为陛下生儿育女。
”我的话说得很诚恳。眼睛里,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裴烬看着我。眼神很深,
看不出情绪。过了很久,他笑了。“好。”“朕给你这个机会。”他说:“从今天起,
你搬出长信宫,住进凤仪殿。”凤仪殿。是皇后的居所。“谢知柔的孩子,不能留。
”他又说。“朕会派人,‘处理’干净。”他说“处理”两个字的时候,语气很轻。
却让我不寒而栗。“还有,”他走到我面前,用手指,轻轻点了点我的小腹。“朕希望,
下一次太医来诊脉的时候,这里,是真的有东西。”他的指尖,带着灼人的温度。隔着衣料,
烫得我皮肤发疼。“懂吗?”我点点头。“臣妾,遵旨。”他满意地笑了。转身离开。
我站在原地,很久都没有动。手心,全是汗。裴烬,比我想象的,要可怕得多。他像一张网。
一张看不见的网。而我,就是网里的鱼。无论我怎么挣扎,都逃不出他的掌控。晚上,
我搬进了凤仪殿。这里比长信宫,要奢华一百倍。地上铺着西域来的地毯,
墙上挂着前朝的名画。连空气里,都飘着一股钱的味道。我却觉得,比长信宫还冷。
躺在又大又软的床上,我一夜没睡。第二天,消息传来。柔贵人“不慎”落水,孩子没了。
人也疯了。被陛下下令,送到皇陵,为先帝守陵。永世不得回宫。我听到消息的时候,
正在喝一碗补药。是裴烬亲口吩咐,太医院为我“固本培元”的。很苦。
我面不改色地喝了下去。谢知柔。我说过,这福气,要给你。现在,你收到了吗?
皇陵的滋味,比冷宫如何?这只是开始。我们之间的账,还没算完呢。
7我成了凤仪殿的主人。但不是皇后。裴烬没有给我名分。宫里的人,都叫我“夫人”。
一个很微妙的称呼。既不是主子,也不是奴才。我成了后宫里,最特殊的存在。
裴烬开始频繁地来我这里。有时候,只是过来坐坐,看看书,不说话。有时候,
会留下来用膳。他吃饭很安静,也很挑剔。不吃的菜,碰都不会碰一下。但他从不留宿。
每次天一黑,他就会离开。我们之间,像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膜。他想戳破。我不敢。
我怕他一碰我,我就会想起上辈子那些血腥的画面。我会发疯的。这天晚上,他又来了。
带着一身酒气。他喝醉了。眼睛里有血丝,脚步有些不稳。“陛下。”我扶住他。他很高,
我需要踮起脚。他顺势靠在我身上。很重。像一座山。“水。”他哑着嗓子说。
我扶他到床上坐下,给他倒了一杯水。他没有接。只是靠在床头,闭着眼睛,眉头紧锁。
好像很痛苦。“陛下,您怎么了?”我问。他没回答。呼吸声,越来越重。我伸手,
想探探他的额头。手刚碰到他,他就猛地睁开了眼睛。那双眼睛,在黑夜里,亮得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