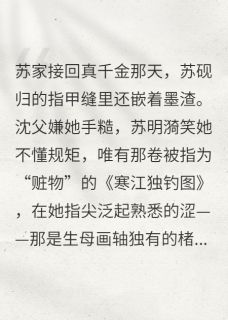
苏家接回真千金那天,苏砚归的指甲缝里还嵌着墨渣。沈父嫌她手糙,苏明漪笑她不懂规矩,
唯有那卷被指为“赃物”的《寒江独钓图》,
在她指尖泛起熟悉的涩——那是生母画轴独有的楮树香。藏在柴房的半方残墨,
裂口里锁着松烟的清苦。她磨墨时总想起书画铺掌柜的话:“好墨经得住熬,就像人。
”谁也没料到,这双手日后会让御笔都沾染上市井墨香,让偷来的身份、盗去的技法,
在真正的笔锋下显露出原形。1、指腹触到那卷《寒江独钓图》时,像摸到冬夜冻裂的窗纸。
糙,且脆。这不是母亲的贡宣。真正的贡宣该带着楮树的软,像浸过月光的云絮,
哪怕在北方存了十余年,纤维里也锁着三分水汽,捏在手里能觉出那点不肯服帖的韧。
我把画轴翻过来,边角沾着梅香墨的粉痕,
遇手汗晕开个浅红的圈——苏明漪日日捧在手里的那方,墨里掺了胭脂屑,
总像害臊的姑娘红着脸。“偷东西的贱婢!”她的尖叫劈下来,像砚台砸在青砖上。
藕荷色罗裙扫过我手背,那凉比深秋的井水还蚀骨。“爹爹要送太傅老夫人的贺礼,
你也配碰?”我攥紧画轴,指腹碾过那些浅红的墨痕。这是东市“墨香居”学徒的仿品,
上个月我还在那铺子帮工,认得掌柜的规矩——学徒试笔必须用这梅香墨,说是练手也练心,
其实是胭脂屑便宜。“我没偷。”声音从喉咙里滚出来,带着书画铺泡久了的松烟气。
三天前被苏家的人从铺子里拽走时,怀里还揣着没写完的《兰亭序》,
那股清苦至今缠在衣襟上,洗不净,像生了根。苏父从雕花屏风后转出来,
手里的羊脂玉佩被捏得咯吱响。他瞥向我袖口的墨渍,眉峰拧成个死结,
“刚从市井捞回来就不安分,当我苏家是收破烂的?”我垂下眼。三天前他们说我是真千金,
此刻看我的眼神,比看门口讨饭的还嫌恶。就因我指甲缝里嵌着墨渣,
指腹带着握笔磨出的茧?那些茧在书画铺长了十几年,分布在食指第二关节和虎口,
像母亲刻在我身上的私章。“爹,妹妹许是不懂规矩。”苏明漪挽住他胳膊,
鬓边珍珠步摇晃得人眼晕。新做的银护甲在阳光下闪,像在炫耀什么,“她在书画铺长大,
哪见过这般金贵物事?要不就……”“不行!”苏父打断她,目光像刻刀刮过我的脸,
“拖去柴房,没我的话,不许出来!”小厮架起我胳膊时,画轴从怀里滑出来。
我看见苏明漪弯腰去捡,指尖在画角的墨痕处顿了顿,
眼里闪过一丝慌——那寒江的波纹用的是侧锋扫笔,母亲的真迹从不这样,
她的笔永远中锋行,一笔到底,像冰面下的流水,藏着不肯断的劲。
柴房的霉味呛得喉咙发紧。**住土墙,从怀里摸出油纸包。半方残墨露出来,
是书画铺掌柜塞给我的,母亲的遗物。墨块上“松雪”二字在昏暗中泛着暗青,
哪怕裂了道缝,磨出的墨汁也带着松烟的苦,绝不像梅香墨那样发腻的甜。
指尖抚过墨上的裂纹,忽然笑了。苏明漪大约不知道,好墨的晕染都藏着记号,
就像我指腹的茧,模仿不来。2、被拖出柴房时,墨锭的腥气往鼻孔里钻,
混着丫鬟们身上的香粉,像发了酵的浆糊,腻得舌尖发苦。苏明漪坐在石榴树下,
狼毫笔在宣纸上顿着。阳光穿过叶隙,在她身上描出细碎的光斑,
倒比她案上的《百鸟朝凤图》鲜活。那画的墨色僵得像没化的冰,
凤凰尾羽歪得像被风吹乱的翎毛。“妹妹醒了?”她抬头,笑在脸上凝着,甜得发僵。
狼毫在“凤凰”尾羽上顿了顿,“帮我瞧瞧,这‘凤羽’用什么墨色称?”我走过去,
捏起她手边的松烟墨。指腹碾过,墨渣簌簌掉,混着沙砾似的硬粒。“这墨含砂。
”她脸色僵了僵,手指绞着帕子,“怎么会?西域来的上等货,十两银子才得这一小块。
”“上等墨不含砂。”我把墨块凑到眼前,断口泛着白,像被虫蛀过的棉絮,
“真正的油烟墨,磨出来的汁该是亮的,能照见人影。”她的声音尖起来,
“我看妹妹是在市井待久了,不懂这些门道!这是新出的制墨法,看着糙,
实则——”指尖在帕子上抠出个小洞,“……总之是好东西。”我没接话。
去年书画铺收过类似的“西域墨”,写出来的字不到半年就发灰,举子当场砸了砚台,
墨里的砂粒把砚面划得全是痕,像道永远填不平的疤。“站住!”她带倒了砚台,
墨汁泼在宣纸上,像朵炸开的黑花,“太傅府的定亲宴近了,你给老夫人抄部《金刚经》吧。
也让她瞧瞧,我苏家的女儿,不只会做粗活。”丫鬟递来的墨锭触手就知是劣货,掺了烟灰,
写在纸上发涩,连“悬针竖”都拉不直,像被风吹歪的麦秆。苏明漪眼里的得意漫出来,
像偷食得逞的猫。我应了。回小院的路上,梧桐叶落了满地,枝桠指向灰蒙蒙的天,
像谁随手画的败笔。夜里,油灯在案头跳。我从油纸包取出生母的“松雪”残墨,
刮下细屑混进劣墨里。墨屑极细,不细看发现不了。我要抄一部特别的《金刚经》,
让他们知道,好笔法能让劣墨生出风骨——就像那些年在书画铺,我用学徒的残墨,
照样写出掌柜称赞的字。3、把抄好的《金刚经》呈给苏父时,
苏明漪的眼睛亮得像要喷出火。经卷上的小楷,近看是浓黑的墨迹,远了瞧,
有层暗青在笔画间流,像月光浸过的冰面。撇捺收笔带着“松雪墨”特有的飞白,
每个字都透着股站得笔直的气。“这……怎写出来的?”苏父指腹在笔画处顿了顿,
他不懂书法,却也看得出这字比苏明漪的多了种劲,像路边的野草,根扎得深。
“掺了点松烟墨。”我的声音轻得像墨线,“刮成细屑混在里面,不惹眼,却能看出笔力。
”苏明漪的笑突然炸开,“妹妹真是好本事,只是这墨……看着眼熟,
好像是我上月丢的那方‘云头艳’?”我指尖一颤。“云头艳”是西域贡墨,
她宝贝得锁在樟木箱里,钥匙串在腕上,怎会丢?她眼里的算计像没藏好的线头,
支棱着刺人。“明漪说什么呢?”苏父把经卷往怀里拢,瞪她一眼,“砚归刚回来,
哪来的贡墨?这字看着寻常,哪有你写的娟秀?”她低下头,声音委屈得发颤,
指尖却在帕子上抠,把朵兰花抠得脱了线,“许是我记错了……爹爹别气,妹妹有这份心,
女儿替您欢喜。”我没作声。怨毒藏在她眼底,像绣错了色的线,遮不住的。定亲宴前三日,
苏明漪的《百鸟朝凤图》挂在客厅中央。宾客们围着称赞,眼角的余光却在挑刺。
凤凰尾羽用了侧锋,仙鹤腿骨是枯笔,满幅墨色发闷,像堆在一起的煤渣。
“妹妹觉得怎么样?”她把画轴往我面前凑,腰间玉佩撞得叮当作响。
“这画不是你一人画的吧?”我的声音不高,够周围人听见。她的脸唰地白了,“你胡说!
”“凤凰尾羽用侧锋,仙鹤腿骨用中锋。”我指尖点过画轴,“侧锋的墨色发死,
中锋的带着活气,明显出自两人之手。侧锋的手劲忽轻忽重,一看就是生手。
”窃窃私语漫过来,像潮水上了岸。她突然拔高声音,脸涨得通红,“你们懂什么!
这是新创的画法,凤凰张扬用侧锋,仙鹤端庄用中锋!”话没说完,一个喷嚏打出来,
画轴晃了晃,边角的梅香墨痕又晕开了些,像块没擦净的胭脂。女眷们笑着打圆场,
把话岔了过去。我转身出了客厅,知道多说无益。定亲宴那日,自会有分晓。
书房的门虚掩着,墨香混着旧书味漫出来,像母亲画架旁的气息。书架最高层,
紫檀木盒子的锁扣上,刻着朵小小的墨莲——和生母残墨上的花纹一模一样。我搬来凳子,
踮脚取下盒子。铜锁咔嗒开了,《墨法秘录》躺在里面,封面的字迹是母亲的,
墨色里藏着松烟的清劲。第一页上写着:“墨法,贵在活。一笔一划,需如行云流水,忌僵。
”指腹抚过字迹,泪突然砸在纸页上,晕开一小团湿。原来母亲一直在这里等我。
那些年在书画铺的苦,那些被人嘲笑的“粗鄙”,突然都有了归宿。4、太傅府的定亲宴,
红绸从大门缠到后院,风一吹,像条活过来的火龙。宾客们的衣香鬓影里,
虚伪的笑沾着脂粉气,眼角却都往客厅中央瞟——苏明漪那幅《百鸟朝凤图》挂在最显眼处,
墨色僵得像没化的冰。苏明漪裹着大红礼服,凤冠上的宝石晃得人眼晕。
她时不时踮脚望门口,嘴角的笑僵着,像被冻住的湖面。我立在角落,
月白衫子素得像没染色的宣纸。手里的《墨法秘录》被指尖摩挲得发暖,
封面的墨莲磨出了浅痕。心湖静得很,像研好的墨汁,不起一丝波澜。
太傅老夫人的石青色诰命服踏进门时,空气都凝了凝。她的眼扫过红绸,掠过宾客,
最后落在《百鸟朝凤图》上。“这画倒热闹。”她走近,玉扳指抚过画轴,
在凤凰尾羽处停了停。苏明漪往前凑,声音甜得发腻,“画了三个月呢,
里面的鸟儿都有讲究。”老夫人的眉突然蹙起,像被针戳了下,“凤凰的尾羽,怎用了侧锋?
”苏明漪的脸唰地白了,指尖绞着裙角,“我……我瞧着侧锋张扬。”“胡闹!
”老夫人的声音沉下来,带着画院练出来的威严,“你母亲的画,向来用中锋行笔,
一笔到底,力透纸背。这点门道都不懂,也敢说自己是她的女儿?”她的嘴唇哆嗦着,
像被风吹得发抖的线头。那些偷来的技法,终究是浮在表面的油花,经不住细瞧。我走出来,
捧着半方残墨。墨块上的“松雪”二字泛着暗青,是松烟墨特有的光。“老夫人瞧瞧这个。
”老夫人的眼突然亮了,像见了故人的灯,“这是……‘松雪墨’!上面的‘飞白’刻字,
是你母亲独有的手法!失传好些年了!你是……”“苏砚归。”我的声音平得像宣纸,
“这是生母柳如眉的遗物。”她的指尖颤了颤,眼眶红了,“你生母是画院的柳画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