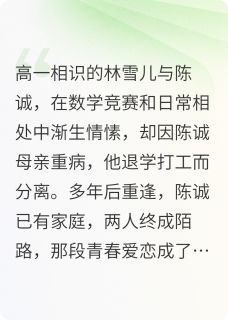
林雪儿第一次听见陈诚的名字时,槐树叶正被九月的风卷得沙沙响。
高一开学典礼的主席台上,少年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站在领奖台中央念发言稿。
阳光把他的影子钉在红色地毯上,她数着他垂在额前的碎发——不多不少,正好七根,
像初春抽出的柳丝。忽然听见身边女生在说:"陈诚是中考状元呢,听说篮球也打得超棒。
"那天的风很软,卷着操场边的槐花香扑在脸上。林雪儿低下头,
在崭新的笔记本上画了个小小的篮球,旁边写着"陈诚"两个字,笔尖戳得纸页微微发皱。
她不知道这个名字会在往后的岁月里,像槐树根一样盘虬在心底,拔不掉,也忘不掉。
就像此刻飘进鼻腔的槐花香,以为是转瞬即逝的偶遇,
却不知早已在嗅觉里刻下了经年累月的印记。他们真正产生交集,
是在三个月后的数学竞赛选拔。林雪儿抱着厚厚的习题集站在公告栏前,
踮着脚看入围名单时,有人从身后轻轻敲了敲她的背:"需要帮忙吗?"她转过身,
撞进一双带着笑意的眼睛里。陈诚举着手里的矿泉水瓶,瓶身上凝着的水珠滴落在他手背上,
像刚落下的晨露。"第三行第七个,是你吧?"林雪儿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果然在密密麻麻的名字里找到了自己。心跳忽然漏了一拍,像老式座钟卡壳的瞬间,
她慌忙点头:"是、是我。""我叫陈诚,"他朝她伸出手,掌心带着点薄茧,
是常年握笔和篮球磨出的痕迹,"以后就是队友了,请多指教。
"那天的阳光把公告栏的玻璃照得发亮,他指尖的温度透过相握的手传来,
像电流一样窜进林雪儿的胳膊。她后来总想起这个瞬间,觉得像是命运悄悄按下了开关,
从此有什么东西开始不一样了。就像解一道复杂的方程,突然找到了关键的未知数,
所有的变量都有了指向。竞赛小组的活动定在每周三放学后。
陈诚的解题思路总是清晰得惊人,复杂的函数题经他一讲,就像拆开折叠的纸飞机一样简单。
林雪儿常常走神,看着他握着笔的手——骨节分明,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
在草稿纸上划过的痕迹都带着某种韵律。她甚至能数清他握笔时指节突出的弧度,
像山峦起伏的剪影。某次她正盯着他的手发呆,陈诚忽然转过头:"这道题的辅助线,
懂了吗?"林雪儿猛地回神,脸颊发烫,像被夕阳吻过的云朵:"啊...不太懂。
"他没笑她,只是把椅子往她这边挪了挪,肩膀几乎碰到一起。"你看,这里应该连接AC,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温热的气息落在她耳边,像羽毛轻轻扫过,"构造全等三角形。
"窗外的槐树叶被风吹得沙沙响,林雪儿闻见他身上淡淡的洗衣粉味,混着阳光晒过的味道,
忽然觉得例题里的辅助线变得格外刺眼。她偷偷用余光看他,
发现他讲解时会下意识地咬着下唇,睫毛在眼睑下方投出浅浅的阴影,像落在湖面的鸟羽。
那瞬间,她甚至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盖过了窗外的风声。那年冬天来得早,
第一场雪落下时,竞赛小组刚结束训练。陈诚抱着篮球往操场走,
林雪儿踩着他的脚印跟在后面,看他在雪地上投篮。篮球砸在篮板上的声音,
混着雪花簌簌落下的声响,在空荡的校园里格外清晰,像一首简单的乐曲。"要试试吗?
"他忽然把球扔过来。林雪儿没接住,篮球砸在怀里弹到雪地上,溅起细碎的雪沫。
她蹲下去捡球时,陈诚已经跑了过来。两人同时抓住篮球,指尖在雪地里相触,
冻得像要掉下来的冰碴,却又带着奇异的暖意,像寒夜里的一点星火。"笨蛋。
"陈诚笑着抽走篮球,往篮筐投了个漂亮的空心球。球穿过篮网的声音,
在寂静的雪地里格外清脆。雪花落在他睫毛上,很快化成小小的水珠。
林雪儿看着他被冻得发红的鼻尖,忽然想起生物课本上说,
冬天人的鼻尖会因为毛细血管收缩而变红。这个念头让她自己都笑了,
陈诚回头看她:"笑什么?""没什么,"她拢了拢围巾,把半张脸藏在温暖里,
"就是觉得...今天的雪很好看。"他抬头望了望天,雪花落进他眼里,
亮得像碎掉的星星:"嗯,是挺好看的。"那天之后,林雪儿的书包里总会多带一条围巾。
有时是灰色的,像清晨的薄雾;有时是藏蓝的,像夜晚的天空,都是她趁着周末挑的。
她总在陈诚打完球回来时,假装不经意地把围巾放在他桌上:"我妈多给我织了一条,
你不介意的话..."陈诚每次都会收下,第二天脖子上准会围着那条围巾。
有次训练结束晚了,林雪儿看见他把围巾摘下来,小心翼翼地叠好放进书包,
动作轻得像在对待什么珍宝。她躲在楼梯口,摸着自己发烫的耳朵,
忽然觉得冬天好像没那么冷了。那条围巾像一条看不见的线,悄悄连接着两个人的世界。
开春后学校组织春游,去郊外的水库写生。林雪儿背着画板走在田埂上,
忽然被路边的石头绊倒。眼看就要摔进泥里时,陈诚从后面冲过来扶住了她。画板摔在地上,
颜料泼了他一胳膊,像突然绽放的野花。"你没事吧?"他皱着眉看她的膝盖,
语气里带着急,像怕珍贵的瓷器摔碎。林雪儿摇摇头,看着他胳膊上的颜料印:"对不起,
把你衣服弄脏了。""这点算什么,"他弯腰捡起画板,忽然笑了,
"不过你的颜料倒是挺会选地方,溅在这儿像朵小花开着。"他指着胳膊上的颜料印,
阳光落在他笑起来的眼角,那里有颗小小的痣。林雪儿忽然想起美术老师说过,
眼角有痣的人,上辈子是替别人流泪的。这个念头让她心里莫名一紧,慌忙移开视线,
像怕被什么看穿心事。写生时林雪儿坐在柳树下,偷偷画了陈诚的侧影。他正对着水库发呆,
风把他的校服领口吹得鼓起来,像只振翅欲飞的鸟。画到他的睫毛时,
笔尖忽然顿住——她好像总能清晰地记得他每个细微的样子,比如他思考时会轻咬下唇,
比如他笑起来时左边嘴角会有个浅浅的梨涡,比如他投篮时会微微皱起眉头。
这些细节像散落的珍珠,被她悄悄串成了项链。收画板时,
陈诚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她身后:"画的什么?"林雪儿慌忙合上画板:"没、没什么。
"他伸手要去拿,她紧紧抱在怀里。拉扯间,画纸从画板里滑出来,飘落在草地上。
陈诚弯腰捡起,林雪儿的心跳得像要炸开,却听见他轻声说:"画得挺好的。
"他把画递回来,指尖不小心碰到她的手背。林雪儿像触电似的缩回手,
看见他耳根悄悄红了,像被晚霞染过。春风卷着柳丝拂过两人的脸颊,远处传来同学的笑声,
衬得这片刻的沉默格外漫长,像一首未完的诗。"那个,"陈诚忽然开口,"下周六有空吗?
市体育馆有场篮球赛,我...给你留了票。"林雪儿的眼睛亮起来,像落满了星光,
用力点头:"有空!"那天的篮球赛,林雪儿坐在观众席最前排。陈诚穿着红色球衣,
号码是7号,在球场上跑得像阵风。每次进球后,他总会下意识地往她这边看,目光相撞时,
又会立刻转回去,耳根却红得像要滴血。她数着他进球的次数,每一次都在心里跟着欢呼,
比自己赢得比赛还开心。中场休息时,他满头大汗地跑过来,林雪儿递给他拧开瓶盖的水。
"打得真好。"她小声说,声音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等赢了这场,"他仰头喝水,
喉结滚动,像吞咽着阳光,"我有话想跟你说。"林雪儿的心跳骤然加速,
指尖捏着没送出去的纸巾,上面被汗湿了一小块。她看着他跑回球场的背影,
忽然觉得阳光格外晃眼,晃得人想流泪。那一刻,她好像已经猜到了他要说的话,
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只觉得心里被填满了,又空落落的。那场比赛他们赢了。
终场哨声响起时,全场都在欢呼。林雪儿跟着人群往出口走时,陈诚在后面喊她的名字。
她转过身,看见他抱着奖杯朝她跑过来,球衣上的号码在夕阳下泛着金光,
汗水顺着他的下颌线往下滴,落在锁骨的凹陷处,像融化的金子。"林雪儿,
"他站在她面前,喘着气,脸颊因为奔跑泛着红,"我..."话没说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