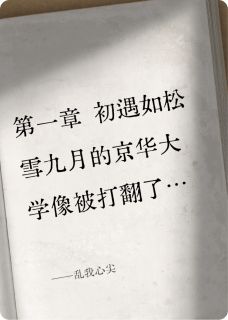
第一章初遇如松雪九月的京华大学像被打翻了的调色盘,银杏叶刚染了浅黄,
悬铃木的绿还浓得化不开,风卷着桂花香往人鼻尖钻。
阮听还抱着半人高的画筒从美术馆出来,白衬衫袖口卷到小臂,露出截细白的手腕,
腕骨分明得像玉刻的。她生得是真绝色。不是那种甜腻的娇俏,
是带着清冷的疏朗—眼尾微微上挑,眼瞳却黑得像浸了墨,
看人的时候总像隔着层薄雾;鼻梁挺翘,山根处有极淡的光影,唇色偏浅,抿着时唇线利落,
笑起来才会泄出点软意。刚才在馆里调颜料,指尖沾了点钴蓝和藤黄,她没顾上擦,
那点斑斓落在白皙的手背上,倒比画筒里的画还惹眼。“听还!这里!
”不远处的香樟树下有人喊她,是思修老师周兰。阮听还抬眸,脚步慢了些,目光越过周兰,
落在她身边站着的男人身上时,步子几不可察地顿了顿。男人很高,得有一米八七往上,
穿件深灰色的定制西装,肩线挺括得像量过尺寸的标尺,腰收得紧,衬得宽肩窄腰,
身形挺拔得像株立在雪地里的松。他没看她,正侧头听周兰说话,侧脸线条利落—眉骨高挺,
压得眼窝有点浅影,鼻梁笔直,鼻尖微翘,下颌线绷得紧,透着股生人勿近的矜贵。
直到周兰推了他一下,他才转过头。视线撞过来时,阮听还心里莫名一跳。他的眼睛太黑了,
像藏着片深潭,没什么情绪,却沉得让人不敢多望,只匆匆扫了她一眼,
又落在她怀里的画筒上,目光在她沾了颜料的指尖停了停才淡声开口。“谢知聿。
”声音是真好听。不是年轻男孩的清亮,是低沉的,带着点磁,像大提琴的最低音擦过弦,
慢悠悠地往人耳朵里钻。阮听还定了定神,抱着画筒微微颔首:“阮听还。”声音清泠,
像山涧淌过的泉水,和他的沉磁撞在一起,竟有种奇妙的和谐。
周兰在旁边笑:“我跟你说的就是她,我们系最厉害的小姑娘,画得好,人也聪明。
知聿你别老摆着张脸,吓着孩子。”又转头拍阮听还的胳膊,“听还,知聿是我大学同学,
现在在⋯•反正就是很厉害的地方做事,你叫他谢哥就行。”谢知聿没接话,
只是看着阮听还,黑眸里情绪不明,过了会儿才补了句:“周老师的学生,不用这么客气。
”顿了顿,又添了个称呼,“阮同学。”这称呼生分,阮听还也不在意,
她本就不是热络性子,只又点了点头,没再多说。倒是周兰热络,
拉着她问刚去美术馆是不是看新展,又转头跟谢知聿夸她上次拿了全国大学生美术展的金奖,
画的那组《旧日京雪》有多惊艳。谢知聿听得认真,偶尔“嗯”一声,
目光却总往阮听还身上飘。她垂着眼,长睫毛像两把小扇子,在眼下投出浅影,风吹过,
额前碎发飘起来,露出光洁的额头,侧脸的弧度柔和又清冷。他喉结不动声色地滚了滚,
指尖在西装裤缝里蜷了下,最终还是没说什么。后来周兰说要请吃饭,
阮听还本想找借口推了—她不喜欢和不熟的人同桌,尤其谢知聿气场太强,让她有点不自在。
可周兰拉着她不放,笑说“就当陪老师”,她没法子,只好跟着往校外走。
谢知聿的车停在路边,是辆黑色宾利,低调得很,却掩不住质感。他先拉开后座车门,
让周兰坐进去,又绕到副驾,手搭在车门上,看向阮听还:“这里。”阮听还愣了下。
按规矩,副驾该是亲近的人坐的。她抬眼看他,他却像没察觉她的迟疑,只垂眸看着她,
黑眸里没什么波澜,手还搭在车门上,没收回的意思。周兰在后座催:“听还快上车呀,
愣着干嘛。”她只好弯腰坐进去。刚关上门,就闻到一股淡淡的味道——不是香水,
是种冷冽的木质香,混着点极淡的烟草味,不冲,很干净,像他的人一样,清矜又让人安心。
谢知聿坐进驾驶座,发动车子时问周兰:“去上次那家淮扬菜?”声音低低的,
在安静的车厢里格外清晰。周兰应着,又转头跟阮听还说那家的软兜长鱼和文思豆腐做得绝,
让她等会儿多吃点。阮听还点头应着,目光落在窗外。京华大学的秋景好看,
银杏道、未名湖,都透着书卷气。谢知聿开车很稳,车速不快,偶尔遇到减速带,
也只是轻轻踩下刹车,几乎没颠簸。她偷偷用余光瞥他。他握着方向盘的手很好看,
骨节分明,手指修长,手腕上戴着块简约的黑表盘手表,衬得皮肤更白。
侧脸线条在光线下更清晰,睫毛很长,垂着眼看前方时,有种难得的温和。正看着,
谢知聿忽然转头,视线和她撞了个正着。阮听还像被抓包的小孩,慌忙转回头,
耳尖有点发烫。他却像没事人一样,淡声问:“晕车?”“不晕。”她声音有点闷,
没敢看他。他“嗯”了声,没再说话,只是伸手调了调空调,把风速调低了些。暖风吹过来,
带着那股冷冽的木质香.阮听还心里莫名松了口气,又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别扭。到了菜馆,
周兰拉着阮听还坐靠窗的位置,谢知聿自然坐在她们对面。服务员递菜单过来,
他先推给周兰,周兰又推给阮听还:“听还看看,想吃什么自己点。”阮听还翻了翻,
没什么特别想吃的,只点了个清炒时蔬。谢知聿接过菜单,扫了眼,没抬头,
声音低低地报了几个菜名:“软兜长鱼,文思豆腐,拆烩鲢鱼头,再要个蟹粉小笼。
”都是周兰刚才提过的,也是淮扬菜里的招牌。周兰笑:“还是你懂我。”他没接话,
只抬眼看向阮听还,黑眸里带了点浅淡的询问:“这些合口味?”阮听还愣了下,
才点头:“都可以。”菜上来得快。文思豆腐细得像发丝,汤清得透亮;软兜长鱼滑嫩,
裹着酱汁,看着就有食欲。周兰给阮听还夹了块豆腐:“快尝尝,
这师傅做了三:年文思豆腐,刀工绝了。”谢知聿夹了一筷子软兜长鱼,没放自己碗里,
反而轻轻放在她盘子边,动作自然得像做过千百遍。“刺挑过了。”他低声说,没看她,
视线落在自己碗里,耳根却悄悄泛了点红。阮听还僵住了。盘子里的长鱼裹着褐色的酱汁,
油光锃亮,和她白净的骨瓷盘对比鲜明。她抬眼看他,他还在低头吃饭,睫毛垂着,
好像刚才那个动作只是无心之举。周兰在旁边没注意,还在说学校里的趣事,
她只好小声说了句:“谢谢。”他“嗯”了声,声音轻得像叹息。
这顿饭吃得阮听还心里有点乱。谢知聿话不多,多数时候是周兰在说,他偶尔应一句,
却总在不经意间照顾她—她杯子里的水快没了,
他会不动声色地让服务员添满;她夹不到远处的小笼包,他会转一下转盘,
把蒸笼推到她面前;她吃鱼头时皱眉挑刺,他会递过公筷,帮她把鱼肉拆出来,放在碟子里。
这些动作都很自然,一点不刻意,可落在阮听还眼里,却让她莫名心慌。她不是傻子,
能感觉到他对自己不一样,可他又太克制,眼神、动作,都透着“分寸”二字,让她猜不透。
吃完饭,谢知聿送她们回学校。到了宿舍楼下,周兰先下了车,说要去办公室拿点东西,
让谢知聿先送阮听还到画室—她晚上要去画室赶稿。车里只剩他们两个人,
气氛忽然静了下来。阮听还抱着画筒,指尖抠着筒身,没说话。谢知聿发动车子,开了段路,
才低声问:“最近在忙什么?”“准备下个月的联展。”她答得简洁“嗯,需要帮忙吗?
”他问,声音很轻。“不用,谢谢。”她拒绝得干脆。她不习惯麻烦别人,尤其是不熟的人。
他没再坚持,只是“哦”了声,车厢里又恢复了安静。只有车轮碾过柏油路的声音,
和空调出风口的微风声。到了美术馆楼下,阮听还解开安全带,刚要推门,
谢知聿忽然叫她:“阮听还。”她回头看他。他侧着头,路灯的光从车窗照进来,
落在他半张脸上,一半明一半暗。他看着她,黑眸里有她看不懂的情绪,
过了会儿才说:“晚上冷,多穿点。”阮听还愣了愣,才点头:“知道了,谢谢谢先生。
他皱了下眉,好像不喜欢这个称呼,却没说什么,只摆了摆手:“进去吧。
”阮听还抱着画筒下了车,没回头。直到走进美术馆,她才靠在墙上,
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耳尖—还是烫的。她抬头看向窗外,那辆黑色宾利还停在路边,车灯亮着,
像双眼睛,静静地看着美术馆的方向。她心里忽然冒出个念头:这个谢知聿,
好像和他看起来的样子,不太一样。第二章藏在细节里的温柔从那次见面后,
阮听还和谢知聿的交集莫名多了起来。周兰像是得了什么指令,隔三差五就约聚餐,
十次有八次谢知聿都在。有时是在学校附近的小馆子,有时是在稍远些的私房菜,
谢知聿每次都来,从不缺席,也从不迟到。他还是话不多,多数时候就坐在那里,
端着茶杯或酒杯,安静地听周兰和其他人说话,目光却总在不经意间落在阮听还身上。
她夹菜时,他会悄悄把她喜欢的那盘往她面前推半寸;她低头看手机时,
他会让服务员把空调风口转个方向,别对着她吹;有次她不小心把水洒在桌子上,他没说话,
先抽了张纸巾递过去,又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杯子往旁边挪了挪,怕水溅到他那里再沾到她。
这些细节太碎,碎到像尘埃,可攒多了,就成了堆,压在阮听还心上,让她没法再当看不见。
她开始留意他。发现他手指很长,
握笔时指节会微微泛白;发现他笑起来时嘴角会有个极浅的梨涡,
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发现他喝的茶总是龙井,而且要温的,
太烫或太凉都不碰;发现他看她的眼神,虽然淡,却总带着点她读不懂的纵容。有次聚餐,
周兰带了个朋友来,是做艺术品投资的,姓刘。刘总大概喝多了,说话没分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