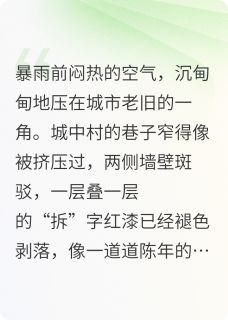
暴雨前闷热的空气,沉甸甸地压在城市老旧的一角。城中村的巷子窄得像被挤压过,
两侧墙壁斑驳,一层叠一层的“拆”字红漆已经褪色剥落,像一道道陈年的伤口。
各种气味在这里混合、发酵——隔夜饭菜的微酸,下水道若有似无的淤塞气息,
廉价油条在油锅里翻滚出的浓烈焦香。林晚端着个磕了边的搪瓷盆,
从巷子深处那个昏暗的、永远弥漫着一股潮湿霉味的水房走出来,盆里的水晃荡着,
溅湿了她洗得发白的牛仔裤脚。“晚丫头,又给你妈打水啊?”巷口小卖部的王伯摇着蒲扇,
声音混在隔壁录像厅震天响的港片枪战声里。林晚“嗯”了一声,算是回应,脚步没停。
她家在巷子最里头,那扇薄薄的木板门虚掩着,里面传来压抑又剧烈的咳嗽声,撕扯着喉咙,
听着让人心头发紧。推门进去,光线更暗了。不到十平米的小屋,
一张木板床几乎占去大半空间。养母苏慧娟蜷在床上,瘦得脱了形,脸上泛着不健康的潮红。
床边小柜子上堆满了药瓶和一个旧电饭煲内胆,里面是半温的小米粥。“妈,擦把脸。
”林晚拧了毛巾,动作麻利地给苏慧娟擦额头和脖子上的虚汗。毛巾触到滚烫的皮肤,
她心里一沉。那咳嗽声又撕心裂肺地响起,苏慧娟身子弓起来,像一只被抽干了力气的虾米。
林晚熟练地扶住她,拍着那嶙峋的背脊,直到那阵撕扯过去,留下粗重艰难的喘息。
“咳咳…晚啊……”苏慧娟喘着气,浑浊的眼睛看向林晚,
带着一种林晚早已习惯的、混合着疲惫和依赖的神情,
“药…钱……”林晚拿起床头那个空了大半的药瓶看了看标签:“嗯,知道了。
下午收了摊就去买。”她声音平静,听不出波澜。安顿好母亲,
她走到屋角那个油腻腻的单灶煤气炉旁,掀开锅盖,
里面是昨晚剩下的半锅没什么油水的青菜面条。她麻利地点火,把面条倒进去热着。
狭窄的空间里,很快又充斥起油烟和药味。口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
不是她那个老掉牙的按键机。林晚动作顿了一下,走到门外,
才摸出那部屏幕有裂痕的二手智能机。屏幕上跳动着“许悠然”三个字。划开接听,
一个清甜、带着点撒娇意味的声音立刻传出来,
背景音是悠扬的钢琴曲和隐约的谈笑声:“喂?晚晚!你到哪儿啦?就等你了!
今天可是我二十岁生日宴哦,你这个主角的‘好姐妹’可不能迟到!
”声音里是毫无阴霾的快乐。林晚握着手机的手指微微收紧,指节有些泛白。巷子外,
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哐当哐当地碾过坑洼的路面,声音刺耳。“知道了,”她声音不高,
压过了那噪音,语气淡淡的,“有点事,处理完就过去。”“快点哦!在帝豪顶层旋转餐厅,
别走错了!门口有人接你!”许悠然那边似乎有人叫她,她欢快地应了一声,“不说了,
等你!”电话干脆利落地挂断。林晚站在原地,手机屏幕暗下去,映出她没什么表情的脸。
帝豪顶层旋转餐厅,那是这座城市的地标之一,一顿饭够她和母亲生活几个月。
她抬头看了看头顶狭窄的一线灰蒙蒙的天空,然后转身,
走回那间弥漫着药味和油烟味的小屋,端起那碗热好的面条。帝豪酒店顶层,
巨大的水晶吊灯倾泻下璀璨光芒,将整个空间映照得如同白昼。
空气里浮动着昂贵的香氛、雪茄的醇厚以及各种名贵酒水的清冽气息。落地窗外,
整座城市的辉煌夜景尽收眼底,车流如金色的光带流淌不息。衣香鬓影,觥筹交错。
许悠然无疑是今晚最耀眼的星辰。她穿着一身当季最新款的香奈儿小礼服,
浅粉色衬得她肌肤胜雪,颈间一条设计精巧的钻石项链熠熠生辉。她像一只快乐的蝴蝶,
轻盈地穿梭在宾客之间,脸上是无可挑剔的甜美笑容,
举手投足间带着被精心教养出的优雅从容。她的父亲许宏远,宏远集团的掌舵人,正带着她,
向几位重要的政商界人物介绍,言语间满是为人父的骄傲。“小女悠然,
刚拿了钢琴演奏的一等奖,这孩子就是坐不住,总想多学点东西。”许宏远朗声笑道,
拍了拍许悠然的肩膀。许悠然适时地微微欠身,笑容温婉得体:“张伯伯过奖了,
爸爸总爱夸我,我还差得远呢。”声音轻柔悦耳,引来一片赞许的目光。
许太太周文倩站在稍后一点的位置,穿着一身宝蓝色丝绒旗袍,仪态万方。
她看着女儿在丈夫身边应对自如,嘴角噙着欣慰满足的笑意,眼神温柔得能滴出水来。
她时不时抬手,替许悠然整理一下并不存在的、垂落颊边的发丝,
或是轻轻抚平礼服上微不可察的褶皱,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透着刻入骨髓的珍视。
有相熟的贵妇过来夸赞许悠然气质好,周文倩便笑着回应:“是啊,
这孩子从小就不让人操心,贴心着呢。”语气里的自豪几乎要溢出来。宴会的气氛正酣。
侍者托着盛满香槟的酒杯穿梭,乐队奏着舒缓的乐章。许宏远似乎想起了什么,
侧头低声问妻子:“悠然那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叫林晚的,不是说也来吗?怎么还没到?
”周文倩脸上的笑容淡了一瞬,很快又恢复如常,声音温和:“哦,那孩子啊。
可能路上耽搁了吧。年轻人有自己的事,能来就好。”她端起酒杯抿了一口,
目光扫过入口处,那里依旧没有出现那个穿着朴素、与这环境格格不入的身影。
她心底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排斥,但面上依旧保持着完美的优雅。就在这时,
宴会厅厚重的大门被侍者无声地拉开。林晚走了进来。
她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硬的米白色棉布连衣裙,款式简单得近乎过时,
脚上是一双刷得干干净净的旧帆布鞋。长长的头发简单地束在脑后,露出光洁的额头和颈项,
没有佩戴任何首饰。她的出现,
像一幅褪色的旧照片突然被投入了色彩饱和度极高的现代油画里,
瞬间吸引了周遭的目光——好奇的、审视的、带着明显优越感的。那些目光像细密的针,
刺在林晚身上。她能清晰地感觉到那些视线在她洗得发白的衣料和空荡荡的手腕上停留。
她脊背挺得笔直,下颌微收,脸上没有任何局促或不安的表情,只有一种近乎淡漠的平静。
她目光径直穿过衣香鬓影的人群,投向会场中心那个光彩照人的焦点——许悠然。
许悠然也看到了她,立刻提着裙摆,像一只真正的粉蝶般轻盈地飞了过来,
脸上是毫无芥蒂的灿烂笑容:“晚晚!你可算来了!我还以为你迷路了呢!
”她亲热地挽住林晚的胳膊,动作自然,
仿佛完全没注意到周围那些投注在林晚身上的异样眼光。“路上有点堵。
”林晚简单地解释了一句,声音不高,但清晰地落在周围几人的耳中。她任由许悠然挽着,
目光平静地迎向走过来的许宏远和周文倩。“许叔叔,周阿姨。”林晚微微点头致意,
称呼客气而疏离。许宏远笑容温和,带着长辈的包容:“小林来了就好,悠然念叨半天了。
别拘束,就当自己家。”他的目光在林晚朴素的衣着上短暂停留了一瞬,并无太多异样,
更多是长辈看晚辈的宽和。周文倩脸上的笑容则显得公式化了许多,她上下打量了林晚一眼,
语气是恰到好处的客气:“是啊,林晚同学,欢迎你来。这边有自助餐点,想吃什么自己取,
别客气。”她抬手示意了一下旁边琳琅满目的餐台,动作优雅,但眼神里那份刻意的距离感,
如同在两人之间悄然划下了一条无形的线。许悠然似乎毫无所觉,
或者说刻意忽略了这份微妙,她拉着林晚的手,兴致勃勃地指向餐台:“晚晚,快看!
有你最喜欢的黑森林蛋糕!我特意让厨师做的!我们去尝尝!”她的声音清脆,
带着不容置疑的亲昵,试图用自己的热情驱散林晚身边的冷清。林晚被拉着向前走去,
她能感觉到背后那些目光并未完全移开。周文倩站在原地,
看着女儿亲热地挽着那个与这环境格格不入的女孩走向餐台,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
她端起酒杯,走向旁边相熟的几位太太,很快,优雅的谈笑声重新响起,
将那个穿着旧裙子的身影暂时淹没在衣香鬓影的浮华里。宏远集团总部顶楼的董事长办公室,
巨大的落地窗将城市天际线尽收眼底,俯瞰芸芸众生。阳光透过百叶窗,
在光洁如镜的深色实木地板上投下利落的条纹阴影,整个空间空旷、冰冷,
弥漫着一种无声的威压。许宏远坐在宽大的真皮办公桌后,眉头紧锁,像两道深刻的沟壑。
他手里捏着一份薄薄的体检报告,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
报告上的几项关键指标被用红笔醒目地圈了出来,旁边是医生龙飞凤舞的专业批注。
空气凝重得几乎能拧出水来,只有他略显粗重的呼吸声。他对面,
站着宏远集团一位资历颇深的老董事,姓陈,也是许宏远多年的好友兼心腹。
陈董事的脸色同样凝重。“确定吗?”许宏远的声音有些沙哑,像是砂纸摩擦过桌面。
他又一次低头看向那份报告,目光死死盯住那几个触目惊心的红圈,
“血型……还有这个遗传标记……怎么可能?”“宏远,”陈董事的声音低沉而严肃,
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沉重感,“报告是权威机构做的,我亲自盯着流程,样本也没问题。
你、文倩,还有悠然……这比对结果……”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词句,“……完全对不上。
悠然她……在生物学上,不可能是你和文倩的亲生女儿。”“不可能”三个字像重锤,
狠狠砸在许宏远心口。他猛地抬起头,眼中是震惊、茫然,还有一种被彻底打败的恐惧。
二十年来精心构筑的、关于家庭和血脉的认知,在这冰冷的科学数据面前,轰然崩塌。
“那……那我们的女儿呢?”许宏远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他像抓住救命稻草般追问,“当年……当年文倩是在哪家医院生的?
”“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陈董事立刻回答,显然已经做了详尽的调查,
“时间点是二十年前的七月十二号凌晨。我让人去查了当年的档案,情况……有点复杂。
”许宏远身体前倾,目光如炬:“说!”“那天晚上,妇产科所在的旧住院楼区域,
发生过一次严重的、持续近半小时的电路故障,整个楼层陷入一片漆黑。”陈董事语速平稳,
但每个字都像冰凌坠地,“档案记录显示,当晚值班护士人手严重不足,
又恰逢同时有几名产妇生产,秩序一度混乱。其中,
文倩的产房和隔壁一位叫苏慧娟的产妇的产房……紧挨着。
”苏慧娟……这个名字像一道微弱的电流,击中了许宏远记忆深处某个模糊的角落。
他似乎听悠然提起过,她那个最好的朋友林晚的母亲,就叫苏慧娟?
一种可怕的、令人窒息的联想瞬间攫住了他。“混乱中,
两个几乎同时出生的女婴……”陈董事的声音艰涩起来,他看着许宏远瞬间变得惨白的脸,
最终还是说出了那个残酷的结论,“……极有可能,在黑暗和混乱中被抱错了。
”“抱错了……”许宏远喃喃地重复着这三个字,像在咀嚼一枚苦果。
他高大的身躯晃了一下,手撑住桌面才勉强站稳。
眼前闪过周文倩凝视悠然时那满含宠溺的眼神,闪过悠然从小到大的点点滴滴,
自己和文倩隐隐有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相似轮廓的脸……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
痛得他几乎无法呼吸。二十年的舐犊情深,原来竟是一场阴差阳错的错位!“查!
”许宏远猛地抬起头,眼中布满红血丝,声音是从未有过的嘶哑和决绝,
带着一种近乎毁灭的气息,“动用一切资源,给我查清楚!那个苏慧娟,还有她的女儿林晚!
我要知道一切!立刻!马上!”城中村低矮、杂乱的自建房之间,电线如蛛网般杂**织。
林晚的“摊子”就在巷口一个相对避风、晚上路灯能勉强照到的角落。
一块脏兮兮的塑料布铺在地上,
上面散乱地摆着些廉价的手机壳、数据线、造型夸张的塑料耳环,
还有一些印着粗糙卡通图案的钥匙扣。一个用硬纸板做的简陋招牌斜靠在墙边,
上面用红漆歪歪扭扭地写着:“手机配件,时尚饰品,便宜好用”。天色将暗未暗,
正是下班和放学的人流经过的高峰期。林晚蹲在摊子后面,面无表情地看着过往行人。
她不像旁边卖水果的大婶那样卖力吆喝,只是偶尔有人驻足询问,她才简短地回答几句价格,
声音平淡无波。几个穿着校服的女学生蹲下来,叽叽喳喳地挑拣着那些色彩鲜艳的耳环,
最后一人买了一对,付了钱,欢笑着跑开。林晚把几张皱巴巴的零钱收好,
塞进腰间的旧腰包里。巷子深处传来苏慧娟压抑的咳嗽声,断断续续,像破旧的风箱。
林晚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她抬头看了看天色,又看了看摊子上剩下的几样东西,
心里盘算着今天赚的钱够不够明天去药店。就在这时,
一阵与城中村环境格格不入的低沉引擎轰鸣声由远及近,最后在巷口戛然而止。
一辆线条冷硬、光可鉴人的黑色宾利轿车,如同闯入贫民窟的钢铁巨兽,
突兀地停在了林晚简陋的摊位前,挡住了大半本就昏暗的光线。车门打开,先下来的是司机,
恭敬地拉开后座车门。许宏远高大的身影跨了出来,他穿着一身剪裁精良的深灰色西装,
面容冷峻,眼神锐利如鹰隼,带着一种久居上位者审视一切的压迫感,
瞬间将巷口这片小小的嘈杂空间笼罩。他身后跟着的,是那位表情同样严肃的陈董事。
这突如其来的“大人物”和豪车,立刻引起了巷子里的骚动。
附近摆摊的、路过的、甚至楼上推开窗户探头张望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过来,
带着惊疑、好奇和毫不掩饰的议论。“我的老天爷……这是谁啊?来找谁的?
”“那车……得值几百万吧?怎么会开到我们这破地方来?”“看那老板,
脸黑得吓人……是来找麻烦的?”“该不会是冲着晚丫头来的吧?她惹上什么事了?
”林晚缓缓站起身。她身上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旧T恤和牛仔裤,
站在那辆豪车和西装革履的许宏远面前,渺小得像一粒尘埃。但她站得很直,
脸上没有任何慌乱或惊讶,只有一种近乎漠然的平静。她平静地看着许宏远,
那双眼睛清澈而深邃,像寂静的潭水,映不出周围的喧嚣和对方身上迫人的气势。
许宏远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牢牢锁定在林晚的脸上。他一步步走近,
皮鞋踩在坑洼不平的水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他仔细地、近乎贪婪地审视着林晚的眉眼、鼻梁、嘴唇的轮廓……越看,
心脏越是剧烈地抽痛。那份调查报告上的结论,那些冰冷的遗传数据,
此刻在林晚这张年轻而倔强的脸上,找到了无比残酷又无比清晰的印证——这眉眼间的神韵,
分明有着自己和文倩年轻时的影子!
那个在许家被精心呵护了二十年的悠然……强烈的痛苦和巨大的荒谬感如同海啸般冲击着他。
他走到林晚面前,距离很近。他能清晰地看到她脸颊上被生活打磨出的细微痕迹,
看到她洗得发白的衣领,看到她眼中那片深不见底的、与年龄不符的沉寂。
这沉寂像一把钝刀,在他心上来回切割。这就是他的亲生骨肉!在这样泥泞的地方,
守着这样不堪的摊子……“林晚?”许宏远的声音低沉沙哑得厉害,
带着一种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强行压抑的颤抖。“是我。”林晚的声音很平静,没有疑问,
仿佛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刻的到来。她甚至微微侧头,看了一眼巷子里自家小屋的方向,
眼神里掠过一丝了然。许宏远顺着她的目光看了一眼那扇破旧的木门,
里面隐约又传来压抑的咳嗽声。他深吸一口气,那带着城中村特有复杂气味的空气涌入肺腑,
却压不下心头的酸楚和翻涌的愧疚。他张了张嘴,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
千言万语最终只化为一句沉痛无比、带着巨大冲击力的话语,
砸在这昏暗嘈杂的巷口:“孩子……我们……可能抱错了。你,才是我的亲生女儿。
”这句话如同平地惊雷,瞬间炸懵了周围所有竖着耳朵听动静的人。短暂的死寂之后,
是更加汹涌的议论浪潮。林晚的身体几不可察地晃了一下。她垂在身侧的手指,
微微蜷缩了一下,指甲陷入掌心,带来一丝尖锐的痛感。然而,
她脸上的表情依旧没什么大的变化,只是那双深潭般的眼睛,
瞳孔深处似乎有剧烈的风暴在无声地酝酿、冲撞,最终又被一种强大的意志力死死压了下去,
归于一片沉寂的冰面。
她只是静静地看着眼前这个自称是她生父、衣着光鲜却满眼痛楚的男人,没有激动地追问,
没有嚎啕大哭,也没有任何失态的举动。那是一种经历过太多生活捶打后,
淬炼出的、近乎残酷的平静。仿佛这惊天动地的身世打败,于她而言,
不过是生活这潭浑水中,又一块投入的、注定会沉底的石头。
许家那栋位于半山腰的独栋别墅,像一座巨大的、沉默的堡垒,
矗立在精心修剪过的草坪和名贵花木之中。巨大的雕花铁门无声滑开,
黑色宾利载着林晚驶入。车子停在灯火通明的门厅前,光洁的大理石台阶反射着冰冷的光。
车门打开,林晚走了下来。她身上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旧T恤和牛仔裤,
背着一个小小的、磨损严重的旧帆布包,站在光可鉴人的台阶下,
与眼前这奢华得如同宫殿的景象形成了刺眼的对比。别墅里明亮的灯光倾泻而出,
将她单薄的身影拉得很长。周文倩早已等在门口。她穿着一身质地柔软的米白色家居服,
脸上没有化妆,眼圈红肿,显然是哭过很久。当她的目光触及林晚那张脸的瞬间,
像是被电流击中,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泪水毫无预兆地再次汹涌而出。
她几乎是踉跄着从台阶上冲下来,完全不顾仪态,带着一阵香风,猛地将林晚紧紧抱在怀里!
“孩子……我的孩子啊……”周文倩的声音破碎不堪,带着撕心裂肺的哭腔,
滚烫的泪水瞬间濡湿了林晚单薄的肩头。她的手臂收得极紧,
仿佛要将这失而复得的骨肉揉进自己的骨血里,身体因为巨大的情绪冲击而剧烈地抖动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