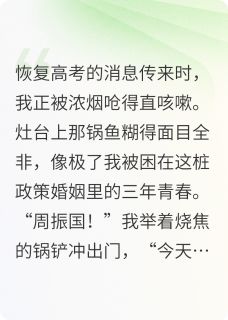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正被浓烟呛得直咳嗽。灶台上那锅鱼糊得面目全非,
像极了我被困在这桩政策婚姻里的三年青春。“周振国!”我举着烧焦的锅铲冲出门,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刚下训的军官老公愣在院门口,
手里还拎着两条活蹦乱跳的鲫鱼。他喉结滚了滚:“林晚秋同志……又、又打仗了?”当晚,
家属院传遍了三营长被媳妇按在厨房学做菜的奇闻。王秀芬嗑着瓜子直摇头:“小周啊,
你这哪是娶媳妇,分明请了个祖宗。”他揉着被油溅红的手背傻笑:“祖宗教得好,
明年就能给她炖高考营养汤了。”——广播里那个字正腔圆的声音,像块烧红的烙铁,
猛地烫进林晚秋的耳朵里,烫得她心尖一哆嗦。“……中央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
恢复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凡符合条件者……”后面播音员那激动昂扬的调子,
林晚秋一个字也没听清。她手里那根还沾着鱼鳞的锅铲,“哐当”一声掉在水泥地上,
发出清脆又孤零零的声响。恢复高考了?真的恢复了?!
一股巨大的、几乎要把她胸腔撕裂的狂喜猛地冲了上来,冲得她眼前发黑,手脚发麻。
那被硬生生按捺了三年,几乎以为早已枯死的念头,像遇了春雨的野草,疯狂地破土而出,
滋长蔓延——回城!读书!离开这个黄土漫天、把她死死钉住的地方!
可这股狂喜还没冲到顶,
一股极其霸道、带着强烈焦糊味的浓烟就蛮横地灌进了她的鼻腔和喉咙。
“咳咳咳……呕……”林晚秋被呛得弯下腰,眼泪鼻涕瞬间糊了一脸,
方才那点不切实际的狂喜被这现实的重拳砸得七零八落。她捂着嘴,狼狈地冲进小小的厨房,
手忙脚乱地去揭那个不断往外喷吐黑烟的木头锅盖。“嗤——!
”一股更猛烈的焦糊味混合着蒸汽扑出来,熏得她倒退两步,眼泪流得更凶了。锅盖烫手,
她“嘶”地一声缩回手,指尖立刻红了一片。锅台上那口铁锅,正上演着一场惨烈的灾难。
里面那条原本还算肥美的草鱼,此刻彻底没了鱼样,乌漆嘛黑地粘在同样焦黑的锅底,
顽强地冒着绝望的小泡。锅沿上糊着一圈黑乎乎的、硬邦邦的东西,像某种邪恶的符咒,
宣告着林晚秋又一次厨房战争的彻底失败。这锅面目全非的鱼,
这弥漫不散、死死缠绕着她的焦糊味,像一面残酷的镜子,
清晰地映照出她这三年的日子——被困在这桩由一纸荒唐政策强行捏合的婚姻里,
困在这黄土坡上的家属大院,困在这永远也搞不定的柴米油盐里,青春和那点微末的念想,
就像这条鱼,被煎烤得面目全非,糊得透透的!一股邪火“噌”地直冲天灵盖,
烧得她眼前都带了红。什么高考,什么回城,眼前这口糊锅和这该死的、甩不脱的婚姻,
才是她林晚秋活生生的地狱!她弯腰,一把抄起地上那把倒霉的锅铲,
也不管它沾着灰土和鱼鳞,像举着冲锋陷阵的红缨枪,
带着一股子要和这操蛋命运同归于尽的狠劲,转身就朝院门口冲。“周振国——!
”这一嗓子,几乎用尽了她肺里所有的空气,
带着三年积攒的委屈、憋闷和此刻被糊锅彻底点燃的暴怒,尖利地划破了家属院傍晚的宁静。
几只停在电线上的麻雀被惊得扑棱棱飞起。院门那两扇刷着绿漆的木门“吱呀”一声被推开,
一个高大的身影恰好出现在门口,挡住了西边天际最后一点残阳的光。周振国回来了。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袖子习惯性地挽到小臂,露出结实流畅的肌肉线条。风尘仆仆,
脸上还带着训练场上滚过的汗渍和尘土。一只手里,正拎着用草绳串起来的两条鲫鱼,
鱼尾巴还在不甘心地、微弱地扑腾着,甩出几滴清凉的水珠,溅在他沾着泥点的军裤上。
林晚秋像颗被点着的炮仗,挟着满身油烟和怒气,直冲到离他一步远的地方才刹住脚。
手里的锅铲几乎要戳到他挺直的鼻梁骨,那上面黑乎乎的焦痕就是她无声的控诉。
周振国显然被这阵仗惊住了。他下意识地站得更直了些,像在营里面对首长的突击检查。
目光飞快地从她气红的脸、糊着泪痕的眼角,扫到她手里那根凶器般的锅铲,
再越过她的肩膀,投向厨房小窗里还在袅袅飘出的、带着不祥味道的黑烟。
他喉结上下艰难地滚动了一下,那双平日里在训练场上锐利如鹰隼的眼睛里,
此刻清晰地映着一个头发微乱、像只炸毛小兽般的林晚秋。他嘴唇动了动,
声音带着点刚下训的沙哑,
被这突如其来的“战斗警报”弄懵了的迟疑:“林晚秋同志……这、这又是……跟谁打仗了?
”他那副标准的军人站姿,配上手里那两条还在徒劳挣扎的鲫鱼,
还有那句懵懂又认真的“打仗了?”,
简直精准无比地戳中了林晚秋此刻那根最脆弱、最易燃易爆的神经!打仗?打什么仗?
她是在跟这口永远烧不熟饭的破锅打仗!跟这洗不完的脏衣服打仗!
跟这黄土坡上刮不完的风打仗!更是跟眼前这个木头疙瘩一样的男人,
以及把他们死死绑在一起的那份该死的“政策”打仗!
委屈、愤怒、不甘心……所有情绪像滚烫的岩浆在她胸腔里翻涌,几乎要冲破喉咙喷出来。
她死死咬着下唇,才没让那点不争气的眼泪再次决堤。握着锅铲的手因为用力而微微发抖,
骨节泛白。周振国看着她死死咬着嘴唇、眼眶通红却倔强地不让眼泪掉下来的样子,
再看看厨房里持续飘出的黑烟,心里那点模糊的猜测终于落了地。
他刚毅的脸上飞快地掠过一丝……大概是叫做“心虚”的情绪?
虽然这表情在他那张线条硬朗的脸上显得极其生硬和不协调。
他赶紧把手里还在扑腾的鲫鱼往旁边地上一放,也顾不上那鱼沾了土,上前一步,
下意识地想接过她手里那根危险的锅铲,声音放低了些,带着点安抚的意味:“锅……糊了?
没事,糊了就糊了,鱼……我再去弄两条……”他试图去拿锅铲的手伸到一半,又顿住,
似乎觉得这动作可能引发新一轮“战争”。“你弄?”林晚秋猛地抬起头,
那点强忍的泪光在夕阳下亮得惊人,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变调,“周振国!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她手里的锅铲猛地一挥,不是打他,而是狠狠指向那间还在冒烟的厨房,
“进去!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学!做!菜!”最后三个字,她几乎是吼出来的,
带着破釜沉舟的气势。家属院里,好几扇窗户后面,人影晃动,显然都被这动静吸引过来了。
周振国被她吼得一愣,高大的身躯下意识地绷紧,脚跟并拢,差点条件反射地喊出“是!
保证完成任务!”但他看着林晚秋那双燃烧着火焰的眼睛,
再看看那间象征着他无数次“滑铁卢”的厨房战场,
一股熟悉的、名为“抗拒”的情绪本能地升腾起来。他浓黑的眉毛拧成一个疙瘩,
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君子远庖厨”之类的古训来抵抗一下,
或者强调一下他作为营长在训练场上的威严。可林晚秋根本不给他开口的机会。她上前一步,
也顾不上什么男女有别了,
空着的那只手一把抓住他结实的小臂——那力道对于周振国来说简直像小猫挠痒痒,
但其中蕴含的决心却不容忽视——连拖带拽地就往厨房里推。“看什么看!进去!
今天不把这糊锅给我收拾明白,再把这俩鱼拾掇干净炖出个汤来,我跟你没完!
”她像个小炮仗,推搡着比她高大健壮不止一圈的男人。周振国被她推得一个趔趄,
脚下那双沉重的军用胶鞋在泥土地上磨出刺啦的声响。他身体本能地想稳住,
想挣脱这小小的钳制简直易如反掌,可目光扫过她气得发红却异常执拗的脸颊,
还有那微微颤抖的肩膀……他喉结又滚了一下,那点本能的抗拒,莫名其妙地,
像烈日下的薄冰,无声无息地化掉了。他绷着脸,嘴角抿成一条僵硬的直线,
高大的身躯带着点不情不愿的笨拙,被那个小小的、燃烧着怒火的影子,
硬生生地“押解”进了那间还弥漫着焦糊味的、狭小的厨房战场。“砰!
”厨房那扇薄薄的木门被林晚秋从外面用力关上,隔绝了外面所有窥探的目光,
也仿佛将周振国关进了他此生最不擅长的“敌后根据地”。家属院的傍晚,
因为这突如其来的一嗓子“周振国”和随后那场小小的“押解”风波,瞬间活泛了起来。
离周家最近的东边窗户“吱呀”一声被推开,
探出王秀芬那张圆圆胖胖、永远带着看热闹兴致的脸。她手里果然没空着,
一把饱满的葵花籽,正熟练地在门牙间磕开,发出清脆的“咔吧”声。她眯着眼,
瞅着周家那紧闭的厨房门,耳朵竖得老高,似乎想捕捉里面传出的任何风吹草动。“啧啧啧,
”王秀芬摇着头,瓜子皮“噗”地一声精准地吐到窗台上的小瓦盆里,声音不高不低,
正好能让周围几户竖着耳朵的邻居听清,“瞧瞧,瞧瞧!
咱们三营长这哪是娶了个媳妇儿进门?这分明是请了尊活祖宗供在灶王爷跟前儿了!
”她话音还没落,隔壁的李爱华也端着个搪瓷缸子凑到了自家门口,
缸子里是刚沏的茉莉花茶,热气袅袅。
她脸上带着过来人那种又同情又好笑的表情:“谁说不是呢!小周同志多好的人呐,
带兵训练那是一把好手,上回帮我家那口子扛粮袋,两百斤扛起来就走,脸都不带红的!
怎么一进厨房,就跟那孙猴子进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似的,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搁了?
”“可不是嘛!”另一个声音从斜对面的屋里飘出来,是刚随军不久的年轻军嫂小赵,
带着点新媳妇特有的腼腆和好奇,“周营长看着多威严啊,我都不敢跟他大声说话。
也就晚秋姐,敢这么……这么……”她一时想不出合适的词,憋红了脸。“敢这么收拾他!
”王秀芬利落地接上,又“咔吧”磕开一粒瓜子,一脸的精明世故,“这叫啥?卤水点豆腐,
一物降一物!小周这头犟驴啊,就得晚秋这丫头片子来收拾!
”众人发出一阵压低了的、心领神会的哄笑。厨房里,
周振国正经历着人生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小小的空间被那股顽固的焦糊味填满,
像无形的敌人,呛得他喉咙发痒。灶台上那口糊得惨不忍睹的铁锅,
就是敌人留下的碉堡遗迹。林晚秋抱着胳膊,像个最严厉的监工,
杵在门口唯一能通点风的缝隙处,脸还绷着,
但眼神里的怒火似乎被这满屋的狼藉和男人手足无措的样子冲淡了些,
只剩下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第一步,刷锅!”林晚秋的声音没什么温度,
简洁得像下作战指令。周振国深吸一口气,仿佛要上战场。他挽起袖子,
露出肌肉虬结的小臂,拿起灶台边那柄硬毛刷子。他动作生猛,力气更是没得说,
对着那口糊锅就是一顿猛擦猛刷,钢铁摩擦发出“嘎吱嘎吱”刺耳的噪音,
在狭小的厨房里回荡。林晚秋眉头拧得死紧:“轻点!锅底都要被你捅穿了!加温水,
放点碱面泡着!”周振国动作一僵,立刻放下刷子,
像个接收到错误指令的士兵迅速调整战术。他舀起一瓢凉水就要倒。“停!
”林晚秋的喝止声几乎是条件反射,“说了温水!刚烧糊的锅直接用凉水激,锅就废了!
灶上暖壶里有热的!”周振国的手顿在半空,黝黑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窘迫,
默默放下水瓢,转身去找暖壶。笨重的军绿暖壶在他大手里像个玩具,
倒水时动作却小心翼翼,仿佛在拆炸弹引线。好不容易按照指示加了温水,撒了碱面,
看着那口锅暂时在盆里“休养生息”。周振国暗暗松了口气,
目光投向地上那两条还在垂死挣扎的鲫鱼。“鱼,我来处理。”他主动请缨,声音沉稳,
带着一丝在战场上面对困难任务时的郑重。这活儿他熟,野外生存时处理过不知多少。
林晚秋没吭声,算是默许。周振国立刻行动起来。他蹲下身,动作麻利地解开草绳,
抓起一条鱼。杀鱼、刮鳞、去内脏,动作干净利落,带着军人特有的力量感和效率。
昏黄的灯光下,他侧脸线条刚硬,神情专注,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沿着下颌线滑落,
滴在军装衣领上,洇开一小片深色。那把小小的菜刀在他蒲扇般的大手里灵活翻转,
寒光闪闪,竟显出一种奇特的、粗粝的美感。林晚秋抱着胳膊看着,
紧绷的脸色不知不觉缓和了一点点。至少,这男人干这种“力气活”还是靠谱的。
鱼处理干净了,放在案板上。周振国站起身,腰板挺得笔直,
像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般看向林晚秋,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求表扬。“下一步,炖鱼。
”林晚秋不为所动,继续下达指令,言简意赅,“热锅,凉油。油热了放鱼,两面煎黄,
再加热水,放姜片、葱段,大火烧开转小火。”周振国脸上的那点轻松瞬间消失,重新绷紧。
他如临大敌,先把刷干净的锅重新架在灶上,
擦干锅底残留的水珠——这一步他记得林晚秋强调过,不然油会炸。然后,他拿起油瓶,
犹豫了一下,估摸着倒了一些进锅里。锅是热的,油一下去,立刻发出细密的“滋啦”声,
油花欢快地跳动起来。周振国看着那滚动的热油,眉头紧锁,仿佛面对的不是烹饪佐料,
而是即将引爆的地雷。他拿起处理好的鱼,动作变得极其谨慎,离着锅沿还有半尺远,
就试图将鱼滑进去。“离那么远干嘛!油都溅不到你!”林晚秋忍不住出声,
语气带着点恨铁不成钢,“靠近点,贴着锅边轻轻放下去!”周振国依言,身体微微前倾,
手臂靠近油锅。就在鱼身接触滚油的瞬间——“刺啦——!”一团油花猛地爆开,
像小型烟花炸裂!滚烫的油星子精准地溅在了他靠近锅沿的手背上!“嘶——!
”周振国猝不及防,倒抽一口冷气,条件反射般猛地缩回手,动作之大差点把案板带翻。
他低头看着自己手背上迅速冒起的几个小红点,眉头拧得更紧了,嘴角也微微抽动了一下。
这点烫伤对训练场摸爬滚打的他来说不算什么,但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和狼狈,
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挫败。“慌什么!”林晚秋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点无奈,
但似乎也藏着一丝几不可察的……笑意?她走上前,从他僵住的手里拿过锅铲,
“看着点油温,鱼身上的水擦干点!
这么大个人了……”她熟练地用锅铲轻轻压住已经下锅的鱼身,防止它粘锅,动作行云流水。
周振国站在一旁,高大的身影在狭窄的厨房里显得有些局促。他看着林晚秋利落的动作,
再看看自己手背上那几个碍眼的小红点,
一股混杂着懊恼、不服气和某种奇异专注的情绪涌了上来。他抿紧唇,
没去管那点微不足道的烫伤,目光紧紧锁定在林晚秋握着锅铲的手上,
像新兵观摩教官示范战术动作一样,看得无比认真。加水,放姜片葱段,盖锅盖。
厨房里暂时只剩下汤水滚沸的“咕嘟”声,焦糊味被新生的鱼汤鲜香一点点驱散、取代。
林晚秋看着锅里翻腾的乳白色汤花,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一点点。她下意识地抬眼,
正好撞上周振国专注凝视她的目光。那目光太直接,太认真,像探照灯一样,
让她心头莫名一跳,赶紧移开视线,假装去拨弄灶膛里的柴火。“火……火候看着点,
转小火。”她声音低了些,带着点不自然的别扭。“嗯。”周振国沉沉地应了一声,
目光却依旧没有离开她。厨房里弥漫着鱼汤的鲜香和一种微妙的、难以言喻的安静。
锅盖边缘,白色的水汽不断逸出,氤氲开来,模糊了两人之间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距离。
厨房门关上后,隔绝了外面的议论,却挡不住那隐约传来的、不甚清晰的动静。
先是刺耳的锅铲刮擦声,像是指甲划过黑板,听得人牙酸。接着是短暂的沉寂,
然后是“哗啦”的水声,夹杂着男人低沉的、模糊的应答。再后来,
是油锅爆响的“刺啦”声,似乎还伴随着一声短促的抽气……王秀芬耳朵贴在自家窗缝上,
瓜子都忘了磕,脸上交织着看热闹的兴奋和一点点不易察觉的担忧:“哎哟喂,
听着动静可不小!别是真打起来了吧?小周那身板……”“不能吧?”李爱华也凑近了听,
皱着眉,“小周脾气是倔,可从来没听说他对晚秋动过手啊。顶多……顶多就是被油烫着了?
”她想起自家男人第一次下厨的惨状。“就是!”小赵也压低声音附和,
“周营长对晚秋姐可好了!上回我见着,晚秋姐在河边洗衣服,周营长训练回来路过,
那么大个背包都不卸,硬是蹲河边帮她把那盆子拧干水了才扛着包走的!”“哟,
还有这事儿?”王秀芬来了精神,眼睛发亮,“那敢情好!看来咱们三营长是块石头,
也快被晚秋这丫头给捂热乎了?”“热乎不热乎的咱不敢说,”李爱华抿嘴一笑,
带着过来人的笃定,“可你们没瞧见?刚才晚秋拽小周进屋那架势,小周那腿脚,真想站住,
十个晚秋也拽不动!人家那是乐意被自个儿媳妇儿管着呢!
”这话引得几个女人又是一阵心照不宣的低笑。“哎,你们说,”王秀芬忽然压低声音,
神秘兮兮地,“就小周那厨房里的‘战绩’,今儿这鱼汤,能成吗?晚秋真能把他教会?
”李爱华啜了口茶,老神在在:“教不教会另说,就冲小周今晚肯进那个厨房门,
被油烫了都没撂挑子,这态度,我看就值当!”“就是就是!”小赵猛点头,“我觉着,
晚秋姐心里其实也未必真那么大火气。你们想啊,恢复高考这么大的事儿,
她心里能没点想法?那锅鱼……咳,就是个引子。”这话让几个女人都沉默了一瞬。是啊,
恢复高考了。这消息像颗炸弹,投进了这个闭塞的家属院,
更投进了林晚秋和周振国这桩政策婚姻的死水里,激起的涟漪,谁知道会引向何方?
王秀芬叹了口气,手里的瓜子也不香了:“唉,也是难为晚秋这丫头了。心气儿高着呢,
生生被绊在这儿三年……”厨房里,
那锅鲫鱼汤最终还是在林晚秋的“遥控指挥”和周振国笨拙而极其认真的执行下,
磕磕绊绊地诞生了。汤色是奶白的,上面飘着零星的油花和翠绿的葱花,
卖相居然意外地还不错。周振国像个等待检阅的士兵,绷着脸,用一块厚抹布垫着,
小心翼翼地将那口滚烫的汤锅端到了外间那张四方小饭桌上。林晚秋已经坐下了,
面前放着一碗刚盛好的、冒着热气的糙米饭。她没动筷子,目光落在那锅汤上,
又飞快地瞥了一眼周振国还微微发红的手背。周振国在她对面坐下,腰杆挺得笔直。
他没急着给自己盛汤,而是拿起林晚秋面前的空碗,动作略显僵硬地用汤勺舀了大半碗,
又特意多捞了几块**的鱼肉,稳稳地放到她面前。“小心烫。”他声音低沉,没什么起伏,
目光却紧紧追随着那碗汤,似乎在确认它的安全系数。林晚秋拿起勺子,没看他,
轻轻吹了吹碗里蒸腾的热气,舀起一小勺乳白的汤,送进嘴里。
周振国握着筷子的手不自觉地收紧,指节微微泛白,目光一瞬不瞬地锁定在她的脸上,
屏住了呼吸,像是在等待一项极其重要的军事演习结果评定。汤入口,是浓郁的鲜。
没有想象中的腥气,也没有糊味。盐放得恰到好处,姜的辛辣很好地压住了鱼的土腥,
葱香也融了进去。虽然肯定比不上林晚秋的手艺,
但这对于一个能把厨房变成战场的男人来说,已经是破天荒的奇迹了!林晚秋的动作顿住了。
她垂着眼,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下投下一小片阴影,遮住了眼底翻涌的情绪。
舌尖上那点温热的鲜味,像一把小钩子,猝不及防地勾起了太多东西。这三年来,
他第一次做出一锅能入口的东西。这笨拙的、迟来的汤,混着恢复高考的消息,
在她心里搅起一阵酸涩的涟漪。她没说话,只是又舀了一勺,这次连汤带鱼肉一起,
慢慢地吃着。周振国一直紧紧盯着她的脸,捕捉着她细微的表情变化。
当看到她微微蹙起的眉头似乎舒展了一点点,咀嚼的动作也没有丝毫勉强时,
他那颗悬在嗓子眼的心,才“咚”地一声落回了肚子里。
一股难以言喻的、巨大的成就感瞬间涌遍全身,比第一次实弹打靶得了优秀还要让他激动!
他紧绷的肩膀一下子松弛下来,嘴角甚至不受控制地向上扯了一下,
露出一个极其短暂、几乎难以察觉的傻笑。他赶紧拿起自己的碗,也给自己盛了一碗,
迫不及待地喝了一大口。滚烫的汤滑过喉咙,鲜味在口腔里炸开。他满足地眯了下眼,
随即又想到什么,放下碗,看向林晚秋,眼神亮得惊人,
带着一种近乎邀功的期待:“怎么样?还行吗?”那语气,
像个刚学会叠被子就急吼吼向班长汇报的新兵蛋子。林晚秋抬起眼,
目光落在他那张带着汗渍和油灰、此刻却焕发着奇异光彩的刚毅脸庞上。
他眼底那点纯粹的、因一碗成功鱼汤而迸发的喜悦,像一道微弱却执拗的光,
猝不及防地刺破了她心里积压的阴霾,让她坚硬的外壳裂开了一丝缝隙。
她没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只是用勺子轻轻搅动着碗里的汤,看着奶白的汤花打着旋儿。
沉默了足足有十几秒,才用一种听不出太多情绪、却比之前柔和了不知多少倍的声音开口,
话题转得有些突兀:“广播……你听到了吧?”周振国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
那股刚升腾起的、热乎乎的喜悦,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冰水,迅速冷却、沉淀。
他握着筷子的手无意识地收紧了,指节再次泛白。他当然听到了。那广播响彻整个营区,
像一声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他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恐慌。他缓缓放下筷子,
碗里那点鲜美的鱼汤仿佛瞬间失去了所有滋味。“嗯。”他低低地应了一声,声音干涩。
目光从林晚秋脸上移开,落在油灯跳跃的火苗上,那小小的火焰在他深黑的瞳孔里明明灭灭,
映照出翻涌的复杂情绪——有早就知道的必然,有无法言说的失落,
还有一丝……近乎卑微的祈求?林晚秋看着他的反应,
心里那点酸涩的涟漪骤然扩大成了汹涌的浪潮,几乎要将她淹没。她深吸一口气,
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用那点尖锐的疼痛逼迫自己保持清醒和冷静。她放下勺子,
碗底磕在木桌上,发出轻轻的“咚”一声。“周振国,”她叫他的名字,声音不高,
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郑重,“那三年的政策……当初说好的,只是权宜之计。现在,
高考恢复了。”她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积蓄勇气,又像是在给他反应的时间。
昏黄的灯光下,她的侧脸线条显得有些紧绷,“我……我想试试。”最后几个字,
她说得很轻,却像投入死水中的巨石,在两人之间激起了无声的巨浪。
饭桌上那点短暂的、被一碗鱼汤勉强维持的温情,瞬间荡然无存。只剩下油灯燃烧的哔哔声,
和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默。那锅热气腾腾的鱼汤,兀自散发着鲜香,却再也无人问津。
周振国猛地抬起头,直直地看向她。那双总是锐利、沉稳或带着点无奈懵懂的眼睛里,
此刻翻涌着林晚秋从未见过的激烈情绪——震惊?不,似乎早有预料。痛苦?清晰可见。
还有一种沉沉的、如同受伤野兽般的压抑。他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
喉咙却像被堵住了,只发出一点模糊的、破碎的气音。他想说“不行”,
想说他这三年来早已习惯了有她在的烟火气,
哪怕这烟火气里总夹杂着焦糊味;想说这黄土坡上的小家,虽然简陋,
但每一块砖瓦都浸透了他笨拙的、无声的期待;想说他其实……其实……可那些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