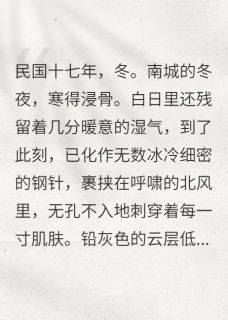
秦铮的目光如同鹰隼,死死锁在她的脸上。那张脸,莹润,沉静,带着大病初愈后的些许柔弱,眉眼温婉,挑不出半分错处。可就是这张看似无害的脸,此刻在他眼中,却蒙上了一层难以言喻的、令人心悸的迷雾。
他沉默着。空气仿佛凝固了,落地罩子灯的暖黄光晕也驱不散这骤然降临的冰冷。外间寒风拍打着窗棂,发出呜呜的声响。
良久,秦铮才开口,声音低沉沙哑,听不出情绪,却带着一种无形的、沉重的压力:“没什么。”他移开目光,不再看她,仿佛多看一眼都会沾染上那冰冷的寒意,“你做得很好。”这句话,更像是一个陈述,而非肯定。
他转身,深灰色的大氅带起一股冷风,径直走向门口,脚步比来时更显沉重。“早些歇息。”丢下这冰冷的四个字,他掀帘而出,身影迅速消失在回廊的黑暗里,没有一丝留恋。
门帘落下,发出轻微的晃动声,隔绝了外面最后一点声响。
内室里,只剩下林书晚一人。
她依旧站在原地,保持着微微抬头的姿势,目光却已从门口收回,落在了方才秦铮站立的位置。那张沉静温婉的脸上,所有的疑惑、温顺如同潮水般褪去,只剩下一种深不见底的平静。如同暴风雨过后,死寂的海面。
她缓缓低下头,目光落在自己那双白皙、骨节分明的手上。指尖,似乎还残留着缝补军装衬衣时,布料粗糙的触感。她轻轻捻了捻指尖,唇角,极其缓慢地、极其清晰地向上勾起。
那是一个冰冷的、无声的、带着了然于心的弧度。
帅府的天,在周慧如死后,并未如众人预想般彻底放晴,反而笼罩上了一层更为诡谲莫测的阴云。
秦铮依旧会来西厢房,只是次数明显减少,间隔也拉长了许多。每次来,他停留的时间都很短,如同例行公事。他不再沉默地坐着看她处理事务或刺绣,而是直接询问府中各项事宜的进展,语气公事公办,冰冷得如同在听取下属汇报军情。偶尔,他那双深不见底的黑眸会锐利地扫过林书晚的脸,带着审视和探究,仿佛要将她平静无波的表象彻底撕开,看清内里隐藏的真相。
林书晚对此,应对得滴水不漏。
她依旧温顺恭敬,姿态放得极低。秦铮问什么,她便答什么,条理清晰,言简意赅,绝不拖泥带水,也绝不多言一句。府务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条,账目清晰,下人规矩,整个府邸运转得如同上了油的机器,比周慧如在时更加高效,也更加……冰冷。
她依旧每日焚香诵经,对着佛龛里那尊白玉观音,神情专注虔诚。素净的衣裙,发髻间那朵小小的白绒花早已摘下,换上了一支素雅的玉簪。她的脸上始终带着一种近乎刻板的平静,仿佛周慧如的死,秦铮的疏离,都不过是窗外飘过的浮云,无法在她心湖激起半分涟漪。
只是,这平静之下,暗流从未停止涌动。
王妈成了林书晚手中最锋利也最隐秘的刀。
正院周慧如留下的人,如同秋后的蚂蚱。那些曾经仗着周慧如势欺压过西厢房的、手脚不干净的、或是知道太多“旧事”的下人,在短短一个月内,以各种“合情合理”的理由被无声无息地清理出了府邸。或是“年老体衰”被恩准回乡养老,或是“手脚笨拙”被调去最苦最脏的庄子,更有甚者,如那个曾为周慧如掌管库房、经手过劣质熏香的李婆子,竟在一天夜里“失足”跌进了后花园结着薄冰的池塘,被发现时早已冻僵。
每一次清理,都做得天衣无缝,证据确凿,让人挑不出半点错处。府中上下噤若寒蝉,看向西厢房那位新太太的眼神里,敬畏之下,更多了一层深入骨髓的恐惧。
西厢房的小佛堂,成了林书晚处理这些“暗务”的场所。袅袅檀香中,她端坐于蒲团之上,手中捻动着冰凉的紫檀佛珠。王妈垂手侍立一旁,声音压得极低,如同耳语。
“……李婆子的儿子在城外赌坊欠了一**债,债主是城西‘斧头帮’的人,下手没轻没重……失足落水,也是‘意外’。”王妈的声音平稳无波,仿佛在陈述一件再寻常不过的小事。
“……周姨娘陪嫁来的那个绣娘,嘴巴不严实,前几日跟浆洗房的婆子嚼舌根,说……说太太您刚进府时,周姨娘赏下的熏香,是她娘家带来的土方子,里面掺了……红花粉……”王妈的声音顿了顿,抬眼飞快地瞥了一下林书晚捻动佛珠的手。
那捻动的手指,没有丝毫停顿,依旧平稳而规律。
“她家里还有个病重的老母亲,在城南的破庙里住着。”林书晚的声音响起,如同古井无波,却带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冰冷,“王妈,你心善,明日送些银钱和棉被过去。告诉她,老人家辛苦一辈子,该……安享晚年了。有些话,听得太多,折寿。”
“是,太太。”王妈心领神会,垂下的眼睑掩去所有情绪,“奴婢会办得‘妥当’。”
佛珠在指尖转动,发出细微的摩擦声。檀香的气息弥漫开来,带着一种诡异的宁神效果。
林书晚的目光落在慈悲的观音像上,眼底深处,却是一片比万年玄冰更冷的寒潭。那潭水之下,是无数被无声吞噬的过往、算计和亡魂。
时间在无声的清洗和表面的平静中滑入深冬。
年关将近,帅府内外却并无多少喜庆气氛。前线战事胶着,秦铮眉头上的川字纹一日深过一日,回府的时间更晚,身上的硝烟和戾气也更重。对林书晚的态度,也愈发冰冷疏离,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审视和警惕。
这天傍晚,秦铮刚踏入前院书房,副官便递上一封加急密电。他拆开一看,脸色瞬间阴沉如铁!电文内容简短,却如同一记重拳砸在他心口——他安插在周家势力范围内的一支精锐别动队,行动路线被泄露,遭遇伏击,几乎全军覆没!
“砰!”秦铮的拳头狠狠砸在厚重的紫檀木书案上!坚硬的桌面发出一声闷响,墨汁飞溅!
“废物!”他低吼一声,眼中戾气翻涌,“查!给我彻查!掘地三尺也要把那个内鬼给我挖出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巨大的愤怒和损失带来的剧痛,让他几乎失去理智。
副官吓得大气不敢出,连忙领命而去。
书房里只剩下秦铮一人,粗重的喘息在死寂中格外清晰。他烦躁地扯开军装领口的扣子,在书房里来回踱步,像一头被困的暴怒雄狮。是谁?是谁泄露了如此机密的情报?周家?还是……府里?
一个冰冷的、带着剧毒的念头,如同毒蛇般猛地窜入他的脑海!林书晚那张沉静温婉、却让他心底发寒的脸,清晰地浮现出来!
是她?会是她吗?
这个念头一旦升起,便如同疯长的藤蔓,瞬间缠绕住他所有的理智!他想起了她眼中那转瞬即逝的冰冷,想起了周慧如死后府中那些“意外”消失的下人,想起了她看似温顺实则滴水不漏的应对……还有,周慧如临死前那歇斯底里的诅咒——“毒妇!**!你不得好死!”
一股冰冷的寒意混合着滔天的怒火,瞬间席卷了秦铮!他猛地转身,像一阵黑色的旋风,冲出书房,带着一身骇人的杀气,直扑西厢房!
沉重的军靴踏在回廊的石板上,发出急促而冰冷的橐橐声,如同死神的鼓点,敲碎了帅府黄昏的宁静。
西厢房内,暖炉烧得正旺。林书晚正坐在窗边的软榻上,就着天光,翻看着一本厚厚的线装古籍。她的侧影安静,眉眼低垂,指尖划过泛黄的书页,发出细微的沙沙声。翠喜安静地侍立在一旁。
“砰——!”房门被一股巨力猛地撞开!
冷风裹挟着浓重的硝烟味和凛冽的杀意,瞬间灌满了温暖的房间!烛火被吹得剧烈摇晃,光影在墙壁上疯狂跳动。
林书晚手中的书卷“啪”地一声掉落在榻上。她惊愕地抬起头。
门口,秦铮高大的身影逆着走廊的光,如同一尊来自地狱的煞神!深灰色的军装大氅沾着未化的雪沫,肩章上的将星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冰冷的寒光。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一片化不开的阴鸷和暴怒!那双深潭般的眼眸,此刻如同燃烧着地狱之火,死死地、毫不掩饰杀意地钉在林书晚的脸上!
翠喜吓得尖叫一声,腿一软,直接瘫坐在了地上,抖如筛糠。
空气仿佛瞬间冻结了!
林书晚脸上的惊愕只维持了一瞬。她看着秦铮眼中那毫不掩饰的、如同实质的杀意,看着他那副要将她生吞活剥的架势,心中瞬间了然。
风暴,终于来了。
她没有像翠喜那样失态。最初的惊愕过后,她的脸色迅速恢复了那种近乎刻板的平静。她缓缓地、极其艰难地从软榻上站起身——动作带着一种大病初愈后的虚弱感,却又异常稳定。
她迎向秦铮那几乎要将她凌迟的目光,没有躲闪,没有恐惧,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慌乱。她的眼神,平静得如同两口深不见底的古井,清晰地映照出秦铮此刻的暴怒和狰狞。
“少帅……”她开口,声音带着一丝因惊吓而起的微颤,却又异常清晰,“您……这是何意?”
“何意?!”秦铮的声音如同冰锥,带着滔天的怒火和刺骨的寒意,狠狠砸了过来!他大步踏入房间,沉重的军靴踏在地毯上,每一步都带着千钧之力!他走到林书晚面前,高大的身影带着巨大的压迫感,几乎将她完全笼罩在阴影里!
“林书晚!”他几乎是咬着牙念出她的名字,每一个字都淬着毒,“收起你那副无辜的嘴脸!告诉我——周家伏击我别动队的消息,是不是你泄露的?!”
他的声音如同惊雷,在房间里炸开!翠喜吓得蜷缩成一团,连哭都不敢哭出声。
林书晚的身体似乎因这巨大的指控而晃了晃,脸色又白了几分。她微微仰起头,迎视着秦铮燃烧着怒火的双眼,那眼神里,竟缓缓地、清晰地浮现出一种……难以置信的悲凉和受伤!
“少帅……”她的声音抖得更厉害了,带着一种被至亲之人背叛的痛楚,“您……您怀疑我?”
“怀疑?!”秦铮猛地抬手,手指几乎戳到她的鼻尖,那根手指因为愤怒而剧烈颤抖,“不是怀疑!是肯定!除了你,还有谁能接触到如此机密?!还有谁,有动机帮着周家对付我?!周慧如死了,周家恨我入骨!而你——林书晚!你巴不得我死!是不是?!”
他的咆哮如同受伤野兽的嘶吼,充满了被背叛的狂怒和毁灭一切的冲动!
林书晚被他逼得后退了一步,后背抵在了冰冷的窗棂上。窗外的寒风透过缝隙钻进来,吹动她鬓边的碎发。她看着眼前这张因暴怒而扭曲的、英俊却无比狰狞的脸,看着那双曾经偶尔流露出复杂情绪、此刻却只剩下杀意的眼睛……
一股巨大的、冰冷的悲哀,如同潮水般瞬间淹没了她!
不是为了自己可能面临的死亡。而是为了……这荒唐的一切!为了她曾经天真可笑的期盼,为了那个在雪夜里被无情碾碎的孩子,为了这深宅大院里日复一日的算计和挣扎!
她的眼眶,瞬间红了。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这彻骨的悲凉和荒谬!
“秦铮……”她第一次,直呼了他的名字。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清晰地盖过了他的咆哮。
秦铮被她这声呼唤和眼中那浓得化不开的悲凉刺得动作一滞。
“你问我……是不是巴不得你死?”林书晚看着他,泪水在眼眶中迅速积聚,却没有落下。那泪光在昏暗的光线下,如同破碎的星辰,映着她惨白的脸,带着一种惊心动魄的凄美和绝望。
她的唇角,极其缓慢地、极其凄楚地向上勾起,那笑容,比哭更令人心碎。
“是……”她看着他,一字一顿,清晰无比,每一个字都像从冰水里捞出来的刀子,带着彻骨的寒意和绝望的控诉,“在你心里,我林书晚,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为了报复你,不惜通敌叛国,引狼入室,也要置你于死地的……毒妇?”
她微微停顿,泪水终于不堪重负,顺着苍白的脸颊滑落,滴在冰冷的窗台上,瞬间凝结成冰。
“那你告诉我……”她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濒死般的凄厉质问,直直刺向秦铮的心口,“当初在雪地里……眼睁睁看着我们的孩子化成一滩血水的时候……在你心里,我又是什么?!一个活该被正室磋磨至死的玩物?一个……连自己骨肉都护不住的废物?!”
“孩子”二字,如同最锋利的匕首,狠狠捅进了秦铮心底最深的、刻意尘封的疮疤!那雪地上的暗红,那绝望的呜咽,那双含泪控诉的眼睛……瞬间无比清晰地在他脑海中炸开!
他所有的暴怒,所有的猜疑,在这一声泣血的控诉下,如同被戳破的气球,骤然一滞!巨大的冲击力让他高大的身躯猛地晃了一下,眼中翻腾的杀意和怒火像是被泼了一盆冰水,瞬间凝固,随即被一种更深的、难以言喻的剧痛和混乱所取代!
他看着眼前泪流满面、眼神绝望凄厉的女人,看着她因激动和虚弱而微微颤抖的身体……那个温顺怯懦的林书晚,那个沉静如水的林书晚,那个在他心底投下冰冷阴影的林书晚……在这一刻,统统消失了!只剩下一个被逼到绝境、撕开所有伪装、只剩下血淋淋伤口和刻骨悲痛的……母亲!
一股强烈的、如同海啸般的愧疚和窒息感,猛地攫住了秦铮的心脏!那愧疚感如此汹涌,甚至瞬间压过了他对泄密事件的愤怒!
“我……”他张了张嘴,喉咙像是被滚烫的烙铁堵住,发出一个干涩的音节,却再也说不出任何指责的话。他伸出的、带着杀意的手,无力地垂落下来。
房间里只剩下林书晚压抑不住的、破碎的抽泣声,和窗外寒风呜咽的悲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