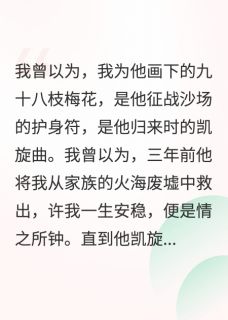
我曾以为,我为他画下的九十八枝梅花,是他征战沙场的护身符,是他归来时的凯旋曲。
我曾以为,三年前他将我从家族的火海废墟中救出,许我一生安稳,便是情之所钟。
直到他凯旋那日,十里红毯,铺的却是通往他白月光府邸的路。直到他命我,
用我这双为他描摹过无数个思念日夜的手,去为那个女人,画一幅贺寿的《喜上眉-梢》图。
我才恍然大悟。我不是他的解语花,我是他豢养的、一支随时可以取用的画笔。我的才情,
我的爱恋,我的一切,都不过是他用来讨好心上人的,一件廉价的礼物。
当他撕碎我用血画就的最后一枝梅时,我便知道,我与他之间,只剩焚心祭骨,再无回头路。
他不知道,他亲手撕碎的,是他此生唯一的救赎。1、大梁,景和三年,冬。北境大捷。
摄政王萧策,率领十万铁骑,踏破敌国都城,凯旋归来。这个消息,像一团燎原的烈火,
在短短一个时辰内,烧遍了整座皇城。百姓们涌上街头,十里长街,红毯铺地,彩旗飘扬。
欢呼声如山崩海啸,几乎要将天际的流云都震散。“王爷千岁!大梁战神!”“王爷威武!
”声浪一波高过一波,穿透了重重宫墙,也穿透了我这“雪芜院”的高墙。雪芜院。
摄政王府最偏僻,也最冷清的院落。是我,姜雪宁,
被他从三年前那场家破人亡的废墟中救出后,便一直居住的囚笼。我是他的侧妃。
一个上不得台面,甚至连皇家玉牒都未曾录入的名分。一个世人皆知,
却又被刻意遗忘的存在。外面的喧嚣,与我无关。我独坐在空旷的画室里,
面前是一张巨大的宣纸。纸上,是九十八枝姿态各异的红梅。或含苞,或怒放,或迎风,
或傲雪。每一枝,都是我用指尖的血,混着上好的朱砂,一笔一笔,勾勒而成。
他出征的九百八十个日夜,我便画了九十八枝梅。日日盼,夜夜盼。盼他平安,盼他归来。
如今,他归来了。成了万民敬仰的英雄,成了大梁说一不二的擎天之柱。可他的铁蹄,
踏遍了京城的每一寸土地,却唯独,没有踏入这王府一步。
我从院里洒扫丫鬟的窃窃私语中得知。他的仪仗,在城门口,便转了道。径直,去了相府。
那里,住着他心心念念的白月光,当朝丞相的嫡长女,沈云瑶。原来,他不是不想回来。
只是,不想回我这里来。我曾天真地以为,我是不同的。三年前,姜家满门获罪,
父亲被冤死狱中,百年基业,一夜之间,付之一炬。是他,将我从那片火海与绝望中,
抱了出来。他将我安置在这王府之中,对我说:“雪宁,从今往后,有本王在,
便无人再敢欺你。你只管安心作画,本王,许你一生安稳。”他曾说,我是他的解语花,
是这世上唯一能懂他心中丘壑之人。他曾说,我的画,是他出征前,必须看到的“凯旋旗”。
那些温柔的话语,犹在耳畔。可那些许诺,却早已,恍如隔世。我深吸一口气,
压下喉间翻涌的苦涩,默默地开始研磨。他回来了,我的画,也该完成了。第九十九枝。
圆满。我拿起桌上的银针,正要刺破指尖,为这九百多个日夜的等待,画上一个句点。
“吱呀——”院门,被重重地推开。我抬起头,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萧策的贴身太监,
李总管。他脸上挂着虚伪的笑容,眼神里,却满是毫不掩饰的轻蔑与不屑。我的心,
不受控制地,猛地一跳。是他……让他来的吗?他终于,想起我了?我放下银针,起身,
想要行礼。“侧妃娘娘,不必多礼。”李总管虚虚一拦,那尖细的嗓音,在寂静的画室里,
显得格外刺耳。“王爷有口谕。”我屏住呼吸,静静地听着。“王爷命您,
即刻画一幅《喜上眉梢》图。”我的心,沉了下去。“要快,要好。”李总管的下巴,
微微扬起,用眼角的余光,瞥着我,“三日后,是沈**的生辰,王爷要拿去,作贺礼。
”轰的一声。我脑子里最后一根紧绷的弦,断了。原来,他不是想起我了。他只是,
想起了我的这双手,想起了我的这点用处。他记得沈云瑶的生辰,却忘了,今日,
也是我的生辰。他记得要讨好他的心上人,便将我的才情,我的心意,
我这三年所有的等待与煎熬,都当成了一件可以随意取用、赠予他人的礼物。我看着李总管,
嘴唇翕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因为李总管脸上的笑容,更冷了,
也更得意了。他上前一步,压低了声音,那声音像毒蛇的信子,嘶嘶作响。“王爷还说了。
”“沈**的一颦一笑,比你这满屋子的画,加起来都金贵。”“侧妃娘娘,您可千万,
别不识抬举。”这轻飘飘的一句话,像一把淬了剧毒的利刃,将我最后一点点可笑的希冀,
绞得粉碎。我死死地咬住嘴唇,直到口腔里,弥漫开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我强忍着,
不让眼泪落下来。不能哭。不能在这个小人面前,露出半分软弱。李总管见我沉默,
似乎很满意我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他哼着小曲,转身,准备离开。在他转身的瞬间,
他手中的拂尘,看似不经意地,轻轻一扫。“啪嗒——”一声脆响。我画案上,
那方我最珍爱的、父亲留给我唯一的遗物——端溪龙纹砚台,应声落地。摔得,四分五裂。
漆黑的墨汁,尽数泼洒而出。将我画案角落里,一幅刚刚画好,墨迹未干的小小画卷,
污了个彻底。那上面,画的是我,和萧策。他穿着玄色铠甲,英姿勃发。我踮起脚尖,
为他理着肩上的披风。那是我凭着记忆,画下的,我们之间,唯一的“合影”。我的心,
像是被那滩冰冷的墨汁,一同浸透了。又冷,又痛,痛到麻木。一滴滚烫的液体,
终究是没能忍住。从我的眼角,悄无声息地滑落,砸在手边的宣纸上。晕开了一小团,
模糊的水渍。李总管走后,画室里,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我再也支撑不住,扶着画案,
剧烈地咳嗽起来。仿佛要将我的五脏六腑,都咳出来。我摊开一方素白的手帕,
想要拭去嘴角的苦涩。手帕上,一抹刺目惊心的红,赫然出现。那颜色,竟比我画上的朱砂,
还要艳丽,还要触目。我看着那抹红色,忽然,就笑了。笑得凄凉,笑得绝望。原来,
我的身体,早就撑不住了。这样也好。或许,等不到画完那幅《喜上眉-梢》,我就可以,
解脱了。2、我的身体,日渐沉重。夜里,总是被彻骨的寒意惊醒,整夜整夜地咳。
咳出的血,也越来越多。我不敢请大夫,也不想请。在这座冰冷的王府里,我是个多余的人。
我的病,自然也是多余的。我唯一的念想,只剩下守住姜家仅存的宗祠牌位。
自我姜家满门获罪,百年清誉毁于一旦后,这些被我从火场中拼死抢救出来的牌位,
便是我与这个世界,最后的联系。是我活下去,唯一的根。我将它们,
小心翼翼地供奉在雪芜院最里间的偏殿里。日日擦拭,夜夜焚香。对着它们,就好像,
还能感受到一丝来自家人的,温暖。这夜,北风呼啸,大雪纷飞。我正跪在冰冷的蒲团上,
为我那被冤死的父亲,祈福。一股浓烈刺鼻的焦糊味,忽然,钻入了我的鼻腔。“走水了!
走水了!”“雪芜院走水了!”院外,传来下人们惊慌失措的叫喊声。我猛地回头,
瞳孔骤然紧缩!只见存放牌位的那间偏殿,窗户里,已经透出了骇人听闻的,冲天火光!
“父亲!”我的脑中,一片空白。所有的理智,瞬间被恐惧和绝望吞噬。
我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直奔那片,足以吞噬一切的火海。滚烫的热浪,扑面而来,
灼烧着我的皮肤,我的头发。呛人的浓烟,让我几乎窒息,眼泪直流。我什么都顾不得了。
我用袖子捂住口鼻,一头,扎进了那片炼狱般的火场。在烈焰与浓烟之中,我凭借着记忆,
找到了那个供奉着我姜家列祖列宗牌位的神龛。
“父亲……女儿来带你们出去了……”我拼死护住父亲的那块主位牌位,用尽全身的力气,
将它紧紧地,抱在怀里。然后,踉踉跄跄地,冲了出来。刚冲出火场,我便腿一软,
重重地摔倒在地。雪花,落在我的脸上,瞬间融化。一双金丝云纹的黑色云靴,
停在了我的面前。那是我最熟悉的,靴子。我抬起头,透过迷蒙的泪眼和烟雾,看到了他。
萧策。他来了。他终于,来了。在我心中,刚刚燃起一丝微弱的希望时。我便看到了,
他身后,那个被他小心翼翼地,护在怀里的人。沈云瑶。她穿着一身华贵无比的狐裘大氅,
此刻却花容失色,柔弱无骨地,靠在萧策宽阔的胸膛里。一双美丽的眸子里,
含着晶莹的泪水,楚楚可怜,我见犹怜。“王爷……我好怕……”她的声音,都在发颤,
小手,紧紧地抓着萧策的衣襟,“这火光……冲天而起,
吓得我……心口好疼……好疼啊……”萧策立刻低下头,那双看我时永远冰冷的眸子里,
此刻,却盛满了化不开的温柔与心疼。“瑶儿别怕,有本王在,不会有事的。
”他柔声安慰着怀中的珍宝。安抚完了沈云瑶,他才终于,将目光,投向了地上,
那个狼狈不堪,满身烟灰的我。他的眼神,没有丝毫的怜惜与担忧。反而,
充满了冰冷刺骨的,厌恶与憎恨。仿佛我不是一个刚刚从火场中死里逃生的人。而是一个,
令人作呕的,肮脏的垃圾。“姜雪宁。”他开口,声音冷得,像是这腊月的寒冰。
“又是你搞的鬼?”我抱着怀中那块被熏得漆黑的牌位,难以置信地,看着他。火,
不是我放的。我甚至,差点死在里面。他看不见吗?“你以为,用这种下作的,
自导自演的手段,就能博得本王的关注?”他一步一步,向我走来。他高大的身影,
投下的阴影,将我完全笼罩。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千斤重的巨锤,
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本王告诉你,你这点肮脏的心思,只会让本王,觉得恶心!
”“你连给瑶儿提鞋,都不配!”他竟然认为,是我,为了与沈云瑶争宠,
不惜放火烧掉自己的院子。我张了张嘴,想解释,想辩驳,想告诉他,
里面是我姜家唯一的宗祠。可我的喉咙,像是被浓烟和绝望,死死地堵住。一个字,
也说不出来。看着我怀中那块黑漆漆的牌位,他眼中的厌恶,更深了。“一个死人的牌位,
也值得你如此大动干戈?”他看也不看那曾是他名义上的岳丈的牌位,只搂着怀中,
还在瑟瑟发抖的沈云瑶。对闻讯赶来的侍卫,冷酷无情地,下达了命令。“把这个疯女人,
给本王关进柴房!”“没有本王的命令,不许出来!”“免得她再跑出来,吓到了瑶儿!
”两个如狼似虎的侍卫,立刻上前,粗暴地,将我从冰冷的雪地里,拖了起来。
“不……放开我……”我挣扎着,想要护住怀里的牌位。挣扎间,我怀中紧抱的牌位,
“哐当”一声,掉落在了地上。萧策正要转身离去,拥着他的心上人,回到那温暖的屋舍。
他的靴子,不偏不倚地,正好,踩在了我父亲的牌位之上。他甚至,没有低头看一眼。脚下,
传来木头碎裂的,轻微声响。他就那样,踩着我父亲最后的尊严,踩着我姜家最后的念想,
拥着他的白月光,头也不回地,走了。我被拖入那间阴冷潮湿、四处漏风的柴房。门,
被重重地锁上。我抱着那块冰冷的、沾着泥土和雪水,已经裂开一道缝隙的牌位。看着窗外,
沈云瑶院落里,透出的那片温暖融融的灯火。绝望的眼泪,混合着脸上的灰尘,划出了两道,
泥泞不堪的痕迹。夜半,寒气入体。我因吸入过多浓烟的肺腑,开始剧烈地,
撕裂般地疼痛起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之后,我再次,咳出了血。紧接着,
一阵前所未有的、剧烈的腹痛,猛地,从我的小腹处,袭来。那是一种,绞痛。像是,
有什么东西,在我的身体里,被活生生地,剥离。我惊恐地,抚上自己的小腹。
那里……那里,似乎有一个小小的,无辜的生命,在无声地,**着这个世界的冰冷与残忍。
我……我竟然,有了身孕。3、王府里,唯一还对我存有几分旧情的张嬷嬷,趁着夜色,
偷偷为我请来了一位年迈的大夫。老大夫不敢进柴房,只能隔着冰冷的门板,为我切脉。
昏暗的油灯下,他的脸色,越来越凝重。许久,他才叹了口气。“恭喜娘娘,是喜脉。已有,
两个月身孕了。”我的心,狠狠一颤。不知是喜,是悲。“但……”老大夫话锋一转,
声音里充满了担忧,“娘娘您忧思过重,心力交瘁,又受了惊吓,吸入烟尘,
寒气入体……这胎像,已是极不稳固了。”“若不立刻静养安胎,用上好的药材温补着,
恐怕……恐怕这孩子,是保不住的啊。”张嬷嬷跪在地上,抹着眼泪,
求我一定要为了孩子保重。她不知从哪里,偷偷求来了一副安胎药,每日躲过下人的耳目,
在柴房那个破旧的小炉子上,为我熬煮。那碗黑褐色的药汁,苦得令人发指。却是我,
和我腹中这个无辜的孩子,唯一的希望。**着这一点点微弱的希望,撑着。这日,
我正小口小口地,喝着那碗滚烫的药。柴房的门,却“吱呀”一声,被从外面,推开了。
刺眼的阳光,照了进来。沈云瑶穿着一身艳丽无比的宫装,珠翠环绕,在几个丫鬟的簇拥下,
款款地,走了进来。她像是来巡视自己领地的女王,嫌恶地用一方绣着金丝牡丹的手帕,
掩住口鼻,打量着这间破败、潮湿的柴房。“姐姐,王爷让妹妹来看看你。
”她在我面前站定,脸上,挂着一抹得体又虚伪的微笑。“姐姐在这里,住得可还习惯?
”我没有理她,只是低下头,护着手中那碗,比我的命还重要的药。她也不恼,自顾自地,
炫耀起来。“姐姐你看,这是王爷昨日派人从东海,为我寻来的夜明珠,好看吗?
”她晃了晃手腕上,那串硕大无比、光华流转的珠串。“哦,还有这个,
”她又抬起另一只手,“西域进贡的血玉镯子,王爷说,最衬我的肤色了。姐姐觉得呢?
”她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根细细的针,不疾不徐地,扎在我的心上。“对了,
”她仿佛忽然想起了什么,用一种天真烂漫的语气,说道:“王爷已经向圣上请旨,不日,
便会立我为摄政王府唯一的正妃了。”“到那时,姐姐可要记得,来喝一杯妹妹的喜酒啊。
”我的手,猛地一抖。滚烫的药汁,差点洒了出来。她的目光,终于,
落在了我手中的那碗药上。她的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ACLE的,恶毒。她忽然,
像是被什么东西吓到了一般,夸张地,向后退了一大步。她一手捂住胸口,柳眉紧蹙,
呼吸瞬间变得急促起来。
“啊……这是什么味道……好难闻……好刺鼻……”她面露痛苦之色,仿佛随时都要晕过去。
“王爷!王爷救我!”她凄厉地,朝着门外喊道,“这药味……与我的八字相冲!
我……我闻了便心如刀绞……好难受……我喘不过气了……”她的声音,凄厉而做作,
足以传遍半个王府。几乎是她话音刚落。萧策高大挺拔的身影,便像一阵旋风似的,
冲了进来。“瑶儿!瑶儿你怎么了?”他一把将摇摇欲坠的沈云瑶,紧紧地搂入怀中,眼中,
满是焦急与心疼。沈云瑶虚弱地,伸出纤纤玉指,指向我,和我手中的那碗药。
“王爷……是那碗药……我好难受……我的心,好痛……”萧策的目光,瞬间,
像两把淬了寒冰的利刃,狠狠地,射向我。“姜雪宁!你的心肠,到底有多恶毒?!
”他不给我任何解释的机会。一个箭步上前,一把,夺过我手中那只滚烫的药碗。然后,
狠狠地,砸在了地上!“啪——!”瓷片,四溅。黑褐色的药汁,溅了我满身满脸。
“为了你肚子里这个孽种,你竟然想用药气,来谋害瑶儿?”他的声音,是暴怒过后的,
极致的冰冷。“你简直,丧心病狂!无可救药!
”“不……不是的……”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我颤抖着,想要解释,
“这是……这是安胎药……是我们的……”“闭嘴!”他粗暴地,打断我的话,
“本王不想听你任何一句狡辩!”他转过头,对跟在他身后的下人,厉声命令道:“去!
把院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草药,都给本王连根拔起!一把火,烧个干干净净!
”“免得再留着,污了瑶儿的眼!”下人们,立刻行动起来。我那些保命的药草,
我孩子的救命药,就那样,被无情地,摧毁,践踏。做完这一切,萧策脸上的怒气,
仿佛才消了些。他从怀中,掏出一颗晶莹剔透、红得滴血的荔枝。那是今年,
快马加鞭从岭南送来的第一批贡品。他亲手,为沈云瑶剥开,温柔地,喂到她的嘴边,
仿佛在奖赏她的“懂事”与“乖巧”。“瑶儿乖,吃了这个,就不难受了。
”沈云瑶在他宽阔的怀抱中,抬起头,对我,露出一抹胜利的、恶毒的微笑。她用口型,
无声地,对我说出了那句,将我彻底打入万劫不复深渊的话。“姐姐,你知道,
王爷为何如此信我吗?”“因为,当年,在火场里救他的人,是**我**啊。
”4、萧策与沈云瑶的大婚之日,到了。整个摄政王府,张灯结彩,鼓乐喧天。大红的绸缎,
从府门一直铺到喜堂,一路喜气洋洋。所有的下人,都换上了新衣,脸上挂着谄媚的笑。
整个京城,都在为这场盛大的婚礼,而沸腾。而我,在冰冷潮湿的柴房里。身下,
是不断涌出的,温热的鲜血。腹中,一阵阵的绞痛,像是要将我的生命,一寸一寸地,
从我的身体里,撕裂出去。我的孩子……我那还未成形的孩子……终究,还是没能保住。
他甚至,都没来得及,看一眼这个,对他来说,太过残忍的世界。在血泊与剧痛的弥留之际,
我的意识,开始变得模糊。我仿佛,回到了五年前的那个雪夜。我从被抄家的火海中,
狼狈逃出。在城外的一间破庙里,遇到了重伤昏迷,奄奄一息的他。他浑身是血,高烧不退。
我用自己身上,唯一还算干净的里衣,撕下布条。我用发簪,划破了自己的指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