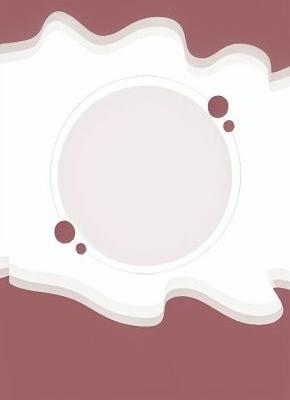
1教授说,我的手指是为钢琴而生的,维也纳音乐学院的保送名额,板上钉钉。
我甚至能想象到金色大厅的穹顶下,我的指尖如何在琴键上起舞。
我捏着那张轻飘飘却重若千钧的通知书,心脏怦怦跳,第一个想告诉顾淮,
我以为我们会共享这无上荣光,他在画布前挥洒色彩,我在琴键上编织旋律。
我在画室找到他时,夕阳正好,给他周身镀上一层虚幻的光晕。他正对着一幅画精雕细琢,
画上是苏晴巧笑倩兮的侧影,连眼角那颗他曾说“平添风情”的小痣,都点得恰到好处,
栩栩如生。听到我的好消息,他握着画笔的手顿了顿,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脸上的笑容从灿烂变得僵硬,最后凝固成一张尴尬的面具。然后他转过身,
用那种我无法抗拒的、带着破碎感和全然的依赖的眼神看着我:“晚晚,没有你,
我的灵感就死了。你看,没有你在旁边弹琴,我这幅画都失去了灵魂。你去那么远,
我怎么办?”他的声音低沉,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沙哑,像羽毛搔刮着我的心尖。
他抓住我的手,指尖冰凉,却带着一种灼人的、不容拒绝的力道:“有个选秀节目找我了,
这是我的机会。留下来,陪着我。你是我唯一的缪斯,等我成功了,我的世界都是你的,
完完全全属于你。”你是我唯一的缪斯。就这一句话,我TM脑子一热,理智瞬间蒸发,
干了这辈子最蠢的事,还自以为是为爱牺牲的伟大壮举。我放弃了维也纳。不是简单的放弃,
是我亲自去找了苏晴,在她家那间奢华得令我窒息的琴房里,
在她看似惊讶、眼底却闪过一丝“果然如此”的了然注视下,
几乎是低声下气地、“请求”她把名额“让”给她。顾淮就站在我身边,亲密地搂着我的肩,
温声劝诱,字字句句却都像在给我的坟墓填土:“晚晚,
苏晴家能在我比赛时提供关键的人脉和资金助力,这是人情,我们得还,
以后对我的事业大有裨益。而且,苏晴也是真心喜欢音乐的,你的名额给她,不算埋没,
是……另一种延续。”我看着苏晴眼底那抹一闪而过的、属于胜利者的轻蔑和嘲讽,
喉咙像是被一团湿透的棉花死死堵住,发不出任何声音。
甚至还在顾淮后续几次看似无意的暗示和抱怨“启动资金不足”、“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下,
我爸妈车祸留下的全部赔偿金——那是我这些年紧紧攥着、不敢多花一分的生活依靠和念想,
连同我那笔本该是大学学费的、象征着我最后尊严的奖学金,厚厚一沓,
带着我体温和最后希望的红色钞票,像个虔诚的、被洗脑的贡女,塞进他怀里:“阿淮,
去追你的梦,我等你。”他用力抱着我,灼热的呼吸喷在我耳边,
说的情话滚烫得几乎要将我融化:“晚晚,我绝不负你。
”那时我被虚幻的爱情蒙蔽了双眼,不知道,有些承诺,从一开始就是精心编织的谎言,
是裹着蜜糖的砒霜,是注定用来背叛的。我去找苏晴“让”名额的那天,
她正在弹奏一首李斯特的《钟》,技巧华丽却毫无感情,像一场冰冷的技巧炫耀。
听到我的来意,她的手指重重落在琴键上,发出一声刺耳的杂音。她站起身,走到我面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说:“林晚,你看,有些东西,
你拼了命也得不到,而我,只需要轻轻伸手。”她抚摸着那架斯坦威钢琴光亮的漆面,
“就像这架琴,就像……顾淮。”那一刻,我清楚地看到了她眼底毫不掩饰的掠夺和快意。
2顾淮真的火了。他那张脸是顶级的通行证,
再加上我熬夜到凌晨三点、呕心沥血给他写的一首首原创曲子——那些旋律,
是我挤在狭窄逼仄、连窗户都对着阴冷通风井的保姆房角落,啃着干硬的面包,
在他和苏晴长时间通话、时而传来的娇笑声背景音里,从快要干涸的灵感沙漠里,
硬生生挤出来的血和泪。他像坐火箭一样蹿成顶流,光芒万丈。而我,
则成了他背后那个不见天日的“影子”。
住在他那套豪华公寓里最小的、仿佛是用来堆放杂物的房间。每天叫醒我的不是梦想和琴声,
是他要喝的、火候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行、否则就会被他皱眉挑剔的养胃粥,
和他那挑剔的白月光苏晴临时起意要求的、需要现榨现调、步骤繁琐的什么鬼低脂沙拉。
我的世界从广阔的肖邦贝多芬,急剧收缩成他密密麻麻的行程表、永无止境的通告单,
和永远也熨不完的、带着苏晴身上那股甜腻得令人作呕的香水味的昂贵演出服。
绯闻开始铺天盖地,全是顾淮和苏晴。金童玉女,天作之合,
仿佛他们是命中注定的灵魂伴侣。一次活动结束,记者堵住他,镜头像长枪短炮般对准,
有人直接问:“淮哥,一直默默跟在你身后那个小姑娘,是谁啊?看起来挺照顾你的。
”我当时就站在他身后两步远,像个透明的影子,
着、以备他不小心被粉丝挤到或酒水泼溅时可以立刻换上的崭新衬衫和温度恰到好口的温水。
我听见他对着镜头,连眼角余光都未曾扫向我,只是轻笑一声,
语气随意轻慢得像是在弹掉身上一点无关紧要的灰尘:“她?就我家一小保姆,用了很多年,
挺懂事,知道分寸,不会烦我。”那一瞬间,
我好像听见了自己心脏被瞬间冻僵然后被无情碾碎的声音。咔嚓,稀里哗啦,碎成一地残渣。
小保姆?挺懂事?知道分寸?
己因为长期浸泡在刺鼻洗涤剂和冰冷水里而发红、破皮、甚至指关节都有些微微变形的手指,
这双手,曾经在黑白琴键上如蝴蝶般飞舞,敲出的每一个灵动的音符,
流淌出的每一段动人的旋律,都被他理所当然地冠上自己的名字,
成了他“音乐才子”王冠上最璀璨、最引人注目的钻石,而我这挖掘钻石的人,
却被他弃如敝履,踩入泥泞。有一次,苏晴“好心”来公寓“探望”顾淮,
实际上是来炫耀她新得的某个珠宝。
她看到我正在手洗顾淮一件珍贵的真丝衬衫(他声称洗衣机洗不干净),
故意“失手”将半杯红酒泼在我刚熨好的、顾淮晚上要穿去领奖的白色西装上。
然后她惊呼一声,对着闻声出来的顾淮泫然欲泣:“阿淮,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晚晚好像没拿稳……”顾淮看都没看那件价值不菲的西装,
立刻心疼地搂住苏晴,转头对我厉声呵斥:“林晚!你怎么做事的?毛手毛脚!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我看着他那张写满维护和不耐烦的俊脸,
和苏晴靠在他怀里投来的、那抹得意而恶毒的眼神,第一次清晰地认识到,
我连“保姆”都不如,我只是他们爱情游戏里一个可以随意牺牲、承担错误的道具。
3顾淮和苏晴的订婚典礼,搞得盛大无比,全网直播,普天同庆,仿佛一场全民狂欢的盛宴。
我像个幽灵一样,缩在保姆房冰冷的角落里,看着屏幕上,
他给苏晴戴上那颗据说价值连城、璀璨夺目的鸽子蛋,苏晴笑得一脸幸福娇羞,
依偎在他怀里,接受着全世界的祝福和艳羡。奇怪,
心口那片早就被反复凌迟、麻木不堪的荒地,此刻居然连一丝涟漪都泛不起了,
只剩下无边无际的空洞风声,呼啸着穿过我残破的灵魂。也就在那天晚上,
当外面的烟花绚烂照亮夜空时,医院打电话来了,
说我几个月前因为持续低烧和身上莫名出现淤青去做的全面检查,结果出来了。“林**,
您的基因病确诊了……是一种非常罕见的隐性遗传病,情况很不好,剩余时间,
可能不到三个月了。”医生的声音平静而残酷,像是在宣读一份与我无关的判决书。
电话那头还在说着什么可能的治疗方案、注意事项、需要家属陪同,我已经完全听不见了。
耳朵里嗡嗡作响,只有屏幕上订婚宴的喧嚣背景音和医生那句“不到三个月”在反复回荡。
我看着屏幕上烟花绚烂,映照着顾淮和苏晴深情拥吻的身影,
又低头看了看自己苍白瘦弱、青紫色血管清晰可见的手腕,那里似乎已经能闻到死亡的气息。
我突然就笑了,笑得眼泪都涌了出来,却又赶紧死死捂住嘴,怕被隔壁或许存在的谁听见,
连悲伤都不敢放肆。**应景啊。我的爱情和我的命,手拉着手,
一起给我下了最后的死亡通知,连个缓刑都不给,干脆利落。我没哭没闹,甚至异常平静。
我安静地收拾了我那点寒酸得可怜的行李,连一只小小的行李箱都没装满。临走前,
我把那厚厚一沓,
细编曲思路、甚至是我在无数个深夜里灵感迸发时随手记下的、沾着泪痕或咖啡渍的碎纸片,
全都分门别类、整整齐齐地,堆在了他客厅那张意大利定制、光可鉴人、价值不菲的茶几上。
像一座沉默的,为我自己痴傻的付出、也为这段彻底死亡的感情,亲手垒起的、冰冷的坟墓。
在整理手稿时,我翻到了最初为他写《星辰》的那张草稿纸,
背面还有他当年写下的、如今看来讽刺无比的“给晚晚,我的星辰”。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拿起笔,在那行字下面,
用力地、几乎划破纸背地写下了两个字:祭品。是的,我就是那个被献祭的祭品,
用我的才华、我的梦想、我的爱情,甚至我的生命,供奉了他和苏晴的“爱情神话”。
4我的消失,起初果然没掀起半点波澜,
或许顾淮正彻底沉浸在和他的白月光柔情蜜意、规划未来的温柔乡里,
根本没发现身边少了个“懂事”、“知道分寸”的保姆。直到他信心满满地筹备新专辑,
却发现自己江郎才尽,灵感枯竭,交上去的demo被金牌**人直接摔在桌上,
骂得狗血淋头,丝毫不留情面:“顾淮!你TM以前的灵气呢?被狗吃了吗?!
《星辰》那种惊为天人、灵气逼人的歌你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啊?!
你现在写的这都是什么垃圾!狗屁不通!没有一首能用的!
你知不知道公司在你身上投了多少钱?你就拿这玩意儿来糊弄?”他焦头烂额,压力巨大,
脾气也变得异常暴躁,终于在某个深夜,醉醺醺、脚步踉跄地回到家,
看到了茶几上那堆他之前一直以为是废纸、碍眼却又没空收拾的东西。他烦躁地抓起来,
看也不看就想揉成一团扔进旁边的垃圾桶。然后,他的动作猛地僵住了,
醉意瞬间清醒了大半,脸色一秒刷白,嘴唇失去血色,像是被人迎面用铁锤狠狠打了一拳,
踉跄着后退了一步,撞到了身后的沙发。那上面,是他所有成名曲的、**裸的原始手稿!
从让他一曲封神、被无数粉丝奉为“出道即巅峰”、“不可复制神作”的《星辰》,
到奠定他乐坛地位、拿奖拿到手软、被乐评人誉为“年度金曲”的《永夜》,
再到后面每一首维持他热度的歌曲……每一首,每一个跳跃的、充满灵性的音符,
每一段精妙绝伦、让人拍案叫绝的**进行,
些让他被专业人士夸赞“富有创意和想法”的编曲巧思和天衣无缝的段落过渡……密密麻麻,
力透纸背,全是我林晚的笔迹!有些地方,
还有我为了推敲一个更合适的音符或**而反复涂抹、修改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