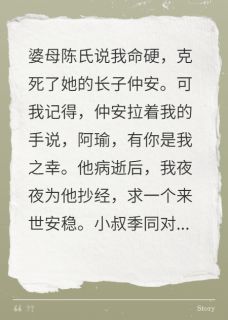
婆母陈氏说我命硬,克死了她的长子仲安。可我记得,仲**着我的手说,阿瑜,
有你是我之幸。他病逝后,我夜夜为他抄经,求一个来世安稳。小叔季同对我说,嫂嫂,
兄长不在了,还有我。他跪在祠堂,求婆母允他兼祧两房,为兄长留后。我感激涕零,
以为他是我的救赎。直到那夜,我送安神汤去婆母房中,听见季同在笑。“娘,您放心,
大哥那碗药,我亲手加的量。”“他那病秧子身子,怎么配得上阿瑜?如今她是我的人了,
肚里的孩子,也是我的种。”我端着汤碗的手,抖得几乎握不住。原来我日夜祈福的亡夫,
是被他亲弟弟害死的。我腹中所谓的“遗腹子”,竟是仇人的骨血。回到房中,
我将抄了半年的经文一页页撕碎,混着安神汤,喂给了窗台那盆他最爱的兰花。
1那盆“君子兰”是季同送来的,他说,这是仲安生前最爱的品种,花开清贵,最配嫂嫂。
我曾信了。如今,我亲手将这碗为我“安神”,为仲安“超度”的毒汤,
尽数浇灌进它的根部。不过片刻,那原本翠绿的根茎,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发黑、腐烂。
真好,连它都知道该去死。“阿瑜?”房门被推开,季同走了进来。他看到我,
看到我脚边的狼藉,看到那盆垂死的兰花。“嫂嫂,你这是做什么?我知道你心里苦,
可也不能这样作践自己,作践兄长喜欢的东西啊。”他快步上前,握住我的手腕。
他的掌心温热,带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气息。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几乎要吐出来。
我没有挣扎,只是任由他握着,身体止不住地颤抖。他以为我是悲伤过度,将我揽进怀里。
“别怕,嫂嫂,都过去了。兄长泉下有知,也不愿看你如此。你如今有了身孕,
要为季家的骨肉保重身体。”我强忍着心头的恶心,将脸埋在他的胸口,
用最微弱的语调开口。“季同,我...我只是又想起了仲安...”“我总觉得,
是我没有照顾好他,他走的那几日,喝的药是不是太苦了?我记得府医说那药性子烈,
可他为什么...为什么还是撑不住...”我能感到季同的身体僵硬了一瞬。
他拍着我的背,用一种自以为万分温柔的语气安抚我。“傻嫂嫂,这怎么能怪你。兄长的病,
积重难返。府医开的药,都是吊着命的虎狼之药,是药三分毒,伤身子是难免的。
”“我去看他时,他还和我说,幸好有你陪着,他才没那么疼。”他顿了顿,
似乎在斟酌用词。“至于那最后一味药引,陈皮...是我亲自去加的。大夫说,
陈皮能固本培元,兴许能有奇效。谁知...天命如此,非人力可回天啊。”陈皮。
我心中一片冰冷。仲安自幼便对柑橘类的东西过敏,入口即发风疹,呼吸困难。整个季家,
无人不知。而他季同,此刻正用最温柔的谎言,亲口向我承认了他的罪行。一个多么微小,
却又多么致命的破绽。我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用疼痛来维持清醒。我不能倒下,不能崩溃。
我的仲安,我那温润如玉的夫君,他还在等我。等我把这些披着人皮的畜生,一个个,
都拖进无间地狱。我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他。“原来是这样,季同,
幸好还有你...”我主动伸出双臂,环住他的腰。他以为我找到了新的依靠,
身体放松下来,回抱住我,在我耳边低语。“嫂嫂,你放心。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天,
你和孩子,我都会照顾好的。”“兄长不在了,他的所有,就都由我来继承。
”他说得理所当然,带着胜利者的炫耀和对猎物的占有欲。我闭上眼睛,任由泪水滑落。
好的,季同。这出戏,我陪你演。你的“深情”,你的“担当”,你的“救赎”。
我会一件一件,亲手帮你剥下来,让你露出血肉模糊的骨头。就从我肚子里,
你最看重的这块肉开始。翌日清晨,我便“病”了。孕吐不止,水米不进。
2婆母陈氏带着府中医士来看我时,我正抱着痰盂,吐得脸色惨白。“真是没用的东西,
怀个孩子都这么娇气。”陈氏嫌恶地用帕子掩着口鼻,尖酸的话语毫不掩饰。
“快让王医士给你瞧瞧,我季家的长孙,可不能有半点闪失。”我虚弱地摆了摆手,
不等那姓王的医士上前,便气若游丝地开口。“母亲,儿媳不敢劳烦王医士。
只是这胎动来得凶险,儿媳信不过旁人,想请我娘家常用的张大夫来看看。
”“他最是了解我的身子,也最稳妥。”陈氏的眉头拧成一团。“你娘家的人?一个外人,
哪有府里的府医用着放心!”季同适时地走了进来,扶住陈氏的胳膊。“娘,
您就依了嫂嫂吧。她如今身子重,心情最要紧。再说,张大夫在城中也是有些名望的,
不会出岔子。”他转向我,语气关切。“嫂嫂,你别急,我这就派人去请张大夫。
”陈氏冷哼一声,大约是觉得我翻不出什么风浪,便不再坚持。“罢了罢了,随你。
只要我孙子安安稳稳的,什么都好说。”她说完,便扭着腰走了,
仿佛多待一刻都会脏了她的鞋。张大夫来得很快。他是我母亲家的大夫,看着我长大,
忠心耿耿。屏退左右后,我将房门死死闩上。“张叔。”我跪倒在地。张大夫大惊,
连忙扶我。“**,你这是做什么!快起来!”“张叔,求您救我。”我的声音里带着哀求。
我没有说季家的隐私,只说仲安死得蹊跷,而我腹中这个孩子,我不能要,
却又必须做出它“自然流掉”的样子。张大夫是聪明人,他看着我决绝的神情,没有多问。
他为我诊了脉,确认了我那不足两月的身孕。“**放心。”他从药箱里取出两个纸包,
一个大,一个小。“这包大的,是固本的药,你每日服用,能保你身体无虞。这包小的,
是霸道的红花草,只需一剂,便能造成血崩之相,神仙难辨。”我接过药包,重重叩首。
“阿瑜,谢张叔再生之恩。”从那天起,我便开始了我的表演。
陈氏每日都让厨房炖了“安胎药”送来,说是她亲自盯着的,十全大补。
我每次都当着下人的面,感激涕零地喝下。转身,便悉数吐在早已备好的花盆里,
再用清水漱口,换上张叔给我的固本的汤药。我的“孕吐”渐渐好了,
气色也一日日红润起来。我开始在府中走动,尤其爱去人多的地方。“母亲真是疼我,
这血燕和人参,日日不断,我这肚子都显怀了呢。”我手不自觉地抚上还很平坦的小腹,
对路过的管事媳妇说。“我娘家陪嫁的那些田产铺子,契约都在我这儿压着。我还想着,
等孩子生下来,就都记在他名下,也算是我为季家开枝散叶的一点心意。
”我对前来探望的族中女眷说,一脸不谙世事的幸福。这些话,
一字不漏地传到了季同和陈氏的耳朵里。我偷偷站在他们房外,听到他们压低了声音的交谈。
“那小**手里的嫁妆可不是一笔小数目,等孩子生下来,她一个妇道人家,
哪还用得着管这些。”“要不是你长兄不能生育,我也不会...”陈氏忽然感慨。“娘,
您别想这么多了。如今她对我言听计从,那些东西,早晚都是我们的。等她生了,
就说她产后失调,不宜操劳,名正言顺地把中馈和地契都接过来就是。
”是季同志在必得的笑声。“到时候,是让她病死,还是送去家庙,不都由我们说了算?
”3**在冰冷的墙壁上,听着里面母慈子孝的谋划。真好。鱼儿已经看到了饵,并且坚信,
那是最肥美的一餐。他们放松了警惕,露出了最贪婪的獠牙。而我,
只需要静静地等待一个最合适的时机,收网。季家的家族祭祀,是府中一年一度的头等大事。
这一日,所有族人都要到祠堂祭拜先祖。我穿着一身孝服,跪在仲安的牌位前。
我听着族长冗长的祭文,听着周围人虚伪的叹息。时机到了。在众人起身准备行礼的瞬间,
我身体一软,直直地朝着地面倒去。“大少奶奶!”身边的丫鬟发出一声惊呼。
祠堂里瞬间乱成一团。“快!快扶大少奶奶回房!”“是不是动了胎气了?”“真是罪过,
在列祖列宗面前...”我被几个下人七手八脚地扶着,一路“昏迷”着回了我的院子。
我被安置在床上,双目紧闭,眉头却痛苦地蹙着。“水...药...”我开始胡言乱语,
声音微弱,却足以让围在床边的人听清。
我没有照顾好你...”“为什么...为什么喝了药还是那么疼...”丫鬟们面面相觑,
不知所措。一个机灵的,赶紧跑去前院报信。没过多久,季同就疾步走了进来。“都出去!
”他喝退了满屋子的下人,亲自走到我床边。“阿瑜?阿瑜你怎么了?”他握住我的手,
我能感到他掌心的湿冷。他怕了。我继续“说胡话”,声音里充满了惊恐和自责。“药,
那碗药...是我端过去的,是我害了你...”“不是的!不是你!”季同急切地打断我,
他俯下身,凑到我耳边。“阿瑜,你清醒一点!兄长的死与你无关!你没有害他!
”我倏地睁开眼睛,一把抓住他的衣襟,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真的吗?真的不是我?
”“当然不是你!你怎么会害兄长呢?”季同为了安抚我这个“受惊过度”的孕妇,
几乎是口不择言。“那,那是谁?仲安他走的时候那么痛苦...”我死死地盯着他,
不放过他脸上任何一丝细微的变化。他被我看得有些狼狈,移开了视线。“阿瑜,你听我说。
兄长他...病得太重了,活着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他深吸一口气,
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换上了一副悲天悯人的腔调。“是我...是我帮他解脱的。
令兄长过敏窒息而亡的陈皮,是我加进汤药里面的。”我的心颤抖不已,随即是滔天的恨意。
他终于承认了。4“我实在不忍心看他再受苦,更不忍心看你跟着他一起受苦。
他那个破败的身子,根本给不了你幸福,你们是生不下孩子,为我季家留后的。阿瑜,
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你啊!我是为了你,为了我们季家。”他握住我的手,
放在他的心口。“你懂吗?我是在救你,也是在救他。他解脱了,而你,
可以得到真正的幸福。我们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一起,我们的孩子,
将来会是季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这番话,他说得深情款款,仿佛自己是牺牲一切的英雄。
将弑兄夺嫂的龌龊,包装成伟大的爱情和慈悲的解脱。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之人。
胃里翻涌的恶心感再也压不住,我倏地推开他,趴在床边干呕起来。
他以为我是被真相吓到了,连忙给我拍背顺气。“别怕,阿瑜,别怕。事情已经过去了,
以后有我。你只要安心养胎,把我们的孩子生下来,其他的一切,都交给我。
”我慢慢地直起身,用帕子擦了擦嘴。我看着他,脸上还挂着泪,
却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季同...你说的是真的?你...都是为了我?
”“当然!”他斩钉截铁。“我信你。”我轻声说,然后主动靠进他怀里,
将头埋在他的肩膀。“我以后...都听你的。”他满意地笑了。而我,在他看不见的地方,
对着房门外的人影,也笑了。季同,谢谢你。谢谢你这份亲口说下的,送你去地狱的供词。
几日后,我算准了日子,将张大夫给我的那包红花草,混在陈氏送来的“安胎药”里,
一饮而尽。腹部很快传来一阵剧烈的绞痛。我咬着牙,不让自己叫出声,
直到一股温热的液体从我身下涌出。鲜红的血,迅速浸透了我的亵裤,蔓延到素白的床单上,
像一朵开在雪地里的、妖异的食人花。“来人啊——!”我用尽全身力气,
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我的肚子...我的孩子...!”5丫鬟们撞门进来,
看到满床的血,吓得魂飞魄散。整个季府,瞬间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搅得天翻地覆。
季同和陈氏最先赶到。他们冲进房间,看到的不是我痛苦的脸,而是那片刺目的红。
季同的脸在一瞬间变得铁青。陈氏更是直接冲到床边,不是看我,而是死死盯着那片血迹,
她保养得宜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裂痕。“孩子...我的孙子!”她尖叫起来,
那声音不像悲伤,更像是输光了所有筹码的赌徒。他们唯一的遮羞布,
他们名正言顺侵吞我嫁妆的唯一借口,没了。愤怒,取代了所有伪装。“你这个丧门星!
克死了我儿子,现在又克死了我的孙子!”陈氏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
“我们季家是造了什么孽,娶了你这么个扫把星进门!”我躺在床上,
任由她的唾沫星子喷在我的脸上,心中一片快意。对,就是这样。再愤怒一点,再恶毒一点。
把你们最真实的面目,都暴露出来。事情的发展,比我预想的还要激烈。
陈氏在我的院子里闹了一通还不够,她直接召集了所有族中长老,将我从床上拖拽到了祠堂。
我“虚弱”地被两个粗壮的婆子架着,跪在冰冷的地面上。仲安的牌位就在我面前,
冷冷地看着这一切。祠堂里,坐满了季家的长辈。他们个个面色凝重,看向我的目光,
充满了审视和不屑。“各位叔伯长辈,今天请大家来,是为我们季家做主!”陈氏站在堂中,
声泪俱下。“这个女人,进门不到一年,克死了我的仲安。如今好不容易怀上我季家的骨血,
又被她自己作没了!她就是个灾星,要毁了我季家满门啊!”一位胡子花白的长老捻着胡须,
开了口。“弟妹,话不能这么说。大少奶奶失了孩子,心里也难过。”“难过?
”陈氏冷笑一声,“我看她是巴不得!我们季家待她不薄,她却如此不忠不孝,不贞不洁!
这样的女人,我们季家断不能留!”季同站了出来,一脸“悲痛”地唱着红脸。“母亲,
您息怒。嫂嫂她...她也不是故意的。只是兄长新丧,她又失了孩子,身心俱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