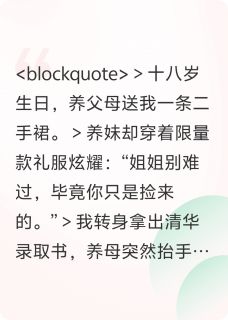
>十八岁生日,养父母送我一条二手裙。>养妹却穿着**款礼服炫耀:“姐姐别难过,
毕竟你只是捡来的。”>我转身拿出清华录取书,养母突然抬手撕碎:“野种也配上清华?
”>暴雨夜我被打到流产,血水中攥紧通知书残片。>七年后我成金牌名师,
电视直播里养妹哭求我原谅。>“林老师,当年顶替您上清华的是我!
”>养母冲进演播厅大骂:“血缘算什么?柔柔才是亲女儿!”>我笑着放出录音:“妈,
当年你偷走的人生……”>“该还了。”窗外,夏末最后一声蝉鸣有气无力地拖着长调。
餐桌上铺着块洗得发白却浆挺的旧桌布,中央摆着一个小小的、孤零零的蛋糕。
劣质奶油的甜腻香气混在空气里,沉甸甸地压着人的肺。今天,我十八岁了。
养母李金花把一个扎着廉价彩带的纸盒推到我面前,脸上堆着一种近乎刻意的笑,
褶子挤在眼角:“晚晚,生日好!喏,妈给你买的,新裙子!”那笑容像一张没贴牢的面具,
边缘微微翘起,透出底下敷衍的底色。纸盒里躺着一条颜色灰扑扑的连衣裙,
领口处磨损得泛白,袖口甚至脱了线,散发着一股樟脑丸和陈年衣柜的混合气味。
一件从里到外都写着“二手”二字的礼物。心口像是被粗糙的砂纸狠狠擦过,闷闷地疼,
但我还是努力弯起嘴角,舌尖尝到一丝铁锈味:“谢谢妈。”“哎呀,姐姐,生日快乐呀!
”一个娇脆的声音像玻璃珠子砸在地板上。养妹苏柔像只翩跹的蝴蝶,
踩着轻盈的步子从旋转楼梯上飘下来。她身上那件缀满细碎水钻的淡紫色小礼服,
在顶灯下流光溢彩,刺得人眼睛发痛。她走到我身边,刻意地转了个圈,
裙摆漾开华丽的光晕,目光扫过我盒子里的旧裙子,嘴角弯起一个天真又刻毒的弧度,
“别难过嘛姐姐,毕竟……你跟我们不一样,你是爸妈‘捡’来的呀。”那个“捡”字,
被她咬得又轻又重,像一根冰冷的针。捡来的。这三个字像淬了毒的冰锥,
瞬间捅穿了这些年我小心翼翼维持的、摇摇欲坠的温情的壳。
我猛地攥紧了桌布下微微发抖的拳头,指甲深深陷进掌心。所有的委屈和愤怒在胸腔里冲撞,
几乎要破膛而出。不行,不能在这里,不能是现在。我深吸一口气,指尖冰得吓人,
摸索着伸进书包最里层,触碰到那份硬挺的、带着油墨香的纸张边缘。
这几乎是我此刻唯一的浮木。我把它抽了出来,鲜红的“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几个字,
在有些昏暗的灯光下,像一团小小的、灼热的火焰,试图驱散周遭的冰冷和恶意。
我把它轻轻放在那件旧裙子旁边,声音干涩却清晰:“爸,妈,我考上了。清华。
”没有看任何人,视线固执地落在通知书上那庄严的校徽上。死寂。
空气仿佛凝固成了粘稠的胶质,让人窒息。“什么?!”李金花尖利的声音骤然撕裂了沉默,
像指甲刮过玻璃。她脸上的假笑瞬间崩塌,只剩下**裸的震惊和一种近乎狰狞的扭曲。
她猛地一步跨上前,枯瘦的手指像鹰爪般抓住了那张薄薄的纸,速度快得惊人。“刺啦——!
”纸张被粗暴撕裂的声音,尖锐得如同惊雷,炸响在死寂的客厅里。一下,又一下!
鲜红的校徽被扯开,我的名字“林晚”被残忍地撕成两半。碎片像濒死的蝴蝶,簌簌地飘落,
散在油腻的桌布上,落在灰扑扑的旧裙子上。“野种!你也配?!
”李金花的声音因极度愤怒而嘶哑变形,唾沫星子喷溅到我脸上,带着令人作呕的腥气。
她扬起手,厚实的巴掌裹挟着风声,狠狠掴向我的脸!预想中的剧痛没有落在脸上。
身体深处,一股无法形容的、撕裂般的剧痛猛地炸开!
像有无数把烧红的刀子在小腹里疯狂搅动、切割。眼前骤然一黑,天旋地转。
我甚至没来得及发出一声痛呼,整个人就像断线的木偶,从椅子上软倒下去,
重重砸在冰冷坚硬的地砖上。“砰!”骨头撞击地面的闷响。紧接着,
一股粘稠、温热的液体,失控地从双腿间汹涌而出,迅速浸透了单薄的裤料,
在地砖上洇开一片刺目惊心的、不断扩大的暗红。
浓烈的血腥味瞬间冲散了蛋糕的甜腻和空气里的腐朽气息,浓得化不开。“血!她流血了!
”苏柔刺耳的尖叫划破空气,带着一种夸张的惊恐,更多的却是看戏般的兴奋。“晚晚!
”养父苏大强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住了,迟钝地喊了一声,下意识想上前,
却被李金花像护崽的母兽般狠狠推开,踉跄着撞到桌角。
李金花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
但立刻被更深的怨毒和一种扭曲的“果然如此”的鄙夷取代。她指着地上蜷缩抽搐的我,
声音尖刻得能刮下人的皮肉:“贱骨头!小小年纪就不学好!活该!报应!给我滚出去!
别脏了我的地!”她歇斯底里地吼着,仿佛地上流的不是血,而是什么污秽至极的东西。
外面,酝酿了一整天的暴雨终于倾盆而下。豆大的雨点疯狂地砸在窗户上,噼啪作响,
像是无数冰冷的石子投掷下来。门被李金花粗暴地拉开,湿冷的狂风裹挟着密集的雨点,
瞬间灌了进来,抽打在身上。她像拖拽一袋垃圾,抓住我的胳膊,用尽全身力气把我往外拖。
粗糙的手指几乎要嵌进我的皮肉里。腹部的剧痛排山倒海,
每一次被拖动都带来新一轮的撕裂感,视线模糊一片,雨水和泪水糊了满脸。
冰冷的雨水无情地浇在头上、身上,迅速带走本就所剩无几的体温。“滚!丧门星!
死在外面干净!”李金花最后恶毒的诅咒被淹没在震耳欲聋的雷声里。她用尽力气,
狠狠一推!我像一片枯叶,被抛进了门外翻腾的、冰冷的黑暗水世界。身体失去支撑,
重重摔倒在院门外的水泥地上,肮脏的雨水混合着泥浆瞬间包裹了全身。
小腹处的剧痛和失血带来的冰冷虚弱让我几乎无法呼吸,每一次喘息都牵扯着撕裂般的疼痛。
冰冷的泥水灌进口鼻,窒息感汹涌而来。世界在旋转,在崩塌。
就在意识即将彻底沉入黑暗的深渊时,求生的本能让我用尽最后一丝残存的力气,
颤抖着、痉挛着,在身下冰冷粘稠的泥水中摸索。指尖,
触碰到一片被雨水泡软的、熟悉的纸片边缘。是我的录取通知书。那上面,
被撕碎的“林晚”两个字,被泥水和……我自己的鲜血,晕染得一片模糊,
却又顽强地粘连着。清华……我的清华……冰冷的雨水疯狂地砸在脸上,像无数根钢针。
我死死攥紧了那片湿透的、沾满血泥的纸片,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仿佛要将它嵌入自己的骨头里。一股滚烫的、带着血腥味的液体从喉咙深处涌上来,
又被我死死咽了回去,灼烧着五脏六腑。血与泪在脸上混合,又被暴雨冲刷。
身体在泥水里冷得像一块冰,腹部的剧痛依旧在疯狂叫嚣,
每一次心跳都沉重得像是最后的挣扎。意识在极致的寒冷和灼痛中漂浮,
仿佛下一秒就要彻底消散。可那片沾着血泥的纸片,硌在手心,像一块烙铁,
烫穿了所有的麻木和绝望。痛吗?痛彻骨髓。恨吗?恨意滔天。可就在这濒死的边缘,
在这天地间最狂暴的雨幕里,在那片被撕碎的名字上,一种更冰冷、更坚硬的东西,
从五脏六腑深处,从每一滴流淌的血里,一点点凝聚起来。它压过了剧痛,
盖过了恨意的狂潮,像深渊底部最坚硬的磐石,沉甸甸地沉淀下来。不能死。至少,
不能死在这里。不能死在这滩泥水里,死在他们的冷漠和诅咒之下。那撕碎的纸片,
是过去的林晚被埋葬的祭品。也是……新生的号角。牙关死死咬紧,
尝到了唇齿间浓重的血腥味。我用尽全身残存的力气,攥着那片纸,
像攥着一把淬了血与恨的匕首,支撑着几乎散架的身体,一寸寸,从冰冷粘稠的泥水中,
抬起头。视线穿过迷蒙的雨幕,望向苏家那扇透出昏黄暖光、此刻却如同地狱入口的窗户。
里面人影晃动,隐约传来李金花尖利的咒骂和苏柔娇滴滴的安慰声。那点灯光,
曾是我小心翼翼维系了十八年的、虚幻的暖巢。现在,它是地狱的业火,
烧尽了最后一丝可笑的眷恋。喉咙里发出一声模糊的、野兽般的嗬嗬声,不是哭泣,
是筋骨被强行碾碎又重铸的哀鸣。血债,必要血偿。欠我的,连本带利,
一分不少……都得还!身体里的血还在流,混着雨水,带走温度。
但心口那团被恨意和屈辱点燃的火,却越烧越旺,几乎要将这冰冷的雨水煮沸。我挣扎着,
试图挪动身体,每一次动作都牵扯着腹内翻江倒海的剧痛,冷汗混着雨水滚落。
就在意识快要被黑暗彻底吞噬的边缘,一道刺目的车灯划破雨幕,像一把利剑劈开黑暗,
直直地刺了过来。轮胎碾过积水的刺耳刹车声,盖过了暴雨的喧嚣。车门“砰”地被推开,
一个高大的身影顶着狂风暴雨冲了下来。脚步声沉重而急促,踩踏着泥水,飞快地逼近。
“喂!你怎么样?撑住!”一个陌生的、带着急切和震惊的男声在头顶响起,
穿透了雨声和耳中的嗡鸣。他蹲了下来,试图查看我的情况。模糊的视线里,
只能看到他深色的裤脚被泥水溅湿,一只温热的大手带着犹豫,轻轻碰了碰我冰冷的肩膀。
“天啊!流这么多血!别怕,我马上送你去医院!”他的声音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坚决,
带着一种让人想要依赖的力量。是幻觉吗?还是……真的?
求生的本能让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抬起那只紧攥着碎纸片的手,沾满泥污和鲜血的手指,
徒劳地伸向他,喉咙里发出破碎的气音:“救…救…通知书…清华……”后面的话,
被更汹涌的黑暗彻底吞没。身体一软,最后一丝力气耗尽,彻底坠入了无边的冰冷深渊。
2七年后。深城卫视一号演播厅。聚光灯炽热得如同正午的太阳,精准地打在我的脸上。
台下,无数双眼睛聚焦于此,带着好奇、探究、崇拜。空气里弥漫着直播特有的紧绷电流感。
我坐在宽大的嘉宾椅上,一身剪裁利落的米白色西装套裙,头发一丝不苟地挽在脑后,
露出光洁的额头。七年时光和无数个日夜的淬炼,早已将当年泥水里的狼狈洗刷干净,
沉淀下的只有眉宇间的从容和眼底那抹洗练过的、不易察觉的锐利。主持人笑容可掬,
声音通过麦克风清晰地传遍全场:“……所以,林老师,您认为在现行教育体制下,
寒门学子真正的‘破局点’在哪里?您作为‘金牌名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