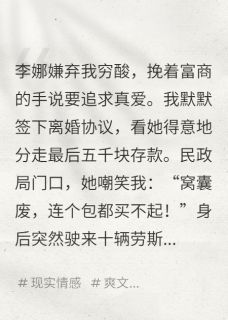
李娜嫌弃我穷酸,挽着富商的手说要追求真爱。我默默签下离婚协议,
看她得意地分走最后五千块存款。民政局门口,她嘲笑我:“窝囊废,连个包都买不起!
”身后突然驶来十辆劳斯莱斯,律师恭敬递上文件:“张总,瑞士银行128亿已到账。
”我笑着撕碎协议:“刚才是逗你玩的。”“忘了告诉你,
你情夫的公司...其实是我家产业。”闪光灯下,我宣布将半数财产捐给贫困儿童基金会。
当晚热搜炸了:拜金女遭天谴、隐形富豪教科书级打脸。李娜跪在暴雨中求复合时,
我的私人飞机正掠过城市上空。“脏了的东西,我张强从来不要。
”雨点砸在油腻腻的厨房窗户上,噼啪作响,像无数只冰冷的小手在胡乱拍打。
出租屋狭窄的厨房里,弥漫着一股廉价方便面调料包混合着隔夜油烟的沉闷气味。我,张强,
正对着那扇糊满油污的玻璃,慢吞吞地刷洗着昨晚留下的碗碟。水龙头有点漏,
细细的水流落在不锈钢水槽里,发出单调而持续的滴答声,和窗外的雨声混在一起,
敲得人心烦意乱。客厅里传来一阵刻意压低的、带着娇嗔的笑声,是李娜。那笑声粘腻腻的,
像掺了蜂蜜的毒药,钻进我的耳朵里。我不用回头,
也能想象出她此刻的样子——一定是斜倚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旧沙发上,手机紧紧贴在耳边,
脸上挂着那种我很久没见过的、近乎谄媚的笑容。这笑容,曾经只属于我。“哎呀,王总,
您真会开玩笑……”她的声音又飘了过来,甜得发齁,“……那家新开的法餐厅?
听说位置好难订的……嗯?您有办法?那当然好呀……”我的手指在油腻的碗沿上顿了一下,
冰凉的油腻感顺着指腹蔓延上来。胃里那点刚吃下去的面条,此刻像一团冰冷的铅块,
沉沉地坠着。我继续刷碗的动作,只是更用力了些,瓷碗碰撞着水槽边缘,
发出轻微的磕碰声。这声音在寂静的出租屋里显得格外刺耳,但客厅里的笑声没有丝毫停顿,
反而更加轻快了些。水流冲刷着碗碟,带走油污,却带不走心头的阴霾。
这间四十平米不到的出租屋,是我和李娜在这个城市挣扎了五年换来的“家”。
墙皮有些地方已经剥落,露出里面灰暗的水泥底色;家具是房东留下的,
陈旧得掉漆;唯一值点钱的,大概是那台嗡嗡作响的老式冰箱。李娜的抱怨,
从最初的偶尔流露,到如今几乎成了每天晚饭桌上的固定节目。她抱怨这屋子太小太旧,
抱怨我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衫,抱怨我连个像样的包都舍不得给她买,
抱怨我“窝囊”、“没本事”、“一辈子也就这样了”。起初,我还会解释,
会笨拙地承诺以后会好起来。后来,我选择了沉默。沉默地听着,
沉默地承受着那些刻薄的言语,像一块浸透了水的海绵,吸饱了却无力挤出。
我理解她对更好生活的渴望,谁不想呢?但我的沉默里,并非全是无奈,
还有一丝连我自己都难以察觉的冰冷。我看着她眼中日益增长的、对金钱**裸的渴望,
看着她对我那份曾经纯粹的感情一点点被物欲侵蚀、消磨殆尽。她不知道,
在她抱怨着“窝囊废”的时候,在我每天挤着地铁去那个不起眼的公司打卡时,
在我面对她那些名牌包包、高档餐厅的暗示只能沉默以对时,我的口袋里,
揣着一张足以买下这座城市最昂贵地段一栋楼的银行卡。那是爷爷临终前,
用枯槁的手紧紧塞给我的,一个来自遥远瑞士银行的信物,
一个关于庞大到令人窒息的家族遗产的秘密。爷爷浑浊的眼睛里,
“强子……藏好它……不到万不得已……别露出来……人心……经不起试啊……”我藏住了。
藏得严严实实,像一个真正的、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底层上班族。我需要知道,
当剥去金钱的滤镜,当我一无所有时,李娜,这个曾经在校园里说“喜欢我踏实”的女孩,
是否还愿意与我同行。这像一场残酷的赌局,赌注是我和她之间仅存的那点情分。只是,
这场赌局,我似乎已经看到了结局。客厅里的笑声终于停了。
高跟鞋踩在廉价复合地板上的声音,由远及近,带着一种轻快的、迫不及待的节奏,
停在厨房门口。我关上水龙头,甩了甩手上的水珠,转过身。李娜斜倚在门框上,
双臂环抱在胸前。她今天显然精心打扮过,脸上是新做的韩式半永久眉,妆容精致,
身上穿着一件明显超出我们消费能力的崭新连衣裙,剪裁得体,
面料在昏暗的厨房灯光下也泛着不寻常的光泽。她嘴角微微上扬,
勾勒出一个弧度完美的、带着胜利者姿态的笑容,眼神却像淬了冰的刀子,直直地刺向我,
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和一种……终于解脱了的轻松。“张强,”她开口了,声音清脆,
带着一种刻意的、居高临下的腔调,“我们谈谈。”我看着她,没说话。
只是用挂在墙上的旧毛巾,慢慢地擦着手上的水渍。毛巾很旧,有些地方已经磨得发硬了。
我的沉默似乎给了她更大的勇气,或者说,让她更急于摆脱这令人窒息的“困境”。
她向前走了一步,高跟鞋在地板上发出清晰的“笃”声。“我受够了。”她下巴微抬,
语气斩钉截铁,“受够了这个破地方,受够了你身上这股子穷酸味儿,
受够了这种一眼望得到头的日子!”她顿了顿,目光扫过我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
鼻翼厌恶地翕动了一下,仿佛真的闻到了什么难以忍受的气味,“跟你在一起,
我看不到任何希望。每天精打细算,连买件像样的衣服都要犹豫半天,这种日子,
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厨房里安静得可怕,只有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
还有老旧冰箱压缩机发出的沉闷嗡鸣。空气里弥漫的廉价方便面调料味,此刻显得格外刺鼻。
我依旧沉默着,只是擦手的动作停了下来。毛巾粗糙的质感摩擦着掌心。“所以,
”她深吸一口气,像在宣布一个重大决定,声音拔高了些,带着一种奇异的兴奋,
“我们离婚吧。”这三个字,像三颗冰冷的钉子,狠狠楔进空气里。她终于说出来了。
没有想象中的震惊或痛苦,反而是一种尘埃落定的麻木感,
混杂着一丝冰冷的、早已预知的嘲弄。我看着她,看着她眼中闪烁的、名为“解脱”的光芒,
看着她精心描绘的唇线,
看着她身上那件价格不菲的裙子——它无声地宣告着另一个男人的存在。“好。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响起,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甚至有些干涩。
仿佛只是答应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晚上吃面条”或者“把垃圾带下去”。
我的干脆利落显然出乎她的意料。
她脸上那丝胜利者的得意和准备迎接一场“战斗”的紧绷感,瞬间凝固了一下,
随即被一丝不易察觉的恼怒取代。她大概期待看到我的失态,我的哀求,我的痛苦,
好让她在离开时,能更心安理得地享受那种“甩掉包袱”的**。
“你……”她似乎想说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是那轻蔑的眼神更浓了,
“算你还有点自知之明。窝囊废!”她不再看我,仿佛多看一眼都是对她的玷污,
转身踩着高跟鞋,哒哒哒地走回客厅。很快,传来翻箱倒柜的声音,还有打印机启动的嗡鸣。
几分钟后,她拿着一份打印好的文件走了回来,啪的一声,拍在厨房那张油腻的小餐桌上。
劣质的打印纸边缘有些卷曲。“协议我打好了,”她指关节敲了敲桌面,
语气带着施舍般的倨傲,“看清楚了,房子是租的,没你份儿。家里那点存款,
总共就五千三百块,零头我抹了,给你五千。我够意思了吧?拿着这点钱,够你撑一阵子了,
赶紧找个正经地方住,别赖在这儿碍眼。”她刻意强调了“五千”这个数字,仿佛在提醒我,
这是她对我这个“窝囊废”最后的、天大的恩赐。我的目光落在协议上。条款清晰而冷酷。
没有共同财产分割,只有这五千块的“遣散费”。
她甚至没有提任何共同债务——虽然我们几乎没有。这更像是一种姿态,
一种彻底划清界限、宣告我毫无价值的姿态。我拿起笔。那是一支普通的黑色签字笔,
笔杆有些磨损。我拔开笔帽,目光扫过签名处。没有犹豫,没有停顿,笔尖落在纸上,
发出沙沙的轻响。张强。两个字,写得平稳而清晰。签完字,我放下笔,
将协议轻轻推到她面前。整个过程,安静得像一出哑剧。李娜拿起协议,
飞快地扫了一眼我的签名,嘴角勾起一个极其满意的弧度,像是终于卸下了千斤重担,
又像是完成了一桩精明的买卖。她迅速地在乙方位置签下自己的名字,字迹潦草而张扬,
带着一种迫不及待的解脱感。她甚至没再看我一眼,仿佛我已经从这个空间里消失了。
“明天上午十点,民政局门口。”她甩下这句话,像女王下达最后通牒,
然后拿起那份签好的协议,踩着高跟鞋,头也不回地走向卧室。门在她身后关上,
发出“砰”的一声闷响,隔绝了两个世界。厨房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窗外,雨下得更大了,
密集的雨点砸在玻璃上,发出哗哗的声响。那碗没吃完的方便面,汤水早已冷透,
浮着一层凝结的油花。我走到窗边,看着外面被雨水冲刷得模糊不清的城市夜景。
霓虹灯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拉出长长的、扭曲的光影,像一张张无声嘲笑的鬼脸。口袋里,
那张冰冷的、印着复杂花纹的金属卡片,隔着薄薄的布料,传递着一种沉甸甸的存在感。
爷爷临终前那枯槁的手,浑浊而忧虑的眼神,那句“人心……经不起试啊……”的叹息,
此刻异常清晰地回响在耳边。我掏出手机,屏幕的光在昏暗的厨房里显得有些刺眼。
手指在通讯录里滑动,精准地找到了那个名字——陈默。一个我几乎从未主动联系过的人。
拨号键按下,短暂的等待音后,电话被接通了。“陈律师。”我的声音低沉而平稳,
听不出任何情绪,像在陈述一件与己无关的工作,“是我,张强。明天上午十点,
我需要你帮我处理一件事……对,在市民政局门口。带上我存在你那里的所有文件,全部。
另外,帮我准备一份文件,
关于向‘萤火虫’贫困儿童医疗救助基金会捐赠我名下百分之五十流动资产的意向声明,
要具有法律效力,明天一起带过来。”我顿了顿,补充道,“还有,通知一下瑞士银行那边,
我需要一份即时资产证明,明天上午十点前,发送到我的加密邮箱。
再联系一下我们在本市的几家分公司,让他们明天上午十点左右,
各派一辆车到民政局附近待命……嗯,要最好的车,低调点,但得让人一眼就看出分量。
”电话那头,陈默的声音清晰而专业,没有丝毫惊讶,
仿佛只是在处理一件日常公务:“明白了,张先生。资产证明、捐赠声明、车辆安排,
明天上午十点前,全部到位。需要我提前和民政局方面沟通吗?”“不用。”我打断他,
目光依旧落在窗外模糊的雨幕上,“按正常流程走。你只需要在‘合适’的时候出现。
”“好的,张先生。”陈默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了然。挂断电话,屏幕暗了下去。
厨房里重新陷入昏暗,只有窗外路灯透进来的微弱光线,勾勒出家具模糊的轮廓。
我收起手机,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那张冰冷的金属卡片。爷爷的警告犹在耳畔,
但此刻,那警告更像是一句早已注定的谶言。人心,果然经不起试。
我拿起桌上那碗冷透的方便面,走到水槽边,毫不犹豫地将它倒掉。
油腻的汤水和凝结的面条滑入下水道,发出咕噜一声轻响。明天,一切都会不一样了。
第二天,是个难得的大晴天。阳光炽烈,一扫昨日的阴霾,将城市街道照得亮堂堂的,
仿佛昨夜那场冷雨从未存在过。空气里弥漫着初夏特有的、带着点燥热的气息。
我站在民政局门口那棵枝繁叶茂的老槐树下,浓密的树荫勉强遮挡着刺目的阳光。
身上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熨烫得还算平整,
但在这光鲜亮丽、人来人往的民政局门口,依旧显得格格不入,像个误入高档场所的落魄者。
我甚至能感觉到周围投来的、或好奇或怜悯的目光。李娜来得很准时。十点差五分,
一辆崭新的黑色奔驰S级轿车稳稳地停在了民政局门口的路边。车窗降下,驾驶座上的男人,
正是照片上那个油头粉面、手腕上戴着块金灿灿劳力士的“王总”——王振海。他探出头,
脸上堆着殷勤的笑容,对正准备下车的李娜说了句什么。李娜推门下车。
她今天打扮得更加光鲜亮丽,一身香奈儿的经典款套装,拎着最新款的LV手袋,
脚上的高跟鞋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脸上妆容精致,神采飞扬,
一扫昨天在出租屋里的刻薄怨气,整个人容光焕发,像一只终于挣脱了牢笼的金丝雀。
她关上车门,对着车窗里的王振海甜甜一笑,挥了挥手。那笑容明媚得晃眼。
奔驰车缓缓开走。李娜转过身,脸上的笑容在看见树荫下的我时,瞬间收敛,
换上了一副毫不掩饰的鄙夷和嫌弃。她踩着高跟鞋,哒哒哒地向我走来,
每一步都带着胜利者的姿态,仿佛在走红毯。“哟,还挺准时。”她在我面前站定,
双臂抱胸,上下打量着我,眼神像在看一堆碍眼的垃圾,嘴角挂着讥讽的弧度,
“就穿这身儿来离婚?也对,反正你也就这点家当了。啧,看着就晦气。
”阳光透过树叶缝隙,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她身上昂贵的香水味混合着新皮具的味道,
强势地侵入我的感官,与这市井的气息格格不入。我没有回应她的嘲讽,
只是平静地指了指民政局的大门:“进去吧,该办手续了。”我的平静似乎激怒了她,
或者让她觉得一拳打在了棉花上。她冷哼一声,下巴抬得更高:“急什么?
耽误不了你几分钟!张强,我真替你感到悲哀。”她声音拔高,带着一种刻毒的怜悯,
像是要在离开前,再狠狠地踩上几脚,“你看看你,活了**十年,混成什么德性?
老婆跟人跑了,连个屁都不敢放!离个婚,还得靠我施舍你那五千块钱!窝囊废!废物!
你这种人,活该一辈子打光棍,活该穷死!”她的声音不小,
引得周围几个等待办理手续的人侧目看来。那些目光里有好奇,有看热闹,也有隐隐的同情。
李娜似乎很享受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更加变本加厉,她扬了扬手中的LV手袋,
那闪亮的金属LOGO在阳光下格外刺眼:“看见没?王总昨天刚送的!就这一个包,
顶你一年工资!你这种人,奋斗一辈子,也买不起我一个包带子!”她越说越激动,
仿佛要将这些年积压的不满和怨毒,在离开前全部倾泻出来,“跟着你,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窝囊废!废物点心!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就在这时,
一阵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引擎轰鸣声由远及近,以一种不容忽视的姿态,
粗暴地打断了李娜尖刻的咆哮。那声音浑厚、稳定,带着一种金属的质感,
瞬间盖过了民政局门口所有的嘈杂人声和车流声。所有人的目光,包括李娜,
都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过去。只见一辆通体漆黑、线条流畅优雅的劳斯莱斯幻影,
如同移动的黑色堡垒,缓缓地、极其平稳地停在了民政局正门口的路边。
光可鉴人的车身在阳光下反射出近乎完美的镜面效果,
车头那标志性的“欢庆女神”立标熠熠生辉,无声地宣示着它的尊贵与不凡。
这只是一个开始。紧接着,第二辆、第三辆……清一色的黑色劳斯莱斯幻影,
如同训练有素的仪仗队,一辆接一辆,无声而精准地停靠在第一辆车后面,
排成了一条笔直而威严的长龙。整整十辆!它们静静地停在那里,
庞大的车身在阳光下沉默地散发着无形的压力,将周围的一切都衬托得黯淡无光。
空气仿佛凝固了,民政局门口瞬间变得鸦雀无声,
所有人的目光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堪称震撼的豪车阵仗牢牢钉住,
脸上写满了震惊、茫然和难以置信。这阵势,别说办离婚的,就是来领结婚证的,
也从未见过如此夸张的场面!李娜的嘴巴还保持着刚才咒骂时的口型,眼睛却瞪得溜圆,
脸上那刻薄的讥讽和胜利者的得意瞬间冻结,被一种巨大的、无法理解的震惊所取代。
她下意识地后退了一小步,高跟鞋踩在地砖上发出轻微的一声“咔”,
像是被眼前这无声的威势吓到了。在死一般的寂静中,
为首那辆劳斯莱斯的后车门被一只戴着白手套的手轻轻推开。
一个穿着剪裁完美、一丝不苟的深灰色高定西装的男人,从容地下了车。他约莫四十岁上下,
面容沉静,眼神锐利而内敛,手里提着一个看起来极为考究的黑色真皮公文包。
他的步伐沉稳有力,带着一种久居上位者的从容气度,径直朝着民政局门口——确切地说,
是朝着树荫下,我的方向走来。民政局门口那些原本只是看热闹的目光,
此刻齐刷刷地聚焦在我身上。那些目光里充满了惊疑、探究和难以置信。
刚才还被李娜指着鼻子骂“窝囊废”、“穷酸”的男人,此刻竟成了这震撼车队的目标?
西装男人走到我面前,在距离我一步远的地方停下。他微微躬身,动作标准而恭敬,
却又不显得卑微,声音清晰而沉稳地响起,不高不低,
恰好能让周围竖起耳朵的人听得清清楚楚:“张总,抱歉,路上有点堵,让您久等了。
”张总?!这两个字,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瞬间在人群中炸开了无形的涟漪。
窃窃私语声再也压抑不住,嗡嗡地响了起来。刚才还对我投以同情或鄙夷目光的人们,
此刻脸上的表情精彩纷呈,震惊、错愕、恍然大悟,甚至还有一丝丝后怕。
李娜更是如遭雷击!她脸上的血色“唰”一下褪得干干净净,惨白如纸。
那双描画精致的眼睛瞪得几乎要裂开,死死地盯着那个西装男人,又猛地转向我,
眼神里充满了极致的惊骇、茫然和一种被彻底愚弄的、无法置信的荒谬感。她张着嘴,
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抽气声,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身体微微颤抖着,
仿佛随时会瘫软下去。她精心描画的唇线,此刻因为震惊而扭曲,显得异常可笑。西装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