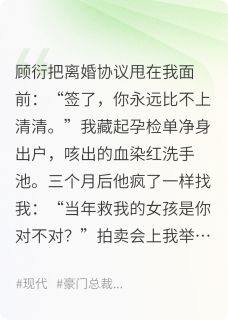
顾衍把离婚协议甩在我面前:“签了,你永远比不上清清。”我藏起孕检单净身出户,
咳出的血染红洗手池。三个月后他疯了一样找我:“当年救我的女孩是你对不对?
”拍卖会上我举牌压他十倍报价,无名指钻戒刺得他眼眶通红。“顾总认错人了。
”我晃着孕检单轻笑,“现在我和孩子,你高攀不起。
”————1、冰冷的纸张擦过我的脸颊,轻飘飘落在深色的大理石茶几上,
发出一点几不可闻的声响。空气里弥漫着昂贵香薰刻意营造的暖意,此刻却像凝固的冰,
沉沉压在我的胸口。“签了。”顾衍的声音从头顶砸下来,没有一丝波澜,
淬着冬夜寒潭的冷。他高大的身影笼罩着我,带来一片无法驱散的阴影,
像一座我永远无法翻越的山。我垂着眼,视线落在“离婚协议书”那几个加粗的黑体字上。
每一个笔画都像淬了毒的针,密密麻麻扎进眼底。心脏的位置,
那处早已被他反复揉搓碾磨得麻木的地方,还是传来一阵尖锐的、撕裂般的抽痛,
瞬间蔓延至四肢百骸,指尖都控制不住地微微发麻。喉头涌上一股熟悉的腥甜锈味,
我用力咽了下去,强迫自己抬起头。顾衍就站在那里。
剪裁完美的深灰色西装勾勒出他宽肩窄腰的挺拔轮廓,
水晶吊灯冰冷的光线落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
那双曾让我无数次沉溺其中、以为藏着星辰大海的深邃眼眸,
此刻只剩下冰封的漠然和一丝毫不掩饰的厌倦。他看我的眼神,
和看一件碍眼的旧家具没有任何区别。时间,真是最无情的刻刀。“为什么?
”我的声音干涩得厉害,像是砂纸在粗粝的木头上摩擦,每一个字都耗尽了力气。
其实答案早已心知肚明,苏清清那张清纯无辜的脸庞几乎夜夜出现在我的噩梦里,
可我依旧固执地问出口,像是要亲手把最后那点卑微的念想彻底掐灭。
顾衍的唇角极其轻微地向上扯了一下,那弧度冷硬得没有任何温度,只有浓浓的讥诮。
他俯下身,动作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感,修长的手指伸向我的左手。冰凉的触感传来。
那枚象征着我们三年婚姻的硕大钻戒,被他以一种极其粗暴的方式从我无名指上撸了下来,
戒指边缘刮擦过指骨,带起一阵细微的刺痛。紧接着,“叮”的一声脆响,
那枚曾经承载着我所有愚蠢幻想的冰冷石头,被他随意地、像丢弃垃圾一样,
扔在了那份离婚协议旁边,在光滑的桌面上弹跳了一下,滚了两圈,不动了。光芒刺眼。
“为什么?”他重复着我的问题,声音低沉,却字字如刀,精准地剜向心脏最软的地方,
“林晚,这个问题,从三年前你处心积虑爬上我床的那天起,就该问你自己了。”他直起身,
目光越过我,投向虚无的远方,仿佛那里才有值得他温柔以待的人,“你永远比不上清清。
她干净,纯粹,不像你,心机深沉,令人作呕。”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冰锥。“干净?
纯粹?”我几乎要笑出声,胸腔里那股翻腾的血气再也压不住,猛地冲了上来。
我死死咬住下唇内侧,尝到了更浓的铁锈味,硬生生将那股腥甜咽了回去,
连同所有的质问、委屈和不甘一起,狠狠压回五脏六腑深处。
三年前那场意外……我至今记得他滚烫的体温,记得他混乱中一遍遍喊着“别走”,
记得他醒来后看到我时,眼中一闪而过的错愕和随即升起的冰冷审视。原来,在他心里,
那场意外,是我精心策划的“处心积虑”。而那个真正“干净纯粹”的苏清清,
不过是后来机缘巧合,凭借着一枚相似的廉价银链子,
轻易就占据了他心中那抹白月光的位置。多么讽刺。我低下头,不再看他的眼睛。
目光落在茶几上那枚冰冷的钻戒上,它折射的光芒,像无数根针,扎得我眼睛生疼。
我伸出手,指尖控制不住地颤抖,拿起旁边那支沉甸甸的金笔。
冰凉的金属触感刺得我一激灵。笔尖悬在“乙方”签名处,停顿了足有十几秒。
空气凝滞得令人窒息。我能感觉到顾衍的目光依旧钉在我身上,带着审视和不耐烦。
心口那片被反复凌迟的地方,痛到了极致,反而生出一种诡异的麻木。算了,林晚。
我在心底对自己说,这个男人,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强求来的,终究是镜花水月。
放手吧,放过他,也放过自己。笔尖落下,划过昂贵的纸张。
沙沙的声音在死寂的客厅里异常清晰。每一笔,都像是在亲手斩断自己过去三年的痴心妄想,
每一划,都带着淋漓的血肉。我签得很快,字迹却歪歪扭扭,像垂死挣扎的爬虫。
最后一笔落下,我仿佛被抽空了所有力气。“如你所愿。”我把笔轻轻放回原位,
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涟漪,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我站起身,没有再看那份协议,
也没有再看那枚戒指一眼,径直走向楼梯。身后,顾衍没有任何回应。没有一丝挽留的迹象,
甚至连一句虚伪的客套都吝于给予。他大概早就迫不及待,等着这一刻,
好去迎接他心中真正的白月光了。也好。这样,断得干干净净。
回到那个只属于我、却从未真正被顾衍踏足过的客卧,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空旷的寂寥。
我背靠着冰冷的门板滑坐在地板上,身体里的力气被彻底抽干。小腹深处,
隐隐传来一丝细微的、几乎难以察觉的牵扯感,提醒着我那个刚刚在身体里扎根的秘密。
颤抖着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片——孕检单。
B超图像上那个小小的孕囊,模糊得像一个不真切的梦。指尖拂过“早孕约6周”那几个字,
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疼得我几乎无法呼吸。眼泪终于决堤,汹涌而出,
无声地砸落在冰凉的纸面上,迅速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孩子……妈妈该怎么办?
剧烈的咳嗽毫无预兆地袭来,喉咙里那股压抑了许久的腥甜再也无法控制。
我踉跄着冲进浴室,趴在冰冷的洗手台上,咳得撕心裂肺。温热的液体猛地从喉咙里涌出,
“噗”地一声喷溅在纯白的陶瓷盆壁上。刺目的鲜红,在白色背景下绽开,
像一朵朵绝望而妖异的花。殷红的血丝顺着光滑的瓷壁缓缓向下蜿蜒流淌,触目惊心。
镜子里映出一张惨白如鬼的脸,嘴角还残留着刺眼的血渍,眼神空洞得吓人。
我扶着冰冷的台面,大口喘息,身体因为剧烈的咳嗽和失血的眩晕而微微摇晃。
指尖死死抠着冰凉的台面边缘,骨节泛白。不能再留在这里了。为了这个孩子,
为了我自己仅剩的尊严,必须离开。没有带走任何一件顾衍买的衣服首饰。
衣柜里那些价值不菲的奢侈品,此刻看来都像一个个无声的嘲讽。
我换上了自己三年前带来的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旧棉布裙子,
将那张染了泪痕的孕检单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裙子内侧的口袋,紧贴着心脏的位置。
唯一带走的,是脖子上那根细细的、早已失去光泽的旧银链。
链坠是一个小小的、粗糙的月亮形状。这是妈妈留给我唯一的东西,
也是我关于“家”最后一点模糊的念想。下楼时,偌大的客厅空无一人。
那份签好字的离婚协议和那枚刺眼的钻戒,依旧孤零零地躺在茶几上,像一个巨大的讽刺。
顾衍大概已经走了,去奔赴他崭新的、没有我的幸福生活。也好。我拉开沉重的雕花大门,
外面是沉沉的暮色。没有回头再看一眼这座华丽冰冷的牢笼。晚风带着夏末的凉意吹在身上,
我拢了拢单薄的旧裙子,挺直脊背,一步一步,走进了渐浓的夜色里。身后,
那扇象征着顾太太身份的大门,在我身后缓缓合拢,发出沉重而决绝的一声闷响。
彻底关上了。2、三个月的时间,足以让一座城市从夏末的燥热步入深秋的萧瑟。
市中心寸土寸金的顶级私立医院顶层,VIP病房的落地窗外,
是这座繁华都市永不熄灭的璀璨灯火。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消毒水气味,
被昂贵的香氛小心地调和过,并不难闻。我半靠在宽大柔软的病床上,
身上盖着轻暖的羽绒薄被,手背上扎着留置针,透明的药液正通过细细的软管,
一滴一滴安静地输入我的静脉。化疗带来的脱发期已经过去,
新长出的发茬柔软地贴在头皮上,像一层绒绒的青苔。脸颊凹陷得厉害,
脸色是久不见阳光的苍白,嘴唇也几乎没有血色。只有那双眼睛,因为瘦脱了形,
反而显得更大、更黑,沉静得像两潭深不见底的古井。病房门被无声地推开,
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清脆而有节奏。关玥一身利落的白色高定西装,
手里拿着一份厚厚的文件,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她是我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依靠,
我的表姐。“晚晚,感觉怎么样?”她快步走到床边,放下文件,伸手探了探我的额头,
又仔细看了看我的脸色,眉头才稍稍舒展,“气色看着比前几天好点了。今天这瓶输完,
明天就能出院回家休养了,后面定期复查就行。”她的语气是刻意放轻的安抚。
我牵了牵嘴角,想给她一个安心的笑容,却有些力不从心。“嗯,好多了,姐。
”声音依旧带着大病初愈的虚弱沙哑,“辛苦你了。”“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
”关玥嗔怪地瞪了我一眼,随即拿起带来的文件,眼神瞬间变得锐利而明亮,
带着一种复仇般的快意,“看看这个!律师刚送来的最终确认件,
老头子留下的海外信托基金和所有股权,全部完成交割了!现在起,
你就是林氏集团最大的股东,也是我们关家海外投资的实际控制人。顾衍那点家底,
在你面前,连个水花都算不上!”她将文件递到我面前。纸张散发出淡淡的油墨气息。
我垂下眼帘,目光扫过那些代表着天文数字的条款和签名。心湖像是投入了一颗石子,
却只漾开了一圈微不可察的涟漪,很快就恢复了沉寂。财富?权势?
曾经或许是我仰望顾衍时,渴望用来拉近与他距离的东西。可如今,
它们更像是一副沉重冰冷的铠甲,被命运强行披挂在我伤痕累累的身上。没有喜悦,
只有一种沉甸甸的、近乎麻木的责任感。关玥看着我平静得过分的反应,叹了口气,
语气软了下来:“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好受。孩子的事……”她顿了顿,
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我的表情,“医生说了,你这次能扛过来,已经是奇迹。
孩子……是老天爷眷顾,也是这孩子自己命硬,跟着你熬过来了。以后好好养着,都会好的。
”我的手,下意识地、极其轻柔地覆上依旧平坦的小腹。那里,有一个顽强的小生命,
陪着我经历了化疗的地狱,熬过了最凶险的感染期,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
它是我在这无边黑暗中,唯一抓住的、微弱的暖光。“嗯。”我低低应了一声,
掌心传来自己温热的体温,心底那片荒芜的冻土,似乎终于裂开了一道缝隙,
透进一丝微弱的暖意。就在这时,关玥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屏幕突兀地亮起,
伴随着嗡嗡的震动声。她瞥了一眼,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像是看到了什么极其厌恶的东西。
“又是他。”关玥的声音冷得像冰渣子,带着毫不掩饰的嫌恶,“顾衍。这三个月,
他简直像条疯狗!先是动用所有关系满世界找你,
后来不知道怎么查到了苏清清那条破链子的来源是仿品小作坊,现在大概回过味来了,
死咬着当年火灾的事情不放,掘地三尺也要挖出那个‘真正’的救命恩人。
电话、短信、邮件,甚至堵到我公司楼下……呵,现在知道急了?早干嘛去了!
”她拿起手机,手指悬在挂断键上,眼底满是厌烦。
我看着屏幕上那个不断跳跃的名字——“顾衍”。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了一下,
闷闷地疼。那些刻意尘封的画面不受控制地翻涌上来:他冰冷的眼神,扔戒指时的轻蔑,
那句“你永远比不上清清”的诛心之语,
还有离婚后那三个月在病床上生不如死的煎熬……每一帧,都清晰得如同昨日。
一股冰冷的恨意,顺着脊椎悄然爬升。凭什么?在我被病痛折磨、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时候,
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和苏清清双宿双飞?在我失去一切尊严、像垃圾一样被他抛弃之后,
他又凭什么,像个幡然醒悟的痴情种一样,满世界寻找一个他早已亲手推开、踩进泥里的人?
“姐,”我开口,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的、淬了冰的平静,
“让他打吧。”关玥猛地转头看我,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和不解:“晚晚?
你……”“他不是想知道真相吗?”我微微勾起唇角,那笑容苍白而冰冷,没有一丝温度,
眼神却锐利如刀锋,“那就让他,好好听听。”关玥盯着我看了几秒,
似乎想从我眼中找出哪怕一丝的脆弱或不忍。最终,她在我那双深潭般的眸子里,
只看到了沉寂的恨意和一种近乎冷酷的决心。她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指尖划过屏幕,按下了免提键。顾衍那熟悉又陌生的、带着一种焦灼沙哑的声音,
立刻充满了整个病房:“关玥!我知道晚晚在你那里!你让她接电话!我有话跟她说!
我必须马上见到她!”他的声音失去了往日的沉稳和掌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