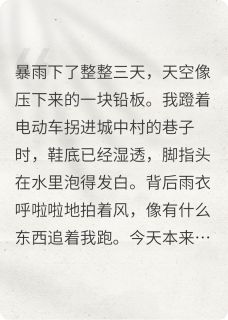
暴雨下了整整三天,天空像压下来的一块铅板。我蹬着电动车拐进城中村的巷子时,
鞋底已经湿透,脚指头在水里泡得发白。背后雨衣呼啦啦地拍着风,像有什么东西追着我跑。
今天本来是我转日班的第一天。夜班虽然单价高,但身体扛不住,
父亲的手术定金还差一万多块,最近只能拼单量。雨天单子多,我一早就接了十几个单,
来不及吃东西,靠一瓶温热的功能饮料撑着。最后一单送到小区南门口,
一位老客户笑着接过去,还打趣说:“你这鞋里能养鱼了。”我笑了笑没回,
心里只想着快回家冲个热水澡,换掉这身湿透的衣服。刚进小区,
就看到门卫室的玻璃窗上糊着一张湿漉漉的白纸:今晚十点起,全区停水检修。
字迹被雨水冲开,墨水晕成一片灰。几个居民凑在门口议论,有人说只是例行保养,
有人说是上游水库泄洪惹的祸。我心里一紧。停水这种事,消息总是传得乱,有的夸大,
有的干脆瞎编。我原本想先回家再说,
可手伸进口袋时摸到了一样硬邦邦的东西——一台旧手摇收音机,
是前几天在快递驿站看到的,老板嫌占地方让我顺手拿走。我随手拧了几下发条,
咔嗒咔嗒的声音在雨声里格外清楚。进门第一件事,我把水桶、水壶全搬到厨房,
拧开水龙头。第一股水冲出来时,我愣住了。水里夹着一股刺鼻的焦油味,颜色像冲了泥巴。
半分钟后才逐渐变清,但漂着细细的黑色碎屑。我抿了一口,苦得发涩,立刻吐进水槽。
楼道外传来物业经理的嗓音:“今晚十点停水,提前储备,水要烧开再喝!
”有人在楼下问为什么停水,他含糊地说是例行维护。我回到客厅,拧开收音机,
“市自来水厂临时停运……二次供水可能存在污染风险……居民请注意……”话音戛然而止,
像被人掐断了线。我把音量调到最大,却只剩下一片沙沙声。外面的雨声更大了,
拍在窗玻璃上,把小区灯光打得一片模糊。微信群里消息刷个不停,
有人发超市空货架的视频,有人说送水车今晚就来。真假难辨。楼上传来脚步声,是林乔,
社区门诊的护士。她撑着一把半坏的伞,手里提着塑料袋,里面露出几瓶药水瓶的瓶口。
她看到我,先笑了笑,又低声说:“家里有水桶就先装满,最好找点净水片备用。
”我点点头,问她是不是有大事。她摇了摇头:“不清楚,但门诊药品库存紧,
我们也在想办法。”说完,她转身走进雨里,背影很快被湿漉漉的雾气吞没。
我灌满了所有能装水的容器,水槽边还排着两个脸盆。看着它们,
我突然想起父亲在电话里叮嘱我:“多存点干粮,别光顾着赚钱。”那时候我还笑他想太多。
收音机依旧沙沙作响,偶尔夹进一声短促的提示音,却不再有播报。我盯着那台旧机器,
心里第一次有种莫名的不安。雨势似乎更大了,楼道里潮气弥漫,偶尔有人拖着购物袋经过,
袋子里是成排的方便面和瓶装水。我想出去再跑一趟,看看能不能多买点东西。刚换好鞋,
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屏幕弹出红底白字的紧急通知:“城区A片区全面停水48小时,
请居民自行储备生活用水。”我盯着那行字,喉咙里涌起一股燥热的味道。
窗外的雨声仿佛在推着我往外走,脚步自己就迈出了门。
楼下的空气里混着汽油味和湿漉漉的土腥味,路边的排水口咕噜咕噜冒着泡。
门口的保安亭灯光昏黄,几个邻居围在一起小声商量去哪个超市还能买到水。
有人说城东商场还有货,但得赶紧。我拉紧雨衣的拉链,
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时间不多了。红色的停水公告还没在手机屏幕上消退,
我已经把背包翻了个底朝天。现金不到三百,零钱一把,硬币多到能把口袋撑鼓。剩下的,
是几包速食面和一个两升的塑料水壶。我蹲在地上画了一张简陋的“最低储备清单”,
五条:净水、干粮、药品、燃料、信息。信息那一栏,我写的是“收音机”,旁边加了个圈。
背好包刚走到楼下,就被门口的喧闹声拦住。几个人排成一列,守在小区门岗前。
铁门半掩着,一个穿迷彩外套的保安站在门口,大声嚷:“出去买东西的,先登记用途,
回来要检查。”登记?我皱了皱眉。往常连打个招呼都懒得的门岗,
现在却像守大门的关卡兵。前面有人抱怨:“就两桶水,还要写用途?”“统一调配。
”保安不耐烦地指了指门里的一张表,“水先集中到物业仓库,到时候按人头分。
”我看了看表上的名字,密密麻麻已经写了好几行。心里冒出股不安,但还是压下去,
低头往旁边的小路绕。雨势减弱了些,巷子里的积水退了一点,地面露出斑驳的水泥面。
城中村的小卖部灯光昏黄,柜台后坐着的老板正看着手机直播。见我进来,
他抬眼笑了笑:“水没了,饼干要吗?”我指了指角落那排灰尘落得厚厚的蜡烛,
“这个多少钱?”“一块一个,拿十个给你便宜。”我又要了几包压缩饼干和一袋盐,
盐是林乔提醒我准备的。老板收钱时顺手从柜台下面翻出一个旧塑料盆,
塞给我:“算搭把手,能装水。”出来时雨又密了,背街的水沟里漂着塑料袋和菜叶。
拐到商场背后的卸货口,正好遇到两个搬运工推着手推车出来,车上是几桶没标签的矿泉水。
我凑过去低声问:“这个卖吗?”其中一个打量我一眼:“现金?
”我把剩下的两百多都掏出来,他点了点,递给我两桶。“快走,别让前面看见。
”一路小跑回小区时,铁门口挤了更多人。赵连胜——前业委会主任,正站在台阶上,
手里拿着对讲机,身后跟着两个年轻人。他看见我,伸手拦住:“桶给我,先统一登记。
”“这是我自己买的。”我压着火气。“买的也是小区的资源。”他的语气不容商量,
“不登记,谁知道你藏多少?”我想过去抢,但看到旁边已经被扣下水桶的邻居,
硬生生忍住。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把桶抬进门岗旁的储物间,门啪地关上。
心里的火一直烧到家门口。刚放下包,手机响了,是林乔:“你在哪?门诊停电了,
冷柜里的疫苗和胰岛素快报废了。”我愣了两秒,“还有多久?”“最多两小时。
学校实验楼白天还有电源,能撑一阵。你能帮我搬过去吗?
”我看了眼空空的水桶和已经少得可怜的物资,喉咙像被堵住。搬冷链过去,
意味着我得再出一趟门,还要冒着被门岗拦下的风险。可要是不搬,那些药全毁了,
接下来整个小区都得为缺医少药付代价。“好。”我听见自己说。下楼时,雨停了片刻,
空气里全是积水蒸发的湿热味。路过地库时看见老付正蹲在发电机旁捣鼓,他抬头看见我,
嘴里叼着烟:“水你存够了吗?”“存不够。”我说,“赵那边扣了。”“那就盯着蓄水箱,
阀门锈死了,我找时间修。”他把烟吐到一边,“今晚或者明早,雨水会冲满箱子。
”我没来得及多问,继续往门诊跑。推开那扇半掩的玻璃门,里面一股冰柜化霜的冷味。
林乔蹲在柜子前,戴着手套搬药盒,额头渗出细汗。“帮我抬这一箱。
”她指了指一个白色冷链箱,“别碰侧边的锁扣。”我们推着手推车走到学校围墙边,
积水在拐角处最深,轮子陷进去的时候,冷链箱差点滑出来。我死死抱住,背心被冷汗浸透。
好不容易推到实验楼门口,林乔拿出备用钥匙开门,里面的灯光刺得我一眯眼。
老付赶来帮忙接通了蓄电,冷柜嗡嗡地运转起来。那一刻,我才长出一口气。
“水的问题怎么办?”林乔问。“想办法绕过去。”我说,“不然迟早被那帮人卡死。
”回去的路上,我特意绕开正门,从商场背街穿回小区。雨又落下来,
打在外套兜里的收音机上,发出闷闷的声响。我拧了几下发条,调到熟悉的频段,
中忽然传来一句含糊的低语:“……东郊……不要相信——”然后又被彻底淹没在沙沙声里。
夜色里,楼道的灯闪了两下,赵连胜的身影在尽头出现,手里拿着一串钥匙,朝我这边走来。
赵连胜的影子越拉越长,灯光在他脚下断断续续闪着。我顺势把收音机塞回外套口袋,
装作只是路过。他眼睛盯了我一瞬,嘴角勾了勾:“晚上这么晚,还到处跑?
”“帮林乔搬点东西。”我淡淡地应,绕过他往楼上走。他的视线像钩子一样黏在我背上,
直到我推开家门才消失。屋里安静得出奇,只有雨点轻轻敲在窗台。水桶还空在角落,
那两桶被扣下的水始终是个硬结。我把湿外套挂在门后,手里那股紧绷的劲却怎么都放不下。
收音机突然“哔”了一声,吓得我差点掉地上。调频盘自己跳到一个频段,
传出低沉的男声:“市政管网全面停运,供水优先保障医疗单位,
其余居民请自行取水……”话没说完,又是沙沙一片。我盯着收音机,
脑子里冒出个念头——如果真只给医疗单位供水,那社区就只能靠蓄水箱和雨水活命。
可赵连胜他们,肯定会把控阀门。第二天一早,小区广场上多了几个蓝色塑料桶,
边上摆着写着“物业专用”的牌子。几个壮实的年轻人守在旁边,谁要取水都得排队签字。
我混在人群里,看见赵正拿着个小本子记录,每人只发半桶。
一个年轻母亲抱着孩子排到前面时,赵皱着眉说:“小孩也算一份。”“那我这桶不够啊。
”女人急了。“规矩就是规矩。”赵摆摆手,示意下一个。我退到队伍外,
看着他那副得意的样子,心里已经开始盘算怎么绕开这套规则。老付说过,
蓄水箱的阀门坏了,只要下雨水就会灌进去。可阀门位置在地库后面,平时有锁链。
要是能先修好阀门,再接个暗管通到楼道,那我们这一栋至少能多撑几天。回到楼上,
我敲开老付的门。他正用螺丝刀修一个旧风扇,见是我,抬了下眼皮:“怎么?
”“帮我弄阀门。”我开门见山,“再晚就来不及了。”老付叼着烟想了两秒,
放下螺丝刀:“晚上十点,趁他们收桶回去睡觉,我们去看看。”那天白天,
我装作没事人一样继续送单。中午路过菜市场,顺手买了几块帆布和一捆塑料软管。
摊主好奇地问**嘛用,我笑着说是接阳台雨水。他没多问,还多给了我一截细管。
晚上十点,雨又落下来,淅淅沥沥。广场上的人散得差不多,
几个看守的年轻人正缩在门岗屋里打牌。我和老付绕到地库后,锁链锈得厉害,
他用钳子剪了几下,咔的一声断开。阀门比我想的还旧,螺丝全是锈斑,
转的时候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雨水顺着排水槽流进来,很快就有水注进箱体。
“这管子你留着,用的时候套在这里。”老付指着旁边的溢水口,“这样他们查不到。
”我用帆布把管子缠了几圈,固定在阴影处。做完这些,我们像没事人一样回了楼。
第二天清晨,我试着打开软管,冰凉的水立刻流进盆里。看着水面上浮着的细小泡沫,
我心里一松。至少这一栋的人,不必看赵的脸色喝水。可没高兴多久,
林乔打来电话:“门诊被人翻了,药品丢了几箱。”我心头一紧,“谁干的?”“不知道,
监控被拔了线。”她语气有些疲惫,“你路上注意点。”挂了电话,我忽然意识到,
这不仅仅是水的问题。有人在故意搅局,把大家推向互相猜忌。傍晚时分,
收音机里又断断续续传来声音,
这次比之前更急促:“……城西**点……安全期限不明……物资有限……”我握着调频盘,
想继续听下去,却被一阵敲门声打断。开门,是个我没见过的男人,穿着湿漉漉的外套,
手里提着个破皮箱。他抬起头,目光直直盯着我:“听说你这里,有水。”男人的声音低沉,
却带着一股不容拒绝的笃定。我盯着他脚边的破皮箱,拉链歪着,
缝隙里露出几个锈迹斑斑的金属罐,表面印着已经模糊的英文字母。
那是我在任何本地超市都没见过的包装。“你是谁?”我压低声音,目光扫了一眼楼道,
空无一人,但湿漉漉的空气让人有种被窥视的错觉。“朋友介绍来的。”他像是随口说的,
但眼神紧紧盯着我的脸,“我有物资,你有水,公平交换。”我犹豫着没让开门。
他却用脚轻轻碰了碰皮箱,金属罐撞在一起发出沉闷的声响。那声音像一颗钉子,
精准地敲在我胃里那块最饿的地方。“罐头?”我问。“牛肉的,真空密封,能放五年。
”他咧嘴笑了笑,露出一口不整齐的牙,“你要几个,就给我多少升水。”我思索了几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