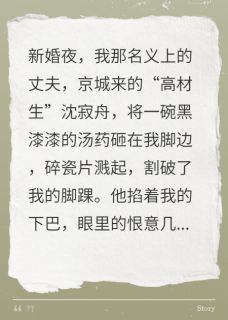
新婚夜,我那名义上的丈夫,京城来的“高材生”沈寂舟,将一碗黑漆漆的汤药砸在我脚边,
碎瓷片溅起,割破了我的脚踝。他掐着我的下巴,
眼里的恨意几乎要将我吞噬:“你最好别有别的念头,否则我不介意让你守一辈子活寡。
”我没告诉他,这门亲事,是我用我爸半辈子的工分求来的。为的,
就是让他这辈子都“离不开”我。毕竟,一个瘸子,在这北大荒的农场里,离了我,
他要怎么活?01“林晚意,你就这么缺男人?
上赶着嫁给一个瘸子、一个前途尽毁的‘右派’?”“你图他京城户口?别做梦了,
人家这辈子都回不去了!你这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我听说他那方面……也不行了。
你这辈子完了!”新婚第一天,我端着一盆水出门,就被堵在门口的几个婆娘围住了。
她们的话像淬了毒的钉子,一句句扎进我心里。我刚想反驳,
我那新婚丈夫沈寂舟就拄着拐杖,出现在了门口。他倚着门框,脸色比塞外的雪还白,
眼神却像刀子,冷冷地刮过每一个人。婆娘们瞬间噤声,讪讪地散了。整个北大荒七分场,
谁不知道沈寂舟?他是从京城下放来的工程师,原本是天之骄子,却因为一场意外,
摔断了腿,还被扣上了沉重的帽子,从云端跌落泥潭。他英俊、有文化,
可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这些屁用没有。他孤僻、冷漠,看谁都带着一股疏离的审判感,
仿佛我们这些土里刨食的乡下人是什么脏东西。没人敢靠近他,除了我。我,林晚意,
七分场场长家的闺女,偏偏一头撞了上去。他回到屋里,重重地将门关上,
巨大的声响震得墙上的灰直往下掉。我端着水盆进去,他正坐在床沿,
费力地想给自己倒杯水。我快步上前,从他手里拿过水壶和杯子。“我来。”他没有拒绝,
只是用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盯着我。他的手指很长,骨节分明,不像个干活的人。只是此刻,
那只手上布满了裂口和冻疮。我倒好水递给他,他却不接,目光落在我脚踝的血痕上。
那是昨晚他砸碎的碗片划的。“疼吗?”他突然开口,声音沙哑,像是很久没说过话。
我愣了一下,摇了摇头:“不疼。”他忽然笑了,那笑容里没有半分暖意,
全是嘲弄:“林晚意,你可真是个‘好人’。”这三个字,他说得格外重。我知道,
他在讽刺我。全场的人都觉得我是个“烂好人”,才会接手他这个**烦。我没接话,
蹲下身,准备收拾地上的碎瓷片。昨晚他情绪激动,我没敢收拾,怕再**他。
我的手指刚碰到一片锋利的碎瓷,一只手就猛地抓住了我的手腕。他的力气很大,
捏得我生疼。“谁让你动的?”他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种危险的气息。
“我……”“滚出去。”我不动,抬头倔强地看着他。我们之间,隔着天差地别的出身,
隔着无法言说的仇恨与误解。但既然嫁给了他,我就没想过退缩。“沈寂舟,
”我一字一句地说,“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妻子。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他眼中的嘲弄更深了,慢慢松开我的手,转而抬起我的下,迫使我与他对视。“妻子?
”他咀嚼着这个词,像是在品尝什么笑话,“你不过是你爸派来监视我的工具。或者,
是你自己别有所图?”他的话像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我看着他,心脏一阵抽痛。
我图什么?我图你三年前,在大雪封山的夜里,把最后一个馒头和半瓶救命的消炎药,
留给了素不相识的我弟弟。那时候的你,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可这些,我不能说。
我只能压下所有情绪,扯出一个僵硬的笑容:“对啊,我图你长得俊,行不行?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久到我几乎要维持不住脸上的表情。然后,他缓缓放开我,
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用布包着的东西,扔到我怀里。“这是什么?”我打开一看,
是一块雕刻了一半的木头小鸟,翅膀的线条流畅又优美,只是还没完工。“见面礼。
”他靠回床头,闭上眼睛,脸上是化不开的疲惫和厌倦,“拿了东西,就安分点。
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我握着那块半成品的木鸟,指尖传来冰凉的触感。
这就是他给我的下马威,一个未完成的、残缺的礼物,就像他自己一样。我没有再说什么,
默默地收拾好地上的狼藉,端着水盆走了出去。刚走到院子,
就看到邻居家的王嫂子对我挤眉弄眼,压低声音说:“晚意,你家那口子,是不是不行啊?
新婚第二天就让你出来干活,晚上没折腾你?”我脸上一热,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听到身后传来拐杖杵地的声音。沈寂舟站在门口,冷冷地看着王嫂子:“我的女人,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议论?”02王嫂子被沈寂舟那要吃人的眼神吓得一哆嗦,
嘴里嘟囔着“有什么了不起的”,灰溜溜地跑了。我有些意外地回头看他。这是他第一次,
在外人面前维护我。“看什么?”他却别过脸,语气依旧冰冷,
“我只是讨厌苍蝇在我耳边嗡嗡叫。”说完,他转身回了屋,留给我一个孤傲的背影。
我知道,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嘴上不饶人,心里却未必那么想。就像一只受了伤的刺猬,
用最硬的刺对着全世界,只是为了保护自己柔软的腹部。接下来的日子,
我和沈寂舟过着一种诡异的“同居”生活。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睡在同一张土炕上,
中间却隔着一条能跑马的楚河汉界。他睡姿很规矩,总是背对着我,像一尊没有温度的雕像。
他话很少,每天除了看书,就是坐在窗边发呆,或者拿着那块小木鸟,
用一把破旧的小刀慢慢地刻。他的手很巧,那只鸟的羽毛在他手下渐渐变得栩栩如生。
农场的活很重,我每天累得像条狗,回来还要给他做饭、洗衣、烧水烫脚。
他那条伤腿一到阴雨天就疼得厉害,我偷偷托人从县城买了草药,熬好了让他泡脚。
他从不说道谢,但每次我把药水端过去,他都会默默地把脚放进去。场里的人都笑话我,
说我放着场长的千金不当,非要去伺候一个废物。我爸妈也唉声叹气,
觉得我毁了自己一辈子。我妈不止一次地拉着我的手说:“晚意,你要是受不了,就跟他离。
爸妈还能养你一辈子。”我每次都只是摇头。他们不懂,沈寂舟不是废物。
他的那些设计图纸,随便拿一张出来,都比场里那些老技术员的强百倍。只是现在,
龙困浅滩罢了。这天,场里开大会,要评选劳动标兵。这种事本与我们家无缘,
沈寂舟是“问题人员”,没有资格参加。我正准备出门上工,他却叫住了我。“等一下。
”我回头,看见他递给我一个饭盒。“我今天不想吃食堂。”他说。我打开饭盒,
里面是两个白面馒头,中间还夹着几片咸菜。在顿顿都是玉米糊糊的农场,这简直是奢侈品。
我知道,这是他省下来的口粮。“你……”“废话真多。”他打断我,
目光却落在我因为长期干重活而变得粗糙的手上。他的喉结动了动,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我心里一暖,提着饭盒去了会场。评选大会冗长又无聊,场长在台上念着发言稿,
我在下面昏昏欲睡。突然,我听到了我的名字。“……下面,我们要批评一个人!
就是我们场的林晚意!”我一个激灵,猛地站了起来。说话的是副场长的老婆,
也是之前说闲话的王嫂子的亲戚。她站在台上,指着我,满脸鄙夷:“林晚意同志,
你身为场长的女儿,思想觉悟却极其低下!放着大好的青年不嫁,
偏偏嫁给一个背景不清不白的‘右派’!你这是在给我们七分场抹黑!
你这是阶级立场有问题!”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有同情,有幸灾乐祸,有鄙夷。
我气得浑身发抖,嘴唇哆嗦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这个年代,“阶級立场”这顶帽子,
足以压死人。我爸脸色铁青地站起来,刚要说话,一个清冷的声音却从会场后方传来。
“她的阶级立场,有问题?”众人回头,只见沈寂舟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走了进来。
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踩在所有人的心上。场内的喧嚣瞬间静止。他走到我身边,站定,
目光扫过台上的女人,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朵里:“我沈寂舟,
是国家派来支援边疆建设的工程师,不是‘右派’。我的问题,组织上自有公断,
轮不到你在这里给我定性。”他顿了顿,伸手,将我拉到他身后。他的手心干燥而温暖,
给了我无穷的力量。“至于林晚意,”他看着所有人,一字一句,掷地有声,
“她是我沈寂舟的妻子。谁敢动她,就是跟我沈寂舟过不去。”全场死寂。
没人见过这样的沈寂舟。他不再是那个阴郁沉默的瘸子,而是像一头被唤醒的狮子,
浑身散发着令人不敢直视的锋芒。副场长的老婆被他看得心虚,张了张嘴,
却没敢再放一个屁。沈寂舟拉着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出了会场。阳光下,
他的背影挺得笔直。我看着他紧握着我的那只手,忽然觉得,北大荒的风雪,
似乎也没有那么冷了。回到家,他松开我的手,立刻又恢复了那副冷冰冰的样子,
仿佛刚才那个为我出头的男人只是我的幻觉。他坐回窗边,拿起那只木鸟,继续雕刻。
他刻得很专注,小刀划过木头,发出沙沙的声响。我发现,那只鸟的眼睛,
已经被他刻出来了,黑亮黑亮的,像是有生命一样。我走过去,轻声说:“谢谢你。
”他手上的动作没停,头也没抬:“我说了,我讨厌苍蝇。”我知道他又是口是心非。
我看着他,鼓起勇气问出了那个一直想问的问题:“沈寂舟,
如果……如果有一天你的问题解决了,你会回京城吗?”他手上的刀,停了。
屋子里一片寂静,我紧张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过了很久,他才重新开口,
声音里听不出情绪:“你问这个做什么?”“没什么,我就是……”“回京城,”他打断我,
抬起头,目光像两口深井,要把我吸进去,“然后,跟你离婚。”03“然后,跟你离婚。
”这六个字,像一把淬了冰的刀,狠狠扎进我的心脏。刚刚升起的那点暖意,
瞬间被冻结成冰,碎了一地。我看着他,嘴唇动了动,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原来,
他为我出头,不是因为在意我,只是为了维护他那可怜的自尊。原来,在他心里,
我始终是个麻烦,是个一旦有机会就要立刻甩掉的包袱。他似乎很满意我的反应,
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怎么?你不会以为,
我沈寂舟会心甘情愿跟一个乡下女人过一辈子吧?”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却被我硬生生逼了回去。我不能哭,尤其不能在他面前哭。那会让他更看不起我。
我深吸一口气,挺直了背脊,学着他的样子,扯出一个无所谓的笑容:“离婚就离婚。
反正你一个瘸子,我伺候你也亏了。等你回了京城,我正好找个身体好的,你可别后悔。
”说完,我转身就走,不敢再多看他一眼。我怕自己会忍不住,在他面前溃不成军。
我冲出屋子,一口气跑到农场后面的白桦林。深秋的林子里,落叶满地,踩上去沙沙作响。
**在一棵白桦树上,眼泪终于决了堤。我以为,我的付出,我的忍耐,他多少能看到一点。
我以为,人心都是肉长的,就算是块石头,也该被我捂热了。我错了。沈寂舟的心,
不是石头,是万年不化的寒冰。我在林子里哭了很久,直到天色渐暗,才擦干眼泪往回走。
日子还得过,婚暂时也离不了。只要他一天没回京城,我就还是他沈寂舟的妻子。回到家,
屋里黑漆漆的,没有点灯。我心里一沉,快步走进去。“沈寂舟?”没人回答。
我摸索着点亮了煤油灯,昏黄的灯光下,屋子里空无一人。他不在。我的心猛地揪紧了。
天这么黑,他腿脚不便,能去哪儿?我忽然想起今天在会场,他虽然气势逼人,
但脸色却异常苍白,额头上全是冷汗。我疯了一样冲出去,一边喊他的名字,一边四处寻找。
场里的人告诉我,下午就没见过他。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个可怕的念头冒了出来。
他会不会……想不开了?我越想越怕,沿着农场周围的土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跑。
夜里的风很冷,刮在脸上像刀子割。我不知道跑了多久,喊得嗓子都哑了,
还是没有他的踪影。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我听到了远处传来一阵压抑的咳嗽声。
我循着声音找过去,在农场东边废弃的蓄水池边,找到了他。他蜷缩在地上,
身体不住地发抖,脸色白得像纸。他那条受伤的腿,以一个扭曲的姿势伸着,
裤腿上渗出了暗红的血迹。“沈寂舟!”我扑过去,声音都在颤抖,“你怎么了?
”他抬起头,看到是我,眼中没有丝毫意外,只有一片死寂的灰败。他想推开我,
却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别……管我。”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我看到他身边,
散落着几片止痛药。他竟然是疼得受不了,一个人跑到这里来硬扛。我的眼泪又下来了,
又心疼又气。我扶起他,想把他背回去,可他一个大男人,我根本背不动。“你别动,
我去找人!”“不许去!”他死死抓住我的胳膊,力气大得惊人,“我这副样子,
你还嫌不够丢人吗?”“命重要还是面子重要!”我冲他吼道,“沈寂舟,你是不是男人!
这点疼都受不了,还要死要活的!”他愣住了,大概是没想到我敢吼他。我看着他,
放缓了语气:“你听话,我扶你,我们慢慢走回去。家里有我给你买的草药,
泡一泡会好很多。”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同意。最后,他闭上眼睛,
像是放弃了抵抗,轻轻“嗯”了一声。我把他的胳膊架在自己肩上,用尽全身的力气,
才勉强把他撑起来。他的身体大半都压在我身上,很沉。他身上的味道很好闻,不是汗味,
而是一种淡淡的墨水和肥皂混合的气息。回去的路,比来时更漫长。每走一步,
我们两个都气喘吁吁。“林晚意,”他忽然在我耳边开口,声音很轻,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我的脚步一顿。月光下,我能看到他长长的睫毛,
在眼睑下投下一片阴影。他的眼神很复杂,有探究,有迷茫,
还有一丝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脆弱。我避开他的目光,低声说:“因为我是你老婆。
”“呵……”他低笑一声,又是那种嘲弄的语气,“你还真入戏。”我没再说话,
只是咬着牙,一步一步地把他拖回了家。我把他安顿在炕上,烧了热水,把草药放进去,
端到他面前。他这次没有抗拒,默默地脱了鞋袜,把脚浸入水中。我看到,他那条受伤的腿,
脚踝处肿得像个馒头,上面还有一道狰狞的旧疤。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
我蹲下身,伸出手,轻轻地握住他的脚踝,帮他**。他的身体一僵,想把脚抽回去。
“别动。”我按住他,抬头看着他,“你想早点好起来,就得听我的。”他没再动,
只是用一种我看不懂的眼神,定定地看着我。灯光下,我的手指在他的皮肤上轻轻揉捏。
他的脚很冷,我用自己的体温,一点点地温暖它。不知过了多久,他忽然开口,
声音沙哑得厉害:“今天在会场,你为什么不反驳?”“我……”我说不出话。
我能怎么反驳?说他不是废物?说他总有一天会一飞冲天?在别人眼里,那只会是个笑话。
“林晚意,”他看着我,一字一句地问,“你是不是也觉得,我这辈子都完了?
”我猛地抬头,对上他漆黑的眸子。那里面没有了冰冷和嘲讽,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
几乎要将人溺毙的痛苦和绝望。我的心,在那一刻,疼得无法呼吸。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做了一件我自己都意想不到的事。我俯下身,在他的那道伤疤上,轻轻地落下一个吻。
一个温柔的,不带任何情欲的,只关乎怜惜的吻。他整个人都僵住了,像一尊石雕。
我抬起头,看着他震惊的眼睛,认真地说:“沈寂舟,在我心里,你从来都不是废物。
”“你是我一个人的,盖世英雄。”这是我第一次,对他袒露我的心声。也是第一次,
我在他眼中,看到了那片万年寒冰,有了一丝裂缝。04那一晚之后,
沈寂舟和我之间的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不再对我冷嘲热讽,话虽然还是很少,但至少,
他不再把我当成空气。我给他端水送饭,他会默默接过去。我给他泡脚**,
他也不会再抗拒。有时候**活回来晚了,会发现锅里温着热水,
灶台边上放着一个干净的碗。我知道是他做的,但我从不点破,他也从不承认。
我们就像两只小心翼翼的刺猬,在寒冷的冬夜里,试探着靠近彼此,想要取暖,
又怕被对方的尖刺所伤。那只被他雕刻了一半的木鸟,也终于完工了。他把它放在了窗台上,
小鸟的姿态是展翅欲飞的,充满了生命力。每天清晨,阳光照在上面,都像是要活过来一样。
我给他缝补衣服的时候,发现他口袋里有一个小本子。我好奇地打开,
里面全是他画的各种机械图纸,精密又复杂,旁边还标注着密密麻麻的数据。我看不懂,
但我知道,这些东西很宝贵。他的世界,离我那么遥远,又那么吸引我。转眼间,冬天来了。
北大荒的冬天,能冻掉人的下巴。场里的活也停了,进入了“猫冬”时期。这天,
我从娘家拿了些冻白菜回来,刚进院子,就听到屋里传来争吵声。“沈寂舟,
你别给脸不要脸!我们家小琴看上你,是你的福气!你一个瘸子,还带着‘帽子’,
有什么资格挑三拣四?”是副场长老婆的声音。我心里咯噔一下,推门进去。
只见副场长老婆和她的女儿刘琴正站在屋子中央,刘琴满脸娇羞地看着沈寂舟,
而她妈则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沈寂舟坐在炕上,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我再说一遍,
”他的声音冷得像冰,“我结婚了。请你们出去。”“结婚了又怎么样?可以离嘛!
”副场长老婆撇撇嘴,“林晚意那种粗手笨脚的乡下丫头,哪配得上你?
我们家小琴可是高中生,跟你才有共同语言!”刘琴也跟着附和:“沈大哥,
我知道你是有才华的人。只要你跟了我,我爸肯定会想办法帮你把‘帽子’摘了,
说不定还能让你回城呢?”我听着这些话,只觉得一阵恶心。这是**裸的交易和收买。
我走上前,把冻白菜重重地放在桌上,发出“砰”的一声。“刘琴,
当着我这个正牌老婆的面,挖墙脚,不太好吧?”我冷笑着看着她,“你这么上赶着,
是怕自己嫁不出去?”“你!”刘琴被我噎得满脸通红。
副场长老婆立刻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起来:“林晚意,你怎么说话呢?
我们家小琴是可怜他,想拉他一把!你别不识好歹!”“我就是不识好歹,”我寸步不让,
“我男人,就算是个瘸子,是个‘右派’,也轮不到你们来嫌弃,更轮不到你们来施舍!
他好与不好,都是我林晚意的男人!”我一口一个“我男人”,喊得理直气壮。
沈寂舟一直没说话,只是抬起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什么东西,
正在悄然融化。“你……你真是不可理喻!”副场长老婆气急败坏,拉着刘琴,“我们走!
我倒要看看,你们俩能得意到什么时候!”母女俩摔门而去。屋子里终于安静下来。
我脱了外套,开始收拾白菜,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又酸又涩。“你刚才,
”沈寂舟忽然开口,“说的是真心话?”我手上的动作一顿,没回头:“不然呢?
演戏给她们看?”“你就不怕,我真的跟她走了?”他追问。我转过身,
看着他:“你要是那种人,我林晚意就当自己眼瞎了。”他沉默了。过了许久,
他从炕上下来,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走到我面前。他比我高出一个头,我必须仰视他。
他低下头,目光灼灼地看着我,像是要把我看穿。“林晚意,”他伸出手,
轻轻抚上我的脸颊。他的指尖带着薄茧,划过我的皮肤,带来一阵战栗。这是他第一次,
如此主动地碰触我。“你……”我紧张得心脏都快跳出来了。“你过来。”他拉着我的手,
把我带到炕边。他坐下,然后拍了拍身边的位置。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坐了过去。
他从枕头下,拿出了那个他一直画图纸的小本子,翻开,递到我面前。“你看。
”我低头看去,看到的却不再是那些复杂的机械图,而是一幅素描。画上,是一个女孩。
她坐在窗边,低着头,正在缝补一件破旧的男式外套。煤油灯的光晕染在她身上,
给她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她的侧脸很专注,神情温柔又宁静。画的右下角,
有一行小字:吾妻,晚意。画上的人,是我。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从来不知道,他竟然……画了我。“你什么时候……”“你睡着的时候。”他看着我,
眼神里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林晚意,你是不是觉得,我铁石心肠?”我咬着唇,没说话。
他自嘲地笑了笑:“我只是……怕了。”他很少说起自己的事,这是第一次。我静静地听着。
“我曾经也以为,我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家世,光明的前途,
还有……一个我以为会爱我一辈子的未婚妻。”提到“未婚妻”三个字,我的心猛地一缩。
“那场意外,我摔断了腿,也摔碎了我的前程。那些平时围着我转的人,一夜之间都消失了。
我的未婚妻,在我最需要她的时候,递给我一封退婚信,
转头就嫁给了那个……把我从云端推下来的人。”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我能听出那平静之下,
压抑着多大的痛苦和恨意。“我被送到这里,所有人都把我当成瘟神。我以为,
我这辈子就会烂在这里了。”他顿了顿,转头看着我,目光变得无比深邃,“直到你出现。
”“我以为你和她们一样,是带着目的接近我。我羞辱你,冷待你,想把你赶走。
可是你……”他伸出手,紧紧握住我的手,“你像个傻子一样,一次又一次地靠近我,
温暖我。”“林晚意,你告诉我,我该拿你怎么办?”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迷茫和无助。
我看着他,看着这个在我面前卸下所有防备的男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伸出双臂,
紧紧地抱住了他。“沈寂舟,”我把脸埋在他胸口,声音闷闷的,“什么都别办。就这样,
让我陪着你。不管以后怎么样,我都陪着你。”他的身体僵了一下,随即,一双有力的臂膀,
缓缓地,却无比坚定地,回抱住了我。窗外,大雪纷飞。屋內,两颗孤寂的心,
终于在这一刻,紧紧地贴在了一起。05那个拥抱,像一个开关,
彻底打破了我和沈寂舟之间的壁垒。我们依然睡在土炕的两端,
但中间那条无形的“楚河汉界”消失了。夜里,我偶尔会不小心滚到他那边,
碰到他温热的身体。他会僵一下,但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立刻躲开。他的话渐渐多了起来。
他会给我讲京城的事,讲他读过的书,讲那些我闻所未闻的道理。我听得津津有味,
觉得他就像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他也开始对我的世界产生好奇。他会问我农场里的事,
问我小时候的趣闻。我告诉他,我小时候为了掏鸟蛋,从树上摔下来,摔断了胳膊,
我爸气得要揍我,是我妈把我护在身后。他听完,会看着我,眼神里带着笑意,然后伸出手,
摸摸我的头,像在安抚一只小动物。他的腿,在我的精心照料下,好了很多。
虽然还是不能干重活,但至少阴雨天不再疼得那么厉害。他开始走出那间小屋,
在院子里活动。他甚至用木头给我做了一个小板凳,还修好了吱呀作响的院门。
场里的人看我们的眼神也变了。从前的嘲笑和鄙夷,渐渐变成了好奇和探究。
尤其是上次沈寂舟在全场大会上维护我之后,再也没人敢当面说三道四。只有副场长一家,
看我们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刘琴好几次在路上碰到我,都重重地“哼”一声,
用眼白看人。我懒得理她。我现在满心满眼都是沈寂舟,哪有空跟她计较。这天,场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