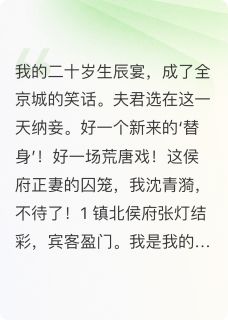
我的二十岁生辰宴,成了全京城的笑话。夫君选在这一天纳妾。好一个新来的‘替身’!
好一场荒唐戏!这侯府正妻的囚笼,我沈青漪,不待了!1镇北侯府张灯结彩,宾客盈门。
我是我的二十岁生辰宴。我的夫君,镇北侯谢景昀,当众执起一个女子的手。
那女子一身素白衣裙,眉眼低垂,与我竟有七分相似。“今日双喜临门。”谢景昀声音清朗,
盖过丝竹。“柳如烟姑娘温婉贤淑,本侯决意纳为贵妾,居落梅苑。”他顿了顿,
目光掠过我瞬间苍白的脸,又补了一句,“如烟性喜清静,往后府中诸人,不得怠慢。
”落梅苑,那是紧挨着他主院“临风阁”最好的院子。我嫁进来三年,
求过三次想搬去夏日避暑,他都以“不合规矩”搪塞过去。如今,
一个酷似他亡妻苏婉的替身,倒合了规矩。满堂宾客的抽气声和探究目光像针,
密密麻麻扎在我背上。我攥紧了袖中的手,指甲陷进掌心,才没让脊梁弯下去。
贴身丫鬟云袖在身后发抖,我反手轻轻按了按她。“侯爷,”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可怕,
像结了冰的湖面。“今日是妾身生辰,您这份礼,真叫人……难忘。
”谢景昀眉头几不可察地一蹙,似乎没料到我还能维持体面。他习惯了。
习惯了这三年里我对他百依百顺,像一幅没有脾气的仕女图。
他递过来一只锦盒:“夫人辛苦,这柄羊脂玉如意,权作补偿。”补偿?
我看着他眼中那点施舍般的愧意,只觉得胃里翻江倒海。宾客席上传来压低的嗤笑。
谁不知道,镇北侯心尖上的白月光苏婉,是五年前病逝的。我沈青漪,
不过是仗着眉眼间那点相似,才得以填了侯夫人的位置。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死寂里,
一道通传撕裂了空气:“骠骑大将军萧珩到——凯旋献捷,特来贺侯夫人芳辰!”轰!
仿佛一道惊雷劈在头顶。我猛地抬头,看向那洞开的朱漆大门。逆着光,
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影大步踏入。玄铁轻甲未卸,战袍下摆沾染着塞外的风尘,
更衬得他气势凛冽,如出鞘寒刀。三年沙场磨砺,褪去了他最后一丝少年意气,
只余下刀锋般的冷峻。那双曾盛满星子的眼睛,此刻深潭一般,扫过全场,最终,
沉沉地落在我脸上。萧珩。我的……前未婚夫。空气凝固了。满堂王孙贵胄,
谁不知道那段旧事?礼部尚书沈家的嫡女沈青漪,曾与少年将军萧珩青梅竹马,指腹为婚。
三年前萧珩奉旨北征前夕,沈家卷入科场弊案,大厦倾颓。我那骄傲了一生的父亲,
在狱中一根白绫了断。母亲忧惧成疾,药石无医。彼时,
是谢景昀递来了橄榄枝——嫁入侯府为继室,他保我沈家女眷平安。我嫁了。
在萧珩死战漠北、音讯全无的时候。“侯爷,夫人。”萧珩的声音低沉,听不出情绪。
他抱拳行礼,目光却如有实质,钉在我脸上,“萧某奉旨回京述职,闻听夫人寿辰,
特来叨扰。薄礼一份,不成敬意。”副将捧上一个狭长的紫檀木匣。谢景昀脸色难看至极,
却不得不强扯出笑:“萧将军凯旋,乃国之柱石,大驾光临,蓬荜生辉。
”他示意管家接过礼匣,目光在我与萧珩之间逡巡,带着审视与愠怒。
柳如烟怯生生地往谢景昀身后躲了躲,细声问:“侯爷,
这位将军是……”萧珩的目光终于从我脸上移开,落在柳如烟身上。只一瞬,
他唇角勾起一抹极淡、极冷的弧度,像是淬了冰的嘲讽:“这位姑娘,倒有几分故人之姿。
侯爷好福气,旧梦重温,易如反掌。”这话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谢景昀脸上。
他额角青筋跳了跳。柳如烟的脸瞬间煞白,泫然欲泣。我心头却莫名一刺。故人?
他指的是苏婉,还是……我?看着柳如烟那张与我相似、此刻却楚楚可怜的脸,
一股深重的疲惫和荒谬感席卷而来。四个人,两个替身。好一场荒唐戏!
心口熟悉的闷痛毫无预兆地袭来,针扎一般。我呼吸一滞,下意识地按住左胸,指尖冰凉。
“夫人?”云袖低呼。几乎同时,一道黑影已掠至我身侧。是萧珩!
他身上还带着塞外的凛冽寒气,动作却快得惊人。一件厚重的大氅带着他的体温,兜头罩下,
将我裹得严严实实。“穿堂风劲,夫人仔细身子。”他声音不高,却压过了所有窃窃私语。
隔着大氅,他扶住我小臂的手沉稳有力,带着薄茧的指腹无意擦过我腕间的冰凉肌肤,
激起一阵战栗。谢景昀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
目光如刀剜过萧珩扶住我的手:“不劳萧将军费心!内子自有本侯照料。”他上前一步,
欲将我扯过去。我猛地抽回手臂,动作大得自己都踉跄了一下。心口的痛楚骤然加剧,
眼前阵阵发黑。“侯爷既知费心,方才就不该让夫人站在风口。”萧珩的声音冷硬如铁,
半步未退,稳稳托住了我的肘弯,隔开了谢景昀伸来的手。他低头看我,眉心紧锁,
“脸色这么差?旧疾又犯了?”旧疾……他如何得知?三年前那个雨夜,
得知沈家倾覆、父亲自尽的消息,我呕出一口心头血,从此落下这心痛的病根。那时他人,
生死不明。“无妨。”我咬牙站直,推开他的手,也推开了那点不合时宜的暖意,
声音冷得像冰,“一点小毛病,死不了。谢将军挂怀。”我刻意咬重了“谢将军”三字,
划清界限。谢景昀被我当众拂了面子,又见萧珩对我如此熟稔关切,妒火与怒意交织,
眼神阴沉得能滴出水。他猛地攥住我的手腕,力道大得几乎要捏碎骨头:“沈青漪!
你……”“侯爷!”我疼得倒抽一口冷气,却昂起头,迎着他喷火的目光,
用尽全身力气一字一句道,“妾身乏了,想回‘清漪院’歇息。这生辰宴,您和柳姑娘,
尽兴。”说罢,我狠狠甩开他的手,扯下肩上那件还带着萧珩气息的大氅,掷在地上。
不再看任何人,挺直脊背,转身就走。云袖慌忙跟上。身后,是死一般的寂静,
和两道几乎要将我烧穿的目光。2清漪院的夜,冷得像冰窖。心口的闷痛一阵紧过一阵,
像有只无形的手在狠狠攥捏。我蜷在窗边的软榻上,望着外面黑沉沉的夜,
手里无意识地摩挲着一只小小的素面银盒。盒里是我自己调制的“宁神香”,气味清苦微凉,
指尖沾上一点,揉在太阳穴,勉强能压下那翻涌的血气。“夫人,
您多少喝口参茶……”云袖捧着温热的茶盏,眼圈通红。我摇摇头。谢景昀没有追来,
意料之中。此刻,他大概正在落梅苑,对着那张酷似苏婉的脸,缅怀他那早逝的白月光,
顺便唾弃我这个不识抬举的正妻吧。“砰!”院门被粗暴地撞开。
谢景昀裹挟着一身酒气和寒气闯了进来,脸色铁青。“沈青漪!”他几步冲到榻前,
一把攥住我的下巴,迫我抬头看他,眼中是毫不掩饰的暴怒和……一丝被戳破心事的狼狈,
“当着满京城的面,你就那么急着往旧情人怀里扑?萧珩一回来,你就忘了自己是谁的夫人?
!”旧情人?我看着他因愤怒而扭曲的、与萧珩有三分神似的眉眼,胃里一阵翻腾。
当初嫁他,何尝不是因为这几分相似?我们都不过是画皮难画骨的可怜虫。“侯爷醉了。
”我用力掰开他的手,声音冷寂,“萧将军不过是看在故人之谊,扶了一把。
侯爷若觉得丢了脸面,一纸休书,我即刻就走。也省得……碍着您与柳姑娘重温旧梦。
”“你!”谢景昀被我的话刺得浑身一震,扬手就要落下。我闭上眼,不闪不避。
预期的耳光没有落下。他死死瞪着我,胸膛剧烈起伏,像一头困兽。“重温旧梦?沈青漪,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若非你这张脸……”他话没说完,但那未尽的羞辱,比耳光更响亮。
我扯了扯嘴角,尝到一丝腥甜:“是啊,若非这张脸像极了苏婉,
侯爷怎会施舍我这一席之地?我沈青漪,不过是个趁手的替身,
一个您摆在正室位置上、聊解相思的玩意儿。如今正品赝品都齐了,我这西贝货,
也该退场了。”“替身?”谢景昀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猛地拔高声音,
眼底的慌乱一闪而过,随即被更深的怒意覆盖,“胡说八道!
本侯待你……”“侯爷待我如何,你我心知肚明。”我打断他,疲惫像潮水般淹没四肢百骸,
“三年了,您书房里那幅苏婉的小像,我日日请安都能看见。您醉酒时喊的是谁的名字,
伺候的嬷嬷听得一清二楚。您甚至……”我顿了顿,心口那根刺又深了几分,
“连我熏什么香,都要按着她的喜好来。”谢景昀脸色骤变,
像是从未想过这些隐秘的心思会被我如此直白地撕开,一时竟哑口无言。“侯爷,
”我撑着身子站起来,与他平视,一字一句,清晰无比,“这替身的戏,我演够了。
也请您高抬贵手,放我这赝品,一条生路。”死寂在屋内蔓延。谢景昀死死盯着我,
眼神复杂变幻,愤怒、难堪、还有一丝被彻底看穿的狼狈。最终,
所有的情绪都化为一声冷笑。“生路?沈青漪,你以为离了侯府,离了本侯的庇护,
你一个罪臣之女,带着个病秧子身体,能有什么活路?”他逼近一步,
带着酒气的呼吸喷在我脸上,满是恶意,“还是你觉得,萧珩回来了,就能当你的救命稻草?
别忘了,当初是你在他尸骨未寒时就另攀高枝!你猜他萧大将军,
肯不肯要一个背信弃义、还被我谢景昀穿过的破鞋?!”“啪——!”清脆的耳光声,
响彻寂静。我用尽了全身力气,手掌震得发麻。谢景昀偏着头,脸上迅速浮起鲜红的指印,
他难以置信地瞪着我,像看一个疯子。“滚。”我指着门口,声音嘶哑颤抖,
心口的痛楚排山倒海般袭来,眼前阵阵发黑,“谢景昀,你给我滚出去!”他捂着脸,
眼神阴鸷得像毒蛇,最终却只是狠狠啐了一口,摔门而去。
巨大的关门声震得梁上灰尘簌簌落下。我再也支撑不住,喉头一甜,
一口鲜血猛地喷在榻前的地毯上,洇开刺目的暗红。“夫人——!”云袖的哭喊声变得遥远。
黑暗彻底吞噬意识前,我恍惚闻到了一缕极淡、极熟悉的冷冽气息,裹挟着塞外的风沙味道,
似乎就在窗外。是幻觉吗?3再醒来,已是次日晌午。心口依旧闷痛,但比昨夜缓和许多。
嘴里残留着苦涩的药味。云袖红肿着眼睛守在床边。“夫人,您可算醒了!”她抹着泪,
“昨夜您吐了血,吓死奴婢了!侯爷他……”“别提他。”我声音沙哑地打断,
“谁给我看的诊?”昨夜府里的大夫被谢景昀下令不得进清漪院,我是知道的。
云袖眼神闪烁了一下,低声道:“是……是顾太医。
萧将军天没亮就拿着帖子去太医院请来的。”顾衍之?那位医术高明、性情温和,
常在京中贵妇圈中被提及的年轻院判?我微微一怔。萧珩他……“顾太医怎么说?
”我敛下心绪。“顾太医说您是急怒攻心,引动旧疾,万不能再受**。开了方子,留了药,
还……”云袖从怀里掏出一个更小的、朴素的青瓷药瓶,“还给了这个,
说是他自配的‘定心丸’,若心口实在绞痛难忍,可含服一粒救急。”我接过药瓶,
入手温润。拔开塞子,一股极其清冽、微带甘凉的药香散出,瞬间压下了心头的烦恶。
这香气……很特别,也很舒服。不像府里那些大夫开的药,总是苦得令人作呕。“他人呢?
”“留了药和方子就走了,说是不便久留。”云袖顿了顿,欲言又止,“夫人,
萧将军他……在院外站了一夜。顾太医来之前,
是他用内力护着您心脉……”我攥紧了手中的药瓶,指尖冰凉。窗外,
似乎还残留着一丝未散的、属于塞外的凛冽气息。何必呢?萧珩。当初我背弃婚约嫁入侯府,
我们之间,早已恩断义绝。接下来的日子,清漪院成了真正的冷宫。谢景昀再未踏足,
只命人按时送来份例,不多不少,透着刻意的冷淡和惩罚。倒是柳如烟,
顶着那张与我相似的脸,以“给姐姐请安”的名义来过两次,
话里话外都是炫耀谢景昀如何宠爱她,落梅苑如何精致。我只当她唱戏,连眼皮都懒得抬。
她自觉无趣,也就讪讪地不来了。我开始整理东西。嫁妆单子、地契,
谢景昀以为离了他我活不下去?真是笑话。沈家虽败,但我沈青漪,
并非只会依附男人的菟丝花。母亲出身江南香道世家,一手调香绝技曾名动京师。
我自幼耳濡目染,只是嫁入侯府后,为了迎合谢景昀,或者说迎合他心中苏婉的形象,
刻意藏拙,只熏些清浅寡淡的花香。如今,这身本事,或许能换条活路。
购置了最普通的香药原料:檀香、降真、苏合、甘松、冰片……就在清漪院偏僻的西厢房里,
关起门来,凭着记忆和母亲留下的残破笔记,一点点尝试。失败是常事。有时气味混杂刺鼻,
有时香粉难以成型。烟熏火燎中,心疾也偶尔发作。每当此时,
我便含一粒顾衍之留下的“定心丸”。那清凉甘冽的药香总能奇异地抚平心绪,
也给了我继续摸索的勇气。就在我几乎要放弃时,一日午后,
我尝试着将一味晒干的苦橙花蕊加入基底。当香粉在掌心搓捻开,
一股极其清雅、微带苦涩却又回味悠长的奇特香气弥散开来。它不似寻常花香甜腻,
也不似药香沉重,而是一种澄澈、宁静、仿佛能涤荡尘埃的味道。成了!我心头一阵激动,
给这香取名——“烬余”。香灰烬尽,余韵新生。我将第一批制成的“烬余”香粉装入素囊,
托云袖悄悄送到城南一家不起眼的香料铺子“芳歇斋”寄卖,
只说是家道中落的香道传人所制,不留姓名。三日后,云袖带回一锭沉甸甸的银子,
还有芳歇斋老板激动的话语:“那位客人说,此香清苦自持,暗含筋骨,绝非俗物!
问是否还有?他愿出高价全收!”握着那锭银子,我枯寂的心湖,终于投进了一丝微光。
原来,靠自己的手,真的能挣出一条路。然而,平静并未持续多久。一日,我正埋头筛香,
院门再次被粗暴地踹开!谢景昀带着一身煞气闯了进来,身后跟着哭哭啼啼的柳如烟。
“沈青漪!”他目光如电,
瞬间锁定了我桌上未及收起的香药器具和几枚刚制好的“烬余”香囊。他一把抓起一枚香囊,
放在鼻端狠狠一嗅,脸色瞬间变得铁青扭曲,眼中翻涌着惊怒和一种被彻底愚弄的狂躁。
“这香!这香不是苏婉生前最爱的‘雪中春信’!你一直在骗我?!”他怒吼着,
将香囊狠狠摔在地上,香粉四溅,“你根本不喜欢这种寡淡的香气!你一直在装!
装成她的样子讨好我?!”他像一头暴怒的狮子,几步冲到我跟前,
劈手夺过我手中装着“烬余”香粉的瓷罐,高高举起,眼看就要砸下!“不要——!
”那是我熬了多少个日夜的心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玄色身影如鬼魅般掠入,
带着雷霆之势!只听“砰”的一声闷响,谢景昀手腕被一只铁钳般的大手死死扣住!
那只举着瓷罐的手,硬生生僵在半空。萧珩面沉如水,眼神冷得能冻裂金石:“谢侯爷,
对女人动手,算哪门子英雄?”4小小的西厢房内,气氛剑拔弩张。
谢景昀的手腕被萧珩死死扣住,动弹不得。他脸色铁青,额角青筋暴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