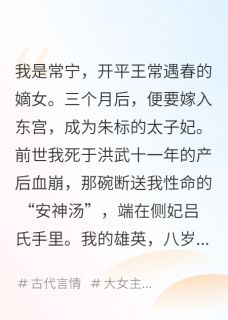
我是常宁,开平王常遇春的嫡女。三个月后,便要嫁入东宫,成为朱标的太子妃。
前世我死于洪武十一年的产后血崩,那碗断送我性命的“安神汤”,端在侧妃吕氏手里。
我的雄英,八岁便上吐下泻没了气,太医只说是“急病”;允熥虽活下来,
却被吕氏养得怯懦如羔羊,最终成了任人拿捏的棋子。此刻我在闺房绣床上睁眼,
窗外飘着洪武三年的雪。重来一世,那些淬了毒的笑、藏了刀的礼、害了命的手,
我都要一一拨开。朱标,雄英,允熥,还有常家满门——这一次,我常宁在,
便要护他们一世安宁。第一章血色重归洪武三年的雪,比往年来得更急。
我在一阵刺骨的寒意中睁开眼,鼻尖萦绕着熟悉的、常府闺房里特有的沉水香。
绣床的锦缎被面蹭着脸颊,触感柔软得不像真的——上一刻,
我分明还躺在东宫的血泊里,产褥上的温热正被死寂的冰冷一点点吞噬。“姑娘,您醒了?
”贴身丫鬟绿萼端着铜盆进来,鬓边斜插的银簪子在烛火下泛着冷光。
我盯着她袖口若隐若现的水绿色绣线,心脏骤然缩紧——那是吕家特有的缠枝莲纹样,
前世我竟从未留意过。她将铜盆搁在妆台上,帕子递到我面前时,
手腕上的双鱼玉佩轻轻晃动。那玉佩成色普通,却是吕氏去年生辰时赏下的物件,
绿萼当时还喜滋滋地说“吕**待我真好”。原来如此。前世的记忆如决堤的洪水,
瞬间冲垮了混沌的意识。洪武十一年十一月,我刚生下允熥,血还在汩汩地淌,
吕氏端来一碗“安神汤”,笑得温婉:“姐姐辛苦了,喝了这碗汤好生歇着。
”我那时昏沉,只当是好意,仰头便灌了下去。后来血崩不止,太医们束手无策,
我躺在朱标怀里,看着他通红的眼睛,才后知后觉地尝到那汤里藏着的、极淡的红花味。
更早之前,洪武十五年五月,雄英上吐下泻,太医院的人来了一波又一波,
都只说是“中了暑气”。我抱着他渐渐冷下去的小身子,眼睁睁看着他断了气,
却连是谁下的手都查不出。直到出殡那日,吕氏来慰问,袖中掉出个空了的蜜饯盒子,
里面残留的粉末,与雄英呕吐物里的苍术屑一模一样。还有父亲常遇春,
洪武二年在柳河川病逝,尸骨未寒,兄长常茂就因鲁莽被削了爵位;蓝玉舅舅功高盖主,
最后落得个剥皮实草的下场……桩桩件件,像一把把淬了毒的尖刀,
扎得我五脏六腑都在疼。“姑娘?”绿萼见我发怔,伸手想来碰我的额头,
“您是不是魇着了?脸色这么白。”我猛地抬手,攥住她的手腕。她的掌心有层薄茧,
绝不是养在深闺的丫鬟该有的——那是常年握笔抄录密信才会磨出来的痕迹。“这玉佩,
倒是别致。”我指尖摩挲着冰凉的玉佩,声音平静得听不出波澜,“吕家**赏的?
”绿萼脸色骤变,眼神慌乱地躲闪:“是……是吕**瞧着奴婢本分,才……”“本分?
”我松开手,从枕下摸出一枚银簪,抵在她颈侧,“那你说说,
昨夜你借着去厨房取参汤的由头,在角门跟谁见了面?”这话是诈她的。
前世我从未留意过这些细枝末节,但重生回来,只需稍加回想,便知哪些地方藏着猫腻。
绿萼果然吓得腿一软,“噗通”跪在地上,眼泪直流:“姑娘饶命!奴婢是被猪油蒙了心!
是吕家的嬷嬷说,只要奴婢替她们传些消息,
日后就能给奴婢寻个好人家……”我看着她涕泪横流的模样,
想起前世她在我床前哭着说“姑娘安心去”的嘴脸,心头一片冰凉。
但现在还不是动她的时候,吕家在京中盘根错节,贸然处置,只会打草惊蛇。“起来吧。
”我收回银簪,语气缓和了些,“念在你伺候我两年的份上,我不揭破你。但从今日起,
你去账房领三个月月钱,回原籍去吧。”绿萼愣了愣,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轻易放过她,
磕了三个响头,连滚带爬地出去了。我掀开被子下床,走到妆镜前。铜镜里映出的少女,
梳着双丫髻,脸上还带着未脱的稚气,只有那双眼睛,盛满了与年龄不符的沧桑和冷冽。
这是洪武三年冬,我刚满十五岁,距离与朱标大婚,还有整整半年。
父亲常遇春上个月刚在军中病逝,兄长常茂承袭了爵位,却因性子鲁莽,
正被皇伯父朱元璋敲打。而吕氏,此刻还是吏部尚书吕本的掌上明珠,已经通过了选秀,
成了太子侧妃的备选人选——前世,正是她,一步步蚕食了我和孩子们的性命。
指尖抚过妆台上那方尚未绣完的鸳鸯帕,针脚疏浅,是我前几日为大婚准备的。
前世我满心欢喜地绣完,却不知这帕子最终会被吕氏拿去,染上雄英的血,
成了她污蔑我“克子”的证据。“嗤——”我拿起剪刀,将那方帕子绞得粉碎。
窗外的雪还在下,簌簌有声,像是在为前世的亡魂哀悼。我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隙,
冷冽的空气灌入肺腑,让我更加清醒。这一世,我不能再像前世那样天真。我要护住常家,
不能让兄长重蹈覆辙,不能让父亲用性命换来的功勋付诸东流;我要护住朱标,
那个总是温温和和唤我“阿英”的男人,不能让他再因忧思过度,
年纪轻轻就撒手人寰;我更要护住我的孩子们,雄英,允熥,我要让他们平安长大,
而不是成为宫廷斗争的牺牲品。还有马皇后。前世她总说我“身子骨弱,要好好调养”,
临终前还把太医院秘制的固本丸塞给我。可我记得,她从洪武五年起,就时常咳血,
太医们都说是“忧思成疾”,却查不出根由。这一世,我或许能救她。
前几日我让账房先生寻来的《千金方》还在枕下,我取出来,借着烛火翻看。书页泛黄,
却字字清晰,仿佛藏着改写命运的密码。“姑娘,该用晚膳了。
”外间传来嬷嬷李氏的声音,她是母亲的陪房,忠心可靠。“知道了。”我应了一声,
将《千金方》藏进妆奁最深处,又换上一副温和的表情。推开门,李氏正端着食盒进来,
看见地上的碎帕子,皱了皱眉:“这是……”“绣坏了,扔了便是。”我笑了笑,
状似无意地提起,“对了嬷嬷,前几日吕家送来的那匹‘麒麟送子’锦缎呢?我想看看。
”李氏脸上露出一丝嫌恶:“那锦缎看着光鲜,摸着却有些扎手,我让人收起来了。
姑娘要它做什么?”我眼底掠过一丝冷光。果然,和我想的一样。那锦缎的丝线里,
掺了极细的寒性药材,长期接触,会损伤女子根本,影响生育。吕氏这是从一开始,
就没安好心。“没什么。”我淡淡道,“就是觉得绣工不怎么样,配不上东宫的规制。
明日让人烧了吧,省得留着碍眼。”李氏愣了愣,随即点头:“姑娘说的是。”晚膳很简单,
一碟青菜,一碗小米粥。我慢慢喝着,脑子里却在飞速盘算。距离大婚还有半年,
足够我做很多事。第一步,就是清理门户,将吕氏安插在常府的眼线,一个个拔干净。
第二步,是稳固常家的地位。兄长常茂虽鲁莽,却重情义,我得想办法劝他收敛锋芒,
多在皇伯父面前显露忠勇,少掺和勋贵间的争斗。第三步,便是马皇后。过几日是她的生辰,
我正好可以借着请安的由头,去坤宁宫看看她的状况,或许能找到调理她身体的法子。
至于吕氏……我舀粥的手顿了顿,唇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游戏才刚刚开始,她欠我的,
欠我孩子们的,我会一点一点,连本带利地讨回来。窗外的雪不知何时停了,月光透过云层,
洒在庭院里的梅枝上,映出点点寒星。我知道,前路必定布满荆棘,但这一次,
我不会再退缩。因为我不仅是常家的女儿,未来的太子妃,我更是从地狱爬回来的复仇者,
是要守护至亲的执剑人。第二章绣针藏锋洪武三年的腊月,寒风卷着碎雪拍在窗棂上,
像无数只爪子在挠。我坐在暖阁里翻《武经总要》,
指尖划过“行军布阵”的图谱——这是父亲生前常看的书,
前世我只当是枯燥的兵书,如今才懂里面藏着的不仅是战术,更是护身的铠甲。“姑娘,
吕家又派人来了。”李氏掀帘进来,脸色沉得能滴出水,“说是送年礼,
领头的是吕尚书的远房侄女,点名要见您。”我合上书,炭盆里的银骨炭烧得正旺,
映得指尖泛着暖红。“让她在花厅等着。”起身时,我特意换上那件石青色暗纹褙子,
领口绣着极小的常家虎头徽记——这是父亲特意让人给我做的,说是“常家女儿,
不必藏锋”。花厅里果然挤满了人。吕家那侄女穿得一身绯红,珠翠满头,见我进来,
假惺惺地福身:“常**安好,小女代家姑母送年礼来,其中那匹‘麒麟送子’锦缎,
是姑母特意寻苏州绣娘赶制的,说是最配**的身份。”她话音刚落,
厅里几个仆妇便跟着附和:“吕**真是有心了”“这锦缎看着就金贵”。我扫了一眼,
都是平日里见风使舵的角色,绿萼在时,她们常凑在一起嚼舌根。“哦?”我走到锦缎前,
故作惊讶地伸手去摸,指尖刚触到丝线,便“呀”了一声缩回手,指尖已被扎出个血珠,
“这绣线怎么如此粗糙?竟藏着细针似的硬物。”李氏眼疾手快地捧来帕子,我却没接,
只盯着那侄女:“吕姑娘,这锦缎是给未来太子妃用的,若是伤了龙胎,谁担待得起?
”那侄女脸色一白,强笑道:“怎、怎么会?许是绣娘不小心……”“不小心?
”我冷笑一声,突然扬手将锦缎掷在地上,“我常家世代忠良,
从不收这种藏污纳垢的东西!来人,取火盆来!”仆妇们吓得直往后缩,没人敢动。
我看向李氏,她立刻让人端来火盆。火苗舔上锦缎的瞬间,
我清楚地看见那侄女眼中的慌乱——她定是知道丝线里的猫腻,
此刻正怕火势烧出什么证据。“慢着!”一个胖脸仆妇突然尖叫,
“这可是吕尚书府里送来的,烧了就是打吕家的脸啊!”我认得她,是厨房管事的媳妇,
前几日还偷偷向绿萼打听我的喜好。“打吕家的脸?”我缓步走到她面前,
声音不高却带着冰碴,“我常氏的婚事,是皇伯父亲赐的,轮得到你一个奴才置喙?
”胖仆妇“扑通”跪下,磕头如捣蒜。我却没看她,只盯着那堆渐渐蜷曲的锦缎,
扬声道:“今日我把话放这儿——常府虽不是侯门王府,却也容不得宵小作祟。
谁要是敢吃里扒外,别怪我不顾情面!”火盆里的灰烬飘起,落在那侄女的斗篷上,
她抖得像筛糠。我转身坐下,端起李氏递来的热茶:“吕姑娘,回去告诉你家姑母,
年礼我心领了。但往后,不必费这些心思了。”她哪还敢多言,
匆匆行了礼便带着人落荒而逃。打发走众人,我让李氏把那胖仆妇拖去柴房禁足,
又让人去查府里所有仆妇的底细。李氏看着我,
欲言又止:“姑娘今日……是不是太刚硬了些?吕家毕竟是尚书府……”“嬷嬷,
”我打断她,指尖捏着茶杯取暖,“前世我就是太绵软,才让豺狼进了门。这一世,
我不咬人,但也绝不能任人啃噬。”李氏沉默半晌,叹了口气:“姑娘长大了。”入夜后,
我披着斗篷去柴房。胖仆妇见我进来,哭得涕泪横流:“姑娘饶命!是吕家的嬷嬷找我,
说只要我盯着您的动静,就给我儿子谋个差事……”“绿萼跟你联系过几次?”我蹲下身,
借着月光看她的眼睛。“就两次!她说您……您近日总看医书,
怕是身子不妥……”我心头一凛。绿萼果然把我看《千金方》的事报给了吕家,
她们定是在猜我是不是察觉了什么。“你儿子叫什么?在哪当差?”“叫狗剩,
在锦衣卫当杂役……”我站起身,语气平静:“明日让你儿子来府里领五十两银子,
去应天府当差。但你得记住,往后常府的事,若有一字传到吕家耳朵里,
你母子俩就等着去流放吧。”胖仆妇连连应诺,眼里的恐惧掺着感激。我知道,
放她一条生路,远比杀了她有用——她会成为我安在府里的另一双眼睛。回到暖阁,
李氏正等着我,手里拿着个小布包:“姑娘,这是从绿萼床板下搜出来的。”打开一看,
是几张字条,上面用炭笔写着“常氏近日研习医术”“常茂昨日在酒楼与人争执”。
最底下一张,画着个歪歪扭扭的莲花——吕家的标记。我将字条凑到烛火上烧了,
灰烬随风飘出窗外。“嬷嬷,明日陪我回趟外祖家吧。”“去蓝府?”李氏愣了愣,
“可是为了……”“嗯。”我望着窗外的寒月,“舅舅蓝玉性子烈,我得去提醒他,
别被吕家抓住把柄。”更漏敲了三下,我却毫无睡意。铺开信纸,
研墨写下“当归三钱、黄芪五钱”——这是给马皇后准备的方子,过几日入宫请安,
正好用上。笔尖悬在纸上,忽然想起前世朱标总说我“手太嫩,握不住笔”,
那时我只当是玩笑,如今才懂,这双手不仅要握笔,还要握刀,握得住命运的丝线。
窗外的雪又下了起来,落在梅枝上簌簌作响。我知道,这只是开始。吕家在暗处的爪牙,
宫廷里潜藏的杀机,还有那些等着看常家笑话的人……我要一根根拔,一步步破。
因为我身后,是不能再失去的亲人,是必须守护的未来。这一次,我手中的绣针,
藏的不是花,是锋。第三章灯影杀机洪武四年的上元灯节,
南京城的朱雀大街被灯笼照得像条火龙。我披着月白斗篷站在桥头,
看小贩们吆喝着卖走马灯,指尖无意识摩挲着袖中那枚银针——这是昨日从蓝府回来时,
舅舅蓝玉硬塞给我的,说“女儿家出门,总得有些傍身的东西”。李氏跟在身后,
手里提着刚买的糖画:“姑娘,咱们还是早点回吧,人太多了。”我摇摇头。
昨夜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一本旧账册,记着洪武三年冬有批军粮在运输途中“失窃”,
经手人正是吕本的门生。今日出来,一是想散散心,二是想看看能不能撞见些线索。正走着,
忽然听见前方一阵喝彩。挤进人群,见是个猜灯谜的摊子,掌柜的举着个绢灯,
上面写着“天下安”,打一字。周围人七嘴八舌猜着“平”“宁”,都被掌柜摇头否了。
“是‘泰’字。”我话音刚落,就见人群里转出个青衫男子。他身形挺拔,
腰间悬着块羊脂玉佩,眉眼温润,正是朱标。只是此刻他没穿蟒袍,换了身便服,
倒少了几分东宫的威严,多了些少年气。他显然也认出了我,微微一怔,
随即拱手:“常**。”周围的人顿时安静下来,目光在我们俩身上打转。我脸上一热,
忙低头道:“殿下。”掌柜的却没察觉异样,乐呵呵地说:“这位**说对了!
‘天下安’便是‘泰’,取国泰民安之意。”他递过奖品,是支青玉簪,“姑娘好才思。
”我刚要接,朱标却忽然开口:“掌柜的,这簪子我买了。”他解下腰间钱袋,
“再加两盏走马灯,送这位**。”我愣了愣。前世我们的初见是在马皇后的寿宴上,
他规规矩矩地行了礼,说“常**安好”,我则红着脸福身,全程没敢抬头。哪像此刻,
他站在灯笼影里,眼底带着笑意,竟有些像寻常人家的少年。“殿下不必破费。
”我推辞道。“拿着吧。”他将簪子塞进我手里,指尖不经意擦过我的掌心,
温热的触感让我心头一颤,“方才那灯谜,常**解得极妙。我猜了半晌,
只想到个‘晏’字,终究不如‘泰’字周全。”正说着,街对面忽然传来一阵骚动。
几个戴斗笠的汉子挤开人群冲过来,其中一人手里寒光一闪,竟是把短刀!“小心!
”我几乎是本能地拽住朱标往旁边躲,同时将袖中的银针狠狠掷出去。银针虽小,
却精准地扎在那汉子的手腕上,短刀“当啷”落地。这一下用了十足的力气,
是父亲生前教我的防身术,说是“一寸短,一寸险”。朱标的护卫反应极快,
瞬间拔刀护住我们。那几个汉子见行刺不成,转身就往巷子里跑,转眼没了踪影。
周围的人群尖叫着散开,朱标攥着我的胳膊,声音里带着后怕:“你没事吧?”我摇摇头,
才发现手心全是汗。方才那汉子的眼神,像极了前世绿萼临死前的狠戾,
十有八九是吕家派来的——他们不敢对太子动手,
却能借“意外”除掉我这个未来的太子妃。“殿下可知是谁要行刺?
”我定了定神问道。朱标眉头紧锁:“近来朝堂不宁,想动我的人不少。
只是没想到……”他看向我,目光复杂,“常**竟会武功?”“略懂些防身术,
是家父教的。”我避重就轻,从地上捡起那支青玉簪,“这簪子倒是锋利。
”他顺着我的目光看去,忽然笑了:“看来是天意,让它护了你我一次。
”灯笼的光落在他脸上,映得睫毛投下浅浅的阴影。我忽然想起前世他抱着雄英的小棺木,
一夜白头的模样,心口像被针扎了下。“殿下,”我鼓起勇气抬头,“那些人行刺前,
一直在看您腰间的玉佩。”朱标愣了愣,摸了摸那块羊脂玉:“这是父皇赐的,
寻常人认不出。”“可他们认得出殿下的身形气度。”我轻声道,“往后出门,
还是多带些护卫才好。”他定定地看着我,忽然问:“你似乎……很懂这些?
”我心跳漏了一拍,忙找借口:“只是听父亲说过些江湖伎俩。”正说着,
他的贴身太监匆匆赶来,见我们没事,吓得腿都软了:“殿下!您可算让奴才找着了!
皇后娘娘都急坏了!”朱标叹了口气,对我道:“今日多谢常**。
改日我会让内务府送些谢礼到常府。”“殿下客气了。”我福身道别,
看着他被众人簇拥着离去,背影消失在灯影里。李氏扶着我往回走,
手还在抖:“吓死老奴了!那些人是冲着谁来的?”“冲着我,也冲着殿下。
”我握紧手中的青玉簪,簪尖冰凉,“吕家急了。”回到府中,
我立刻让人去查那几个刺客的下落。李氏不解:“官府自会查办,咱们何必多事?
”“官府里未必干净。”我铺开宣纸,凭着记忆画出那几个汉子的身形,
“你看他们的步法,是军中才有的踏雪无痕,定是被人收买的死士。
”李氏倒吸口凉气:“吕尚书竟敢……”“他不敢,但有人敢。
”我想起前世吕氏那副温婉面具下的狠辣,“吕氏想当太子妃,就得先除掉我。
这次行刺不成,下次只会更狠。”正说着,门外传来脚步声。
是去蓝府送信的小厮回来了:“姑娘,蓝将军说知道了,还让小的把这个给您。
”他递来个小盒子,打开一看,是枚虎符碎片,上面刻着“常”字。
这是父亲生前的信物,舅舅竟给了我。“舅舅还说什么?”“将军说,让姑娘放心,
他会盯着吕家的动静,绝不会让他们伤了姑娘。”我捏着那半枚虎符,眼眶有些发热。
前世蓝玉舅舅因“谋反”被诛,连累了多少常家子弟。这一世,我绝不能让悲剧重演。
夜深人静,我坐在窗前,看着那支青玉簪在烛火下泛着光。
朱标今日的眼神总在我脑海里盘旋,他看我的时候,没有把我当成“常遇春的女儿”,
而是当成了一个能与他并肩的人。这或许就是重生的意义。不仅要复仇,要守护,
还要让那些本该温暖的人,真正看到我的心。窗外的灯笼还在亮着,像无数双眼睛。我知道,
吕家绝不会善罢甘休,东宫的路还很长。但握着手中的簪子,
想着朱标那句“常**解得极妙”,我忽然有了底气。这一世的棋局,该由我来落子了。
第四章流言淬刃上元节的刺杀案像颗石子投进玄武湖,表面上很快平息,
底下的暗流却越发汹涌。三日后我去给母亲请安,刚踏进垂花门,
就听见几个仆妇在墙角嚼舌根。“听说了吗?前日灯会上,咱们**把太子殿下拽得可紧了,
哪有未出阁姑娘的样子?”“何止啊,我听吕府的人说,咱们**在府里动不动就打骂下人,
性子烈得很,将来怕是容不下侧妃……”李氏听得火冒三丈,撸起袖子就要去理论,
被我一把拉住。“让她们说。”我声音平静,指尖却攥皱了手里的帕子,“越急着泼脏水,
越说明她们慌了。”回到暖阁,我让人把那几个嚼舌根的仆妇调到庄子上,
又让人去查是谁把“打骂下人”的话传到吕府去的。
李氏替我研墨:“姑娘就这么放她们走?该掌嘴才是!”“掌嘴太便宜了。”我铺开信纸,
写下“军中遗孤”四个字,“把她们赶到庄子上,才能让她们看看,
我常宁是不是真的性子烈。”次日一早,我带着府里新做的五十件寒衣去了城西的育婴堂。
这里住的都是父亲生前救下的军中遗孤,前世我只在年节时让管家送些银钱,从未亲自来过。
孩子们见我进来,起初有些怕生,缩在角落里偷看。我蹲下身,
把带来的蜜饯分给他们:“我是常遇春的女儿,你们的父亲都是我父亲的袍泽。
”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仰起脸:“你就是那个要嫁给太子殿下的姐姐?”我笑着点头,
他却突然鼓起腮帮子:“吕家的姐姐说,你要是当了太子妃,就不让我们进东宫玩了。
”果然是吕氏。我摸了摸他的头:“不会的。将来你们若是有出息,
东宫的大门永远为你们敞开。”正说着,门外传来脚步声。转身一看,
竟是马皇后身边的陈嬷嬷。她捧着个食盒,见了我,笑着说:“皇后娘娘听说姑娘在这儿,
让老奴送些点心来。”我心里一动,忙请她进来。陈嬷嬷看着孩子们穿着新寒衣,
眼眶有些红:“姑娘有心了。这些孩子苦,亏得姑娘惦记。”“嬷嬷说笑了,这是我该做的。
”我状似无意地提起,“只是不知是谁嚼舌根,说我性子烈,怕是要委屈了这些孩子。
”陈嬷嬷何等精明,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姑娘放心,皇后娘娘心里有数。有些人呐,
就是见不得别人好。”离开育婴堂时,陈嬷嬷悄悄塞给我张字条,上面写着“初三,
御花园”。我知道,这是马皇后要见我。初三那日,我特意换上素雅的湖蓝色衣裙,
去了御花园。马皇后正坐在暖亭里喂锦鲤,见我进来,
招手让我过去:“听说你给育婴堂的孩子们送了寒衣?”“回母后,都是些小事。
”“可不是小事。”她递给我块桂花糕,“你父亲生前最疼惜将士,你能记着他们的孩子,
他在天有灵,也该欣慰。”她顿了顿,话锋一转,“只是近来有些闲话,
说你……”“母后,”我打断她,语气诚恳,“儿臣知道有人说我性子烈,容不下人。
但儿臣以为,东宫不是争风吃醋的地方,是辅佐殿下治国的根基。若连侧妃都容不下,
将来如何容得下天下百姓?”马皇后眼中闪过一丝赞许:“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正说着,朱元璋带着一群大臣走了过来,身后跟着朱标和几位皇子。
原来今日是朱元璋考较诸臣女的日子,吕氏也在其中,正站在人群里,看见我时,
眼神淬着毒。“哦?常丫头也在?”朱元璋笑着说,“正好,朕问你们,何为‘齐家’?
”吕氏抢先开口:“回陛下,臣妾以为,齐家在于顺从,妻敬夫,妾敬妻,方能和睦。
”这话看似有理,实则把女子框在了后宅里。我上前一步,朗声道:“陛下,儿臣以为,
齐家在于同心。夫有仁心,妻有慧心,上下一心,方能共渡难关。就像这御花园的锦鲤,
若只顾着争抢食饵,迟早会翻塘。”朱元璋抚掌大笑:“说得好!‘同心’二字,
比‘顺从’更有见地!常丫头,你这见识,不输男儿!”朱标站在朱元璋身后,
看向我的目光里带着骄傲,像在说“我就知道你能行”。吕氏的脸却白了,死死攥着帕子。
考较结束后,朱标借口谢恩,走到我身边:“方才你说的‘同心’,我很赞同。
”“殿下过奖了。”我低下头,心跳有些快。“上元节那日,还没好好谢你。
”他从袖中取出个小盒子,“这个送你。”打开一看,是枚玉佩,上面刻着“泰”字,
与那日灯谜的答案一样。玉佩的边角被打磨得光滑,显然是用心准备的。
“殿下……”“拿着吧。”他把玉佩塞进我手里,声音压得很低,“往后若再遇危险,
不必护着我,先顾好自己。”看着他转身离去的背影,我捏着那枚玉佩,
忽然觉得前路的风雪都温柔了些。回到府中,我让人把朱元璋赏赐的绸缎都送到育婴堂,
又让人去提醒兄长常茂,明日朝堂上千万别冲动,吕本定会借故找茬。夜深人静,
我坐在窗前,看着那枚“泰”字玉佩。吕氏今日输得彻底,定会狗急跳墙。但我不怕,
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马皇后的支持,朱元璋的认可,朱标的信任,
还有舅舅和兄长的守护,这些都是我最坚硬的铠甲。窗外的月光落在玉佩上,泛着温润的光。
我知道,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但这一次,我握紧了手中的刃,也看清了前行的路。
第五章红妆破局洪武四年四月十六,漫天红绸把常府罩成了火海。我坐在镜前,
看着李氏为我绾上凤钗,铜镜里的人影穿着十二幅的霞帔,
沉重得像要把人压进前世的泥沼里。“姑娘,喝口安神茶吧。”李氏递来茶盏,
指尖微微发颤。她昨夜查了三次,确认今日伺候的仆妇都是心腹,可迎亲的队伍还没到,
她的手心已全是汗。我接过茶盏,却没喝。茶水里飘着极细的合欢花,看着无害,
混着霞帔上的龙涎香,便成了**的药——这是吕氏的手段,想让我在大婚当日失态,
落下“轻狂”的话柄。“嬷嬷,把这茶倒了吧。”我轻声道,“换壶新的雨前龙井来,
要温的。”李氏会意,转身时狠狠瞪了那送茶的小丫鬟一眼。那丫鬟是吕家陪嫁来的远亲,
此刻正垂着头,耳尖却红得发烫。吉时到的时候,朱标的仪仗正好停在府外。
我踩着红毡子出门,看见他骑在白马上,穿着大红蟒袍,比上元节时更显英挺。
他的目光穿过人群落在我身上,带着笑意,却在触及我鬓边的赤金步摇时,
微微蹙了下眉——那步摇是吕氏昨日送来的“贺礼”,钗尖藏着极小的倒钩,
稍一动弹就会划破肌肤,若是渗了血,便是“不祥之兆”。我不动声色地抬手,
借着整理鬓发的动作,将步摇拔下来递给身后的侍女:“太沉了,先收着。
”朱标的眉头松开了,眼底闪过一丝赞许。迎亲的路很长,红毡子从常府一直铺到东宫。
路过朱雀大街时,人群里忽然挤出来个老妇,
捧着个红布盖着的托盘跪在轿前:“太子妃娘娘,老妇有薄礼献上,祝娘娘早生贵子!
”轿子停了下来,侍女正要去接,我却掀开轿帘一角,朗声道:“老人家请起,礼物心领了。
只是宫规森严,外姓之物不可随意带入东宫。”那老妇的手僵在半空,眼神慌乱。
我看得清楚,她袖口露出的水绿色绣线,与绿萼、吕家侄女的一模一样。托盘里的红布下,
隐约是个锦盒,想来不是毒簪就是蛊虫——吕氏连最后的体面都不要了。“来人,
赏老人家十两银子,送她回家。”我吩咐道,语气温和却不容置疑。护卫们立刻上前,
半扶半请地将老妇带离,谁也没敢碰那托盘。朱标骑马走在轿旁,
隔着轿帘低声道:“你做得很好。”我捏着袖中的泰字玉佩,指尖传来温润的暖意。
原来被人看穿心思并护着的感觉,是这样踏实。拜堂的时候,朱元璋看着我们,
笑得眼角堆起皱纹:“标儿,常丫头,往后东宫就交给你们了。”马皇后拉着我的手,
塞给我个暖炉:“里面是当归和黄芪,冬日里揣着,养身子。”我知道,这是她在提醒我,
吕氏的手段不止明枪,还有暗箭。送入洞房时,已是黄昏。朱标掀开盖头,烛火落在他脸上,
映得那双眼睛格外亮。“累了吧?”他递来杯合卺酒,“先喝口酒暖暖身子。
”酒杯是錾金的,雕着鸾凤和鸣,看着喜庆,杯沿却有些发黏。我指尖碰上去的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