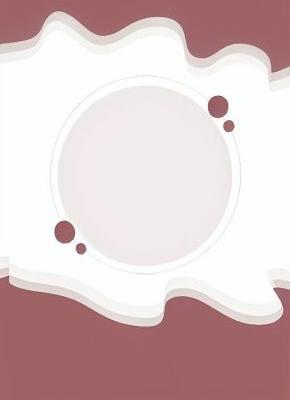
雨声是突然大起来的。
林晚停下手里的镊子,抬头望向窗外。修复室的玻璃窗上,雨水蜿蜒如泪痕,将庭院里那棵银杏树染成一片模糊的金黄。她微微怔住——原来又到了银杏叶落的季节。
“小林,这批敦煌残卷的修复方案你再看一下。”导师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德国人特有的严谨,“尤其是《长生诀》这部分,缺损太严重了。”
林晚收回视线,重新戴上放大镜。灯光下,泛黄的经卷碎片脆弱得像蝴蝶翅膀,墨迹在千年时光中洇开、淡去。她用最细的狼毫笔蘸取特制胶水,一片片拼接着那些关于“长生”的谎言。
修复文物这些年,她学会了一件事:所谓完整,不过是精心掩饰的破碎。
手机在桌角震动,屏幕上跳出来电显示——“母亲”。林晚盯着那两个字看了三秒,指尖无意识地抚过左手腕内侧。隔着皮肤,蝴蝶形状的胎记微微发烫,仿佛也在提醒她归期已至。
接起电话,母亲周敏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温柔:“晚晚,航班没延误吧?你哥今天特意从上海飞回来,说要给你接风。”
“嗯,六点落地。”林晚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像在描述别人的行程,“不用接,我自己回去。”
“那怎么行!景深已经让司机去机场了。”母亲顿了顿,语气里添了丝不易察觉的试探,“你们...有五年没见了吧?”
镊子尖端在经卷上停顿了一瞬。林晚垂下眼帘:“嗯,五年。”
电话那头传来轻叹:“当年的事...都过去了。这次回来就多住段时间,家里需要你。”
挂断电话后,修复室重归寂静,只剩雨声和心跳。林晚摘下放大镜,起身走到窗边。玻璃上映出她的脸——二十四岁,眉眼继承了江南女子的温婉,只有抿紧的唇角泄露了某种倔强。
五年前,她也是这样站在机场,头也不回地登上去柏林的航班。那时陆景深在安检口外看着她,什么也没说,只是那眼神像淬了冰的刀,一刀刀刻在她二十三岁的记忆里。
他们本该是兄妹,如果不是那场意外。
---
飞机降落在江城国际机场时,暮色正浓。秋雨未停,整个城市浸泡在水雾中,霓虹灯的光晕散成一片朦胧。
林晚拖着行李箱走出到达口,一眼就看见了那辆黑色轿车。以及,站在车旁的男人。
陆景深穿着深灰色西装,没打伞,细密的雨珠落在他肩头,氤开深色的痕迹。五年时间将他身上最后的少年气打磨干净,现在的他像一柄收入鞘中的剑,沉静,锋利,不动声色。
“林**。”司机老陈接过她的行李,恭敬地拉开后座车门。
这个称呼让林晚脚步微顿。从前在家里,所有人都叫她“晚晚”,只有陆景深连名带姓地喊她“林晚”。那时她觉得这是疏远,后来才明白,那或许是他唯一能保持的距离。
“谢谢。”她低声说,弯腰坐进车内。
陆景深从另一侧上车,带进一阵清冷的雨气。车厢内空间宽敞,两人的距离却近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林晚侧头看向窗外,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手腕。
“柏林的项目结束了?”他的声音在封闭空间里响起,低沉,听不出情绪。
“嗯,昨天刚做完交接。”
“还走吗?”
这个问题太直接,林晚一时语塞。她转头看他,恰好撞上他的目光。车窗外流动的光影掠过他轮廓分明的侧脸,那双眼睛深邃得让她想起修复室里的古井水——表面平静,底下藏着什么,谁也看不清。
“看情况。”她最终选择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
陆景深似乎也不期待明确回复,只是点了点头。接下来的路程陷入沉默,只有雨刷器规律地摆动。林晚注意到他左手无名指上有一道浅白色的疤痕——那是她十四岁时,他为她挡下破碎花瓶留下的。这么多年过去,痕迹还在。
车子驶入半山别墅区时,雨势渐小。林家宅院隐在银杏树后,灯火通明,像一个等待已久的梦境。
“晚晚!”母亲周敏早已等在门口,一见她就红了眼眶,“瘦了,在国外是不是没好好吃饭?”
拥抱的温度熟悉又陌生。林晚轻轻回抱母亲,目光却越过她的肩头,看向客厅里站着的父亲林振华。五年不见,父亲的鬓角添了白发,但看她的眼神依旧温和。
“回来就好。”林振华走过来,拍了拍她的肩,“先去换衣服,一会儿开饭。景深,你陪妹妹说说话。”
这个称呼让空气凝滞了一瞬。陆景深站在玄关的阴影里,脸上没什么表情:“我先上楼换衣服。”
他转身时,西装下摆擦过林晚的手背。细微的触感,却让她指尖一颤。
---
晚餐的氛围比想象中更微妙。
长餐桌上摆满林晚喜欢的菜式,周敏不停给她夹菜,询问她在柏林的生活。林振华偶尔插话,话题绕不开文物修复行业的现状。陆景深坐在她对面,沉默地用餐,只有在父亲问及公司事务时才简短回应几句。
一切都正常得近乎刻意。
直到周敏提起明天的安排:“对了,明晚苏家有个酒会,你们苏阿姨特意嘱咐,一定要带晚晚去。苏晴那孩子听说你回来了,可高兴了。”
刀叉碰触瓷盘的轻微声响。林晚抬头,发现陆景深停下了动作。
“她刚回来,需要休息。”他的声音听不出波澜,但林晚捕捉到了其中一丝不同寻常的紧绷。
“只是去露个面,不累的。”周敏笑道,“而且苏晴和景深还有合作要谈,正好。”
林晚垂下眼帘,切着盘中的牛排。苏晴——苏家的独生女,芭蕾舞演员,也是陆景深这五年间为数不多的绯闻对象之一。八卦杂志拍过他们一同出席慈善晚宴的照片,标题是“金童玉女,豪门佳偶”。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记得这些。
饭后,周敏拉着林晚在客厅喝茶。林振华和陆景深去了书房谈公事,隐约能听见低沉的交谈声。
“晚晚,”母亲忽然压低声音,“有件事妈妈想问你。”
林晚端起茶杯,热气氤氲了视线:“您说。”
“你在柏林...有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周敏的语气小心翼翼,“妈妈不是催你,只是你也二十四了,该考虑......”
“还没有。”林晚打断她,声音平静,“工作忙,没时间。”
周敏眼中闪过复杂的情绪,像是松了口气,又像是愧疚。她握住林晚的手,指尖冰凉:“妈妈只是希望你能幸福。有时候我在想,如果当年......”
话音未落,书房门开了。陆景深走出来,视线落在她们交握的手上,只一瞬便移开。
“我出去一趟。”他说着,拿起搭在沙发上的外套。
“这么晚了还出去?”周敏问。
“公司有点事。”
他经过林晚身边时,她闻到了淡淡的雪松香——是他惯用的香水,也是她记忆里属于“哥哥”的味道。但此刻这味道让她喉头发紧。
门关上的声音传来,客厅里重归寂静。周敏轻叹一声,拍了拍林晚的手:“你也累了,早点休息吧。房间每天都打扫,和你走时一样。”
---
二楼的走廊很长,深色地毯吸走了所有脚步声。林晚的房间在走廊尽头,隔壁就是陆景深的卧室——这是十年前她搬进来时,周敏特意安排的,说“兄妹俩好有个照应”。
推开门,时光仿佛倒流。房间陈设一如五年前,连床头那盏银杏叶造型的台灯都还在原来的位置。书架上整齐排列着她大学时的专业书籍,还有几本相册。
林晚放下行李,走到窗前。从这个角度能看见庭院里的银杏树,树下那把长椅在夜色中只剩模糊轮廓。十四岁那年,她曾在那把椅子上哭了一整夜,因为学校里有人嘲笑她是“捡来的孩子”。后来陆景深找到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坐在旁边陪她到天亮。
那时她才来林家三个月,对这个名义上的“哥哥”又怕又依赖。怕他冷峻的眼神,依赖他沉默的守护。
手机震动,是柏林导师发来的邮件,询问她是否考虑接手国内博物馆的一个修复项目。林晚正要回复,忽然听见楼下传来轻微的声响。
她轻轻打开门,看见周敏端着一杯热牛奶走向书房。书房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林振华讲电话的声音:
“......当年医院那件事千万不能让两个孩子知道,尤其是晚晚......对,苏家那边也打点好了......我知道这对景深不公平,但现在已经是最好的局面......”
声音压得很低,但在这寂静的深夜里,每个字都清晰得刺耳。
林晚站在楼梯阴影里,手紧紧握住栏杆。木质纹理硌着掌心,带来细微的痛感。她听见母亲推门进去,交谈声戛然而止,然后是刻意提高音量的家常话。
转身回房,关门,上锁。一系列动作机械而迅速。
背靠着冰冷的门板,林晚缓缓滑坐在地毯上。左手腕内侧的胎记又开始发烫,像某种不祥的预兆。她闭上眼睛,脑海里反复回响着那句话——“当年医院那件事”。
窗外,雨又下大了。银杏叶在风雨中飘零,金黄的碎片贴在玻璃上,像一封封无人能读的信。
而在这座华丽宅邸的某个角落,真相正沉睡在时光深处,等待一个契机破土而出。
就像那些她修复的文物,表面的完整之下,往往藏着最深的裂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