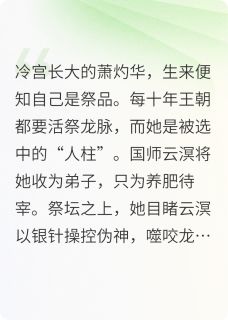
冷宫长大的萧灼华,生来便知自己是祭品。每十年王朝都要活祭龙脉,
而她是被选中的“人柱”。国师云溟将她收为弟子,只为养肥待宰。祭坛之上,
她目睹云溟以银针操控伪神,噬咬龙魂。濒死之际,她看见瞎眼的祭司谢无涯,正以血绘阵。
“想弑神吗?”他空洞的眼窝转向她,“用你的血,点燃我的咒文。
”灼华咬破手指按上阵眼,龙脉在她体内彻底苏醒。“原来,我才是真龙。
”伪神撕裂的刹那,云溟的银针转向新帝。龙鳞覆体的灼华挡在御座前:“师父,
该您献祭了。”---雨水带着暮秋的肃杀,鞭子般抽打在冷宫倾颓的断垣残壁上。
十五岁的萧灼华像一株被遗忘在石缝里的野草,单薄得惊人。她死死趴在半堵湿透的断墙后,
冻得发青的指尖抠进冰冷的泥泞里,眼睛却一眨不眨,
死死盯着前方那片被巨大青铜鼎占据的庭院空地。鼎是前朝遗物,刻满了狰狞的兽面,
雨水冲刷着鼎身暗红近黑的污垢,汇成一道道蜿蜒黏稠的血溪。鼎内,
一个穿着素白祭服的少女被强行按在冰冷的铜壁上。少女徒劳地踢蹬着,
喉咙里发出嗬嗬的、被扼断的呜咽,绝望如同濒死的幼兽。一道惨白的闪电撕裂墨黑的苍穹,
瞬间将庭院照得亮如白昼,也照亮了鼎前那个身着玄黑云纹国师袍的男人——云溟。
他面容俊美得近乎妖异,在电光下却毫无温度,如同玉石雕琢的假面。他微微抬手,
指尖夹着一根细长、闪烁着不祥幽光的银针。动作优雅,甚至带着一丝悲悯的意味,
轻轻刺向少女的眉心。针尖没入皮肤的刹那,少女身体猛地绷直,像被抽走了所有骨头,
软软瘫倒。那根幽冷的银针,如同活物般贪婪地汲取着生命最后的流光,针尾微微震颤,
发出令人牙酸的嗡鸣。就在同时,
一股尖锐的、仿佛来自骨髓深处的剧痛狠狠攫住了萧灼华的左腕!她猛地咬住下唇,
血腥味在口中弥漫,才勉强咽下那声痛呼。她颤抖着撩起湿透的衣袖。闪电的光已逝,
但借着远处宫墙角微弱的灯笼残光,她清晰地看见自己苍白的手腕内侧,
几片细小的、半透明的金色鳞片,正悄然浮现!鳞片边缘带着灼热的刺痛,微微翕张,
的、正在被残忍吞噬的东西——那是深埋地底、维系着大景王朝气运的龙脉发出的无声哀鸣。
每一次十年一度的活祭,都是对龙脉的凌迟。而她萧灼华,生在这冷宫,长在这冷宫,
从记事起就清楚自己的宿命——她是被精心挑选的“人柱”,是下一个十年,
注定要躺进那口青铜鼎,用血肉和魂魄喂养这摇摇欲坠王朝的祭品。雨更大了,
冰冷的雨水灌进她的脖颈,她却感觉不到冷,只有腕间那诡异的灼痛和心底翻涌的冰寒。
她最后看了一眼青铜鼎旁,云溟正漠然地看着侍从将少女僵硬的尸体拖走,
仿佛拂去一粒尘埃。萧灼华缩回身体,像一只受惊的狸猫,悄无声息地滑下断墙,
瘦小的身影迅速消失在冷宫迷宫般幽深破败的回廊深处。---十年光阴,
足以让冷宫角落的野草枯荣数度,也足以让一个瘦骨伶仃、时刻恐惧着祭鼎的小女孩,
长成国师府最受“器重”的弟子。国师府深处,丹房。
浓得化不开的药味裹挟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仿佛来自地底深处的腥甜气息,
沉甸甸地压迫着每一寸空气。巨大的丹炉在房间中央嗡鸣,炉火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青紫色,
炉壁上雕刻的龙形纹路在火光映照下扭曲蠕动,如同活物。炉膛深处,
偶尔传来一声沉闷悠远的龙吟,夹杂着令人头皮发麻的、仿佛血肉被碾碎般的痛苦嘶鸣。
萧灼华垂首侍立在丹炉旁,一身素净的月白弟子服,衬得她面容愈发沉静如水。
她熟练地用银钳拨弄着炉火,调整着火力。动作精准,一丝不苟。十年间,
云溟亲自教导她辨识世间奇珍异草,传授她引气炼药的秘法,
甚至允许她翻阅府中部分关于龙脉地气的古老典籍。在外人看来,这是无上荣宠。
只有她自己知道,这十年,她像一株被精心培育在琉璃罩中的灵药。
云溟投喂的每一份灵丹妙药,灌输的每一缕精纯灵力,
都带着砧板上为待宰羔羊增膘的冷酷意味。她吃得越多,学得越好,离那口青铜鼎就越近。
“十年了。”云溟的声音自身后传来,清越如玉石相击,却冷得没有一丝人味。他缓步走近,
玄黑的袍角拂过光洁的地面,无声无息。目光落在萧灼华身上,
如同审视一件即将完工的器具,“地气将涌,龙脉躁动,正是‘人柱’归位之时。你,
可准备好了?”萧灼华拨弄炉火的手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腕骨内侧,
那几片沉寂了十年的细小金鳞,骤然变得滚烫!
一股源于血脉深处的悸动猛烈撞击着她的心脏,几乎要破腔而出。她强行压下翻腾的气血,
放下银钳,转身,对着云溟深深一礼,姿态恭顺到极致:“弟子蒙师尊十年养育教诲,
无以为报。为陛下分忧,为王朝续脉,弟子万死不辞。”她的声音平稳无波,
眼神温驯地落在云溟袍角精致的云纹上。十年的伪装早已深入骨髓。在云溟眼中,
她依旧是那个被掌控、被豢养、对命运懵懂或已认命的完美祭品。
云溟唇角勾起一丝极淡的弧度,似是满意。他不再多言,目光投向嗡鸣的丹炉,
仿佛那里面即将炼成的,才是他真正关心的东西。---祭坛高耸入云,
通体由一种温润却坚硬的青色玉石筑成,历经千年风雨,表面光滑如镜,
倒映着苍穹变幻的云影。古老的符文深深镌刻在玉璧之上,每一笔都透着苍凉蛮荒的气息。
坛顶中央,正是那口巨大的青铜鼎,鼎身暗红,无声诉说着千年血祭的罪恶。
鼎口氤氲着肉眼可见的、淡金色的地脉龙气,丝丝缕缕,如同垂死的呼吸。祭坛之下,
黑压压跪满了身着朝服的文武百官,山呼万岁之声如同沉闷的海潮。御座之上,
年轻的景帝面色苍白,眉宇间积郁着浓重的病气与更深的不安。他望着祭坛顶端,
眼神复杂难辨。萧灼华身着繁复华美的祭服,赤着双足,一步步踏上冰冷的玉石台阶。
冰冷的触感从脚心直窜头顶,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她垂着眼睫,
表情是献祭者应有的空茫与顺从。唯有紧握在袖中的手,指甲深深陷进掌心,
带来一丝尖锐的痛楚,提醒她保持清醒。国师云溟立于鼎前,玄袍在风中猎猎作响。
他手中托着一个玉盘,
刻满细密符咒的镇魂钉;一把寒光闪闪的短刀;还有一枚比十年前那根更长、更幽邃的银针,
针尖一点寒芒流转,仿佛能吸走魂魄。“吉时已到!”云溟的声音不高,
却清晰地压过了祭坛下的所有喧嚣,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神威,“引地脉龙气,奉祭人柱,
慰我大景山河永固!”他双手结印,口中念诵起古老晦涩的咒言。
祭坛上镌刻的符文次第亮起,青蒙蒙的光芒流转不息。鼎口氤氲的金色龙气骤然变得狂暴,
如同被无形之手撕扯、搅动,发出阵阵痛苦低沉的咆哮!整个祭坛开始微微震颤,
连带着大地都在**。云溟眼中闪过一丝狂热。他拈起那枚幽冷的银针,高高举起,
针尖对准了鼎口翻腾的龙气核心,仿佛要刺穿虚空,召唤某种沉睡的恐怖存在。就在这时,
祭坛边缘,一个几乎被所有人遗忘的角落里,一道身影动了。
那人一身褪色发白的粗布祭司袍,身形清瘦,长发凌乱地披散着,遮住了大半面容。
他背对着祭坛中央的鼎与云溟,正用一根枯枝般的手指,蘸着自己腕间涌出的鲜血,
在冰冷的玉阶上飞快地描绘着。他的动作快得几乎留下残影,
血珠在玉石上拖曳出奇异的轨迹,构成一个个扭曲、古老、与祭坛上符文截然不同的咒文。
那些血咒文散发出微弱却纯粹的金色毫光,与鼎中翻腾的龙气隐隐呼应。萧灼华的目光,
在云溟举起银针的瞬间,被那股微弱却倔强的金光吸引了过去。她看到了那个背影,
看到了他指尖流淌的、仿佛带着生命重量的鲜血,看到了那些在绝望中顽强绽放的咒文。
时间仿佛凝固了一瞬。然后,她听到了一个声音。那声音并非来自耳朵,
而是直接在她脑海深处响起,低沉、沙哑,带着一种穿透灵魂的疲惫与决绝,
如同在无垠荒漠中跋涉了千年的旅人:“想弑神吗?”那个正在以血绘阵的布袍身影,
动作没有丝毫停顿,却缓缓地、极其艰难地侧过了半张脸。凌乱枯槁的发丝滑开,
露出他左眼的轮廓——那里没有眼珠,只有一个深陷的、空洞的眼窝!
仿佛所有的星辰都被那黑暗吸走、囚禁。那空茫的“视线”,
准确无误地“落”在了萧灼华身上。明明没有眼睛,萧灼华却感到一股冰冷而锐利的穿透力,
直刺她灵魂深处。那沙哑的声音再次在她脑中炸开,
每一个字都带着血的腥甜和火的灼热:“用你的血,点燃我的咒文!
”---云溟手中的银针,带着千钧之力,刺向了鼎口狂暴龙气的核心!“嗡——!
”一声仿佛来自洪荒的巨吼撕裂了所有人的耳膜!并非龙吟,
那声音充满了扭曲、贪婪、非人的恶意!鼎口狂暴的金色龙气猛地向内坍缩,紧接着,
一个巨大、模糊、由纯粹怨念与黑暗能量构成的庞然巨影轰然挤出!它没有固定的形体,
只有无数只痛苦挣扎、由黑气凝聚的扭曲手臂,一张布满獠牙、吞噬光明的巨口!
这就是云溟“侍奉”的伪神!它甫一出现,
无数只扭曲的黑手就疯狂地抓向鼎中翻腾的金色龙气,巨口贪婪地噬咬、撕扯!
真龙之魂发出凄厉到极致的悲鸣!整个祭坛剧烈摇晃,玉璧上的符文明灭不定,
仿佛随时会崩碎!坛下百官惊恐尖叫,乱作一团。景帝猛地从御座上站起,脸色惨白如纸,
身体摇摇欲坠。就在伪神巨口即将吞噬掉最大一股龙气的刹那!萧灼华动了。
云溟的银针、伪神的嘶吼、真龙的哀鸣、坛下的混乱……一切都成了模糊的背景。
她的眼中只剩下祭坛边缘那个血色的咒阵,只剩下那个空洞眼窝中燃烧的、无声的决绝火焰。
“弑神……”这两个字在她心头滚过,如同点燃了沉寂万古的火山。没有丝毫犹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