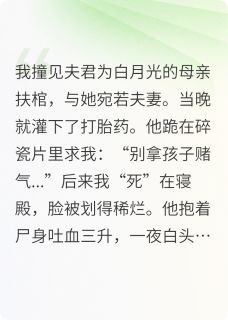
我撞见夫君为白月光的母亲扶棺,与她宛若夫妻。当晚就灌下了打胎药。
他跪在碎瓷片里求我:“别拿孩子赌气...”后来我“死”在寝殿,脸被划得稀烂。
他抱着尸身吐血三升,一夜白头。再相遇时我牵着儿子转身:“王爷认错人了。
”他红着眼扯开衣襟,心口烙着我的名字:“烧成灰...你也得跟我回家。
”———我第一次见萧景渊,是在京城的城门口。那日风大,吹得我鬓边的碎发乱飞。
我刚从边关来,一身洗得发白的布裙,背着个打了补丁的旧包袱,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
像个格格不入的土包子。他就站在不远处的柳树下。月白锦袍,腰束玉带,身姿挺拔如松。
手里捏着朵皱巴巴的小雏菊,花瓣被风吹得颤巍巍的,却偏被他护得仔细。
他像是感受到我的目光,转过头来。四目相对的瞬间,我慌得像只受惊的兔子,忙低下头去。
脚步声由远及近,停在我面前。“姑娘,”他的声音清润如玉石相击,带着笑意,
“这花配你。”我抬头,撞进他弯弯的笑眼里。那双眼,亮得像边关夜晚的星辰,
看得我心尖都在发颤。接过花时,指尖不小心碰到他的,烫得我猛地缩回手,
脸“腾”地红透了,转身就跑。跑出去老远,才敢回头看。他还站在原地,朝我挥了挥手,
笑得温柔。后来才知道,他是当朝永安王,萧景渊。再后来,他像是认准了我似的,
三番五次地出现在我面前。带我去吃京城最有名的那家糖糕铺,
掌柜的谄媚地称呼他“王爷”,我才惊觉自己竟和皇子走得这样近。他却毫不在意,
捻起一块桂花糖糕递到我嘴边:“尝尝,这家的糖糕,甜而不腻。”我小口咬下,
甜意从舌尖蔓延到心底。上元节灯会,他挤在人潮里,把一盏兔子灯塞到我手里。“卿颜,
”他凑近我耳边,声音压低,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认真,“嫁给我,以后我护着你。
”我望着他眼里映出的灯火阑珊,傻乎乎地就点了头。我爹是镇守边关的苏将军,
三年前战死沙场,家里除了我,再没别人。我以为,萧景渊是上天派来疼我的。大婚那天,
凤冠霞帔压得我脖子发酸,可摸着头上沉甸甸的凤冠,心里却很甜。我想,
以后我也是有归宿的人了。2萧景渊待我,是真的好。我说爱吃城南的糖糕,
他第二天就让人把整个铺子买了下来,搬到王府后街,只做给我一人吃。我说夜里怕黑,
他就夜夜陪着我,讲些朝堂趣闻,或是江湖轶事,直到我睡着才敢轻手轻脚地离开。
府里的下人都说,王爷把王妃宠成了眼珠子。我也这么觉得。那时的永安王府,
总是飘着甜丝丝的气息。他会亲手为我描眉,会在我生辰时亲自下厨做一碗长寿面,
会在我受了委屈时把欺负我的人狠狠处置。我常常靠在他怀里,听他有力的心跳,
觉得此生别无所求。直到林婉儿出现。林婉儿是萧景渊恩师的女儿,
一个听起来就温婉柔弱的名字。府里的婆子们私下嚼舌根,
说王爷年少时曾与林姑娘情投意合,只是后来林姑娘随父远走他乡,这才断了联系。
我从没当回事。萧景渊握着我的手,眼神真挚:“卿颜,那都是过去式了。我娶的是你,
以后眼里也只有你。”我信了。我甚至主动提出,要把林婉儿接到府里来住,毕竟她刚丧父,
孤苦无依。萧景渊夸我懂事,眼里的笑意却淡了几分。那天,我亲手做了些精致的点心,
想去书房给他送过去。刚走到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压抑的哭声。是林婉儿的声音,
细细软软的,像羽毛搔在心尖上,却带着说不出的委屈:“景渊哥哥,我娘也走了,
如今我真的只剩一个人了……”萧景渊叹了口气,声音是我从未听过的温柔,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纵容:“别怕,有我在。”我站在门口,手里的食盒烫得像团火,
烧得我指尖发麻。原来,他的温柔,并不只给我一个人。3林婉儿她娘,没过多久就去了。
萧景渊忙前忙后,几乎住在了林府。我去找他,他总是皱着眉,语气带着几分不耐:“卿颜,
婉儿可怜,恩师临终前将她托付给我,我不能不管。”我没话说。毕竟是恩师的遗孀,
于情于理,他都该照拂。可我心里,像被塞进了一团乱麻,密密麻麻地疼。直到出殡那天。
我本不该去的,可鬼使神差地,我还是去了。远远地站在街角,看着那支肃穆的队伍。
萧景渊走在最前面。一身素衣,腰里系着白麻,身姿挺拔,却扶着那口黑漆棺材,一步一步,
走得沉重。那姿态,像个尽孝的儿子,又像个送葬的丈夫。林婉儿一身孝服,哭得梨花带雨,
时不时虚弱地靠在他胳膊上。他没有推开,只是放缓了脚步,任由她依赖。
周围的人议论纷纷。“看,永安王对林姑娘是真上心。”“可不是嘛,这扶棺的规矩,
除了至亲,就是女婿才能做……”后面的话,我没听清。耳朵里嗡嗡作响,
像有无数只蚊子在里面横冲直撞。风把我的披风掀起,猎猎作响,像一面破碎的旗帜。
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剜了一下,疼得我几乎喘不上气。原来,他说的眼里只有我,
是骗人的。原来,我终究是个外人。我踉跄着转身,一步步往王府走。阳光刺眼,
我却觉得浑身冰冷,像是跌进了冰窖里。4回府时,我的脚步发飘,丫鬟见我脸色不对,
忙递上一碗参汤。我没接,径直回了房。夜里,萧景渊回来了。带着一身香烛味,
还有……林婉儿身上那股清雅的脂粉气。他走过来想抱我,我下意识地躲开了。“怎么了?
”他皱眉,语气里带着几分疲惫和不悦。我看着他,嗓子干得像要冒烟:“你今天,
以什么身份去扶的棺?”他愣了一下,随即沉下脸:“卿颜,你别无理取闹。”“无理取闹?
”我笑了,眼泪却不争气地掉了下来,“萧景渊,我是你的王妃!你去给别的女人的娘扶棺,
还像个女婿一样,我问问都不行?”“我都说了,婉儿可怜!”他提高了声音,
眼里满是失望,“苏卿颜,你能不能懂事点?”懂事?我懂事,
所以看着你对别的女人嘘寒问暖,视若珍宝?我懂事,所以忍着心里的疼,
装作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那天晚上,我们吵得很凶。他摔了桌上的茶杯,
碎片溅了一地,说我不可理喻。我缩在床角,一夜没睡。天亮的时候,我趴在床边,
剧烈地干呕起来。丫鬟慌慌张张去请太医。诊脉的时候,我盯着帐顶的流苏,心里一片麻木。
太医笑着恭喜:“王妃,您有喜了,一个多月了。”萧景渊就在旁边,闻言脸色变了变,
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只叹了口气。我摸着小腹,那里有个小生命在悄悄发芽。
可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这个孩子,来得真不是时候。5萧景渊对我好了几天。按时回府,
陪我用膳,话里话外都是小心翼翼。可我知道,那是因为孩子。他心里,还是惦记着林婉儿。
那天他又晚归,身上带着浓重的酒气。我坐在桌边,看着那碗黑漆漆的药。是我让人去抓的。
郎中说,这药喝下去,孩子就没了。我端起来,闻着那股苦涩的味道,手控制不住地发抖。
这是我的孩子啊。是我在这个冰冷的王府里,唯一的牵绊了。可我不能留着他。
我不能让我的孩子,生在一个爹不疼,娘不爱的地方。不能让他像我一样,被人骗得团团转,
最后只剩下满心的疼。“卿颜,你在干什么?”萧景渊闯进来,看到我手里的药碗,
脸色骤变。他冲过来,一把打掉药碗。瓷碗摔在地上,碎成了好几瓣,
黑色的药汁溅了我一身,也溅了他一脸。“你疯了?!”他抓住我的手腕,
力气大得几乎要捏碎我的骨头,眼睛红得吓人,“那是你的孩子!你想干什么?”我看着他,
突然觉得很累很累:“萧景渊,这孩子,我不想要了。”“你说什么?
”他不敢置信地瞪着我,声音都在发颤,“就因为婉儿?苏卿颜,你别拿孩子赌气!”赌气?
我笑了,眼泪混着药汁往下掉,滴在他手背上,滚烫:“是,我就是在赌气。
可你要是心里有我,我用得着赌吗?”“你……”他语塞,随即狠狠把我甩开,
我踉跄着撞到桌角,疼得闷哼一声,“你想都别想!这孩子必须留着!”他转身就往外走,
走了两步又回头,眼神冰冷得像淬了毒的刀:“把她看好了,不许她踏出房门半步!
”6我被关起来了。偏院的门被锁上,窗户也钉了木板。像个密不透风的囚笼。
萧景渊每天都会来看我。有时带些我爱吃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却不敢看我。
有时什么都不说,就坐在旁边,目光复杂地看着我,像是在看一件失而复得,
却又即将破碎的珍宝。他以为这样就能让我回心转意?真是可笑。我的心,
在他扶着那口棺材的时候,就已经死了。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我能感觉到小家伙在里面动。
有时是轻轻的一下,像小鱼在吐泡泡;有时是调皮地踢一脚,力道不大,
却能让我清晰地感受到他的存在。每次他动,我都忍不住掉眼泪。对不起啊,宝宝。
是娘没用,不能给你一个好的将来。林婉儿来看过我一次。隔着门板,她的声音柔柔的,
却带着刺:“苏姐姐,景渊哥哥也是身不由己,他心里是有你的,你就别怪他了。
”我没理她。她又说:“听说姐姐有了身孕,真是恭喜。只是……景渊哥哥心里苦,
姐姐该多体谅他才是。毕竟,我娘和我爹,对他有再造之恩。”体谅?我体谅他,谁体谅我?
谁体谅我肚子里这个还没出世,就不被期待的孩子?她走后,我对着门板,笑出了声。
笑得眼泪直流,笑得浑身发抖。7我开始筹划逃跑。我不能就这么被困死在王府里。
我找了个机会,买通了一个送饭的小丫鬟。她是我从边关带过来的,叫春桃,忠心耿耿。
我让她去联系我爹以前的旧部。那些人,当年受我爹恩惠,如今分散在京城各处,
一直感念我爹的恩情。我告诉他们,我要离开,需要他们帮忙。他们很快就回信了,
说一切都安排好了。日子定在十五那天。那天是月圆夜,王府的守卫会松懈些。我摸着肚子,
心里既紧张又期待。萧景渊还是每天都来。他看我的眼神越来越复杂,带着愧疚,
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讨好。他甚至开始对我讲他和林婉儿的事。
说他老师当年如何在危难中救他,说他老师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让他务必照顾好林婉儿,
护她一生周全。说他对林婉儿,只有责任,没有别的。我只是听着,不说话。责任?
责任就能让他不顾自己的妻子,不顾自己的孩子?这种话,他骗骗自己就好。别来骗我了。
十五那天,夜很静。月亮又大又圆,照得院子里像铺了层白霜。我按照计划,
换上了早就准备好的粗布衣服。春桃给我递来一个小小的包裹,里面是一些干粮和碎银。
“王妃,都安排好了,后门那边有人接应。”她的声音带着哭腔。我拍了拍她的手:“别怕,
等我走了,你就说我睡着了,晚点再报信。”她点点头,转身去放风。我深吸一口气,
刚走到门口,就听见外面传来熟悉的脚步声。是萧景渊。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他怎么来了?“卿颜,睡了吗?”他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带着几分酒气。我没敢出声,
躲在门后,心脏砰砰直跳,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他没再说话,好像就站在门外。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叹了口气,脚步声渐渐远了。我松了口气,刚想开门,
就闻到一股浓烈的烟味。不对!烟味越来越浓,还有火光!着火了!
8火是从西边的柴房烧起来的。风很大,火势蔓延得很快。很快,整个偏院都被火光吞没了。
浓烟滚滚,呛得我直咳嗽,眼泪直流。“王妃!快走!”春桃冲进来,脸上沾着烟灰,
拉着我的手就往外跑。我跟着她,在浓烟里摸索着往前走。火舌舔着门窗,噼啪作响,
像是无数只恶鬼在嘶吼。热浪灼得我皮肤发疼,头发都被烤得卷曲起来。我们绕到后院,
那里果然有两个人在等。是我爹的旧部,王伯和李叔。“**,快!”他们扶着我,
往墙上搭好的梯子跑去。爬上墙头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偏院已经成了一片火海,
映红了半边天。我的心,像被火烤过一样,又烫又疼。再见了,萧景渊。再见了,永安王府。
从今往后,世上再没有苏卿颜。我们一路往南走。避开了官道,专挑小路走。我身子重,
走得慢。王伯和李叔对我很照顾,什么重活都不让**,夜里轮流守夜。可我还是累。
身体累,心更累。走到一处破庙歇脚的时候,我突然肚子疼得厉害。血,顺着裤腿流了下来,
染红了身下的干草。我知道,孩子没了。我躺在冰冷的草堆上,咬着牙,没哭。
早就预料到的,不是吗?一路颠簸,惊惧交加,他怎么可能留得住。
只是……心里还是空落落的。像被剜掉了一块,冷风呼呼地往里灌。孩子没了之后,
我的身体好了些,却也彻底垮了。我们继续赶路,最后在一个偏远的江南小镇停下。
那里山清水秀,没人认识我们。我开始学着像个普通人一样生活。洗衣,做饭,缝补。
有一天,我照镜子。镜子里的人,脸色苍白,瘦得脱了形。更重要的是,我的脸上,
多了一道疤。是那天在火里被掉落的木柴划到的。从眼角,一直到嘴角。狰狞而丑陋。
我摸了摸那道疤,笑了。这样也好。再也没人能认出我了。9我在小镇住了下来。
给自己取了个新名字,叫阿言。开了家小小的布店,卖些自己织的粗布。日子过得很平淡。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镇上的人都很好,淳朴善良。没人问我的过去,
也没人在意我脸上的疤。有个姓温的郎中,叫温衍,人很温和。知道我一个女人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