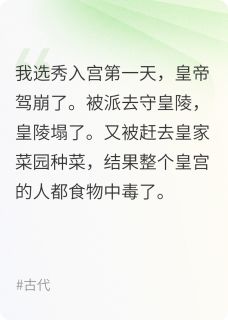
我叫沈菀,小名阿菀,今天是我选秀入宫的第一天。卯时不到就被嬷嬷们从炕上薅起来,
扒拉着穿上一身簇新的粉绿宫装,发髻上还别了支亮晶晶的珠花。
同屋的秀女们个个紧张得手心冒汗,我倒还好,啃着块桂花糕,
琢磨着御花园的牡丹该开了吧。引路的太监刚把我们领到太和殿前的广场,
还没等我看清金銮殿的龙纹有多气派,就听身后传来一阵惊天动地的哭嚎。
“陛下——驾崩啦——”我嘴里的桂花糕「啪嗒」掉在地上。周围的秀女们瞬间乱成一团,
有吓哭的,有当场跪地上的,还有个晕乎乎往回跑,差点撞翻捧着圣旨的公公。我愣在原地,
看着那支还在头上晃悠的珠花,突然觉得这宫里的日子,可能比我娘说的要**点。
皇帝驾崩,选秀自然是黄了。可我们这些已经进了宫的秀女,遣散回去不像话,
留在宫里又碍眼。内务府的公公们合计了三天,最后一拍板:去守皇陵!
于是我拎着个小包袱,跟着一群面如死灰的姐妹,坐了半个月的马车,到了远在京郊的皇陵。
皇陵这地方,依山傍水,风景倒是不错,就是太安静了,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我们的活儿也简单,每天给先帝的牌位擦擦灰,晨昏三炷香,剩下的时间就坐在石阶上发呆。
我这人闲不住,找了把小铲子,在陵寝后面的空地上种了些从家里带来的菜籽。
姐妹们都说我心大,这地方哪有心思种菜,我却觉得,总得有点绿颜色看着才舒坦。
菜籽刚冒出芽那天,出大事了。那天我正蹲在地里给菜苗浇水,忽然觉得脚下的地晃了晃。
起初我以为是自己蹲久了头晕,直到听见「咔嚓」一声巨响,转头一看,
差点把手里的水壶扔了——先帝陵寝的一角,塌了!不是小范围的掉几块砖,
是真真切切塌了个大洞,尘土飞扬的,看得人眼都直了。守陵的卫兵们疯了一样冲过去,
我们这些秀女吓得抱成一团。最后还是总领太监颤巍巍地让人快马加鞭回京报信,
临走前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什么灾星。我也委屈啊,我就浇个水,它自己塌的,
关我什么事?皇陵塌了,我们这些守陵的自然也待不住了。这次内务府没再合计,
直接把我扔去了皇家菜园。理由是,我不是爱种菜吗?那就去种个够!
皇家菜园可比皇陵热闹多了,大片大片的菜地,绿油油的看着就喜人。
园子里的老嬷嬷见我是新来的,还特意嘱咐:“姑娘啊,这菜是要供宫里贵人吃的,
可得仔细着,别让人祸祸了。”我拍着胸脯保证:“嬷嬷放心,我最会侍弄菜了!
”头几天确实顺顺当当,我除了浇水施肥,还跟园子里的老把式学捉虫。
那些啃菜叶的小青虫,被我捏起来能串成一串,看得旁边的小太监直捂嘴。
直到宫里来人要一批新鲜蔬菜,说是摄政王要宴请大臣。那天我起得格外早,
挑了最新鲜的小白菜、刚摘的黄瓜,还有一篮子顶花带刺的嫩茄子,
仔细打包好交给来取菜的太监。看着太监走远,我还挺得意,觉得自己种菜的手艺没白练。
结果当天下午,就有一队禁军气势汹汹地冲进了菜园。“谁是负责摘今天这批菜的?
”领头的校尉一脸杀气。我心里咯噔一下,怯生生地站出来:“是……是我。”“带走!
”我被捆着扔进马车的时候,还听见园子里的老嬷嬷在哭:“造孽啊!宫里传来信,
吃了今儿的菜,皇上太后还有各位大人,全、全食物中毒了!
”我:“……”我真的就只是捉了虫啊!那些虫我都扔去喂鸡了,没往菜里放啊!
再次被押到皇宫的时候,我腿都软了。从选秀第一天皇帝驾崩,到守皇陵皇陵塌了,
再到种个菜把全皇宫的人放倒,我觉得自己大概是史上最倒霉的秀女了。
这次没人再把我往犄角旮旯送,直接把我扔进了摄政王的书房。摄政王萧珩,是先帝的弟弟,
如今整个大启的江山都攥在他手里。我以前只远远见过一次,记得他穿着玄色蟒袍,
眉眼冷得像冰。我被按着跪在冰凉的青砖地上,一动不敢动。书房里静得可怕,
只能听见自己越来越响的心跳声。
一炷香过去了......两炷香过去了......我的膝盖从发麻到失去知觉,
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滴,滴在地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就在我怀疑自己是不是要跪死在这儿的时候,头顶终于传来一道低沉的声音,慢悠悠的,
听不出情绪:“汝甚好。”我懵了。好?我把先帝陵寝弄塌了,把全皇宫的人毒倒了,
这叫甚好?我迟疑地、弱弱地抬起头,刚好对上摄政王那双深邃的眼睛。
他嘴角似乎还噙着点若有若无的笑意,看得我心里直发毛。没等我想明白,
就听他又说:“像你这样的人才,不送去敌军和亲真是可惜了。”我:“???”等等,
这展开好像有哪里不对?!和亲?给那个据说凶神恶煞、打了三年仗没输过的北狄首领?
我看着摄政王眼里那点越来越明显的笑意,突然觉得,比起去和亲,
好像还是跪死在这儿比较划算?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像是有无数只被我捉过的小青虫在里面乱撞。和亲?
那不是书里写的、把公主或贵女打包送给敌国首领的玩意儿吗?
怎么就轮到我这个连皇帝面都没见过、克塌皇陵还毒倒一宫人的倒霉蛋了?
摄政王见我瞪着眼张着嘴,半天没反应,挑了挑眉,那抹笑意更明显了些:“怎么?你不愿?
”我这才回过神,膝盖像是突然找回了知觉,疼得我差点龇牙咧嘴。我赶紧把头埋得更低,
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王、王爷,臣女……臣女蒲柳之姿,笨手笨脚,
怕是、怕是会辱没了大启国威……”再说了,北狄首领要是知道我这丰功伟绩,
会不会以为大启是故意派个灾星过去祸祸他?到时候再打起来,我不成了千古罪人?
摄政王没立刻说话,我听见他翻动书页的声音,沙沙轻响,却比刚才的沉默更让人揪心。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慢悠悠道:“哦?你倒有自知之明。”我心里刚升起一丝侥幸,
就听他话锋一转:“正因如此,才合适。”我:“……”这是什么歪理!
“北狄首领骁勇善战,性子烈得像草原上的风,”摄政王的声音带着点漫不经心,
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前几日还派人来放话,说要娶个咱们大启最金贵的女子回去,
才算显他能耐。”我缩了缩脖子,心想那也该送个真正金贵的啊,送我去算怎么回事?
难不成摄政王是想告诉北狄:看,我们把最“特别”的给你了?
“可他要是知道我……”我实在忍不住,又小声嘟囔了一句,“我这运气,万一到了北狄,
他们的王帐塌了,牛羊全病倒了……”话没说完,就听见摄政王低低地笑了一声。
那笑声不像冷笑,倒像是真觉得好笑,震得我耳朵尖都发烫。“你倒坦诚。”他说,
“不过你放心,北狄的王帐是毡子做的,想必没皇陵那么不经塌。
至于牛羊……他们擅长牧养,许是比宫里的御厨更扛得住你的‘照料’。
”我:“……”这位摄政王,是不是把我当成什么有趣的玩意儿了?
正琢磨着怎么才能把自己这“人才”的帽子摘下来,就见摄政王放下了书,站起身。
玄色的衣袍扫过地面,带起一阵微凉的风。他走到我面前,停下了脚步。我不敢抬头,
只看见他皂色靴面上绣着的暗纹,精致得晃眼。“这事就这么定了。”他的声音就在头顶,
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三日后启程。去了北狄,好好‘待’着。”最后那两个字,
他说得格外轻,却让我后颈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我还想再挣扎一下,刚要开口,
就被他打断了:“你若不去,以你毒倒太后和众臣的罪过,此刻该在天牢里等着秋后问斩了。
去和亲,好歹还能换个郡主的名分,衣食无忧。”我瞬间闭了嘴。
天牢和和亲……好像确实后者稍微强那么一点点?虽然那个“衣食无忧”听起来也悬得很。
摄政王似乎满意了我的沉默,又道:“下去吧,让内务府给你准备些嫁妆。
别再惹出什么乱子,不然,就算北狄那边肯要你,本王也保不住你。
”我被太监们从地上扶起来的时候,膝盖已经麻得站不住,几乎是被半架着出去的。
路过内务府的时候,正好撞见几个公公在低声议论。“听说了吗?就是那个秀女,
把皇陵弄塌了,还毒倒了一宫的人!”“可不是嘛!现在好了,要被送去北狄和亲了!
”“啧啧,摄政王这是……把祸水往外引啊?”“嘘!小声点!不过说真的,
这姑娘要是去了北狄,北狄那边怕是要热闹了……”我:“……”“热闹?你们怕是不知道,
她能搞出来的热闹,可比你们想的要**多了。我怀疑她……”回到临时被安排的住处,
我看着内务府送来的一堆绫罗绸缎和金银珠宝,突然有点破罐子破摔的冲动。
选秀第一天皇帝驾崩,守皇陵皇陵塌,种菜毒倒全皇宫……再来个和亲对象出点什么事,
好像也不是不可能?我摸了摸头上那支从入宫第一天就没摘下来的珠花,它还亮闪闪的,
不知道是不是也在期待着北狄的“热闹”。三日后,我穿着一身大红的嫁衣,
被送上了去往北狄的马车。车窗外,摄政王站在城楼上,远远地望着。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只觉得那目光像是在看一件即将送往远方的、有趣的礼物。马车轱辘轱辘地驶离京城,
我掀开一点车帘,看着越来越远的城门,心里叹了口气。罢了罢了,去就去吧。
好歹北狄没有先帝的皇陵让我塌,也没有那么多贵人让我毒。
说不定……我还能在草原上种点菜籽?就是不知道,北狄的首领,抗不抗造啊?
马车走了半月,终于踏入北狄地界。草原的风带着沙砾,刮得车帘簌簌响,我掀帘看出去,
只见天高地阔,漫山遍野的牛羊像撒在绿毯上的碎珠,远处的毡房冒着袅袅炊烟,
倒比京城多了几分野趣。护送的将士递来一块硬邦邦的麦饼,我咬了一口,差点硌掉牙。
正对着麦饼发愁,就听外面传来一阵马蹄声,越来越近,最后停在马车旁。
“大启的新娘子到了?”一个粗嘎的声音响起,带着浓重的口音,“我们首领在前面等着呢。
”我心里咯噔一下,攥着麦饼的手紧了紧。掀帘下车时,
被眼前的景象惊得忘了动作——一群穿着兽皮、腰挎弯刀的北狄勇士围着马车,
个个高鼻深目,眼神像鹰隼似的锐利。而人群中间,一个骑着黑马的男人正望着我。
他穿着玄色皮袍,腰间系着镶金的腰带,长发用一根玉簪束起,脸上带着道浅浅的刀疤,
非但不狰狞,反倒添了几分悍勇。见我看他,他忽然咧嘴一笑,
露出两排白牙:“你就是大启送来的郡主?”我赶紧福了福身,
刚想按嬷嬷教的礼仪说几句客套话,就听他又道:“早听说大启的女子娇弱,看你这样子,
倒不像只会哭鼻子的。”这话让我愣了愣,抬头看他,他眼里没有轻蔑,反倒带着点好奇,
像是在打量什么新鲜物件。正想回话,突然听见“咔嚓”一声——他胯下的黑马不知怎么,
前蹄一软,竟直直跪了下去,把他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周围的北狄勇士瞬间惊呆了,
我也张着嘴,半天没合上。那首领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
看我的眼神突然多了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他盯着我看了半晌,
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有意思!果然是个特别的!”我心里却在哀嚎:不是吧?
刚见面就把人家坐骑给克了?这北狄首领,该不会现在就想把我送回去吧?
首领倒是没提送我回去的事,只是翻身从地上站起来时,看我的眼神里多了些探究,
像是在打量什么会自己蹦跶的稀罕物件。他拍了拍黑马的脖子,那马不知怎的,
刚才还蔫头耷脑,这会儿竟打了个响鼻,又晃晃悠悠站了起来,只是再看我时,
耳朵往后抿着,像是怕得很。“看来我的马比我懂规矩。”贺兰砚朝我伸出手,
掌心带着层薄茧,“我叫贺兰砚。跟我来吧,草原上的风比不得你们京城柔和,别冻着了。
”我迟疑着把手搭上去,被他一把拽下马车。他的力气极大,我踉跄了两步才站稳,
抬头时正撞见他眼里的笑意,倒比摄政王那藏着算计的笑直白多了。
北狄的王帐比我想象中宽敞,羊毛毡子层层叠叠搭起,里面铺着厚厚的兽皮,
角落里燃着个铜炉,暖烘烘的。贺兰砚让侍女给我端来碗热奶茶,奶香味混着点盐粒,
竟意外地顺口。“听说你在大启……很有名?”他捧着奶茶碗,眼睛亮晶晶地看我,
像是等着听故事的孩子。我一口奶茶差点喷出来,赶紧摇头:“没有没有,
我就是个普通秀女……”“普通秀女能让皇帝驾崩?”他挑眉,“还能让皇陵塌了?
连种菜都能毒倒一宫的人?”我:“……”合着我的丰功伟绩已经传到北狄了?
摄政王是生怕贺兰砚不知道他送了个什么“宝贝”过来吗?见我脸红得像块烧红的烙铁,
贺兰砚笑得更欢了:“别紧张,我觉得你这样挺好。我们北狄人不讲究那些弯弯绕绕,
有本事的人,不管是能打仗还是能……”他顿了顿,像是在找合适的词,“能搞出大动静,
都值得敬三分。”我怀疑他对“敬”这个字有什么误解,但看着他腰间那把闪着寒光的弯刀,
还是识趣地闭了嘴。傍晚时,贺兰砚带我去参加草原上的篝火宴。男人们围着篝火摔跤喝酒,
女人们唱着调子古怪的歌,烤肉的香气飘得老远。贺兰砚给我递来一块烤得油滋滋的羊肉,
我刚咬了一口,就听“哐当”一声——旁边一个正喝酒的壮汉手里的铜碗突然裂了道缝,
酒液顺着裂缝哗哗往下流。那壮汉愣了愣,低头看了看碗,又看了看我,突然“嗷”一声,
抱着头就往远处跑,边跑边喊:“邪门了!邪门了!”我:“……”手里的羊肉突然不香了。
贺兰砚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又转回来盯着我,
嘴角的笑意快绷不住了:“你这体质……还真是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啊。
”我尴尬地想把羊肉塞回他手里,他却按住我的手,
把自己那碗没动过的奶茶推过来:“吃吧,我这碗结实,摔地上都不会裂。”正说着,
就见篝火“噼啪”一声,不知怎的,火苗突然窜起老高,火星子溅了旁边的柴堆一脸,
竟把搭在旁边的晾肉架子给燎着了。众人手忙脚乱地扑火,贺兰砚却突然凑近我,
压低声音问:“你老实说,你是不是还会点别的?比如呼风唤雨什么的?
”我看着他眼里闪着的兴奋光芒,突然觉得这位北狄首领,好像比摄政王更不对劲啊?
我被他问得一怔,手里的羊肉差点掉在地上。呼风唤雨?我连自己什么时候能闯祸都算不准,
哪有这本事?“我……我就是运气不太好。”我喏喏地说,看着火苗被众人用沙土盖灭,
留下一地焦黑的木架子,脸颊烫得能煎鸡蛋。贺兰砚却显然不信,他挑眉打量我,
像是在看一块藏着玄机的奇石:“运气不好能让皇陵塌了?运气不好能毒倒一宫的人?阿菀,
你这运气,怕是比草原上的龙卷风还厉害。”他竟直接叫我的乳名,亲昵得让我有些不自在。
我正想辩解,
就见不远处几个正在鞣制兽皮的妇人突然尖叫起来——她们架在火上的铜锅不知怎么翻了,
滚烫的热水泼在刚鞣好的皮子上,原本油亮的皮毛瞬间缩成了一团。
那几个妇人瞪着地上的废皮,又齐刷刷转头看我,眼神里带着惊恐,像是见了什么洪水猛兽。
我:“……”我发誓,我连看都没往那边看啊!贺兰砚顺着她们的目光望过来,
嘴角的弧度压不住地往上翘,最后索性仰头笑出声,笑声在空旷的草原上荡开,
惊飞了头顶几只夜鸟。“罢了罢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不轻,“看来今晚不宜热闹。
走,我带你去看星星。”我被他拽着往山坡上走,身后传来众人如蒙大赦的吸气声。
夜风带着草香扑在脸上,倒比王帐里的铜炉更让人清爽。贺兰砚不知从哪儿摸出个酒囊,
递给我:“尝尝?我们北狄的马奶酒,烈得很。”我抿了一小口,
辛辣的暖意顺着喉咙往下滑,烧得五脏六腑都热起来。抬头时,
突然被头顶的星空惊住了——没有京城的宫墙遮挡,星星密得像撒了把碎钻,
银河清晰得仿佛伸手就能摸到,连风里都带着星光的味道。“好看吧?
”贺兰砚在我身边坐下,仰头灌了口酒,“你们京城看不到这个。”“嗯。”我点头,
心里的窘迫渐渐散了,“比宫里的琉璃灯好看多了。”他侧头看我,月光落在他脸上,
那道浅疤竟柔和了许多:“你在宫里,过得不开心?”我想起选秀那天掉在地上的桂花糕,
想起皇陵塌时漫天的尘土,想起被押到摄政王面前时膝盖的疼,
忍不住苦笑:“也不是不开心……就是太热闹了,有点扛不住。”贺兰砚低笑起来,
酒液顺着他的下颌线往下滑:“你倒是坦诚。不过你别怕,我们北狄人实诚,
你就算再弄塌几个毡房,毒死几头牛羊,我们也不会把你怎么样。
”我:“……”这安慰还不如不说。正想反驳,脚下突然晃了晃。
起初我以为是自己喝了点酒站不稳,
直到听见身后传来“轰隆”一声——我们刚才坐过的那块大石头,
不知怎么从山坡上滚了下去,砸在下面的空地上,裂成了好几块。
贺兰砚:“……”我:“……”夜风突然静了,连草叶摩擦的声音都听得见。他缓缓转头,
看向我的眼神里,兴奋和惊恐终于各占了一半。过了半晌,他才艰难地开口:“阿菀,
你……你刚才是不是踩那块石头了?”我僵硬地点了点头。他默默往旁边挪了挪,
拉开半臂远的距离,像是怕被我传染什么“霉运”。但过了会儿,又像是觉得不妥,
重新挪回来,只是表情严肃得像是在商量什么军机大事:“要不……咱们还是回王帐吧?
我怕再待下去,这山坡都得塌了。”我看着他难得一见的紧张模样,突然忍不住笑出了声。
月光下,他的耳朵悄悄红了,伸手挠了挠头,倒像是个被抓包的少年郎。原来北狄的首领,
也有怕的东西啊。贺兰砚被我笑愣了,随即也跟着笑起来,刚才那点紧张散了大半。
他抬手揉了揉我的头发,动作自然得像是做过千百遍:“笑什么?我说的是正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