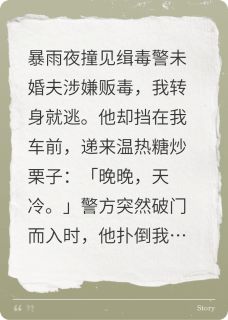
暴雨夜撞见缉毒警未婚夫涉嫌贩毒,我转身就逃。他却挡在我车前,
递来温热糖炒栗子:「晚晚,天冷。」警方突然破门而入时,
他扑倒我耳语:「别碰糖炒栗子,里面装了定位器!」下一秒,子弹穿透他胸膛。
醒来我假装失忆,忘掉他所有温柔陷阱。
直到在病房监控里看见——他强撑病体爬向我的轮椅,落下带血的吻:「别怕姜晚,
这次我一定让你亲手抓到我。」湿冷的雨水疯了似的抽打着挡风玻璃,
雨刮器开到最快也像蒙着一层流动的灰纱。路灯的光晕被砸得粉碎,
在积水的路面上胡乱流淌。我心里那股翻腾了一整晚的莫名烦躁,像被这鬼天气加了把火,
烧得太阳穴突突直跳。鬼使神差地,方向盘就往郊外那个废弃的老码头去了。
沈惟的越野车就停在那个地方。他电话里含含糊糊说所里有紧急任务,彻夜不归。
可心底有个声音在尖锐地叫嚣:不对!沈惟最近的状态像一张绷紧的弓,
看我的眼神复杂得能拧出水来,几次欲言又止,最后总是被一个突然响起的电话打断。
破旧的集装箱层层叠叠,铁锈的腥气混着咸湿的雨雾直往鼻子里钻。我熄了火,
车灯瞬间熄灭,整个人被浓重的黑吞没,只剩下雨水敲打车顶的鼓点。心跳却像失控的马达,
震得耳膜嗡嗡作响。手心里全是冷汗,我把车窗降下一条缝隙,
冰凉的雨水和带着海腥气的风一起灌进来。几道人影就在前面不远处。
车灯熄灭前的最后一瞥,死死烙在了脑子里。其中一个人侧对着我,身形高大挺拔,
是刻在骨头里的熟悉——沈惟。我的未婚夫,江城刑侦支队的副队长。一个缉毒警,
他本该在警局彻夜分析那些触目惊心的证据,将那些把生命当儿戏的渣滓绳之以法。
可他怎么会深更半夜在这里?他面前的两人像阴沟里的老鼠,身形佝偻在湿透的宽大外套里,
看不清脸。其中一个正把一个鼓鼓囊囊的黑色塑胶袋塞进沈惟怀里。动作隐蔽又透着熟稔。
嗡——世界瞬间失声。窗缝里漏进来的那句含糊对话,被风撕碎了,没飘进耳朵。
可我看见了动作!他收下了!“咳。”黑暗里传来一声压抑的干咳,惊雷一样炸开。
不是沈惟的咳嗽,也不是我的,像是……对面包厢旁的那人!那咳嗽声仿佛一个信号。“谁?
!”沈惟暴喝出声,厉如金石,猛地回头!
刺目的车灯光被他锐利的视线瞬间锁定——我暴露了!“呃!”我脑子一片空白,
身体的本能却比思维快,右脚已经重重跺在油门上!引擎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咆哮,
车轮疯狂空转,卷起漫天污水。沈惟脸色在车灯照耀下瞬间褪尽血色,惨白如纸。“姜晚!!
”他的嘶吼穿透狂暴的风雨,竟然没有丝毫犹豫,几个箭步就朝着我这个方向猛冲过来!
不是奔向他的“同伙”寻求掩护,而是迎着我疾驰的车头!“停车!姜晚!停下!”这疯子!
我想尖叫,喉咙却像被铁钳死死扼住。他像是不要命了,双臂大张,直直地挺立在车前!
湿透的警服紧贴在身上,勾勒出贲张的肌肉线条,雨水顺着他冷硬的侧脸线条淌下。
离得太近了,近到我能看清他眼底那片血色的红丝,像燃烧的火焰,
带着一种近乎绝望的力度。刹车太迟了,车头凶狠地顶了上去——沉闷的撞击声响起,
并不特别剧烈,但足够让前冲的庞然大物戛然而止!隔着沾满雨水的挡风玻璃,
他的身影摇晃了一下,却硬生生扎在原地。我惊魂未定,大脑宕机,手脚冰凉,
连牙齿都在打颤。他竟然还抬起了手,抹了把糊住眼睛的雨水,
然后径直走到我的驾驶位旁边。他用力扣响车窗。笃笃笃。车窗降下一条缝。他身体前倾,
手臂撑在窗框上,高大的身影带着巨大的压迫感几乎笼罩了整个窗框,
带着冰冷雨水的气息压近。一股熟悉的微甜焦香味道,热乎乎地钻进鼻腔。“晚晚,天冷。
”他的声音低沉微哑,带着一点喘息,和刚才那声撕心裂肺的吼叫判若两人。
他甚至……还扯了扯嘴角,像是想安抚地笑一笑。一只裹着油纸、冒着丝丝热气的糖炒栗子,
被他小心翼翼地从车窗缝隙塞了进来,稳稳当当地放在了我僵硬的手边。温热。
带着街头巷尾烟火气的熟悉温暖。这一刻的温情,像最恶毒的毒药!
巨大的荒谬感海啸般冲垮了我紧绷的神经。
震惊、恐惧、被愚弄的滔天怒火……我猛地抬头盯住他近在咫尺的脸,
试图从那双曾让我无数次沉溺其中的深邃眼眸里,找到一丝虚伪造作的痕迹,
或是……哪怕一丝一毫的难堪和解释?没有!除了那片刺目的红血丝,
那目光坦荡得令人心寒!他收下了那袋东西,他此刻塞给我一颗糖炒栗子!这算什么?
打完一巴掌再给颗糖吃?让我对他的罪恶视而不见?
还是……要把我这个唯一的目击者也拖下水?“沈……”我的嘴唇都在哆嗦,声音嘶哑难辨。
砰!砰!砰!话音被粗暴打断!车右前方集装箱的阴影里传来几声闷响!有人痛叫着倒下!
混乱的脚步声和撞倒金属物的刺耳摩擦声瞬间撕破雨幕!紧接着,
左前方沈惟身后的集装箱转角,猛地窜出两个黑影!动作快得像扑食的猎豹!“警察!别动!
”“趴下!全部趴下!”厉喝声如同惊雷炸响!几束强光手电齐刷刷刺破黑暗,
精准地锁定我们!刺目的光线交织,雨水在光柱中拉出绝望的银线。
巨大的声响仿佛直接在耳膜上炸裂!完了!被堵死了!
那两个老鼠一样缩在后排集装箱旁的身影惊恐地怪叫一声,拔腿就向码头边缘的江水里扎!
场面瞬间彻底失控!水花四溅,警方的脚步声急促而沉重地逼近,
手电光柱在破旧的集装箱、潮湿的地面和奔逃的身影上疯狂跳动切割,明暗交错,
每一道光影都像死神的镰刀挥舞!子弹破空的尖啸刺得人头皮发炸!我被困在车里,
方向盘上的指关节捏得发白,每一寸皮肤都能感知到那死神擦肩的冰冷战栗!
眼前一片兵荒马乱,所有声音都扭曲了,只感觉自己的心脏快要从喉咙里呕出来!“晚晚!
”又是一声嘶吼!近在咫尺!车门猛地被人从外面强行拉开!
一股浓重的雨水和铁锈的咸腥味扑面而来!一只冰冷、带着粗粝擦痕的手猛地扣住我的肩膀,
巨大的力道带着令人窒息的恐惧感,根本不容反抗!力道精准、不容置疑,
熟悉又陌生——是擒拿!他想干什么?抓我做人质?!那念头让我全身血液骤然结冰!
电光石火间,眼前天旋地转!我被那股蛮力硬生生从驾驶座上狠拽出来!
身体失控地往前扑倒!恐惧的尖叫卡在喉咙深处。预期的撞击地面的钝痛并没有传来。
一个炽热、带着熟悉松木香气的胸膛猛地迎了上来,精准地承接住我全部下坠的力量!
我被死死地、不顾一切地按进一个剧烈起伏的怀抱里!湿透的警服冰得刺骨,
但胸口之下那擂鼓般沉重急促的心跳,滚烫地烙印着我的脸颊。
混合着雨水、汗水的男性气息粗暴地将我淹没。他的手死死扣着我的后脑勺,
像是要把我摁进他的骨血里。这个拥抱带着一种绝望的禁锢!耳朵骤然一热!
他滚烫的嘴唇紧贴上来,带着濒死般的窒息感。压低的、被风雨冲得支离破碎的气声,
每一个字都像是被硬生生从喉咙深处抠出来,
重的血腥气和焦灼:“别…别碰糖炒栗子…里…里面有…有东西……定位器……”滚烫的唇,
冰冷刺骨的警告!糖炒栗子…定位器?!嗡!脑子像被重锤狠狠凿穿!
混乱的迷雾里仿佛骤然劈进一道惨白的电光!下一秒!“唔!
”沈惟高大的身躯猛地向下一沉!那一声痛苦至极的闷哼如同滚烫的烙铁,
狠狠烫在我与他紧贴的皮肤上,那声音就贴着我颈侧的脉搏发出,震得我灵魂都在颤栗!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他瞬间绷紧、继而剧烈痉挛的每一块肌肉!
那力道几乎要把我的肋骨也一起勒断!他搂着我的手瞬间收得死紧,指关节突出泛白,
像是在用尽生命最后的力量护住什么!温热的、粘稠的液体,
带着一种令人作呕的铁锈腥甜气息,毫无预兆地、汹涌地喷溅开来。我的侧脸,
我的脖颈皮肤,骤然被浸透、濡湿。温热的。带着生命流逝的温度。“沈惟——!!!
”凄厉到变调的嘶喊冲破喉咙,像垂死的困兽,劈开了漫天瓢泼的冷雨。
世界的声音瞬间远去,只剩下怀里身躯失重般下沉的钝感,
还有那片骤然扩散、带着刺目温度的猩红。刺眼的、带着消毒水冷硬味道的白光。
它像个固执的钩子,一下一下,不依不饶地撩拨着我厚重的眼皮。累。
浑身骨头像被重型卡车碾过一遍又一遍,连动一下手指都嫌费力。喉咙干得发痛,
像塞满了砂纸,每一次细微的吞咽都带着摩擦血肉的不适。眼皮沉重地黏在一起,
像被厚厚的胶水死死封住。“晚晚?晚晚?”一个熟悉又带着陌生哭腔的女声,
小心翼翼地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是堂姐姜蕊。“晚晚醒了!医生!医生!
”另一个声音像是隔着一层厚玻璃传来,是妈吗?她的手好像覆在我的手背上,
滚烫又颤抖。“……晚晚,听得到我说话吗?”是赵法医?声音压抑又紧绷。
眼皮终于被撬开一丝缝隙。雪白的天花板,悬着的点滴瓶,
还有几张凑得很近、写满焦虑和疲惫的脸。姜蕊的眼圈红肿,妈吗的头发乱糟糟的,赵法医,
沈惟的师姐,向来冷静的眼神里也蒙着一层阴翳。我转动了一下眼珠,视线迟钝地扫过她们。
最后,落到自己手臂上。盖着医院的薄被,被子下,腰腹处缠着厚厚的纱布,
每一寸活动都牵扯着深层肌肉尖锐的酸痛。是车祸撞的,
还是……当时被沈惟扯出来时撞在车上?我张了张嘴,想说话,喉咙却只有干涩的摩擦声,
吐不出清晰的音节。所有的疑问,所有的恐惧,所有的……那最后一片温热的猩红,
都像冰碴子卡在胸口,压得我无法呼吸。护士赶来了,小心地喂我喝了点温水。
温水流过的感觉像是在灼烧。“晚晚,”姜蕊的声音带了点试探,小心翼翼地,
像是怕惊走什么,“你……你记得是怎么出车祸的吗?”出车祸?我皱紧眉头,
努力地“回想”。脑子里的画面却是一片混乱的雪花噪点,
伴随着尖锐的耳鸣和剧烈的眩晕感。什么码头,什么雨夜,
什么沈惟……仿佛都被投入了一个巨大的、浑浊的搅拌机,
只剩下支离破碎的、毫无意义的彩色碎片。一片茫然。我缓慢地摇头,动作有些僵硬。
“那……”姜蕊喉咙滚动了一下,声音更轻了,“沈惟呢?记得他吗?”沈惟。
这两个字像两颗高速飞行的子弹,精准地射向大脑深处某个隐蔽的角落,
激起一阵尖锐到令人窒息的绞痛!“嘶……”我倒抽一口冷气,
脸上所有“努力回忆”的表情瞬间被一种生理性的痛苦取代。
太阳穴的神经像是被无形的手死死揪住,那痛感如此真实,像是被生生劈开了一道裂缝!
伴随着这剧烈的头疼,脑中属于沈惟的画面被强制唤醒,但内容却是一片令人惊悸的空白!
一片冰冷的、毫无感情的空白!那个名字,那张脸,此刻在我的感知里,
只剩下**源般的排斥!我的眉头死死拧紧,牙关紧咬,发出细微的声响。
一种来自生理本能的戒备和抗拒瞬间绷紧了全身的线条。“沈……惟?
”我试着重复这个名字,每一个音节都像是生锈的刀片在喉咙里刮过,
带着一种毫无伪装的、真实的陌生和探究困惑,“他……是谁?”声音嘶哑虚弱。
赵法医的目光锐利如手术刀,沉默地紧盯着我的反应。姜蕊和妈吗飞快地对视了一眼,
眼神复杂得难以言喻。“是你的未婚夫……”姜蕊艰难地吐出这几个字。我茫然地看着她,
眼睛里的疑惑几乎要满溢出来,仿佛在听一个完全不相干的、遥远而晦涩的词语。未婚夫?
这关系像一块冰冷的石头投入死水,
激不起我内心半点该有的涟漪——甜蜜、害羞、温暖……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荒芜的陌生。
“我们?”我的视线在姜蕊和妈妈惊疑不定的脸上缓缓移动,
又茫然地投向天花板角落某个不存在的点,“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每一个字都透着干涩、困惑。病房里陷入一片死寂。
只有监测仪器发出单调规律的滴答声。赵法医眉头锁得更深,眼底翻涌着复杂的情绪,
疑虑、忧虑……还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沉重。她终究没有继续追问沈惟的事。
“可能是脑震荡引起的逆行性遗忘,加上应激**。”赵法医的声音很低,
像在陈述一个沉重的结论,“车祸的冲击太剧烈。医生说了,情况……比较复杂。
”她顿了一下,目光沉重地扫过我毫无波澜的脸,“他伤得很重。还在ICU,
没脱离危险。”ICU……没脱离危险。这句话像一根冰凉的铁丝,
悄无声息地缠绕上我的心脏,缓慢地勒紧。但我脸上依旧只有那种劫后余生的茫然。
我努力地“回想”着那场所谓的车祸细节,
困惑:“车……我记得我是开车出去……然后……下雨……路很滑……”回忆艰难而破碎,
“后面……好像撞到了什么……然后……就到这里了。”细节像被飓风卷走的沙子,
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车祸框架。姜蕊赶紧点头:“对!就是车祸!
医生说你是严重的脑震荡还有腹腔软组织挫伤,万幸没有伤到头骨内脏!
就是…就是这记忆……”她担忧地看着我。“没事,”我疲惫地闭上眼睛,
好像用尽了所有力气,“慢慢……会想起来的吧。”声音微弱下去。之后几天,
支队和缉毒那边的人络绎不绝地来“慰问”我这个“意外卷入”、失忆了的“无辜未婚妻”。
询问被包装成“关心”,滴水不漏。那些面孔带着职业性的审视和试探,藏在关切的表象下。
“姜总监,当晚怎么会想到去那个废弃码头呢?”“车开那么快,
是看到了什么特别的情况吗?”“对撞上您未婚夫沈队长的车之前的事,
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了?”“那包……哦不,是说车祸现场散落的物品,看到什么没有?
”每一个问题都是带着倒刺的钩子。我躺在床上,像个被程序预设好的木偶,
脸上维持着那种劫后余生的虚弱和对未知的茫然恐惧,
……就觉得心里很闷……想开车出去透透气……”“雨太大了……看不清路……”“撞车前?
我……我头好痛……记不得了……”“……东西?什么散落的东西?
没……没印象……”每一次“遗忘”的应对,
都用尽全力调动脸上和肢体所有能展现困惑和疲惫的神经。脑震荡和失忆是最好的盾牌。
但每一次重复,眼前都无可救药地闪过最后那片温热的猩红,心口就被无声地凿开一个冰窟,
寒气蔓延到四肢百骸。一个礼拜后,腰上的伤好得七七八八,除了动作猛了还有隐痛,
已经不影响自由活动。但医生严肃警告,脑部情况仍需密切观察。
我终于被允许在堂姐的搀扶下,坐着护士推来的轮椅,去看一眼沈惟——在“所有人”眼里,
那个“深爱着我却不幸与我同遭车祸”的未婚夫。ICU厚重的玻璃墙像一道冰冷的银河。
沈惟躺在里面,离得很远。苍白。机器冰冷的线条环绕着他,
屏幕上跳跃的曲线和数字显示着他的生命微弱地起伏。氧气面罩遮住了大半张脸,
只露出紧闭的双眼和高挺的鼻梁轮廓。他的脸毫无生气,像个被抽空了灵魂的精致蜡像。
胸腔的微微起伏微弱到几乎不可察觉。
如果不是那些维系生命的管道和屏幕上固执闪烁的绿色小点,
让人很难相信这具躯壳下还残存着最后一丝活气。“医生说命是暂时抢回来了,
”赵法医低沉的声音在身旁响起,带着一种精疲力尽的沙哑,“肺部被子弹擦穿,
差点打中主动脉,感染关还没过……失血太多…”她深吸一口气,
“脑子也受了震荡……能不能醒,什么时候醒,不好说。
”后半句更像是在陈述一个残酷的事实。堂姐姜蕊捂着嘴,小声地啜泣起来。
我坐在轮椅上,目光隔着冰冷的玻璃,落在里面那张毫无知觉的脸上。陌生,无比的陌生。
那个会笑,会用低沉嗓音叫我晚晚,会把温暖手掌搭在我头顶的人,
被这片刺目的白彻底吞噬、抹去。心里空落落的,冷得像结了层厚厚的冰壳。没有爱,
没有恨,没有悲伤,只有一种尘埃落定后无边无际的疲惫和荒芜。
就像看着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陌生人躺在那里。护士推着我离开。
轮椅滚过光洁如镜的瓷砖地面,发出轻微的滚动声。
身后那片令人窒息的惨白和姜蕊压抑的抽泣声被抛远。直到深夜。
陪护的堂姐姜蕊已经在旁边的陪护床上睡沉了,呼吸均匀。
病房里只剩下监测仪的滴滴声和我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它在撞破了那道厚重玻璃墙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