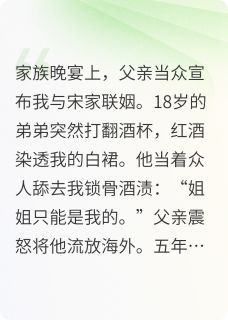
家族晚宴上,父亲当众宣布我与宋家联姻。18岁的弟弟突然打翻酒杯,红酒染透我的白裙。
他当着众人舔去我锁骨酒渍:“姐姐只能是我的。”父亲震怒将他流放海外。
五年后我婚礼当天,他开着直升机降落在教堂草坪。“姐姐的婚纱,只能由我亲手撕碎。
”他播放的录音揭露宋家阴谋时,父亲突然中风倒地。弟弟温柔拭去我眼泪:“现在,
整个沈氏都是你的。”我抚着他手腕疤痕:“包括你吗?
”他笑着撕毁股权文件:“我从来都是姐姐的私有财产。”1,
家族晚宴设在沈宅顶楼的花园露台,这里被精心布置成了城市上空悬浮的星河。
巨大的水晶吊灯从玻璃穹顶垂落,折射着下方无数细碎的光点,
那是宾客们杯中的香槟和女士们颈间的珠宝在窃窃私语。
空气里浮动着昂贵雪茄的醇厚、顶级香水的冷冽,
以及一种更为隐秘的东西——一种被金线织就的、名为“利益”的蛛网,
无声地笼罩着每一个衣冠楚楚的身影。我,沈清宁,穿着一条剪裁极简的象牙白绸缎长裙,
站在父亲沈兆麟身侧,像一件被精心擦拭后摆放在展柜里的瓷器。
脸上维持着恰到好处的微笑,眼神却空洞地掠过一张张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
他们的恭维、试探、奉承,如同背景噪音,嗡嗡作响,却无法真正侵入我的耳膜。
直到一只微凉的手,轻轻碰了碰我垂在身侧的手指。我微微一颤,侧过头。是清珩。
我的弟弟,沈清珩。刚满十八岁的少年,穿着一身合体的黑色西装,身姿挺拔如初生的青竹。
他站在我身边,位置比父亲更近一点。水晶灯的光落在他漆黑的发顶和过分精致的眉眼上,
那张继承了母亲所有优点的脸,此刻在璀璨光芒下,竟透出一种近乎妖异的俊美。
他嘴角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目光却沉静得像月光下的深潭,只映出我一个人的影子。
“姐姐,”他声音压得很低,带着少年人特有的清冽质感,
却又奇异地裹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累了?”他总能轻易捕捉到我细微的情绪变化。
我轻轻摇头,指尖却下意识地蜷缩了一下,将他触碰带来的那点凉意握进掌心。
这个动作细微得几乎无人察觉,却像投入深潭的石子,在他眼底漾开一圈极淡的涟漪。
父亲沈兆麟低沉威严的声音就在这时响起,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
瞬间压下了所有的嘈杂。“诸位,”他举起手中的酒杯,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我身上,
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掌控感,“今天,除了感谢各位赏光,沈某还有一件喜事要宣布。
”我的心猛地一沉,某种冰冷的预感顺着脊椎爬升。“小女清宁,与宋氏集团的宋哲远先生,
情投意合,”父亲的声音平稳无波,像是在宣读一份商业文件,“两家决定联姻,
婚期就定在下月初八。届时,还望各位亲朋赏脸,共襄盛举。
”“轰——”无形的声浪在露台上炸开。
惊讶、艳羡、探究、算计……无数道目光瞬间聚焦在我身上,像探照灯一样灼热。
我站在那里,感觉那件昂贵的白裙变成了冰冷的枷锁,勒得我几乎无法呼吸。情投意合?
多么可笑的谎言。我和宋哲远,那个眼神浑浊、传闻中私生活混乱的宋家独子,
仅仅在家族安排的宴会上见过寥寥数面。
这不过是一场**裸的、用我的婚姻去加固沈宋两家商业版图的交易。指甲深深陷进掌心,
带来一阵尖锐的刺痛,才勉强维持住脸上那摇摇欲坠的得体笑容。
我甚至不敢去看父亲的眼睛,那里面只有冰冷的算计和不容置喙的命令。就在这时,
一声清脆刺耳的碎裂声,如同冰锥,狠狠刺破了这片虚伪的喧哗。“啪嚓!
”我下意识地循声望去。是清珩。他手中的水晶高脚杯,不知为何竟脱手坠落,
狠狠砸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瞬间粉身碎骨。殷红如血的酒液如同泼墨般飞溅开来,
带着一种惊心动魄的艳色,不偏不倚,尽数泼洒在我胸前的白裙上。
冰冷的酒液迅速渗透薄薄的绸缎,黏腻地贴在我的皮肤上,带来一阵寒意。
雪白的衣料被染开一大片刺目的红痕,狼狈不堪。全场死寂。所有的目光,瞬间从父亲身上,
从我这件被毁掉的“展品”身上,齐刷刷地转向了肇事者——沈清珩。少年站在原地,
脸上没有任何闯祸后的惊慌失措。他甚至微微歪着头,那双漂亮得惊人的眼睛,
此刻像淬了寒冰的墨玉,直勾勾地盯着我胸前那片狼藉的红酒渍。那眼神,专注得近乎贪婪,
带着一种令人心悸的、野兽锁定猎物般的侵略性。父亲沈兆麟的脸色瞬间铁青,
额角的青筋隐隐跳动。
他显然没料到一向沉默寡言、甚至有些孤僻的小儿子会在这个关键时刻,
以如此激烈的方式打断他的“喜讯”。“清珩!”父亲的声音压抑着雷霆般的怒火,
“你在做什么?!”清珩像是没听见父亲的斥责。他动了。在所有人惊愕的注视下,
他旁若无人地向前一步,逼近我。
距离近得我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混合着少年气息的冷冽松香。他伸出手,骨节分明的手指,
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缓慢,轻轻拂过我锁骨边缘那片被红酒濡湿的冰凉肌肤。然后,
他低下头。温热、湿润的触感,带着一种不容抗拒的力道,印在了我的锁骨上。
他在舔舐那片酒渍。我的身体瞬间僵硬如石雕,血液仿佛在那一刻凝固。
周围响起一片压抑不住的抽泣声和低低的惊呼。时间被无限拉长。
他的舌尖带着一种近乎亵渎的专注,缓慢地、细致地描摹着那片被酒液染红的肌肤轮廓,
仿佛在品尝世间最珍贵的琼浆。每一次细微的移动,都像电流般窜过我的四肢百骸,
带来一阵阵无法抑制的战栗。那动作充满了占有欲,带着一种不顾一切的疯狂,
清晰地宣告着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他正在用最原始、最直接的方式,
抹去他人可能留下的痕迹,打上属于他的烙印。露台上的空气仿佛被抽干了,
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静和无数道惊骇的目光。他终于抬起头,唇边沾染着一抹妖异的红痕。
那双深不见底的黑眸,此刻清晰地映出我苍白失神的脸。他微微勾起唇角,
那笑容天真又残忍,声音不大,却清晰地穿透了凝固的空气,
砸在每一个人的耳膜上:“姐姐的这里,”他修长的手指,带着灼人的温度,
轻轻点了点那片被他“清理”过、此刻泛着不正常红晕的肌肤,一字一句,清晰无比,
“只能是我的。”“轰——”短暂的死寂后,是彻底的哗然!“天哪!他疯了?!
”“这……这成何体统!
”“沈家这小儿子……”震惊、鄙夷、嫌恶、猎奇……种种目光如同实质的针芒,
刺向场中央的我们。父亲沈兆麟的脸色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那是山雨欲来的暴怒,
整张脸涨成了猪肝色,胸膛剧烈起伏,指着清珩的手指都在颤抖。“逆子!
你这个不知廉耻的逆子!”他咆哮着,声音因为极致的愤怒而扭曲,“来人!
给我把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拖下去!立刻!马上!
”几个身着黑色西装的保镖迅速从人群外围挤了进来,面无表情地伸手去抓清珩的胳膊。
清珩没有反抗。他甚至没有再看父亲一眼,也没有看那些围上来的保镖。他的目光,
自始至终都牢牢地锁在我身上,像两道无形的绳索,将我紧紧捆缚。那眼神里没有恐惧,
没有慌乱,只有一种近乎偏执的专注和一种……奇异的平静。“姐姐,
”在保镖即将碰到他的前一秒,他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穿透所有喧嚣的力量,
清晰地传入我的耳中,“等我。”等我。只有两个字。却像两颗烧红的铁钉,
狠狠楔进我的心脏。一股尖锐的痛楚瞬间攫住了我,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
发不出任何声音。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保镖粗暴地架住胳膊,强行拖离露台。
他始终没有挣扎,只是固执地扭过头,那双黑沉沉的眼睛,隔着混乱的人群,
穿过无数道惊愕鄙夷的目光,依旧死死地钉在我身上。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通往楼下的入口,
那两道目光带来的灼热感,依旧烙印在我的皮肤上,滚烫得令人窒息。“清宁!
”父亲严厉的声音将我惊醒,“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换衣服!看看你像什么样子!
”我低下头,看着胸前那片刺目的、仿佛永远也洗不掉的暗红污渍,
感受着锁骨上残留的、那令人头皮发麻的湿濡触感,身体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起来。
像什么样子?我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是啊,我像什么样子?
一件被泼了污渍的、等待被清洗后再次摆上货架的……商品罢了。
露台上的喧嚣和议论声浪重新涌起,比之前更加嘈杂,像无数只苍蝇在耳边嗡嗡作响。
那些目光,或同情,或幸灾乐祸,或带着**裸的探究,如同芒刺在背。我挺直了脊背,
在父亲的逼视和众人无声的围观下,一步步走向通往休息室的侧门。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胸前那片冰冷的、黏腻的湿意,如同一个耻辱的烙印,提醒着我刚才发生的一切。
休息室里空无一人,只有冰冷的空气和巨大的落地镜。镜中的女人脸色惨白如纸,眼神空洞,
昂贵的白裙上那一片狼藉的暗红,像一朵糜烂的花,开在心脏的位置。锁骨上,
被他舌尖舔舐过的地方,皮肤仿佛还在隐隐发烫,带着一种诡异的、挥之不去的触感。
我拧开水龙头,冰冷的水流冲刷着手指,然后颤抖着覆上锁骨那片肌肤。用力擦拭,
皮肤被搓得发红、生疼,但那湿濡的、带着他气息的烙印感,却顽固地停留在神经末梢,
怎么也洗不掉。“等我。”那两个字,如同魔咒,在死寂的休息室里反复回响。等?怎么等?
父亲震怒之下,等待清珩的会是什么?流放?还是更严厉的惩罚?
他才十八岁……一种巨大的恐慌和无力感攫住了我。我猛地撑住冰冷的洗手台边缘,
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才勉强支撑住摇摇欲坠的身体。我不能倒下。至少现在不能。
门外传来父亲压抑着怒火的低吼,似乎是在处理后续的混乱。很快,有佣人小心翼翼地敲门,
送来了替换的礼服裙。我麻木地换上,是一条同样素净的月白色长裙,
却再也穿不出之前的从容。当我重新回到露台时,气氛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宋哲远,
我那位名义上的“未婚夫”,正端着酒杯,站在父亲身边,
脸上挂着一种混合着玩味和轻蔑的笑容。他看向我的眼神,不再是之前那种带着虚伪的欣赏,
而是毫不掩饰的审视和一丝……令人作呕的腥味,
仿佛在打量一件刚被人弄脏、又被匆匆擦拭过的货物。“清宁,
”父亲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他指了指宋哲远,“哲远特意过来关心你。
刚才的事,只是个意外,小孩子不懂事胡闹,别放在心上。婚期照旧。
”宋哲远适时地伸出手,脸上堆起虚假的关切:“清宁,你没事吧?清珩那小子,
真是被惯坏了,回头我让沈伯伯好好管教他。”他的手指试图搭上我的手臂。
我几乎是本能地后退了半步,避开了他的触碰。
这个细微的动作让宋哲远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眼底掠过一丝阴鸷。“我没事。
”我垂下眼睫,声音干涩,“谢谢关心。”父亲不满地瞪了我一眼,
显然对我的“不识抬举”感到恼火。但他没有发作,只是转向宋哲远,语气缓和地交谈起来,
内容无非是两家合作的项目以及婚礼的筹备。我像个局外人一样站在旁边,
听着他们讨论我的婚姻,我的未来,如同讨论一桩早已敲定的买卖。露台上的灯光依旧璀璨,
宾客们的谈笑声重新变得热烈,仿佛刚才那场惊世骇俗的闹剧从未发生。
只有我胸前那件新换的裙子,依旧冰冷地贴着皮肤,提醒着我,有什么东西,已经彻底碎裂,
再也无法复原。而清珩那句“等我”,像一颗投入深水的炸弹,在我心底掀起惊涛骇浪,
余波久久不息。2,那一晚之后,沈宅的气氛降到了冰点。清珩被连夜送走,
目的地是地球另一端的某个以管理严苛著称的寄宿学校。父亲没有给他任何辩解的机会,
也没有给我任何与他道别的可能。命令下达得冷酷而迅速,如同处理掉一件碍眼的垃圾。
我试图去找父亲,想为清珩求情,哪怕只是减轻一点惩罚。但父亲的书房门紧闭,
管家面无表情地拦在门外:“大**,老爷吩咐了,任何人都不见。
尤其是……关于小少爷的事。”“他是我弟弟!”我声音发颤,带着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尖锐。
管家眼神毫无波澜:“老爷说,从今往后,您只有一个身份,就是宋家未来的少奶奶。
其他的,不该您操心,也请您……忘掉。”忘掉?我踉跄着后退一步,靠在冰冷的墙壁上。
忘掉那个从小跟在我身后,用软糯声音喊我“姐姐”的孩子?忘掉那个在母亲病榻前,
紧紧抓着我的手,把眼泪蹭在我衣襟上的少年?忘掉那个在露台上,
用最惊世骇俗的方式宣告占有,然后对我说“等我”的……疯子?
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痛得无法呼吸。父亲的手段远不止于此。
他冻结了我名下所有的个人账户,收走了我的护照和身份证件,
甚至将我身边用了多年的、可能对清珩抱有同情心的佣人全部调离。取而代之的,
是几个沉默寡言、眼神锐利的中年妇人,她们寸步不离地“照顾”着我,
更像是在执行严密的监视。我的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在沈宅和几家指定的高级会所。
每一次外出,都有人“陪同”。手机被检查,通讯被监听。
我彻底成了一只被拔去羽翼、囚禁在金丝笼里的鸟,唯一的使命,
就是等待那场被安排好的婚礼。宋哲远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的“活动”中。
他带着一种施舍般的优越感,送我昂贵的珠宝,带我去顶级的餐厅,
在旁人面前扮演着深情款款的未婚夫角色。但私下里,他的眼神越来越露骨,
言语间的轻佻和试探也日益明显。“清宁,你那个弟弟……啧,真是可惜了那张脸。
”一次晚餐后,他借着酒意,手指有意无意地划过我的手背,语气带着恶意的揣测,“你说,
他是不是对你……有点什么不该有的心思?难怪沈伯伯要把他送那么远。”我猛地抽回手,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强忍着才没有当场吐出来。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用疼痛提醒自己保持冷静。“哲远,”我强迫自己抬起头,迎上他那双浑浊的眼睛,
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清珩是我弟弟,他只是年纪小,一时冲动。父亲已经处理好了。
请你,不要再说这些没有根据的话。”宋哲远嗤笑一声,靠回椅背,晃着杯中的红酒,
眼神像毒蛇一样黏腻:“行,我不说。反正……”他拖长了语调,意有所指,
“他也回不来了。以后,你只需要想着我就好。”回不来了?
这四个字像冰锥一样刺进我的心脏。我猛地攥紧了拳头,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不。
他一定会回来。那个在露台上,用最疯狂的方式宣告“姐姐只能是我的”的少年,
那个被拖走时依旧固执地对我说“等我”的弟弟……他绝不会就这样消失。这个念头,
成了支撑我在这令人窒息的金丝牢笼里活下去的唯一信念。3,时间在煎熬中缓慢流逝。
我变得异常沉默,像一个精致的人偶,配合着父亲和宋家的一切安排。试婚纱,定菜单,
拍婚纱照……我麻木地完成着每一项流程,脸上挂着练习了千百遍的、标准而空洞的笑容。
只有在夜深人静,当监视的佣人退到外间,我才能卸下所有伪装,蜷缩在冰冷的床上。
黑暗中,我一遍遍回想清珩最后看我的眼神,回想他舌尖的温度,
回想那两个字——“等我”。那不再是简单的承诺,而是我灵魂深处唯一的火种,
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微弱地燃烧着。我开始不动声色地留意。
留意父亲和宋哲远谈话时泄露的只言片语,留意财经新闻里关于沈宋两家合作的动向,
留意任何可能来自大洋彼岸的、极其微弱的信号。我知道清珩被送去的学校管理极其严格,
几乎与世隔绝。但我更知道,我的弟弟,从来就不是一个会坐以待毙的人。
他有着远超年龄的冷静和……近乎可怕的偏执。我等待着。像一个在沙漠中跋涉的旅人,
固执地守望着海市蜃楼中那一点微光。哪怕那光,最终会将我焚烧殆尽。五年。
两千多个日夜,在沈宅这座华丽坟墓般的寂静里,在宋哲远日益不加掩饰的轻慢与掌控中,
缓慢而沉重地流淌过去。我像一株被抽干了水分的植物,
外表维持着豪门千金应有的优雅与光鲜,内里却早已干涸枯萎。
象牙白的婚纱挂在衣帽间最显眼的位置,繁复的蕾丝和璀璨的碎钻在灯光下熠熠生辉,
却只让我感到一种冰冷的讽刺。4,明天,就是婚礼。今夜,沈宅灯火通明,
佣人们脚步匆匆,进行着最后的准备。空气里弥漫着鲜花和香氛的味道,甜腻得令人窒息。
父亲的书房门紧闭着,里面隐约传来他和宋哲远压低的笑谈声,
内容不外乎是婚礼后的某个大型并购项目。我独自站在三楼的露台上,
夜风带着凉意吹拂着单薄的睡裙。远处城市的霓虹连成一片模糊的光海,
喧嚣被距离过滤成一片沉寂的底噪。五年前那个混乱的夜晚,清珩就是从这里被拖走的。
“等我。”那两个字,早已融入我的骨血,成为支撑我呼吸的唯一动力。可五年了,
杳无音讯。父亲的手段滴水不漏,那座寄宿学校如同铜墙铁壁。
我动用了一切我能想到的、极其有限的方式去打听,得到的回复永远是“一切正常”。
他真的能回来吗?在父亲和宋家如此严密的掌控下?一个冰冷的声音在心底响起:或许,
父亲是对的。他回不来了。那个惊鸿一瞥的少年,早已被时间和距离碾碎,
消失在大洋彼岸的某个角落。绝望如同冰冷的潮水,一点点漫过心脏。“大**,
”身后传来佣人刻板的声音,“宋先生来了,在楼下客厅等您。”宋哲远?这么晚?
我蹙了蹙眉,压下心底翻涌的厌恶,转身下楼。客厅里,宋哲远靠坐在沙发上,
手里把玩着一个打火机,发出“咔哒、咔哒”的轻响。他穿着休闲,头发微乱,
身上带着明显的酒气。看到我下来,他抬起眼皮,眼神放肆地在我身上扫视了一圈,
带着一种令人不适的占有欲。“清宁,”他开口,声音有些含混,“明天你就是我老婆了。
”我没有接话,只是在他对面的沙发坐下,保持着距离。他似乎并不在意我的冷淡,
自顾自地说下去:“沈伯伯刚跟我确认了,城东那块地,婚礼一结束就签合同,记在你名下,
算是给你的聘礼。”他顿了顿,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当然,
也是我们宋家进入那个项目的敲门砖。”又是交易。我的婚姻,从头到尾,
都只是一场精心包装的商业筹码。“嗯。”我淡淡应了一声,垂下眼睫。宋哲远忽然站起身,
摇摇晃晃地朝我走来。浓重的酒气扑面而来。他俯下身,双手撑在我沙发两侧的扶手上,
将我困在他的气息范围内。“清宁,”他凑得很近,呼吸喷在我的耳廓,
带着令人作呕的热气,“五年了……你那个好弟弟,怕是骨头都烂在那边了吧?嗯?
”我的身体瞬间绷紧,指甲狠狠掐进掌心。他满意地看着我瞬间苍白的脸色,
笑容更加恶劣:“别想了。沈清珩?呵,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疯子,
早就被沈伯伯收拾得服服帖帖了。以后……”他伸出手,
带着薄茧的手指轻佻地想要触碰我的脸颊,“你只要乖乖做我的宋太太,
伺候好我……”在他的手指即将碰到我的前一秒,我猛地侧头避开,霍然站起身。“宋哲远!
”我声音冰冷,带着压抑不住的颤抖,“请你自重!明天才是婚礼!
”他被我激烈的反应弄得一愣,随即恼羞成怒,脸色阴沉下来:“沈清宁!你别给脸不要脸!
你以为你还是什么冰清玉洁的大**?你弟弟当年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闭嘴!
”我厉声打断他,胸口剧烈起伏,五年前那晚的屈辱和愤怒如同岩浆般喷涌而出,“滚出去!
”宋哲远眼神阴鸷地盯着我,像一条被激怒的毒蛇。他猛地抬手,似乎想做什么,
但最终只是狠狠啐了一口,转身大步离开,将客厅的门摔得震天响。
巨大的关门声在寂静的宅邸里回荡。我站在原地,浑身冰冷,控制不住地颤抖。
不是因为害怕宋哲远,而是因为他的话像淬毒的刀子,精准地捅进了我最深的恐惧里。
清珩……他真的……回不来了吗?这个念头一旦滋生,就如同藤蔓般疯狂缠绕,
勒得我几乎窒息。支撑了我五年的信念,在这一刻摇摇欲坠。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卧室,
反锁上门,背靠着冰冷的门板滑坐在地毯上。月光透过巨大的落地窗洒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