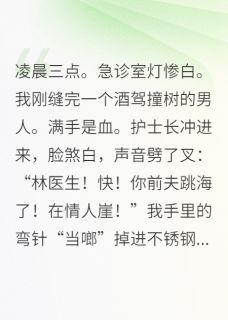
凌晨三点。急诊室灯惨白。我刚缝完一个酒驾撞树的男人。满手是血。护士长冲进来,
脸煞白,声音劈了叉:“林医生!快!你前夫跳海了!在情人崖!
”我手里的弯针“当啷”掉进不锈钢盘。声音刺耳。“谁?”我听见自己问。干巴巴的。
“季崇州!你前夫!季崇州!”护士长急得跺脚,“刚捞上来!送咱们这儿抢救了!
”季崇州。这名字像根生锈的钉子,猛地楔进我脑子。钝痛。他跳海?为我?殉情?放屁。
我和他,五年前就完了。离得干干净净。他搂着新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样子,
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那种人,舍得死?血也顾不上洗。我扯下口罩就往抢救室冲。
走廊冰冷,消毒水味呛人。拖鞋拍在地上,啪啪响。像打在我自己脸上。抢救室门口堵着人。
黑压压一片。闪光灯噼里啪啦。记者。季崇州大小算个名人,本地青年才俊,科技新贵。
他跳海,是条大新闻。“让开!”我吼。嗓子眼发紧。人群裂开条缝。我挤进去。
看见担架床推进来。上面的人,湿透了。头发贴在惨白的额头上。嘴唇发紫。闭着眼。
是季崇州。**是他。他秘书小陈哭得眼睛肿成桃,扑过来抓住我胳膊:“林医生!
林医生你救救季总!他…他都是为了你啊!他看见你的讣告就疯了!”讣告?
我脑子里嗡一声。对了。上周老家山体滑坡,死了几个人。有具无名女尸,
身形年龄和我差不多。我爸妈年纪大,又久没我消息,接到通知就以为是我,
哭天抢地给我办了个葬礼,还登了报。这事我知道。没吱声。我和季崇州离婚后,
几乎断了所有联系。我换了城市,换了医院,换了手机号。就想彻底抹掉过去。那讣告,
估计是他手下哪个“忠心耿耿”的,翻旧报纸翻到了,献宝似的捧给他看。他信了?还跳海?
抢救室里忙成一团。心肺复苏。插管。电击。监护仪滴滴乱叫。我站在门口。像个局外人。
手上还沾着别人的血,干了,黏糊糊的。我看着里面那个被电击得身体弹起的男人。
我的前夫。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只觉得荒谬。主刀的刘主任出来,满头汗,看我一眼,
摇摇头又点点头:“命保住了。但人还没醒。肺部感染严重,脑缺氧时间不短,
后续…不好说。”我点点头。连“谢谢”都懒得说。跟我有什么关系。记者的话筒又捅过来。
“林医生!季总殉情未遂,您现在什么感受?”“季太太!哦不,林医生!
季总对您真是情深似海啊!”情深似海?我差点笑出声。喉咙里一股铁锈味。
我拨开那些烦人的话筒,声音冷得像冰:“我不是季太太。早离了。他跳不跳海,是他的事。
与我无关。”说完,我转身就走。一步都不想多待。身后炸开了锅。“听见没?这么绝情?
”“啧啧,心真硬啊……”硬?我扯了扯嘴角。五年前他搂着那个叫苏曼的女人,
在我精心布置的家里滚床单,被我撞破时,他眼神比我还冷。他说:“林窈娘,
你看看你自己,跟块木头似的,有意思吗?”那时候,我的心就死了。死得透透的。
我请了假。把自己关在租的小公寓里。窗帘拉得死死的。外面铺天盖地都是新闻。
“科技新贵季崇州为前妻殉情未遂!情痴人设不倒!”“独家探访!
季崇州病房外日夜守候的痴情前妻!”配图是我那天在抢救室门口冷着脸的照片。角度刁钻,
看着倒真像在担忧守候。真能编。手机快被打爆了。陌生号码。老同学。
甚至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都是来“慰问”的,顺便旁敲侧击打听八卦。我直接关机。
世界清静了。三天后。门被敲响。很急。我以为是房东催租。不耐烦地拉开条缝。
外面站着季崇州的妈。我以前的婆婆,周美云。几年不见,她老了很多,头发白了大半,
脸上精致的妆容也盖不住憔悴。她身后跟着个穿黑西装的男人,拎着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
像是助理。“妈?”我下意识叫出口,随即改口,“周阿姨。”声音干涩。
周美云眼圈瞬间红了。她没像以前那样挑剔地打量我的穿着和这寒酸的出租屋,
反而一把抓住我的手。她的手冰凉,抖得厉害。“窈娘…窈娘啊!”她声音哽咽,带着哭腔,
“阿姨求你!去看看崇州吧!求你了!”我下意识想抽回手。她抓得更紧,
指甲几乎掐进我肉里。“他醒了…可他不认人!不说话!医生说是创伤后应激障碍!
他…他就认得你啊窈娘!”她眼泪掉下来,烫在我手背上,“他昏迷的时候,
一直喊你的名字!喊得撕心裂肺啊!阿姨求你了!你就去看他一眼!就一眼!
说不定…说不定他就好了!”助理在一旁帮腔,语气沉重:“林**,
季总这次…打击太大了。心理医生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您,可能唤醒他。
”我看着她哭得红肿的眼睛,听着助理恳切的话。心口那块早就冷硬的地方,
似乎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不疼。但有点闷。季崇州。他也会崩溃?
也会像个无助的孩子一样喊我的名字?那个永远意气风发、视感情为玩物的季崇州?
鬼使神差地。我点了点头。声音轻得像叹息:“行吧。我去看看。”周美云像抓住救命稻草,
连声道谢。助理立刻递过来一个厚厚的牛皮纸文件袋。“林**,这是季总的一些私人物品。
在他跳海前,他…他一直贴身带着。或许,您带去,对他有帮助。”助理眼神有点躲闪。
我没多想,接了过来。有点沉。高级私立医院。顶层VIP病房。
空气里弥漫着昂贵的香氛味,盖过了消毒水。我推开病房门。脚步很轻。
季崇州靠在巨大的病床上。穿着蓝白条纹病号服,显得异常单薄。他瘦了很多,
脸颊凹陷下去,下巴冒出青色的胡茬。曾经那双总是带着点戏谑和算计的桃花眼,
此刻空洞地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像个被抽走了灵魂的精美木偶。周美云跟在我后面,
小声抽泣:“崇州,你看谁来了?窈娘来看你了!”他毫无反应。眼珠都没动一下。
我走到床边。离他半米远。看着他这副样子,心里那点闷胀感又来了。不是心疼。
就是…有点陌生。有点堵。“季崇州。”我叫他。声音不高。他依旧没动。我沉默了几秒。
想起助理给的文件袋。打开。里面东西不多。一个旧手机,屏幕碎了。
一个泡了水、皱巴巴的皮夹。还有…一个更小的,密封的防水袋。我拿出那个防水袋。
透明塑料膜里,静静躺着两样东西。一张泛黄的拍立得照片。是我和他。大学刚毕业那会儿,
在学校的操场上。我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和格子衬衫,笑得没心没肺,眼睛弯成月牙。
他搂着我的肩,下巴搁在我头顶,眼神亮得惊人,满满都是少年人的得意和爱恋。照片背面,
是他龙飞凤舞的字迹:“林窈娘专属。季崇州。2009年夏。”另一件东西,
让我的呼吸骤然停了一拍。一枚戒指。很素净的铂金圈。
内圈刻着细小的字母:L&JForever。不是我们结婚时那对昂贵的钻戒。
是我们刚毕业,穷得叮当响时,他在地摊上花五十块钱买的情侣对戒。我的那枚,
离婚时被我扔进了护城河。他留着这个?还放在防水袋里贴身带着?
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又酸又胀,还有点喘不上气。我捏着那个小小的防水袋,
指尖冰凉。就在这时,病床上那个一直像雕塑般的人,眼珠极其缓慢地转动了一下。视线,
一点一点,艰难地聚焦在我脸上。然后,他干裂的嘴唇,极其轻微地翕动了一下。
发出一个模糊破碎的音节。“…窈…娘?”声音嘶哑,轻得像羽毛。却像一颗石子,
猛地砸进我死水一潭的心湖。周美云捂住嘴,喜极而泣:“他认出来了!他认出来了!崇州!
是窈娘!是窈娘啊!”季崇州的眼睛死死盯着我。那空洞里,似乎有了一点微弱的光,
像风中残烛。他费力地抬起没打点滴的那只手,颤抖着,一点点朝我伸过来。似乎想碰碰我,
确认是不是真的。我看着那只苍白瘦削的手。看着他那双盛满了脆弱和迷茫的眼睛。
看着他病号服下露出的、因心肺复苏而留下的大片淤青。脑子里一片空白。我该怎么做?
像他当年甩开我那样,冷漠地转身就走?还是……我僵在原地。身体里像有两个人在撕扯。
一个在冷笑:别信!他装的!当初怎么对你的忘了?另一个却在低语:他跳海了,差点死了,
还留着这张破照片和这破戒指……那只手还在固执地伸着,抖得越来越厉害。
他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像破旧的风箱。鬼使神差地。我向前挪了一小步。极其缓慢地,
抬起手。指尖,轻轻碰触到他冰冷的指尖。那一瞬间,季崇州像触电般猛地一颤。随即,
他那只手猛地用力,死死攥住了我的两根手指!力气大得惊人,
完全不像一个刚从鬼门关回来的人!他抓得太紧,指甲几乎抠进我的皮肉。我痛得皱了下眉,
想抽回手,却被他更用力地攥住。他看着我,眼睛里的光剧烈地闪烁着,
恐惧、依恋、还有某种近乎绝望的哀求,混杂在一起,汹涌而出。嘴唇哆嗦着,
反复地、无声地念着我的名字。周美云在一旁哭得更凶了,一边哭一边念叨:“好了好了,
认出来了就好!窈娘,你多陪陪他!多陪陪他!”我被他攥着手指,动弹不得。
看着他这副完全失控、脆弱到不堪一击的模样。心里那堵冷硬的墙,
好像被什么东西凿开了一道细小的裂缝。很烦。但又有点…说不出的滋味。接下来的几天,
我像被绑在了医院。周美云几乎是把我按在了季崇州病房的陪护椅上。
理由冠冕堂皇:只有我在,他才能安静下来,配合治疗。我一走,他就开始焦躁,拔针头,
甚至试图下床,喉咙里发出困兽般的呜咽。心理医生也在一旁敲边鼓,
说我是他目前唯一的精神锚点,强行离开可能导致病情恶化。我看着季崇州。
他大部分时间很安静,只是固执地攥着我的手腕,或者衣角,像个怕被丢弃的孩子。
眼神空洞,偶尔会聚焦在我脸上,定定地看一会儿,然后又茫然地移开。偶尔,
他会突然惊醒,浑身冷汗,惊恐地四处张望,直到看到我还在旁边,才会慢慢平静下来,
更紧地抓住我。我成了他的一根救命稻草。一个安抚他PTSD情绪的人形抱枕。这种感觉,
荒谬又憋屈。助理来过几次,毕恭毕敬地送来换洗衣物和一些生活用品。每次欲言又止。
终于有一次,在病房外的走廊,他叫住了准备去打热水的我。“林**,”他压低声音,
神色凝重,“有件事…我觉得您应该知道。”我停住脚,看着他。
“季总跳海…可能不完全是…因为看到您的讣告。”他斟酌着词句,“那几天,
公司出了很大的问题。审计组突然进驻,查得很严。有几笔账…对不上。数额巨大。
季总那几天压力非常大,整夜整夜睡不着,烟抽得很凶。”审计?账对不上?我心头一跳。
季崇州的公司这几年发展迅猛,摊子铺得很大。资金链要是出问题……“而且,
”助理的声音压得更低,带着点犹豫,“就在他出事前一天…有人给他寄了东西。
”“什么东西?”“一些…照片。”助理眼神闪烁,“是…是您和…苏曼**的。
”我愣住了。我和苏曼的照片?那个当初插足我们婚姻、后来被季崇州玩腻了甩掉的女人?
“照片内容…不太好。”助理含糊地说,“像是合成的,但看着…很真。寄件人匿名,
查不到。季总看到后,当场就把办公室砸了。然后…第二天就…”助理没再说下去。
意思很明显了。季崇州跳海,那则讣告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前面,
还有公司濒临崩盘的重压,和那些足以让他身败名裂的“照片”**。殉情?
或许有那么一点点成分。但更多的,恐怕是走投无路下的崩溃和逃避。一个懦夫的选择。
我心里那点因他脆弱而滋生的、极其微弱的酸软,瞬间被冰冷的讽刺取代。果然。
狗改不了吃屎。他季崇州,骨子里还是那个自私自利、遇到麻烦就想躲的**。
助理看着我瞬间冷下去的脸色,叹了口气:“林**,我知道您恨季总。但…他现在这样,
公司群龙无首,审计那边步步紧逼,还有那些照片…一旦流出去,后果不堪设想。
季总…他可能真扛不住第二次打击了。”他顿了顿,带着恳求,“就当…看在以前的情分上?
或者,看在他妈妈那样求您的份上?您…多担待几天?等他稍微稳定点?”我没说话。
拎着空热水壶,转身走向开水间。心里一片烦乱。回到病房。季崇州正不安地扭动着,
眼睛在房间里搜寻,看到我进来,立刻安静下来,目光紧紧追随着我。我走到床边,
他立刻伸出手,准确地抓住了我的衣角,攥在手里。力道很轻,带着小心翼翼的依赖。
我看着他那张苍白脆弱的脸。看着他眼底深处无法掩饰的恐惧。
看着他像个无助的雏鸟一样依附着我的衣角。恨意翻涌。夹杂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怜悯?
周美云端着一碗温热的粥进来,看到这情景,眼圈又红了,小声对我说:“窈娘,
辛苦你了…喂他吃点吧?他听你的。”我面无表情地接过碗。拿起勺子。舀起一点白粥,
递到他嘴边。季崇州乖乖地张开嘴。眼神一直没离开我的脸。温顺得不像他。粥喂到一半。
病房门被猛地推开。一个穿着红色紧身裙、妆容艳丽的女人冲了进来。是苏曼。几年不见,
她身上的风尘味更重了。她一进门,目光就死死钉在季崇州攥着我衣角的手上,
眼神像淬了毒的刀子,狠狠剜了我一眼。“崇州!”她娇滴滴地喊了一声,
扭着腰就要扑到床边。季崇州像是被这尖锐的声音和刺鼻的香水味吓到了,身体猛地一缩,
下意识地往我这边靠,攥着我衣角的手收得更紧,喉咙里发出抗拒的呜咽声。苏曼扑了个空,
脸上的笑容僵住,随即转为愤怒。她瞪着我,声音拔高:“林窈娘?你怎么还有脸在这里?!
都是你!要不是你那个假死的破讣告,崇州怎么会跳海?他现在这样,都是你害的!
”她的声音又尖又利。季崇州明显更害怕了,整个身体都开始发抖,拼命往我身后缩,
攥着我衣服的手指关节都泛白了。“出去。”我放下粥碗,声音不大,但很冷。
“你让我出去?你算什么东西!”苏曼气急败坏,指着我的鼻子骂,“一个早就下堂的前妻!
崇州现在需要的是我!是我一直陪着他!他公司出事,是我在帮他周旋!你懂什么?
你除了害他还会干什么?”她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几乎喷到我脸上。季崇州抖得更厉害了,
呼吸急促,眼神涣散,像是陷入了某种可怕的回忆。“我说,出去。”我站起身,
挡在季崇州前面,直视着苏曼喷火的眼睛,“他现在受不得**。你再在这里嚷嚷,
我叫安保了。”“你叫啊!”苏曼有恃无恐地尖叫,“你以为我怕你?我告诉你林窈娘,
别以为崇州现在不清醒你就能趁虚而入!他清醒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副假清高的样子!
他……”她的话戛然而止。因为一直蜷缩在我身后发抖的季崇州,突然抬起头。
他死死盯着苏曼,眼神不再是空洞和恐惧,
而是翻涌着一种极其陌生的、冰冷的、近乎暴戾的凶光!
他猛地抓起我放在床头柜上的那个不锈钢保温杯——里面还有大半杯热水——用尽全身力气,
狠狠朝苏曼砸了过去!“滚!!!”一声嘶哑的咆哮,像受伤野兽的怒吼,炸响在病房里!
保温杯擦着苏曼的耳朵飞过去,“哐当”一声砸在她身后的墙上,热水和茶叶泼溅开来,
弄脏了雪白的墙壁和她昂贵的裙子。苏曼吓得魂飞魄散,尖叫一声,脸都白了,
惊恐地看着状若疯狂的季崇州。“滚出去!不许…骂她!”季崇州胸膛剧烈起伏,喘着粗气,
眼睛血红,像要择人而噬,死死瞪着苏曼,那只没打点滴的手还紧紧攥着我的衣角,
力道大得要把布料撕碎。整个病房死寂一片。只有季崇州粗重的喘息声。苏曼吓得腿都软了,
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惊恐地看了季崇州一眼,又怨毒地剜了我一眼,
狼狈地踩着高跟鞋,“噔噔噔”地跑了。周美云也被儿子的反应吓傻了,捂着心口,
脸色发白。我站在原地。
后背能清晰地感受到季崇州身体剧烈的颤抖和他攥着我衣服那近乎痉挛的力道。
心里那点冰冷的讽刺,被刚才他那一声充满保护欲的嘶吼,撞得支离破碎。他…在保护我?
用这种近乎自毁的方式?我慢慢转过身。季崇州眼中的暴戾和血红正在急速褪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更无助的恐惧和茫然。他看着我,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又像是怕极了我会消失。他松开我的衣角,手颤抖着抬起来,似乎想碰碰我的脸,又不敢,
最终只是小心翼翼地,再次抓住了我的手腕。力道很轻,带着卑微的祈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