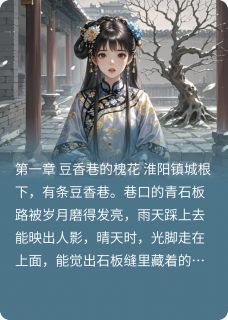
第一章豆香巷的槐花淮阳镇城根下,有条豆香巷。巷口的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发亮,
雨天踩上去能映出人影,晴天时,光脚走在上面,能觉出石板缝里藏着的凉。
这名字是巷里人喊出来的——巷口第一家是秦家豆腐坊,从寅时到酉时,石磨转着,
豆浆煮着,嫩豆腐的清香混着石膏的微涩,顺着风飘遍整条巷,
连墙根的狗尾巴草都像沾了豆味。秦家是实打实的平民。秦老爹脸膛黧黑,
是常年蹲在石磨前推浆晒的,手上布满老茧,指节粗得像老树根,
却偏生有双巧手——磨出的豆浆细得能透光,点出的豆腐嫩得能掐出水。秦娘是个圆脸妇人,
笑起来眼角有两道浅纹,总系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灶上灶下转得不停,
却从不见她急吼吼,连往灶膛添柴都是轻手轻脚的。他们就一个女儿,秦阮阮。
这名字是秦老爹取的。十六年前春天,豆腐坊刚支起松木摊子,秦娘在里屋疼得冒汗,
他蹲在门槛上搓着手等,听见婴儿啼哭时,往里冲得太急,还撞翻了门口的泔水桶。
掀开襁褓看,是个粉团似的丫头,小脸软乎乎,小手软乎乎,连哭声都带着点软。
他咧着嘴笑,反复念叨“软乎,软乎”,秦娘在里屋接了句“就叫阮阮吧”,
这名字便跟着秦家的豆腐香,在巷里叫了十六年。阮阮是秦家的心肝宝贝。秦老爹推磨时,
总把她的小竹凳放在磨盘旁,她踮着脚递布巾,他就故意把磨推慢些,
等她的小手够到他额头;秦娘煮豆腐脑时,灶口的火总烧得温温的,
怕燎着她蹲在旁边的小身子,她递来的粗瓷碗,必定先舀一勺最上面的、撒了虾皮的,
那是她偷偷留的“尖儿”。可秦家宠她,却不是惯着。五岁起,她就跟着秦娘拣豆子,
把瘪的、有虫眼的挑出来,指甲缝里嵌了豆绿,她也不闹,
只举着小手让秦娘用温水洗;十岁时,秦老爹病了,她踩着小板凳推磨,石磨沉得晃,
她咬着牙走半圈歇口气,磨出的豆浆虽不如老爹细,秦娘尝时却红了眼眶。
巷尾的张婆是孤寡老人,秦家总给她送豆腐。有回阮阮端着热豆花过去,
张婆摸着她的头叹:“阮阮这闺女,是天上仙女落了凡吧?”这话不是虚夸。她长到十六岁,
出落得愈发亭亭。皮肤是常年躲在作坊里少见烈阳的白,却不是纸一样的寡淡白,
是透着粉的嫩——像刚剥壳的鲜蚕豆,指尖掐一下,仿佛能渗出水。眼尾微微上挑,
不笑时带点怯生生的柔,笑起来时,眼仁亮得像浸在井水里的墨玉,
连眼尾的细纹都透着灵气。有回卖糖人的老汉路过,看她蹲在门口拣豆子,
手里的糖稀都熬糊了,直拍大腿:“这姑娘,往画里一站,画师都得少用半盒颜料!
”巷尾第三户,是沈秀才家。沈家的门总关着半扇,里面飘出书声,混着墨香。
沈秀才戴副旧铜框眼镜,教着巷里几个蒙童,日子清苦,却总把长衫洗得笔挺。
他家有个独子,沈维柯,比阮阮大两岁。这少年眉目清俊,
是那种读书人特有的干净——皮肤是冷白,鼻梁挺,嘴唇薄,笑时会露出两颗小虎牙,
才添了点少年气。他总穿着件半旧的青布衫,袖口磨出了毛边,却总洗得发亮,
手里常捧着本书,走在巷里,脚步轻得像怕踩疼了青石板。两家是多年的老邻居,
阮阮和沈维柯是打穿一条开裆裤长大的。阮阮三岁时学走路,摇摇晃晃扑进他怀里,
他才五岁,却踮着脚拍她后背,说“不怕”;她七岁学描红,总爱溜出去玩,
是他把攒了半月的桂花糖藏在袖里,哄她“描完这页《千字文》,
糖给你”——那桂花糖是沈夫人用自家院里的桂花腌的,甜得能粘住牙,阮阮为了糖,
歪歪扭扭描完,他就蹲在旁边,用干净的布巾擦她糊了墨的小脸。有年春天槐花开,
阮阮爬墙头摘花,脚下一滑摔了跤,膝盖擦破了皮,血珠渗出来,她咧着嘴要哭,
沈维柯正好放学回来,扔下书箱就蹲下来,看了眼伤口,二话不说背她往医馆跑。
他那时才十二岁,个子刚过她头顶,背得却稳,青衫后襟被她的眼泪打湿了一片,
他还硬撑着说“不疼,我背得动”——后来阮阮才知道,他那天为了跑快点,崴了脚,
却瞒着她,瘸着腿去学堂了三天。秦家豆腐担子重,秦老爹挑着走街串巷,傍晚回来时,
肩膀总被压出红痕。沈维柯放了学,书包都不回屋放,先绕到豆腐坊,抢着挑担子。
秦娘留他吃饭,他红着脸摆手,说“婶子,我娘等着呢”,
却总把沈夫人做的枣泥糕塞给她——那枣泥糕蒸得软,甜不腻,是阮阮最爱的,
他总说“婶子说,给阮阮补身子”,却从不提,那是沈夫人特意多做的一份,
让他给她带来的。长大些,男女有别,两人不再像小时候那样腻在一起,
却多了些心照不宣的默契。沈维柯在门口老槐树下读书,书声朗朗,
眼角余光却总往豆腐坊瞟——看见阮阮出来泼水,他会装作翻书,不经意地抬眼,
问一句“今日的豆腐脑,香得很”;阮阮知道他读书费脑子,去送豆腐路过沈家,
见他在窗下写字,会轻手轻脚把刚出锅的热豆腐放在窗台,
豆腐上还留着她用筷子戳出的小坑,里面藏着点秦娘做的辣酱。转身走时,
总能听见他低低的一句“谢了,阮阮”,声音轻得像槐花瓣落在地上。
两家大人早把这层意思放在心里。秦娘冬夜缝棉袄,给阮阮做的新袄是水红的,
上面绣着缠枝莲,她对着袄面出神,捏着针说:“维柯这孩子,学问好又稳重,
将来考个功名,你嫁过去……”话没说完,见阮阮耳尖红透了,像染了胭脂,
便笑着拍她手背:“傻丫头,脸红什么。”沈秀才也常对沈维柯说:“秦家阮阮是好姑娘,
心善,手脚勤,你得好好念书,将来才配得上——可别学那些酸秀才,忘了本。
”沈维柯听着,手里的笔不停,耳根却悄悄红了,只低低应一声“知道了,爹”。那年端午,
巷里挂了艾草,秦娘包了粽子,有甜有咸。沈维柯来送沈夫人做的香囊,青布做的,
绣着只歪歪扭扭的兔子。他站在豆腐坊门口,手藏在身后,脸憋得通红,等阮阮送他到巷口,
他才从身后拿出样东西——是枚磨得光滑的木簪,黑沉沉的,是巷口老槐树的枝子做的,
簪头刻着朵小小的槐花,纹路有些生涩,边缘却磨得圆润,显然是磨了许久的。
“等我乡试回来,”他声音低得像蚊子哼,耳根红得要滴血,手指捏着木簪,微微发颤,
“我就……我就请我爹去你家提亲。”阮阮攥着那枚木簪,簪身带着他手心的温度,
烫得她指尖都在发颤。她低着头,看见自己的布鞋尖沾了点槐花瓣,轻轻“嗯”了一声,
声音小得像叹气。那时她总坐在豆腐坊门口的老槐树下,看沈维柯的书箱在巷口晃啊晃。
他要去县城参加乡试,秦娘给他装了袋新磨的豆粉,让他泡水喝,补身子。
她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手里攥着那枚槐花簪,心里像揣了碗热豆花,温温的,软软的。
她以为这辈子就该这样:等他考中回来,爹娘请媒人上门,她换上那件水红袄,
把槐花簪插在发间,从此沈家灶房飘着枣泥香,秦家豆腐坊多了个帮衬的女婿,
槐花开了又落,日子像磨浆的石磨,慢却扎实,再无旁骛。
第二章骤雨摧花变故是在暮春的一个清晨来的。那天的雾特别浓,
像把整个豆香巷都浸在了水里,秦家豆腐坊的灯亮时,透过雾看,像团模糊的暖黄。
秦老爹前几日淋了雨,受了风寒,夜里咳得直不起腰,秦娘守在他床边熬药,
天亮时眼泡都是肿的。做豆腐的石磨还得转——秦家的豆腐是街坊们惯了的,断不得。
秦娘要守着作坊点卤,那是做豆腐的关键,石膏水兑多了发苦,兑少了凝不住,
差一分火候都不成。卖豆腐的担子,便落在了阮阮肩上。她比平时起得更早,
帮秦娘把压好的豆腐切成方块,码在铺了湿布的木盘里。秦娘看着她挑担子,总不放心,
反复叮嘱:“路上慢些,别摔了,张婆的豆腐要嫩的,
李叔家要老些煎着吃……”阮阮笑着应:“娘放心,我知道。”她挑着半担嫩豆腐,
粗布裙角扫过青石板,带起细雾,豆香混着晨雾飘了一路,雾里仿佛都结了细细的豆粉。
刚走到巷口,就见雾里停着几辆车——不是寻常的马车,是乌木做的,车厢漆黑,
描着暗金色的龙纹,车轮上裹着厚布,走起来悄无声息。车旁站着些人,穿着皂衣,
腰里佩着刀,眼神冷得像冰,把巷口堵得严严实实。为首的是个穿绯色官袍的中年男人,
肚子微鼓,腰间玉带闪着冷光,手里把玩着串蜜蜡珠子,眼神像鹰隼似的,
在巷口探头探脑的街坊脸上扫来扫去,最后,落在了阮阮脸上。那目光让阮阮心里发慌,
像被针扎了下。她下意识想绕开,往旁边的窄缝走,却被两个膀大腰圆的兵丁拦住。
他们穿着铁甲,甲片摩擦着响,其中一个粗声说:“站住。”阮阮攥紧了担子的绳子,
小声问:“官爷,有事吗?”“这姑娘,不错。”绯衣官慢悠悠开口,
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傲慢,他抬手,用那串蜜蜡珠子指了指阮阮,对身边人说,
“咱家是采选使,奉陛下旨,为后宫选美人。秦家能出这样的姑娘,是福气。”“后宫?
”阮阮懵了,手里的担子“哐当”一声砸在地上,木盘翻了,白花花的豆腐摔得稀烂,
有的沾了泥,有的滚进了水洼,像她瞬间碎了的日子。“我不进宫!我爹娘还在等我!
”她往后退,声音发颤,脚却软得像踩在棉花上。两个兵丁上前,一左一右架住她的胳膊,
铁钳似的,她的手腕被掐得生疼,挣不开。“放开我!你们放开我!”她哭喊着,
声音在雾里散开来,却传不远。巷里的人听见动静,都探出头来,看见是采选使,
吓得又缩了回去——谁都知道,这采选使是替皇上找美人的,被他看上,躲不过。
秦娘在作坊里听见女儿的哭声,疯了似的跑出来,头发散着,蓝布围裙还系在身上,
扑上来想拽阮阮,却被一个兵丁推得踉跄在地。膝盖磕在青石板上,她顾不上疼,
爬过去抱住兵丁的腿,哭喊声撕心裂肺:“放开我闺女!我给你们磕头!求求你们了!
她还小,她配不上宫里啊!”秦老爹也扶着墙走出来,咳得满脸通红,
手里还攥着秦娘给他披的棉袄,他指着采选使,气得浑身发抖,
却只挤出几个字:“你们……你们不能抢人!”巷尾的沈维柯也跑来了。他刚从学堂回来,
手里还拿着本《论语》,青衫上沾着墨,看见这阵仗,脸霎时白了,白得像纸。他想冲过去,
却被采选使身边的护卫拦住——那护卫横刀一挡,刀身映着雾光,冷声道:“秀才郎,
莫要自误。”沈维柯看着阮阮被兵丁架着,她的头发散了,沾着泪,眼睛通红,
伸在空中的手朝着他的方向,嘴里喊着他的名字,声音里满是绝望。他喉咙像被堵住,
发不出声,只能死死攥着拳头,指节泛白,连指甲嵌进掌心渗出血珠都没知觉。
他多想冲上去,把她拉回来,可他只是个穷秀才,手无寸铁,连自己都护不住,更别说护她。
“维柯!”阮阮撕心裂肺地喊他,声音里带着哭腔,
“救我……”采选使不耐烦地挥手:“带走。”兵丁架着阮阮往马车走,
她的脚在地上拖出两道痕,粗布裙被磨破了角。马车帘落下的瞬间,
阮阮看见沈维柯站在槐树下,身影单薄得像片要落的叶子,他手里的《论语》掉在了地上,
书页被风吹得哗哗响。她想再看一眼那枚槐花簪,
却发现慌乱中早已不知掉在了哪里——或许是掉在了摔碎的豆腐旁,
或许是掉在了她被拖拽的路上,就像她被生生扯断的日子,再也捡不起来了。
第三章深宫寒夜进宫后的头三个月,阮阮总觉得是场噩梦。她常常在夜里惊醒,
以为自己还在秦家豆腐坊,能听见石磨的“吱呀”声,可睁开眼,只有帐顶绣着的金线牡丹,
在昏黄的灯影里,像张张陌生的脸。她被带去净身房沐浴时,手脚都在抖。
几个老宫女围着她,扯掉她身上的粗布裙——那是秦娘给她缝的,
裙摆上还绣着朵小小的豆花。——换上件绣着金线的宫装。料子是软缎,滑得像水,
却硌得她皮肤发紧,仿佛不是自己的衣裳。头发被梳成繁复的发髻,老宫女的手又重又急,
木梳扯得头皮疼,发间插着她叫不出名的珠钗,沉甸甸的,压得她脖子都直不起来。
管事嬷嬷是个脸膛刻薄的老妇人,嘴角总是向下撇着,教她规矩时,戒尺不离手。
“说话要低头,眼睛不能乱看,”嬷嬷用戒尺敲着桌面,“见了妃嫔要屈膝,
见了陛下要伏跪,连走路都得碎步,不能发出声响——进了这宫门,
就不是你秦家豆腐坊的阮阮了,记住自己的身份,少给咱惹祸。”阮阮学不会。
她习惯了在巷里大步走,习惯了抬头笑,老嬷嬷的戒尺落在她手背上,一道红痕叠一道,
疼得她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哭出声——嬷嬷说,宫里的眼泪最不值钱。
她因着美貌被封为“贵人”,赐居醉云轩。这名字听着雅致,地方却偏僻得很,
在后宫的角落里,离皇帝住的养心殿远得很。院里的草都快长到台阶上了,
墙角的石榴树也枯了半棵,风一吹,枯枝晃着,像哭似的。头几日还有宫女小心翼翼地伺候,
端水递茶,见她无依无靠——爹娘是卖豆腐的,在宫里连个能递话的人都没有。
——下人们便懒怠起来。送来的饭菜,早上是凉粥配咸菜,粥里还有没淘净的沙,
咸菜齁得发苦;晚上是硬得硌牙的馒头,咬一口能掉渣。冬天来得早,
醉云轩的炭盆里的火总烧不旺,炭是劣质的,烧起来呛人,还总爱灭。阮阮裹着厚被子,
手脚还是冻得发麻,夜里缩成一团,听着窗外的风声,像听见秦娘唤她的声音,
眼泪就忍不住掉下来,湿了枕巾。身边唯一还算忠心的是个叫青禾的小宫女,比她小两岁,
圆脸,梳着双丫髻,是个没什么心眼的姑娘。青禾是罪臣之女,没被发去浣衣局就不错了,
分到醉云轩,见阮阮待她温和,便真心对她。见阮阮对着窗外出神,
青禾会偷偷给她捂个暖炉,小声劝:“贵人,别想了,进了这宫,就得往前看——您看,
这天晴了,院里的梅花开了,咱们去摘朵吧?”阮阮摇摇头。她也想往前看,可前路是黑的,
像被浓雾堵着,看不见光。皇帝倒是来过几趟。初见时,他在养心殿见她,坐在龙椅上,
比她想象中年轻,不过三十出头,眉眼威严,下巴上有层淡淡的胡茬,看她的眼神带着审视,
还有毫不掩饰的惊艳。“你叫阮阮?”他问,声音低沉,带着帝王的威仪,“名字倒是软和。
”他让她抬起头,看了半晌,对身边的太监说:“干净得像新剥的莲子,宫里少见。
”他会偶尔来醉云轩,坐在窗边的椅子上,看她捻针线。他问她民间的事,
阮阮便说豆腐坊如何点卤——“豆浆烧到八成热,石膏水得慢慢兑,搅得匀了,才能凝得好,
嫩豆腐得用布包着压,不能太用力,不然就老了”;说巷子里孩子追着卖糖人的跑,
卖糖人的老汉会吹十二生肖,吹个老鼠,尾巴还会摇;说沈维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
只改成“邻家哥哥总帮着挑豆子,他念书时总被先生罚抄书,抄得手都酸了”。皇帝听得笑,
说:“宫里闷,你这点子鲜活气,倒难得。”可宫里的鲜活气,是留不住的。很快,
皇帝就被新来的宁才人吸引了。宁才人是吏部尚书的女儿,会跳胡旋舞,裙摆一转,
像朵盛开的花;还会说笑话,能把皇帝逗得笑出声。她不像阮阮,笨嘴拙舌,
只会说些豆腐坊的琐事——有回皇帝问她宫里的梅花开得如何,
阮阮说“不如巷口的槐花好闻”。皇帝愣了愣,没说话,后来就来得少了。醉云轩的门,
渐渐落了灰。有回她去坤宁宫给皇后请安,路过宁才人的锦绣宫,见那里车水马龙,
宫女捧着新鲜的荔枝往里送——那是岭南贡品,阮阮只在秦老爹说古时常听人提过,
说那果子甜得像蜜。而她的醉云轩,连春日新采的桃花,都没人记得给瓶里换,
瓶里的水发了臭,花也枯了。下人们的脸色更难看了。有回青禾去领份例,回来时眼圈红了,
手背还有道红痕。阮阮拉着她问,青禾才委屈地说:“管事太监故意克扣炭,
我说贵人冻得睡不着,他还骂我‘伺候个没人要的主儿,也配要新炭’,
推了我一把……”阮阮摸着青禾红肿的胳膊,心里像被冰碴子扎着,又酸又疼。她想过死。
夜里看着房梁,她想找根白绫,或是一头撞死在柱子上——这样就不用受这委屈了,
就能回豆香巷了。可一想到爹娘,想到他们若知道自己死了,秦老爹怕是会咳得更厉害,
秦娘会哭瞎了眼,阮阮就又怯了。她不能死,至少现在不能——她得活着——说不定,
还有机会出去。第四章微光与碎影就在阮阮以为日子就这么熬着,
快要被这深宫的冷寂吞掉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那天晨起,她对着铜镜漱口,刚含一口水,
就猛地一阵恶心,酸水直往喉咙里涌,她扶着镜台,干呕了半天,眼泪都出来了。
青禾慌慌张张去请太医,老太医背着药箱来,给她诊脉时,手指搭在她手腕上,
捻着胡须笑:“恭喜贵人,是喜脉,快两个月了。”阮阮愣在原地,眼泪“唰”地掉下来。
不是伤心,是慌里慌张的欢喜。她有孩子了。在这四方墙里,在这孤孤单单的醉云轩,
她有了个和自己血脉相连的小东西。这孩子像粒种子,落在她荒芜的心里,瞬间发了芽。
这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到皇帝耳中。他几乎是立刻就来了,脚步都比平时急些,进了屋,
一把攥住她的手,眼里的笑藏不住:“好,好!阮阮,你立了大功!”他子嗣单薄,
后宫妃嫔虽多,却只养住了三个皇子两个公主,盼儿子盼得紧。当即下旨晋她为“嫔”,
赏了两箱补品——有燕窝,有参茸,都是阮阮没见过的;还有十匹云锦,红的、粉的、黄的,
鲜亮得晃眼。连醉云轩的下人都换了副嘴脸——以前懒怠的小太监,如今见她出门,
老远就弓着腰候着,端来的安胎药,必定先由绿萼试过,确定没异样,才敢递到她手里。
阮阮开始给孩子做小衣裳。她不用皇帝赏的云锦——那料子太贵重,
只用青禾给她寻来的软棉布,剪成小小的襁褓,小小的衣裤。针脚缝得细细的,
比她当年给秦娘补衣裳还用心,连青禾都笑:“娘娘,这孩子还没影呢,您倒急上了。
”她摸着软乎乎的布料,心里像揣了团暖炭:“得提前备好,我这身子笨,怕到时候赶不及。
”她甚至偷偷想,若是个男孩,就教他像沈维柯那样念书,教他认“天地人”,
教他写自己的名字;若是个女孩,就教她拣豆子,教她做豆腐脑,像她小时候一样,
让她知道,这世上除了宫墙,还有青石板路和槐花香。可她忘了,宫里的暖炭,
从来都烧不长久。那日去坤宁宫给皇后请安,皇后留了各宫妃嫔说话,让大家都沾沾喜气。
阮阮刚要坐下,就见李才人端着茶盏走过来。李才人是京兆府少卿的女儿,平日里就爱炫耀,
头上总插着金步摇,走路叮当作响,见阮阮得宠又怀了孕,眼神里总带着刺,
说话也阴阳怪气的。“秦嫔姐姐有了身孕,可得多补补。”李才人笑着说,话没说完,
脚下不知怎么“踉跄”一下,身子猛地往阮阮身上撞来。阮阮下意识往旁边躲,可还是慢了,
被她手肘狠狠顶在小腹上。“嘶——”阮阮倒抽口冷气,只觉得小腹一阵坠痛,
像有把钝刀在搅,热流顺着裙摆往下淌。她低头,看见月白的裙角染开一片刺目的红,
像朵突然绽开的血花。“我的孩子……”她抓着青禾的裙角,声音抖得不成样,
眼前一阵阵发黑。皇后也慌了,拍着桌子喊:“快传太医!传太医!”她被抬回醉云轩时,
意识都快模糊了,只听见青禾在哭,声音断断续续:“娘娘撑住!太医马上就来!
您别吓奴婢啊!”太医来了,诊脉时脸色凝重,捻着胡须半天没说话,最后只是摇头,
叹着气退出去。青禾红着眼眶凑到床边,哽咽道:“娘娘……孩子……没保住。
”阮阮躺在床上,睁着眼看帐顶的绣纹。那是她亲手绣的缠枝莲,针脚细密,
如今看来却像张网,把她困在里面。是她没护住孩子。她太傻,以为怀了龙胎就能平安,
以为李才人的那点“不小心”只是无心——她忘了进宫时嬷嬷说的话:宫里的人,
笑里藏刀是常事,你不对人狠,人就对你狠。她缩在被子里,三天没吃没喝。
下人见她失了孩子,皇帝也只来看过一次,皱着眉说“节哀”,便再没露面,
态度又冷了下去。送来的饭菜,又成了凉粥咸菜,有回小太监端水,故意把水洒在她床前,
看她扶着墙挪步,还在门外偷笑,声音不大,却字字扎心。直到第七天夜里,
青禾端着药进来,见她还躺着,脸瘦得脱了形,忽然“噗通”跪下。哭得浑身发抖:“娘娘,
那天……那天奴婢去倒药渣,听见李才人的宫女跟人说,是才人故意撞您的!
她说您占了陛下的恩宠,还怀了龙胎,碍了她的路,非除了您的孩子不可!
”阮阮猛地坐起来,眼里的死寂瞬间被恨意烧得滚烫。不是意外。是被人害死的。是了,
这吃人的皇宫哪有什么意外。她那还没来得及看看这世界的孩子,
还没来得及听她叫一声“娘”,就因为嫉妒被那样轻飘飘地害死了。她攥着拳头,
指甲深深掐进掌心,渗出血珠也没知觉。疼。心里疼得像被剜掉了一块。可这疼里,
还生出了别的东西——是恨。她不能就这么算了。她要报仇。为她那未出世的孩子,
也为她自己——她要活下去,活得能护住自己想护的人,活得让那些害她的人,付出代价。
第五章锋芒初露从那天起,秦阮阮像换了个人。她不再整日躺着,第二天就起了床,
让青禾给她梳发。对着铜镜,她看着自己苍白的脸,眼下的青黑,轻声说:“青禾,
给我描眉。”青禾愣了愣,拿起眉笔,小心翼翼地给她描。她的眉本是淡的,
描过后添了几分精神,再看那双眼睛,以前是怯生生的柔,如今却像淬了冰,亮得发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