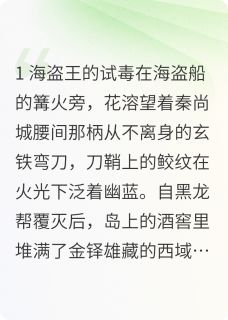
1海盗王的试毒在海盗船的篝火旁,花溶望着秦尚城腰间那柄从不离身的玄铁弯刀,
刀鞘上的鲛纹在火光下泛着幽蓝。自黑龙帮覆灭后,
岛上的酒窖里堆满了金铎雄藏的西域葡萄酒,可秦尚城每次斟酒时,仍会习惯性先替她试毒。
"你说这酒窖的酒,够喝到金逸文的孩子满月么?"花溶指尖摩挲着酒坛上的封印,
忽然想起白日里婉婉红着脸说自己已有身孕的模样。秦尚城正往火里添柴的手顿了顿,
火星溅在他古铜色的手背,"若不够,我明日便带船队去泉州港搬空所有酒庄。"话音未落,
远处海面忽然亮起几点幽绿磷火。张弦踉跄着从瞭望台跌下来,
腰间的佩刀还挂着半片撕破的灰布:"岛主,是东瀛忍者!
他们......他们踩着木板渡海!"花溶攥紧腰间软剑,发现秦尚城的弯刀已出鞘三寸,
刀刃映着他眼底翻涌的暗潮。忍者们踩着特制的浮板在浪尖滑行,月光下可见他们面覆青布,
唯有双眼如毒蛇般阴冷。花溶认出为首者手中握着的正是东瀛伊贺流的忍镖,
当年父亲军中曾有东瀛浪人作乱,她见过这种淬毒的暗器。秦尚城忽然将她拽到身后,
弯刀划出半圆,将三枚破空而来的忍镖斩成两段。"他们是冲宝藏图来的。
"花溶贴着秦尚城的后背低语,感觉到他肌肉紧绷如铁。海盗们已在甲板上列阵,
钱大有举着铁锚链横扫,却被忍者用短刀削断锁链。秦尚城忽然将弯刀抛向空中,
徒手抓住一名忍者的手腕,咔嚓拧断骨头的同时,用对方的忍刀反刺向另一名忍者咽喉。
混战中,花溶瞥见一名忍者正偷偷往火药桶方向移动。她抽出软剑,脚尖点地掠过去,
却被另一人用锁链缠住脚踝。秦尚城的弯刀几乎是擦着她耳畔飞过,将锁链斩断的同时,
刀锋劈开了忍者的面罩。月光下,
花溶看清那忍者左眼下有一道蜈蚣般的疤痕——正是当年在金府地牢见过的黑龙帮余孽。
2忍者突袭"岛主!火药桶要炸了!"张弦的吼声里带着哭腔。
秦尚城突然抱住花溶跃向海中,身后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两人在海浪中沉浮,
花溶呛了几口咸涩海水,却发现秦尚城始终用身体护着她。等他们游回岸边时,
海盗船已烧成灰烬,沙滩上横七竖八躺着忍者的尸体。"他们怎会知道宝藏图在船上?
"花溶拧着湿漉漉的衣袖,火光映得她脸颊泛红。秦尚城忽然攥住她的手腕,
将她拉到礁石后,低头封住她的唇。这个吻带着海水的咸涩与硝烟的味道,
直到花溶推了推他的胸膛,才发现他肩头渗着血——刚才挡了一枚忍者的飞镖。
"明日便去花溶岛。"秦尚城任她用匕首割破衣襟包扎伤口,声音低沉如海啸,
"我要让全天下人知道,你花溶是我秦尚城明媒正娶的妻。"花溶指尖一颤,
想起父亲临终前的叮嘱:"若嫁与海盗,便断绝父女关系。
"可此刻望着秦尚城眼底翻涌的星河,她忽然觉得那些世俗枷锁,不过是海上的浮沫。
三日后,花溶岛张灯结彩。花妈妈特意从银城赶来,带着二十个舞姬在甲板上跳胡旋舞。
金逸文抱着婉婉坐在船头,看着秦尚城穿着花溶亲手绣的大红喜袍,
笨拙地给她戴上珍珠步摇。当花溶将祖传的玉扳指套进秦尚城无名指时,
远处海面忽然传来悠扬的螺号声。"是朝廷的水师!"张弦举着望远镜的手在发抖。
花溶攥紧秦尚城的手,发现他掌心全是汗。水师战船渐渐逼近,船头立着位银甲老将,
正是花溶的叔父花无缺。秦尚城忽然松开她的手,解下腰间弯刀放在甲板上,
单膝跪地:"花将军,我秦尚城今日以海盗岛所有财宝为聘,求娶花溶为妻。
"花无缺盯着秦尚城,忽然仰天大笑:"好个海盗王!当年你义父秦老鬼救过我一命,
这笔债今日便算还清了。"他扔出一支令牌,"拿着这个,朝廷特许你们海盗岛自治。
但花溶,"他转而看向花溶,"你父亲若泉下有知,定要气得从棺材里跳出来。
"3海盗王的求婚当夜,花溶躺在秦尚城怀里,听着海浪拍击花溶岛的声音。
秦尚城把玩着她的长发,忽然从怀里掏出个锦囊:"这是当年在宝藏里找到的安胎药,
唐梦蝶说......"花溶猛地坐起来,
烛光下可见她双颊飞红:"你......你怎会有这个?"秦尚城将她重新按回怀中,
滚烫的呼吸拂过她耳垂:"因为我的新娘,已经有两个月的身孕了。"海风掀起帐幔,
月光如水般漫进洞房。花溶望着秦尚城熟睡的侧脸,忽然想起初见时那个凶神恶煞的海盗王,
如今却会在她孕吐时整夜守在床边,用温热的帕子替她擦汗。她轻轻抚摸着小腹,
忽然听见秦尚城在睡梦中呢喃:"阿昭......""阿昭?"花溶凑近他耳畔,
"这是你想给孩子取的名字?"秦尚城迷迷糊糊睁开眼,
将她往怀里拢了拢:"我梦见北尘说,我们的女儿会像她娘一样,是个穿红衣舞剑的小侠女。
"花溶笑出声,指尖划过他眉间的疤痕:"若真是女儿,
便叫秦昭;若是儿子......""便叫秦承。"秦尚城忽然睁眼,眼底映着窗外的星光,
"承我秦氏血脉,护你花氏周全。"他低头吻住她的唇,帐幔外,
海浪依旧不知疲倦地拍打着礁石,仿佛在诉说着属于海盗王与侠女的永恒传说。
晨光透过雕花窗棂,在锦被上投下细碎的光斑。花溶翻了个身,鼻尖蹭到秦尚城温热的颈窝,
他身上总带着海风与松脂的气息,让她孕期里格外安稳。昨夜孩子又在腹中踢了她半宿,
秦尚城便坐着守了她一夜,此刻眼尾泛着淡淡的青黑,却仍把她圈在怀里,
生怕她翻身时着凉。“醒了?”秦尚城的声音带着初醒的沙哑,指尖轻轻覆在她小腹上,
那里已经微微隆起,像揣着个温热的小面团。他掌心的薄茧蹭过衣料,引得花溶轻轻颤了颤,
“小家伙刚才又动了,许是在跟我打招呼。”花溶笑着拍开他的手:“才三个月大,
哪就听得懂你说话。”话虽如此,指尖却不由自主地跟着他的动作,
感受着腹内那微弱却鲜活的悸动。这感觉奇妙又温暖,让她时常在夜里惊醒时,
只要摸到秦尚城的手覆在上面,便会立刻安心。门外传来轻叩声,
是钱大有粗声粗气的嗓音:“岛主,金公子和婉婉姑娘带着小公子登岛了,
说是给夫人送安胎的补品。”秦尚城皱眉,把花溶往被子里按了按:“让他们在客厅等着,
我先伺候你洗漱。”他如今越来越像个寻常丈夫,从前连自己的腰带都系不利索,
现在却能熟练地替花溶梳起松松的发髻,发尾还缀上颗圆润的珍珠——那是上次去泉州港,
他见渔民卖海蚌,硬是蹲在滩涂上挑了半日,亲手剖出来的珠子。
4海盗岛的喜事花溶坐在镜前,看着镜中两人的倒影。秦尚城的头发比初见时长了些,
她便学着闺中女子的模样,给他绾了个简单的发髻,用根玉簪固定。他本不喜欢这些束缚,
却任由她折腾,只在她不小心扯到头发时闷哼一声,眼底却满是笑意:“再扯下去,
岛主就要变成秃瓢了。”“才不会,”花溶替他理了理衣襟,“我们阿城的头发又黑又密,
比岛上最壮的椰子树还要茂盛。”她故意把“阿城”两个字说得软糯,惹得秦尚城低笑起来,
弯腰在她颊边偷了个吻:“再贫嘴,早饭就凉了。”客厅里早已摆好了茶点,
金逸文正抱着襁褓中的儿子逗弄,婉婉坐在一旁缝着小衣裳,见他们进来,
连忙起身:“溶姐姐,你气色真好。”婉婉产后身子还虚,说话时带着浅浅的笑意,
眼角的温柔却藏不住。金逸文把孩子递给乳母,起身拱手:“尚城兄,
这次带了些江南的苏绣襁褓和燕窝,都是婉婉特意让人寻的上好货色。
”他如今褪去了少年时的青涩,眉宇间多了几分稳重,
却仍改不了见了秦尚城就称兄道弟的习惯。花溶接过婉婉递来的小衣裳,针脚细密,
上面绣着栩栩如生的鲤鱼跃龙门:“这太费功夫了,你刚生了孩子,该多歇歇才是。
”婉婉红了脸:“闲着也是闲着,想着将来孩子们能一起长大,做个伴儿。
”她说着看向花溶的小腹,满眼期盼,“不知是位小公子还是小公主?
”秦尚城替花溶剥着橘子,闻言嘴角扬得更高:“太医说是双胎,一儿一女。”“双胎?!
”金逸文惊得差点把茶杯打翻,“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尚城兄,你这运气也太好了些!
”花溶嗔怪地看了秦尚城一眼:“太医只是说有这个可能,还没定论呢。”话虽如此,
指尖却忍不住轻轻摩挲着小腹,心中早已勾勒出两个粉雕玉琢的小人儿围着她喊娘亲的模样。
正说着,张弦风风火火地跑进来,手里举着个油纸包:“岛主,夫人!
山下渔村送了些刚捕捞的海产,说是感谢我们上次帮他们打跑了倭寇。
”油纸包里是鲜活的鲍鱼和龙虾,还带着海水的腥气。秦尚城挑眉:“倭寇又来作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