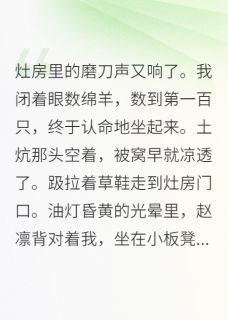
灶房里的磨刀声又响了。我闭着眼数绵羊,数到第一百只,终于认命地坐起来。
土炕那头空着,被窝早就凉透了。趿拉着草鞋走到灶房门口。油灯昏黄的光晕里,
赵凛背对着我,坐在小板凳上。肩膀宽厚,腰背挺直,手里捏着那把割麦子的镰刀,
正一下一下,慢吞吞地磨。磨石发出“嚓…嚓…”单调又刺耳的声响。“凛哥,”我开口,
嗓子有点哑,“三更天了,磨它干啥?”他动作顿住,没回头,声音闷闷的,
带着点刚睡醒的混沌:“……不知道。”又是不知道。这毛病是去年冬天落水后染上的。
捞上来时人都冻硬了,只剩一口气。好不容易救活了,人却变了。话少了,眼神空了,
时不时就坐在那儿发呆,或者像现在这样,深更半夜爬起来,做些他自己也说不上为啥的事。
“睡吧,”我走近几步,“明儿还要下地呢。”他“嗯”了一声,却还是没动。
镰刀雪亮的刃口在油灯下反着光,映着他半张侧脸,鼻梁挺直,下颌绷着一条生硬的线。
明明还是那张脸,那个一起过了三年的男人,可有些东西,就是不一样了。他以前,
从不碰这些锋口朝外的家伙什。我叹口气,没再劝,转身回屋。躺回炕上,
听着那“嚓…嚓…”声,心里像堵了团湿棉花。天刚蒙蒙亮,村东头老槐树下就炸开了锅。
我端着一盆刚淘好的米往家走,远远就看见一群人围在那里,指指点点。“哎呦喂,
吓死人了!”“哪个杀千刀的干的?太狠了!”“脖子上一刀,干脆利落,像是……练家子?
”我心里咯噔一下,挤进去。地上躺着个人,脸朝下趴着,后脖颈一道深深的豁口,
血糊了一地,渗进泥里,颜色发暗。穿着身没见过的黑布衣裳,料子看着不便宜。
村长蹲在旁边,脸色铁青,用根树枝小心地拨弄那人僵硬的胳膊。“嘶啦”一声轻响,
布料被树枝刮开一点,露出那人手腕内侧。一个图案。刺青。像两条盘绕的毒蛇,蛇头狰狞,
吐着信子。我手里的陶盆“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米粒撒了一地。心猛地往下沉,
沉到冰窟窿里。这图案,我见过!就在昨晚。赵凛半夜磨完镰刀回屋,脱外衣时,
袖口蹭上去一截,露出手腕。那皮肤上,就盘着这么个东西!一模一样!当时油灯暗,
我以为是沾了泥还是花了眼,没敢细看,他就把袖子捋下去了。“莫家媳妇,咋了?吓着了?
”旁边王婶扶了我一把。我脸色肯定白得像鬼,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胡乱摇摇头,弯腰捡起盆,也顾不上地上的米,跌跌撞撞就往家跑。推开院门,
赵凛正坐在院里的小马扎上,手里拿着块布,仔仔细细地擦那把镰刀。刀刃雪亮,
映着清晨微凉的光,晃得人眼晕。刀柄上缠着的麻绳,似乎比昨晚更暗了些,
像是……沁进了什么洗不掉的东西。他听见动静,抬起头。眼神还是空,带着点刚醒的迷蒙。
“染尘?”他叫我名字,“米呢?”我死死盯着他擦刀的手,
盯着他那截被袖子遮得严严实实的手腕,感觉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头顶。
“村口……死人了。”我声音发飘,眼睛不眨地看着他。他擦刀的动作停都没停,
眉头都没皱一下,只是“哦”了一声,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太阳不错”。
“脖子被割开了。”我又补了一句,声音有点抖。他终于停下动作,把镰刀靠墙立好,
站起身。高大的影子罩过来,带着一种无形的压迫感。他走到我跟前,低头看我,
眼神里那点迷蒙散了,只剩下深不见底的黑。“死人了,”他重复了一遍,声音低沉,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伸出手,似乎想碰我的脸。我下意识地猛地后退一步,
后背撞在院门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他的手僵在半空。空气瞬间凝固了。他看着我,
黑沉沉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飞快地掠过,快得抓不住。像是困惑,
又像是……一丝被冒犯的冷意。我喘着气,胸口剧烈起伏。恐惧像藤蔓一样缠紧了心脏。
“我……我去看看锅……”我找了个蹩脚的借口,几乎是逃也似的,从他身边挤过去,
冲进了灶房。背靠着冰冷的土墙,我大口喘气,心快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不对劲。
赵凛不对劲。那个死人不对劲。那个刺青……更不对劲!他以前,连杀鸡都不敢看。
日子在一种诡异的平静下熬着。村里人心惶惶,报了官,
几个穿着皂衣的“上面人”来转了一圈,盘问了几家,也没查出个所以然。
那具尸首被草席卷了拉走,老槐树下只剩下几滩洗不掉的暗红印记。赵凛依旧沉默寡言,
白天跟着我下地,锄草,挑水,像个最本分的庄稼汉。只是夜里,
那磨刀声隔三差五就会响起。我夜里不敢睡沉,竖着耳朵听灶房的动静。
有时能听到他低低的、梦呓般的几个词,破碎,听不真切。像“宫墙”,像“暗卫”,
像“殿下”……这些词,像烧红的烙铁,烫得我心惊肉跳。我们这山沟沟里,哪来的宫墙?
殿下又是谁?那晚的刺青和死人,像根毒刺扎在心里。我偷偷翻过他的旧衣服,
袖口都完好无损。他手腕上那个刺青,再也没露出来过。直到那天下午。
我在屋后菜园子里拔草,赵凛在院里劈柴。柴刀剁在木墩上,发出沉闷的“咚咚”声。
一个货郎挑着担子,摇着拨浪鼓从院门口经过。“针头线脑,
胭脂水粉——好看的绢花嘞——”货郎吆喝着,声音不高不低,带着点外地口音。
他脚步慢悠悠,眼睛却像钩子一样,飞快地扫过我们这破败的院子,扫过劈柴的赵凛。
赵凛劈柴的动作,微不可察地顿了一下。仅仅是一下,快得像错觉。斧头稳稳落下,
柴禾应声裂开。货郎没停,吆喝着走远了。我捏着手里带泥的草根,指尖冰凉。
那货郎看赵凛的眼神……不对劲。那不是看一个普通庄稼汉的眼神。像是在确认什么。
“凛哥,”我拿着把蔫了的青菜走进院子,尽量让声音听起来自然,“刚才那货郎,
眼生得很,以前没见过。”赵凛把劈好的柴码整齐,头也没抬:“嗯,路过的吧。
”他拿起斧头,走向下一根木头。弯腰的瞬间,他后腰的旧布衫下,似乎有个硬物的轮廓,
顶起了薄薄的布料。很小,很硬,像……一块玉佩的形状?我以前给他擦背,怎么没注意到?
“晚上想吃啥?”我咽了口唾沫,把青菜丢进盆里,“炒个青菜,再煮点粥?”“都行。
”他挥下斧头。斧刃闪着寒光。我的心跟着那寒光,一抽一抽地跳。不安像滚雪球,
越滚越大。几天后,我去河边洗衣裳。蹲在青石板上,棒槌敲打着湿衣服,“啪啪”作响。
河水哗哗地流。洗到赵凛一件旧褂子时,我习惯性地摸口袋。指尖触到一个硬硬的小东西。
掏出来一看,是块石头。半个巴掌大小,灰扑扑的,毫不起眼,河边随便就能捡到的那种。
我皱了皱眉,他揣块石头在口袋里干嘛?随手就想扔回河里。就在石头脱手的一刹那,
水光折射,那灰扑扑的石面某个角度,忽然闪过一道极其温润、极其内敛的光泽!
那绝不是普通石头的光!我心头一跳,赶紧把石头攥紧,拿到眼前仔细看。沾了水,
石头的真实质感显露出来。入手沉甸甸的,异常温润细腻。
我撩起河水用力搓洗掉表面的泥垢。灰扑扑的外壳下,露出了真容。温润如脂,
白得像刚挤出的羊奶,又隐隐透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极淡的青气。
这光泽……我只在村长家祖传的那块据说值点钱的玉佩上见过一点点影子,远不如这个!
石头底部,似乎还残留着一点点没洗掉的、深褐色的……干涸痕迹?像血。我手一抖,
石头差点掉进河里。一股寒气顺着脊椎爬上来。这块玉,绝不是我们这地方该有的东西!
打量的眼神……半夜的磨刀声……梦呓里的“宫墙”“殿下”……碎片在我脑子里疯狂旋转,
碰撞,一个可怕的、荒谬的念头,像毒蛇一样钻了出来,死死咬住了我的心脏。
我猛地站起身,湿衣服也顾不上,攥紧那块冰冷的玉,跌跌撞撞往家跑。推开院门,
赵凛正在喂鸡。听见动静,他转过头。我站在门口,脸色煞白,胸口剧烈起伏,死死盯着他。
手里那块玉,像块烧红的炭,烫得我几乎拿不住。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紧握的手,
眉头慢慢拧了起来。喂鸡的谷子从他指缝里漏下去,几只鸡咯咯叫着围过来啄食。“染尘?
”他声音低沉,带着疑问。我张了张嘴,喉咙发紧,试了几次,
才发出嘶哑的声音:“这……这是什么?”我把攥着玉的手,朝他摊开。温润的羊脂白玉,
在阳光下流淌着内敛的光华,底部那点暗褐色的污迹,显得格外刺眼。
赵凛的目光落在那块玉上。时间仿佛凝固了。喂鸡的动作彻底停了。
他脸上的平静像潮水一样褪去,露出底下坚硬冰冷的岩石。那双总是带着点空洞的眼睛,
瞬间变得锐利无比,像淬了寒冰的刀锋,直直刺向我。空气沉重得让人窒息。
他一步步走过来,脚步很沉,踩在泥地上几乎没有声音。高大的阴影笼罩住我,
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他伸出手,不是来接玉,
而是猛地抓住了我的手腕!力气大得吓人,骨头被捏得生疼。“哪来的?”他声音压得极低,
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冰碴子,刮着我的耳朵。我疼得抽气,眼泪差点冒出来,
挣扎着:“你……你口袋里……河边洗衣裳……”他根本不听,一把将我拖进屋里,
反手“砰”地一声甩上门!光线瞬间暗下来。他把我抵在门板上,
另一只手粗暴地夺过那块玉,举到眼前,鹰隼般的目光死死盯着玉,尤其是底部那点污迹。
他的呼吸变得粗重,胸膛起伏,眼神里翻涌着惊涛骇浪——震惊、暴怒、难以置信,
还有一种……刻骨的冰冷杀意!那杀意,让我浑身血液都冻住了。“谁让你碰的?!
”他低吼,声音震得门板嗡嗡响,捏着我手腕的力道几乎要捏碎骨头。
“我……我不知道……”我吓得魂飞魄散,语无伦次,
“洗衣裳……摸到的……它……”“闭嘴!”他猛地打断我,眼神凶狠得像要吃人。
他死死盯着那块玉,又猛地看向我,那目光像是要把我穿透,钉死在门板上。
“你看到了什么?”他声音嘶哑,带着一种可怕的审问意味,“说!
”“没……没看到什么……就是块玉……”我疼得直哆嗦,眼泪终于掉下来,
“凛哥……你弄疼我了……放开……”他看着我满脸的泪,眼神剧烈地闪烁了一下,
那骇人的杀意似乎出现了一丝裂痕。捏着我手腕的力道,松了一点点。就在这时——“砰!
砰!砰!”院门被拍得山响!力道极大,带着一种蛮横。“开门!里正查人!
”一个粗嘎的男声在外面吼。赵凛眼神一凛,瞬间松开了我。
他飞快地把那块玉塞进自己怀里最贴身的地方,动作快如闪电。
脸上的暴怒和杀意在门被拍响的瞬间就消失了,快得像从未出现过,
只剩下一种冰冷的、戒备的警觉。他整了整被我挣扎弄乱的衣襟,示意我别出声,
然后才转身,拉开了屋门。我也赶紧抹了把脸,强作镇定地跟出去。院门打开,
外面站着三个人。为首的是村里新来的那个姓李的里正,瘦高个,三角眼。
他身后跟着两个壮汉,穿着普通的短打,但眼神精悍,太阳穴微鼓,腰间鼓鼓囊囊,
一看就不是善茬,更不像普通的乡勇。“李里正,有事?”赵凛挡在门口,
声音恢复了平日的沉闷,但脊背挺得笔直。李里正那双三角眼像毒蛇的信子,
在我们俩脸上来回扫,尤其在赵凛身上停留了很久,像是在确认什么。
他皮笑肉不笑地开口:“赵凛,莫染尘是吧?接到上命,查查各家各户的外来人口。
你这男人,是前年冬天从河里捞起来的?户籍呢?打哪儿来的?”“不记得了。
”赵凛答得干脆,眼皮都没抬,“捞起来就啥都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李里正嗤笑一声,往前逼近一步,眼神变得阴鸷,“这么巧?我看你身手不错啊,
那晚村口死的那条‘野狗’,脖子上的刀口,可利落得很呐。”这话像道惊雷劈在我头上!
他们果然怀疑到赵凛头上了!那晚的死人,他们知道!赵凛依旧面无表情,
甚至眼皮都没动一下:“里正说笑了,我一个种地的,哪懂那些。那晚我在家睡觉,
我媳妇可以作证。”李里正的目光立刻像刀子一样剜向我,带着**裸的威胁:“哦?
莫家娘子,那晚你男人,真的一直在家?没听见什么动静?”我心脏狂跳,
后背瞬间被冷汗湿透。
确实出去过一小会儿……我要是撒谎……可要是说实话……“在……在家……”我声音发颤,
指甲深深掐进手心,“他……他一直睡着……我起夜时……他还在炕上……”李里正盯着我,
那眼神像是要把我的皮扒下来看真假。他身后的两个壮汉,手已经摸向了腰间鼓囊的地方。
气氛紧绷得像拉满的弓弦,一触即发。赵凛忽然动了。他上前半步,看似不经意地,
把我往他身后挡得更严实了些。他抬起眼皮,第一次正眼看向李里正,那眼神平静无波,
深处却像结了冰的寒潭。“里正,”他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
“查户口,该去里正那里画押。盘问妇道人家,不合适吧?我赵凛就在这,哪儿也不会去。
若真有事,拿官府的签票来拿人便是。”他这话说得不卑不亢,甚至有点乡下人的硬气,
但隐隐的,又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底气。李里正被他这眼神和话噎了一下,
三角眼里闪过一丝忌惮。他盯着赵凛看了好几秒,似乎在权衡。最终,
他阴恻恻地哼了一声:“行,赵凛,你最好安分点。我们走!”他带着那两个壮汉,
转身离开,重重摔上了院门。门一关,我腿一软,差点瘫在地上。赵凛一把扶住我。
他的手很稳,也很凉。“没事了。”他说,声音低沉,听不出情绪。**着他,浑身都在抖。
刚才那短短片刻的对峙,耗光了我所有力气。李里正最后那阴毒的眼神,
那两个壮汉腰间鼓囊的东西……都让我不寒而栗。
“他们……他们还会来的……”我声音抖得不成样子。赵凛没说话,只是扶着我的手,
收得更紧了些。他看向院门的方向,眼神深得像寒夜的井。李里正走后,日子像是绷紧的弦,
随时会断。赵凛变得更加沉默,像一座随时会爆发的火山。夜里,他不再磨镰刀,
而是抱着胳膊,靠在炕沿上,睁着眼睛看漆黑的房梁,一看就是大半宿。我躺在他旁边,
能清晰地感受到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冰冷紧绷的气息,像蓄势待发的野兽。那块惹祸的玉,
我再也没见过。但我知道,它就在他身上,像一颗随时会炸的雷。三天后的傍晚,
天阴沉得厉害,黑云压顶,闷雷在云层里翻滚。我去邻村请的兽医还没到,
家里那头拉犁的老黄牛不知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肚子胀得像鼓,口吐白沫,
眼看就不行了。牛是庄稼人的命根子,我急得团团转。赵凛蹲在牛棚里,
大手一下下顺着老牛抽搐的脖子,眉头拧成死结。“我去村口看看兽医来了没!
”我实在等不住,抓起斗笠就往外跑。“别去!”赵凛猛地站起身,声音又急又厉。
我被他吼得一怔,停在院门口:“牛快不行了……”“天要下雨,”他几步跨过来,
一把抓住我胳膊,力道大得惊人,眼神锐利地扫过院外黑沉沉的小路,“危险,在家待着!
”就在这时,一道惨白的闪电撕裂天幕,紧接着——“咔嚓!!!
”一个炸雷仿佛就在头顶劈开!震得人耳膜生疼,整个地面都在抖!老牛受惊,
“哞——”地一声凄厉长嘶,猛地挣脱了缰绳,发疯似的冲出牛棚!“牛!”我失声惊叫。
赵凛反应快得像闪电,立刻松手去追牛。那牛受了惊,又病着,狂性大发,
直直朝着院外冲去!“拦住它!”赵凛吼着追出去。我也顾不上那么多,跟着冲出院门。
老黄牛沿着泥泞的村道狂奔,赵凛在后面紧追不舍。雨点开始砸下来,又大又急,
瞬间就把人浇透了。雷声一个接一个,震耳欲聋。眼看赵凛就要追上牛,斜刺里,
通往山坳的岔路口,突然冲出三个黑影!都穿着蓑衣,戴着斗笠,看不清脸。
但动作快得惊人,像三支离弦的箭!他们手里都握着短刀,刀刃在闪电下反射出刺目的寒光,
直扑赵凛!“凛哥!小心!”我魂飞魄散,尖叫出声。赵凛追牛的身形猛地一顿!
他根本没回头,却像背后长了眼睛,在刀光及体的瞬间,
身体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向侧面滑开!唰!唰!唰!三把刀全部落空!
赵凛借着滑开的势头,脚尖在泥地里一点,身体猛地旋回!动作快如鬼魅!
他根本没去看那三个杀手,目光反而像鹰隼一样,死死锁住了我身后!“趴下!
”他朝我厉吼,声音被雷声和雨声吞没大半。我下意识地扑倒在地,泥水糊了一脸。
几乎同时!嗖!嗖!嗖!三道极细微的破空声从我头顶掠过!是弩箭!埋伏!不止三个人!
还有人在暗处放冷箭!赵凛在吼出“趴下”的同时,身体已经动了。
他像一头被彻底激怒的猎豹,不再掩饰任何锋芒。脚下发力,泥水飞溅,
整个人迎着那三个扑来的杀手冲了过去!没有花哨的动作,只有快!准!狠!
第一个杀手挥刀横斩,赵凛矮身避过,左手如毒蛇出洞,精准地扣住对方手腕,一拧一折!
“咔嚓!”骨头碎裂的声音清晰可闻,被雷声掩盖。杀手惨嚎都来不及发出,
赵凛右手并指如刀,闪电般切在他颈侧!那人哼都没哼一声,软软栽倒。
第二个杀手的刀已经劈到赵凛后颈!赵凛像是背后有眼,头也不回,身体诡异地向后一仰,
刀锋贴着他鼻尖划过!他顺势一个后踢,靴子重重踹在第二个杀手的胸口!“砰!
”闷响夹杂着骨头碎裂声。那杀手倒飞出去,撞在路边的土墙上,滑下来不动了。
第三个杀手显然被这电光火石间的杀戮吓破了胆,动作一滞。赵凛没给他任何机会,
欺身而上,拳头带着破风声,狠狠砸在他太阳穴上!第三个杀手像截木头一样,
直挺挺栽进泥水里。整个过程,不到三个呼吸!冰冷的雨砸在身上,我趴在泥水里,
浑身抖得像筛糠,牙齿咯咯打架。亲眼目睹这种血腥杀戮带来的冲击,
远比那晚看到尸体恐怖一万倍!赵凛解决了三个明面上的杀手,没有丝毫停顿,
猛地转向暗箭射来的方向——路边一片茂密的灌木丛!他像一头锁定猎物的猛兽,
几个纵跃就扑了过去!灌木丛剧烈晃动,传来几声短促的闷响和骨头断裂的脆响,
随即彻底安静下来。雨更大了,冲刷着地上的泥泞和……迅速晕开的暗红色。
赵凛从灌木丛里走出来,手里提着一个人,像提着一只死狗。那人穿着深色的紧身衣,
胸口凹陷下去一大块,嘴角淌着血沫,四肢软软垂下,显然活不成了。
赵凛把他丢在另外三具尸体旁边。他站在瓢泼大雨中,蓑衣早在打斗中不知去向,浑身湿透,
单薄的粗布衣裳紧贴在身上,勾勒出精悍强健的线条。雨水顺着他棱角分明的脸庞往下淌,
冲刷掉溅上的血点。他微微喘着气,胸膛起伏,眼神却冷得像万载寒冰,
扫过地上的四具尸体,没有丝毫波澜。仿佛刚才不是杀了四个人,而是捏死了四只蚂蚁。
然后,他的目光转向我。我趴在冰冷的泥水里,对上他那双毫无温度的眼睛,
巨大的恐惧像一只冰冷的手,扼住了我的喉咙,连尖叫都发不出来。他一步步朝我走来,
踩在泥水里,每一步都像踏在我的心尖上。他走到我面前,蹲下身。
浓重的血腥味混合着雨水的气息,扑面而来。他沾着泥水和血渍的手,朝我伸过来。
我吓得猛地闭上眼睛,身体缩成一团。预想中的剧痛没有到来。那只冰冷的手,带着薄茧,
有些粗粝,却只是轻轻拂开了黏在我脸颊上、糊住眼睛的湿发。
动作甚至……带着一种生涩的,小心翼翼的轻柔。我颤抖着睁开眼。他蹲在我面前,很近。
雨水顺着他额前的黑发滴落,滑过高挺的鼻梁,流过紧抿的薄唇。
那双刚刚还杀意凛然、冰冷刺骨的眼睛,此刻正看着我,眼神极其复杂。
暴戾的杀机还未完全褪去,像冰层下的暗流。但冰层之上,
却翻涌着一种更剧烈的、几乎要将他撕裂的痛苦和挣扎!他的眉头死死拧在一起,
额角青筋暴跳,像是在承受着难以想象的酷刑。“染……尘……”他艰难地开口,
声音嘶哑得厉害,像是很久没说过话,“别……怕……”他试图想对我扯出一个安抚的笑,
可嘴角刚动了一下,就猛地僵住。“呃啊——!
”一声压抑不住的痛吼从他喉咙深处迸发出来!他猛地抱住头,高大的身躯蜷缩起来,
剧烈地颤抖!手指深深**湿透的头发里,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像是要把自己的头颅捏碎!
“头……好痛……”他从牙缝里挤出破碎的音节,痛苦得面目扭曲,
“……杀……不……殿下……逃……”他语无伦次,断断续续地嘶吼着,
像是在和脑子里无数个声音搏斗。一会儿是痛苦的**,
一会儿又蹦出冰冷的、带着血腥气的命令词。“凛哥!凛哥你怎么了?!”我吓坏了,
顾不上害怕,扑过去想扶住他。“别过来!”他猛地抬起头,眼睛赤红一片,像濒死的野兽,
充满了狂乱和暴戾,“走!快走!我会……杀了你!”他猛地推开我,
力道大得让我在泥水里滚了一圈。他踉跄着站起来,抱着头,跌跌撞撞地朝家的方向冲去,
像一头发疯的困兽,冲进了暴雨深处。我坐在冰冷的泥水里,
看着地上四具渐渐被雨水冲刷的尸体,看着赵凛消失的方向,
听着那越来越远的、痛苦绝望的嘶吼,浑身冰冷,大脑一片空白。他不是赵凛。他是谁?
我几乎是爬回家的。推开院门,雨幕中,赵凛蜷缩在屋檐下的角落里,背靠着冰冷的土墙,
头深深埋在臂弯里,肩膀还在无法控制地微微颤抖。
那身湿透的粗布衣裳沾满了泥浆和暗红的血渍,紧紧贴在他身上,
勾勒出精悍却异常脆弱的轮廓。听到我的脚步声,他猛地抬起头。雨水冲刷过他苍白的脸,
那双赤红的眼睛此刻褪去了狂乱,只剩下深不见底的疲惫和一种……近乎绝望的茫然。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却没发出声音。“我去烧点热水。”我嗓子发紧,声音干涩。
避开他的目光,我冲进灶房,手抖得几乎点不着火。柴火噼啪作响,锅里冷水渐渐升温,
冒出白气。我蹲在灶膛前,盯着跳跃的火苗,脑子里却全是刚才雨幕中的杀戮,
赵凛痛苦嘶吼的模样,还有他推我时眼中那骇人的暴戾。他不是我认识的赵凛。
那个老实巴交、连杀鸡都不敢看的庄稼汉,只是一个泡影,一层被河水泡掉的外壳。
热水烧好,我舀进木桶,兑了些凉水。拎着桶走到屋檐下,他依旧蜷在那里,
像一尊被雨水打湿的、冰冷的石雕。“洗洗吧。”我把桶放在他脚边,声音很低。他没动,
只是抬起眼,那双深黑的眸子在昏暗的光线下,沉沉地望着我,
里面翻涌着太多我看不懂的东西。愧疚?痛苦?还是别的什么?“染尘……”他终于开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