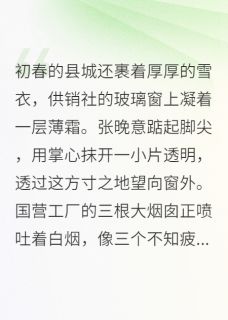
初春的县城还裹着厚厚的雪衣,供销社的玻璃窗上凝着一层薄霜。张晚意踮起脚尖,用掌心抹开一小片透明,透过这方寸之地望向窗外。国营工厂的三根大烟囱正喷吐着白烟,像三个不知疲倦的老烟枪。
"晚意,别愣着了,新到的肥皂要登记。"王主任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哎,马上来。"张晚意麻利地转身,两条乌黑的麻花辫在肩头轻晃。今天她是来供销社帮忙工作一天的,她蹲下身,开始清点纸箱里的肥皂。这些金黄色的肥皂块散发着刺鼻的气味,但在物资紧缺的年代,每一块都是珍贵物资。
她正记录着数量,供销社的木门被推开,带进一阵冷风。张晚意抬头,看见母亲挎着布包站在门口,身后还跟着一个盘着发髻的中年妇女。
"妈?您怎么来了?"张晚意连忙站起来迎了过去。
张母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喜色,快步走过来拉住女儿的手:"晚意,这位是西街的刘婶,有好事跟你说。"她压低声音。转头对王主任说:"王主任,我借闺女说会儿话成不?"
王主任从柜台后探出头,看到刘婶,了然地笑了:"去吧去吧,别太久就行。"
后屋里堆满了未拆封的货箱,三人只能挤在狭小的空隙中。刘婶上下打量着张晚意,目光像在评估一件商品:"模样真俊,身板也结实,是个好生养的。"
张晚意顿时明白了什么,耳根发热。她已经二十二岁了,同龄的姑娘大多已经嫁人,母亲近来总念叨这事。
"西边李家的二儿子,二十四岁,在公社当文书。"刘婶从兜里掏出一张照片,"他爸是公社副主任,家里有台缝纫机,去年还买了永久牌自行车。"
照片上的青年瘦削,眼睛看着镜头外,表情模糊。张晚意接过照片,指尖发凉。
"李家条件多好,"母亲捏了捏她的手,"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
"妈,我还不急......"
"怎么不急?"母亲打断她,"你弟弟马上高中毕业,要是能进公社工作......"话没说完,但意思明显。
刘婶笑眯眯地补充:"李家说了,要是成了,自行车票不是问题。”张母一听这话,脸上的喜色更加掩饰不住了。
回家的路上积雪未化,张晚意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想着家里的情况,父亲是个老实人,母亲总嫌弃父亲没有本事,不能为弟弟搞到一张自行车票,如果跟了李家,那么自行车票就能解决了,母亲也会很开心的。路过工厂大门时,下班的工人们鱼贯而出,她看见几个年轻女工边走边笑,胸前的厂牌在夕阳下闪闪发亮。
晚饭是稀粥和咸菜,弟弟埋头吃着,父亲照例蹲在门槛上抽烟。当母亲提起李家的事时,父亲半天不说话。
"老张,你倒是说句话啊!"母亲把碗重重放下。
父亲在门槛上磕了磕烟斗,火星四溅:"李家那小子,听说性子软得很,全听他娘的,没有一点主见。"
"那有什么不好?总比打老婆的强!"母亲反驳道,转向张晚意,"闺女,妈不会害你
女人总要嫁人,李家条件好,你过去不受苦。"
张晚意望向父亲,瘦弱的,背都开始弯了。父亲还不到50岁呢。
夜里,张晚意躺在炕上,听着弟弟均匀的呼吸声。月光透过窗户纸,在地上投下模糊的光斑。她想起照片上那个眼神飘忽的青年,和刘婶说"自行车票不是问题"时发亮的眼睛。
三天后,在刘婶家,张晚意见到了李国强本人。他比照片上更瘦小,坐在母亲身边像个孩子。整个"相亲"过程,都是李母在说话,从家里的三间大瓦房说到新打的家具,从儿子的稳定工作说到公社里的关系网。
"我们家国强老实,不会那些花言巧语,"李母骄傲地说,"但疼媳妇是肯定的,对吧国强?"
李国强飞快地瞥了张晚意一眼,点点头,又立刻低下头去。
张晚意注意到,每次李国强想开口,都会被母亲的眼神制止。她端着的茶水渐渐凉了,却没人提醒她喝。
回家的路上,母亲满心欢喜:"瞧瞧,多好的人家!婆婆能干,丈夫老实,你过去就是享福的。"
张晚意想说些什么,但看到母亲眼角新添的皱纹,又咽了回去。弟弟明年高中毕业,如果能进公社工作,全家的日子都会好过些。
婚事定得很快。两周后,李家送来了聘礼:一块的确良布料、两斤白糖和一张自行车票。母亲乐得合不拢嘴,邻居们也纷纷来道喜,都说张家闺女找了个好人家。
晚上,张晚意在灯下展开那块淡蓝色的确良布,打算给自己做件新衣裳。就在她抚平褶皱时,突然发现布料中间有一道明显的瑕疵,像是被什么尖锐物勾出了丝。她翻来覆去地检查,确认这不是运输造成的,而是出厂时就有的问题。
"这么好的料子,怎么会有瑕疵呢?"她轻声自语。
窗外,早春的风掠过光秃的树枝,发出呜咽般的声响。张晚意把布料紧紧抱在胸前,忽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