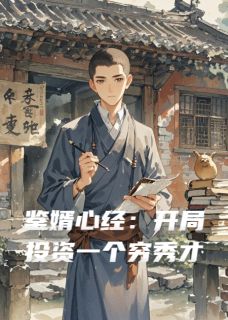
一、沈园春深思择婿媒婆口巧荐才郎姻缘二字岂由天,须向肺腑仔细参。浮华浪蕊易凋落,
松柏经冬始见坚。莫道冰人舌似簧,且睁慧眼窥真颜。东床若得真梁栋,方是家宅安稳年。
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四海升平,万民乐业。正是东京汴梁最为繁盛之时。这汴梁城内,
通衢广陌,人烟凑集,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有词《望海潮》单道这汴京好处:东南形胜,
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注:此处借用柳永词,
略加改动,因柳词虽写杭州,但其繁华景象与汴京相通,且柳永生活于仁宗朝,
符合时代背景。)在这汴梁城西,有一处清雅所在,名曰“榆林巷”。巷内住着一户人家,
家主姓沈名方,表字正圆,原也是两榜进士出身,曾在江淮之地做过几任州官。
因其为人清正,又不善逢迎,见官场倾轧,心灰意冷,便告了致仕,回到这汴京祖宅,
靠着历年积蓄并城外几处田庄、城内两间生药铺面过活。虽比不得那钟鸣鼎食之家,
却也是诗书传礼,丰衣足食,是个殷实的仕宦门第。这一日,正是暮春时节,天气和暖。
沈方在书房中临了几帖王右军的字,颇觉神倦,便信步踱至后园。但见那园中:海棠初谢,
芍药正芳。几处修篁摇翠,一池新萍泛光。蝶戏繁枝,蜂掠蕊香。端的是良辰美景,
奈何那心事悠长。你道沈方有何心事?原来他膝下只有一女,小字淑真,年方二八,
生的是容貌端丽,更兼性情温淑,自小请了先生教导,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一不晓,
乃是沈方夫妇的掌上明珠。如今女儿渐大,这婚姻之事,
便成了沈员外心头第一等要紧的勾当。寻常人家,这般年纪早已许配,只是沈方自视甚高,
等闲人物入不得他眼,故而拖延至今。正沉吟间,老仆来报:“主人,夫人请去前厅叙话,
道是东街的张媒婆来了。”沈方闻言,整了整衣冠,便往前厅来。还未进门,
便听得一阵咯咯笑声,犹如母鸡下蛋一般,正是那张媒婆。这媒婆四十上下年纪,
头上插着一朵颤巍巍的红绢花,脸上搽得雪白,穿一件绿绸衫子,系一条紫绢裙,
正与沈夫人说得热闹。见沈方进来,媒婆忙不迭起身,道了万福,
口里如同倒了核桃车子一般:“哎哟哟,给沈老爷道喜了!老爷夫人真是好福气,
**好造化!今日老婆子我,可是叼扰了一桩天大的好姻缘来!
”沈夫人笑道:“你这张婆子,惯会耍嘴。且坐下,慢慢说是哪一家?”三人分宾主坐了,
丫鬟捧上茶来。张媒婆吃了一口茶,咂咂嘴道:“夫人莫急,且听我细说。
乃是城北开国郡公王老相公家的三公子,单名一个‘珂’字。这位王公子,今年刚满二十,
真真是个潘安貌、子建才的人物!模样儿自不必说,画儿里摘下来的一般。更难得的是,
诗词歌赋,无所不精,前日在那金明池畔的诗会上,拔了头筹,
连晏相公都夸他‘后生可畏’哩!家世显赫,人物风流,与府上**,
岂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沈夫人听了,面露喜色,转向沈方道:“官人,这王郡公家,
门第确是极高的。妾身也曾听闻王家三郎才名,若果真如此,倒是一桩好亲。
”沈方却不动声色,只拈须问道:“张妈妈,这王公子既如此出众,想必平日交往甚广,
不知常与哪些朋友走动?于那经史子集、时务策论上,可也曾下过功夫?”张媒婆一愣,
旋即笑道:“哎哟我的老爷!那般显贵公子,交往的自然都是朱紫子弟、清贵官人。
平日里或是吟诗作赋,或是走马击球,都是极风雅的勾当。至于那劳什子策论,枯燥得紧,
想来王相公家世袭的恩荫,将来自然有官做,何须苦读那个?”沈方听了,微微蹙眉,
沉吟不语。张媒婆见状,忙从袖中摸出一卷花笺,递了上来:“老爷若不信,
这里有王公子亲笔所作的《咏芍药》新诗一首,是他特意让老婆子带来,请老爷品评的。
”沈方接过,展开一看,字迹倒是风流飘逸,诗云:“紫云堆里斗新妆,醉倚东风舞霓裳。
莫道春归无觅处,玉盘承露胜姚黄。”诗辞藻华丽,却也仅止于辞藻华丽而已。
沈方心下暗道:此诗如锦绣屏风,外观绚丽,内里却空无一物。这王公子,
恐怕也是个绣花枕头。但他面上却不显露,只将诗笺轻轻放在几上,道:“诗是好的。
只是婚姻大事,非比寻常,还须从长计议。”张媒婆是个人精,见沈方不甚热络,眼珠一转,
又笑道:“老爷是谨慎人,自然思虑周全。若是觉得王公子太过飞扬,
老婆子这里还有一位人选,乃是个沉稳的——南门大街‘丰和’绸缎庄刘员外的独子,
家中豪富,金山银海一般。刘员外说了,若得与沈老爷这等清贵人家结亲,聘礼愿出这个数!
”说着伸出五个手指晃了晃,“五千贯!另附城外良田百亩!那刘小官人性格最是老实,
只会埋头打理生意,从不出去胡混。**若嫁过去,那是立刻当家做主,享不尽的富贵清闲!
”沈夫人听得聘礼之厚,稍稍动容。沈方却微微一笑,问道:“这刘小官人,可曾读书?
”张媒婆讪笑道:“这个……商贾人家,倒不甚看重这个。略识得几个字,会看账本便罢了。
老爷,不是老婆子多嘴,这实实在在的富贵,可比那虚名强得多哩!
”沈方摇头道:“我沈家虽非大富,却也不贪图这些阿堵物。结亲结的是人,不是钱囊。
若只知看账算利,胸无点墨,将来何以立身?何以教子?此事不妥。”接连两桩都被驳回,
张媒婆脸上有些挂不住,强笑道:“老爷眼界高,老婆子知道了。这汴京城里适婚的才俊,
没有我不晓得的,待我再去细细访查,必能找到十全十美的,再来回禀老爷夫人。”说罢,
便悻悻告辞了。送走媒婆,沈夫人叹口气道:“官人,这张婆子虽嘴碎,但说的这两家,
论门第、论财富,都是上之选,你为何……”沈方摆手打断夫人,正色道:“夫人呐,
你且听我一言。择婿如择木,非止观其花叶之繁茂,更须察其根系之深浅,木质之坚疏。
那王家子,如春日海棠,娇艳易谢;刘家子,如盆中景栽,格局有限。淑真终身所托,
岂可轻率?”“那依官人之见,该当如何?”沈夫人问道。沈方踱至窗前,
望着庭中一株枝叶扶疏的楠木,缓缓道:“须得寻那等材质坚实,耐得风雨,即便一时埋没,
他日亦能参天而起的栋梁之材。家世钱财,俱是外物。
要紧的是此子本身的心性、志气与潜力。”正说着,忽听得窗外淅淅沥沥下起雨来。
春雨如酥,润物无声。沈方忽然想起一事,道:“是了,前月我受邀去‘文渊阁’书局,
参与校勘一批前朝典籍。席间有一李姓书生,来自京东路,寓居城外僧舍,家境似甚贫寒,
却于经史见解不凡,尤擅《春秋》决狱之理,言谈务实,不尚空谈。其风骨铮铮,
倒让我印象深刻。”“哦?竟有此事?”沈夫人奇道,“不知这书生功名如何?
”“听闻已是举人身份,只是连续两次春闱不第,盘缠将尽,
靠在书局抄写、为蒙童授课勉强度日。”沈方沉吟道,“困顿如此,而志不挫,气不馁,
每日仍手不释卷,此非寻常人也。”沈夫人蹙眉道:“如此说来,虽是有志,
然家世未免太寒薄了些。淑真若……”“夫人,”沈方转过身,目光深邃,
“莫被眼前贫寒障目。昔年吕蒙正相公未第时,也曾寄居破窑,乞食僧粥,后如何?
官至宰相,名垂青史。我看此人,眉宇间有静气,谈吐中有经纬,非久困池中之物。
眼下虽无王、刘两家的风光,却胜在根基正、材质好。”沈夫人素知丈夫看人极准,
见他如此推崇,也不由郑重起来:“既如此,官人意欲何为?”沈方道:“不急。玉在璞中,
须细察之。明日我便让沈忠(老苍头)去细细打探一番此人的日常行止、交往之人。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若果真如我所料,再计议不迟。”说罢,沈方目光再次投向窗外。
雨不知何时已停了,一抹夕阳破云而出,照在院中积水上,粼粼泛光。一架蔷薇,经雨洗过,
更显娇艳,而墙角那株楠木,新抽的嫩叶愈发青翠挺直。浪说门楣富贵长,怎如砥柱立中流。
风起青萍窥气性,云开方见月照楼。毕竟不知沈方如何派人打探那李生,且听下回分解。
二、老苍头暗市察骄纵穷举子僧寮守清贫世间真伪怎分明?须向毫微处用心。
骄马踏尘惊市井,孤灯映雪照寒衾。浮名易得终难恃,潜德无闻或可钦。莫道无人识瑾瑜,
风涛暗涌识浅深。话说沈方那日对夫人一番言语,心下已定了主意,
要细察那王、李二人根底。这并非他不信媒妁之言,实是多年宦海沉浮,阅人无数,
深知“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的道理。那显赫家世、斐然文采,
不过是锦袍之外绣,内里是人是鬼,却非深究不可。次日清晨,沈方唤来家中老仆沈忠。
这沈忠年在五十上下,头发已花白,却是沈家几代的老仆,自幼跟随沈方,极是忠心稳妥,
更兼为人木讷老实,心思却细,一双老眼见过不知多少人情世故。沈方屏退左右,
对他细细吩咐道:“今日有两桩事,要你暗中去办。
一桩是去打听那开国郡公王家三公子王珂,平日在外行止如何,交往何人,言论怎样。
另一桩,是去城南大相国寺后身的普惠僧舍,寻一个寓居在此的京东路举子,姓李名文韬的,
看他日常如何度日,与何人往来,言行可有可取之处。切记,只可暗访,不可明问,
更不可露出是我沈家之意。”沈忠垂手听了,道:“主人放心,老奴省得。
这便去市井中走走,定然打听分明。”且说沈忠领了命,也不换衣裳,
依旧是一身半旧不新的青布直裰,出了榆林巷,先往那汴梁城中最为繁华的御街行去。
他知那等纨绔子弟,多在彼处消遣。这日的御街,依旧是:香车宝马争驰过,
绣户珠帘次第开。三街六市货殖丰,九流三教人往来。吆喝声、还价声、丝竹声、笑语声,
嘈嘈杂杂,汇做一片太平气象。沈忠先在王家常订做衣裳的“瑞锦祥”绸缎庄对过茶坊里,
要了一碗廉价的“撒泡”(注:宋时一种低档茶),蹲在门口条凳上,看似歇脚,
实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多时,果见几个鲜衣怒马的少年郎,簇拥着一人而来。
中间那位,头戴束发紫金冠,身穿缕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面若傅粉,唇若涂朱,顾盼神飞,
不是那王珂王三公子又是谁?只见这一行人,径直奔向“会仙楼”。楼前伙计一见,
如同见了活财神,点头哈腰迎将进去。沈忠忙付了茶钱,也蹭到会仙楼门口,
假意与一个卖果子的老儿讨价。就听得楼内传出阵阵喧哗笑闹,丝竹管弦之声不绝。
偶尔有伙计端菜进出,门帘掀动间,可见那王公子高踞上座,左右美人斟酒,面前杯盘罗列,
正与友人高谈阔论。一个卖炊饼的小贩低声道:“瞧见没,王衙内又来了。这一顿酒席,
怕不抵得上俺们一年嚼谷!”另一个道:“嗨,人家拔根汗毛,比咱们的腰还粗哩!
只是听说……嘿嘿,时常挂账,这‘会仙楼’的掌柜,见了他是又爱又怕。”沈忠默默记下。
又在左近盘桓了约莫一个时辰,才见那王公子一行人醉醺醺出来。
王珂翻身上了一匹雪白骏马,也不顾街上行人,一扬鞭,那马便嘚嘚小跑起来,
惊得两旁摊贩慌忙避让,瓜果蔬菜滚了一地。王珂与同伴却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沈忠看得分明,那王公子脸上尽是得意之色,毫无愧疚之意。随后两日,沈忠又辗转打探。
或在王珂常去的赌坊外等候,或向那些府邸里相熟的仆役旁敲侧击。综合各处零碎信息,
拼凑起来便是:这王三公子,确是风流俊赏,文采敏捷,挥金如土,极爱热闹排场。
然性情骄纵,喜怒无常,对下人非打即骂。所交尽是同类纨绔,言谈非风月即博弈,
于经济仕途毫无兴致。更有一桩,虽未定亲,却与几个勾栏中的行首过往甚密,
名声并不十分清白。沈忠心下已自有分数,暗道:“主人所虑不差。此子如琉璃瓶儿,
看着光彩,着实易碎,非可托付之人。”探明了王公子,
沈忠便往城南大相国寺后身去寻那李文韬。这普惠僧舍乃是寺中开辟,
专供贫寒学子、行脚商人暂居,房钱低廉。但见屋舍低矮,墙皮剥落,与那御街繁华相比,
直是天壤之别。沈忠到时,已是申牌时分(下午三点至五点)。向知客僧打听李文韬,
那僧人想了想,道:“可是那京东路来的李秀才?住在最西头那间窄屋。
此刻想必还在寺前摆摊代写书信吧?”沈忠依言寻到寺前广场,果见一溜小摊。
其中一张破旧木案后,坐着一个青衫书生,正低头奋笔疾书。案前围着几个老妪、军汉。
那书生二十上下年纪,面容清瘦,衣衫浆洗得发白,却十分整洁。眉目间虽带倦色,
眼神却澄澈专注。案角放着一个粗布包袱,露出几卷书籍。沈忠假意凑上前看热闹。
只听一个老翁絮絮叨叨:“……信是寄给河间府我儿,他在那厢做个小买卖。
就说家中一切安好,让他勿念,天气转凉,早晚添衣……”那书生——李文韬——频频点头,
笔下不停,片刻便将老翁琐碎言语,凝练成一篇通达温情的家书,念与老翁听。
老翁眉开眼笑,掏出五文铜钱,千恩万谢地去了。又处理完几桩生意,天色渐晚,人迹渐稀。
李文韬这才收拾摊子,将笔墨纸砚仔细包好,又从一个破旧的钱袋里数出十文钱,
向旁边一个卖胡饼的汉子买了两个饼子,揣入怀中,便往回走。沈忠悄步跟上。
只见李文韬并未直接回僧舍,而是拐进一家名为“崇文”的小书局。书局老板似与他相熟,
笑道:“李秀才来了?今日有三册《周易集解》需抄,老价钱,五十文一册,纸墨这里出。
限期三日。”李文韬喜道:“多谢掌柜!定然如期完成。”说罢,郑重地接过书和纸墨,
这才回到普惠僧舍那间仅容一榻一几的斗室。沈忠在窗外,透过破旧窗纸缝隙向内窥看。
但见李文韬将胡饼放在几上,也顾不上吃,先点亮一盏昏黄的油灯,
小心翼翼地将新接的书稿放好。又从墙角一个瓦罐里倒出些粗茶叶末,用开水泡了,
这便是他的晚膳。一边啜着苦茶,啃着冷饼,
一边已然迫不及待地翻开那需抄写的《周易集解》,神情专注,如对珍馐。时而眉头紧锁,
时而颔首微笑,完全沉浸其中,仿佛身外寒酸,尽皆忘却。沈忠暗暗点头。
又向僧舍邻居——一个卖酸浆的老婆婆——打听。老婆婆道:“你说隔壁那后生?
可是个难得的好人!性子静,不吵闹。识文断字,却没半点架子。俺眼神不好,
他常帮俺读家信,写回执,分文不取。有时见俺担子重,还搭把手。就是忒苦了些,
一日两餐,不见荤腥,夜里那灯油味,能熏到俺屋里来。听说考了好几回没中,唉,
这世道……”正说着,忽听僧舍内传来一阵轻微的咳嗽声,持续良久。老婆婆叹道:“瞧瞧,
准是又熬夜用功,惹了寒气。前几日还病了一场,硬撑着不肯抓药,说挺挺就过去了。
”沈忠听在耳中,心下恻然。离了僧舍,他又想起主人曾说对此子学问有印象,
便又设法寻到“文渊阁”书局的伙计,假托想请个学问好的先生,问起李文韬。
伙计道:“您问李秀才?学问是好的!尤其精通《春秋》,能结合实际案例,讲得明白透彻。
前次书局校书,请了几位学子,唯他校的那部分,差错最少。东家都夸他踏实。
只是……性子太直,不会钻营,故而时运不济。”至此,沈忠已将二人情状访查得七八分。
正是:浪荡子,虚掷千金买笑,马踏长街显轻狂。穷书生,坚守一盏孤灯,
笔耕寒夜耐清霜。沈忠回到沈府,将连日所见所闻,一五一十,巨细无靡,皆回禀了沈方。
市井议论其亏空、如何访得李文韬代写书信、深夜苦读、待人厚道、乃至带病勉力支撑等情,
皆娓娓道来。沈方听罢,默然良久。夫人王氏在旁,也听得怔住了。她原更属意王家,
此刻闻得王珂如此行径,不禁面露失望后怕之色;又闻李文韬这般清苦却坚忍,
心下又生感慨。沈方长叹一声:“夫人,如今你可明白了?那王珂,如描金彩瓶,置于华堂,
徒有其表,稍遇磕碰,便成碎片。而这李文韬,却似未经雕琢的璞玉,外虽粗粝,内蕴光华,
更兼材质坚密,耐得磋磨。假以时日,稍加切磋,必成大器。贫贱不移,威武不屈,
此乃真正读书人的气节。淑真若得此良人,眼下虽稍清苦,然未来可期,终身有靠矣!
”沈夫人叹服道:“官人慧眼如炬,妾身险些误了女儿终身。只是……如此虽好,
却如何再进一步相看?总不能直愣愣去僧舍相女婿。”沈方拈须微笑,
成竹在胸:“这个不难。过几日,我便借赏玩新得的一幅《早春图》为由,
下帖请几位清谈的友人与后学子弟来家中小聚。将那王珂与李文韬,皆列在名单之上。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同槽遛遛,便知分晓。”暗涌潜流辨浊清,炎凉世态眼中明。
华堂宴设试才日,方见骐骥蹴踏平。毕竟不知沈方家中小聚,王、李二人又有何等表现,
且听下回分解。三、赏画宴才子斗机锋论实务书生显经纬华堂绮宴聚群英,
玉液珍馐列锦屏。出口成章非难事,临机决断见性情。空谈终是镜花影,
实策方为砥柱汀。莫道浮云能蔽日,真金烈火自澄明。话说沈方定了主意,要设一宴席,
邀那王珂、李文韬并几位素日相得的清谈友人,名为赏玩新得书画,
实则是要亲眼看一看这二人的言谈举止、胸中沟壑。帖子一发出去,那王珂自是欣然而来,
只道是寻常文人雅集,正是他扬才露己的好去处。李文韬接到名帖,却是踌躇良久。
他久闻沈方是致仕的清流官员,学问人品皆受推重,如今竟下帖相邀,心下又是惶恐,
又是感激。虽自惭形秽,却也不好推辞,只得将那件唯一的青衫浆洗得干干净净,忐忑赴约。
到了那日,沈家花园收拾得十分齐整。水阁凉亭,四下敞亮,壁上悬着几轴新裱的字画,
其中正中一幅,便是沈方所言《早春图》(注:假托郭熙之名),笔意苍润,气象浑成。
亭中设下两张大方桌,摆着时新果品、精巧案酒(下酒菜)。
沈方与先到的两位老友——一位是retired的国子监博士周老先生,
一位是书院的山长赵夫子——已在亭中闲谈。不多时,只听一阵说笑,王珂公子到了。
今日他更是打扮得风流倜傥,宝蓝地缠枝牡丹纹锦袍,腰系玉带,手摇一柄苏工泥金折扇,
未语先笑,上前与沈方及诸位先生见礼,言辞便给,礼数周到,引得周、赵二老也捻须微笑。
沈方亦含笑招呼。又过片刻,门子引着一人进来,正是李文韬。他一身半旧青衫,
洗得有些发白,但干净整洁。面对满园富贵、一众名流,他明显有些拘谨,步履沉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