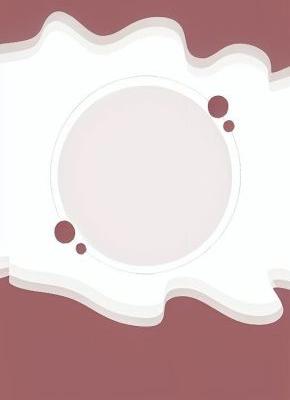
空气像是凝固的水泥,堵塞了陆宴的每一寸气管。
他倒在昂贵的手工地毯上,喉咙里发出破风箱般的嘶鸣。
视线已经模糊,只能看到落地窗前那两个交叠的剪影。
一个是他的妻子,蒋琬。
另一个,是她的男秘书,陈锐。
“药……我的药……”他艰难地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手拼命伸向茶几。
那里,放着他救命的哮喘吸入剂。
窒息感如同一张逐渐收紧的巨网,将陆宴死死包裹。
他的肺部像两个被戳破的气球,拼命收缩,却吸不进一丝氧气。
挣扎中,他看到陈锐慢步走了过来。
那个总是对他毕恭毕敬、谦卑有礼的年轻人,此刻脸上却带着一种诡异的平静。
陈锐弯下腰,捡起茶几上的蓝色吸入剂。
他没有递给陆宴。
而是拿在手里,轻轻抛了抛,像是在把玩一个无足轻重的玩具。
陆宴的眼睛因为缺氧而布满血丝,他死死盯着陈锐,又转向不远处的蒋琬。
蒋琬没有动。
她只是站在那里,冷漠地看着他,仿佛在看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陌生人。
那张他曾深爱过的美丽脸庞,此刻只剩下冰冷的线条。
不。
不对。
这不是他的药!
陆宴猛然意识到,当他按下吸入剂时,喷出的气雾没有任何他熟悉的气味,也没有丝毫缓解他症状的药效。
那感觉,就像吸了一口纯粹的、毫无用处的水蒸气。
是陈锐!
一定是他换了药!
这个念头如同一道闪电劈进陆宴混沌的大脑。
半小时前,他撞破了他们的好事。
没有激烈的争吵,也没有歇斯底里的质问。
陆宴只是推开了书房的门,然后就看到了。
蒋琬坐在他的专属座椅上,陈锐则俯身吻她,双手撑在扶手上,形成一个禁锢的姿态。
两人衣衫还算齐整,但那种狎昵到骨子里的氛围,比赤身裸体更让人作呕。
听到开门声,他们甚至没有立刻分开。
陈锐只是慢条斯理地直起身,回头看了陆宴一眼,嘴角甚至还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而蒋琬,她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领口,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谈论天气。
“你回来了。”
陆宴的心在那一刻沉到了谷底。
他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退了出去,关上了门。
巨大的屈辱和背叛感让他胸口发闷,几乎喘不过气。
他回到客厅,瘫坐在沙发上,多年的哮喘病史在剧烈的情绪波动下被诱发。
他记得很清楚,他拿出药瓶准备自救。
就在那时,陈锐从书房走了出来。
“陆先生,您不舒服吗?”陈锐关切地问,快步走到他身边,“药给我,我帮您。”
当时陆宴已经有些呼吸困难,没有多想,便把吸入剂递给了他。
陈锐的动作很快,快到陆宴没看清他是否做了什么手脚。
现在想来,他当时背对着自己,有一个极其短暂的遮挡动作。
就是那个瞬间!
他换了药!
他们不仅背叛了他,还想要他的命!
陆宴的瞳孔骤然收缩,求生的本能让他爆发出最后的力量。
他放弃了呼救,转而用指甲狠狠掐进自己的掌心。
剧痛让他混沌的意识清醒了一瞬。
不能死在这里。
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他用尽全身力气,翻了个身,头部重重地撞向茶几的金属桌角。
“砰!”
一声闷响,伴随着额角传来的剧痛和温热的液体,陆宴的身体猛地一抽,然后彻底瘫软下去。
他的眼睛缓缓闭上,呼吸也似乎停止了。
客厅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死了?”
蒋琬的声音终于响起,带着一丝不确定。
陈锐没有回答,他蹲下身,伸出手指,探向陆宴的鼻息。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无限拉长。
陆宴能感觉到那根冰冷的手指停留在自己鼻下的皮肤上,带着一丝试探的压力。
他早已用掐烂掌心的剧痛强迫自己进入了龟息状态。
这是一种他幼时跟一位老中医学习的保命技巧,通过极限收缩肌肉和控制心跳,模拟出假死的状态。
代价极大,但此刻,是他唯一的生机。
“没气了。”
陈锐的声音很轻,却像一把锤子,砸在陆宴的心上。
他慢慢收回了手。
蒋琬走了过来,高跟鞋踩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嗒嗒”声。
她停在陆宴的“尸体”旁,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
“处理干净点。”
她的声音里没有半分悲伤,只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冷漠。
“放心吧,琬姐。”陈锐的声音带着一种邀功似的温柔,“救护车我已经叫了,就说是他自己哮喘急性发作,没抢救过来。药瓶上有他的指纹,谁也查不出问题。”
陆宴的心彻底凉了。
原来一切都设计好了。
从他进门那一刻起,他们就在等他发病,等他自己走进这个死亡陷阱。
他甚至能想象到后续的剧本。
悲痛欲绝的遗孀,忠心耿耿的秘书,一场意外离世的悲剧。
而他,陆宴,这个一手创建了商业帝国的男人,最终会成为别人故事里一个懦弱无能、因病猝死的背景板。
他的亿万家产,他奋斗一生得来的一切,都将顺理成章地落入这对狗男女的手中。
绝不!
陆宴的意识在黑暗中咆哮。
只要他还有一口气,他就不会让他们如愿。
他能感觉到陈锐正在擦拭那个伪造的药瓶,然后小心翼翼地塞回他的手中。
冰冷的金属触感,像一条毒蛇。
“琬姐,你先回书房。”陈锐的声音再次响起,“等下救护车来了,你再出来,记得……情绪要到位。”
“知道了。”
蒋琬转身离开,没有再看地上的“丈夫”一眼。
客厅里只剩下陈锐和陆宴。
陆宴能感觉到陈锐的目光在自己身上停留了很久。
那目光里充满了审视和一丝隐藏不住的得意。
仿佛在欣赏一件完美的艺术品。
一件由他亲手完成的,名为“谋杀”的艺术品。
突然,陆宴感觉到自己的手被轻轻抬了起来。
紧接着,一股尖锐的刺痛从他的指尖传来。
陈锐……在用针扎他!
他在确认他是不是真的死了!
这个人心思缜密,手段狠辣,远比他想象的更加可怕。
陆宴的身体本能地想要抽搐,却被他用意志死死压制住。
他将所有的感知都集中在掌心被自己掐烂的伤口上,用那里的剧痛来抵消指尖的刺痛。
一下,两下,三下。
针尖刺破皮肤,带来一阵阵钻心的疼。
陆宴的额头渗出细密的冷汗,但他依旧像一具真正的尸体,纹丝不动。
终于,陈锐似乎放弃了。
他松开了陆宴的手。
陆宴能听到他长舒一口气的声音。
然后是手机拨号的声音。
“喂,120吗?这里是XX小区,有人哮喘发作昏迷了,你们快来!”
陈锐的声音充满了焦急和恐慌,演技堪称完美。
挂断电话后,他没有立刻离开。
而是又在陆宴身边站了一会儿。
陆宴能感觉到,陈锐的脚尖,轻轻碰了碰他的脸。
那是一个极具侮辱性的动作。
充满了胜利者的炫耀和对失败者的践踏。
陆宴的拳头在身侧死死攥紧,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
他记住了这个感觉。
他发誓,总有一天,他会让陈锐用他的头来偿还!
远方传来救护车模糊的鸣笛声,由远及近。
陈锐终于转身,快步离开了客厅。
陆宴紧绷的身体在这一刻才敢有了一丝丝的松懈。
他缓缓地、极其微弱地吸了一口气。
空气,带着血腥味和求生的渴望,涌入他的肺部。
游戏,现在才刚刚开始。
救护车的鸣笛声刺破了小区的宁静。
陆宴被抬上担架的时候,蒋琬“恰好”从书房冲了出来。
她的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震惊和悲痛,眼眶泛红,声音颤抖。
“陆宴!陆宴你怎么了!”
她扑到担架边,试图抓住陆宴的手,却被一旁的陈锐“体贴”地拦住。
“蒋总,您冷静点,让医生先救人!”
陈锐的表演同样无可挑剔,他眉头紧锁,满脸焦急,仿佛真的在为陆宴的生命担忧。
好一对情深义重的“主仆”。
陆宴闭着眼睛,任由他们表演。
他的身体因为长时间的缺氧和假死而虚弱不堪,但他大脑的每一个细胞都在高速运转。
他不能在医院里醒来。
一旦医生宣布他没有生命危险,蒋琬和陈锐就会立刻知道他没死。
那等待他的,将会是第二轮、第三轮,更加隐秘和致命的谋杀。
他必须创造一个让他们绝对放心的“结果”。
担架被抬上救护车,车门即将关上的瞬间,陆宴用尽最后的力气,猛地睁开眼睛,死死盯住了车外的蒋琬。
他的眼神里没有愤怒,没有怨恨,只有一种濒死之人深深的眷恋和不舍。
然后,他的头无力地垂下,一只手也从担架边缘滑落,仿佛彻底失去了生命的气息。
蒋琬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
她对上了陆宴那最后一眼。
陆宴敢肯定,她看懂了。
她看懂了那眼神里的“爱意”,也因此,会更加确信他的“死亡”。
因为一个深爱着她的男人,在临死前,是不会怀疑她的。
这才是最完美的催眠。
救护车内,医生立刻开始抢救。
“病人没有自主呼吸!”
“心跳停止!”
“准备电击!”
电流穿过身体的瞬间,陆宴的身体剧烈地弹起,但他依旧凭借强大的意志力,控制着心脏,不让它恢复跳动。
一次,两次……
医生的额头渗出了汗水。
“肾上腺素一支!”
冰冷的液体被注入血管,药物的强烈**让陆宴几乎失控。
他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攥住,想要疯狂地跳动起来。
压下去!
陆宴在意识的深海中对自己怒吼。
他将所有的意念都集中在一点,死死扼住那颗躁动的心脏。
“不行,还是没有反应。”
随车的护士声音里带上了绝望。
医生叹了口气,放下了电击板。
“记录死亡时间。”
这五个字,对陆宴来说,如同天籁。
他成功了。
在医学上,他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他能感觉到护士在记录着什么,医生摘下了手套,车内的气氛一片沉重。
没有人再关注他这个“死人”。
这给了他宝贵的机会。
在药物的作用下,他的身体机能正在缓慢恢复。
他必须在抵达医院,被送进太平间之前,找到脱身的机会。
救护车在行驶,窗外的光影飞速掠过。
陆宴估算着路线和时间。
快到医院了。
就在救护车转过一个弯,速度减慢的瞬间。
陆宴的眼睛猛地睁开。
他没有丝毫犹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担架上翻身而起,一把拉开车门,跳了下去!
车上的医生和护士被这突如其来的“诈尸”吓得魂飞魄散,尖叫声响彻车厢。
陆宴在地上翻滚了一圈,卸掉冲击力,然后不顾一切地冲向旁边的绿化带。
他额头的伤口因为剧烈的动作再次裂开,鲜血模糊了他的视线,但他一步也不敢停。
身后传来了急刹车和混乱的呼喊声。
他不能被抓住。
一旦被抓住,他假死的事情就会立刻暴露。
蒋琬和陈锐会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扑上来,将他撕成碎片。
他钻进茂密的灌木丛,像一只受伤的野兽,拼命向着黑暗的深处逃窜。
不知跑了多久,直到身后的声音彻底消失,他才敢停下来。
他靠在一棵大树上,剧烈地喘息着,肺部**辣地疼。
他掏出手机。
屏幕上,是蒋琬发来的十几条未读信息。
“老公,你怎么样了?”
“医生怎么说?”
“你别吓我!”
每一条都充满了“关切”和“焦急”。
紧接着,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是陈锐。
陆宴的眼中闪过一丝冰冷的寒意。
他没有接,直接挂断,然后关机。
他不能暴露自己的任何位置信息。
现在,他必须找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
一个蒋琬和陈锐绝对找不到的地方。
陆宴的脑海里闪过一个人。
李默。
他最信任的私人律师,也是他大学时的死党。
陆宴捂着流血的额头,辨认了一下方向,朝着市中心一处老旧的居民楼走去。
那里是李默的一处安全屋,只有他们两人知道。
一个小时后,满身狼狈的陆宴敲响了那扇不起眼的防盗门。
开门的是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男人。
李默看到陆宴的样子,脸上的从容瞬间消失。
“老陆!你这是怎么了?”
他赶紧把陆宴拉进屋,关上了门。
“先进来,快!”
屋内的陈设很简单,但一应俱全。
李默扶着陆宴在沙发上坐下,然后迅速拿出医药箱。
“到底怎么回事?跟人火拼了?”
李默一边用酒精棉球清理着陆宴额头的伤口,一边紧张地问。
“嘶……”陆宴疼得倒吸一口凉气,“比火拼还严重。”
他抬起头,看着李默,一字一句地说道:“蒋琬和陈锐,想杀了我。”
李默的手猛地一顿,酒精棉签掉在了地上。
他脸上的震惊无以复加。
“你说什么?蒋琬?还有她那个秘书?”
陆宴点了点头,将今天发生的一切,从撞破**到被换药,再到假死脱身,全都简略地说了一遍。
李默听完,脸色变得铁青。
他摘下眼镜,用力揉了揉眉心,似乎在消化这个惊人的消息。
“王八蛋!这对狗男女!”李默一拳砸在桌子上,“他们竟然敢这么做!”
“冷静点。”陆宴的声音异常平静,“现在发火没用。”
李-默看着陆宴。
他发现,自己这个好友的眼神变了。
以前的陆宴,虽然在商场上杀伐果断,但面对蒋琬时,眼神总是温柔的。
而现在,那份温柔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冰封千里的寒冷和深不见底的算计。
“你想怎么做?”李默重新戴上眼镜,镜片后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
陆宴靠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似乎在积蓄力量。
再次睁开时,他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
“他们想让我死,那我就‘死’给他们看。”
“我要让他们在最得意的时候,从天堂坠入地狱。”
“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然后,让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vei付出代价。”
李默看着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好,我帮你。”
“第一步,我需要你帮我办一件事。”陆宴看着李默,“帮我以匿名的形式,向警方报案。”
李默愣了一下:“报案?报什么案?”
陆宴的目光投向窗外无尽的黑夜。
“就报……海天别墅区,发生了一起疑似入室抢劫杀人案,死者,名叫陆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