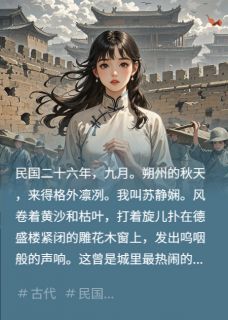
与此同时,在城东破败的城隍庙里,另一场私下的会面也在进行。
警察局长李万山,这个平日里总是满脸堆笑、八面玲珑的“笑面虎”,此刻却脸色阴沉,眼中闪烁着狡黠和不安的光芒。他面前站着两个穿着普通百姓衣服、却眼神凶狠、带着戾气的汉子。他们是城里有名的地痞头目,手下纠集着一批亡命之徒。
“都听清楚了?”李万山压低了声音,像毒蛇吐信,“七天后,德盛楼投票!姓陆的和他手下那帮丘八,是铁了心要拉着全城人陪葬!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一个脸上有刀疤的汉子啐了一口:“李局长,您就说怎么办吧!弟兄们听您的!他妈的,好死不如赖活着!投降日本人怎么了?换个主子吃饭而已!”
“对!姓陆的和姓周的想当英雄,老子们可不想当炮灰!”另一个矮壮的汉子附和道。
李万山眼中闪过一丝狠厉:“投票那天,见机行事!如果姓陆的占了上风……哼!”他没说下去,只是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制造点混乱,让那帮泥腿子知道,跟着姓陆的只有死路一条!让陈启明那帮软蛋看看,想活命,就得听我们的!”他掏出几块大洋,塞给两人,“去,联络可靠的兄弟,到时候听我信号!”
打发走两个地痞,李万山独自站在破败的城隍爷神像前,脸上阴晴不定。他并非不怕日本人,但他更怕失去现在的权势和搜刮来的财富。他深知自己手上不干净,陆文远早就对他不满。一旦城破,跟着陆文远死战,他必死无疑。如果投降,凭借他警察局长的身份和手下这些人马,或许还能在新主子面前谋个位置。为了活命和利益,他选择了背叛。阴险的种子,在恐惧的土壤里悄然发芽。
而在尘土飞扬的城墙上,周振武和赵烽靠在一个沙袋掩体后,短暂地休息。夕阳将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大哥,”赵烽的声音依旧低沉,却带着一丝忧虑,“城里……人心不稳。李万山那老狐狸,还有陈启明那边……”
周振武拿起水囊灌了一大口水,水顺着他干裂的嘴角流下。他抹了一把脸,眼神冷硬如铁:“管不了那么多了!该来的总会来!我们只管把城守好,能多杀一个鬼子,就赚一个!”他拍了拍赵烽的肩膀,“兄弟,怕吗?”
赵烽摇摇头,目光下意识地望向城墙下,那里隐约能看到一个穿着粗布衣服、正在帮忙抬石头的娇小身影——苏静姝。“不怕。”他顿了顿,声音更低沉了些,“就是……有点放不下。”
周振武顺着他的目光看去,脸上那道狰狞的疤痕似乎也柔和了些许。他沉默了片刻,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油纸包着的小布包,递给赵烽。“拿着。”
赵烽疑惑地打开,里面是一块成色很好的羊脂玉佩,上面刻着一个小小的“安”字。
“这是我娘……留给我的。”周振武的声音有些干涩,“说是给我未来媳妇的……怕是……等不到了。”他看向赵烽,眼神复杂,“若真到了那一天……你……帮我给她……留个念想。”他没有说“她”是谁,但目光却不由自主地飘向远处女校的方向。
赵烽握紧了那块温润的玉佩,感觉它像烙铁一样烫手。他明白了团长的意思。“大哥……”他想说什么,却哽住了。
“别婆婆妈妈的!”周振武猛地站起身,恢复了那副冷硬的模样,仿佛刚才那一瞬间的柔情只是幻觉,“走!去西边看看!那段墙太薄了!”他大步流星地走开,背影在夕阳下显得孤独而决绝。
赵烽默默地将玉佩贴身藏好,看了一眼城下那个忙碌的小身影,眼神变得更加坚毅,快步跟了上去。悲壮之中,那一点点关于未来的、无法实现的念想,更显得锥心刺骨。
第六天。距离最后的通牒期限,只剩下一天了。
一种山雨欲来的压抑感,笼罩着整个朔州城。恐惧仿佛达到了顶点,又似乎被一种麻木的平静所取代。街头巷尾,人们不再议论,只是默默地做着最后的准备,或是等待命运的宣判。
傍晚,文远回来了。他显得异常平静,甚至比前几天都要平静。只是那平静之下,是一种尘埃落定的决绝。
他简单地吃了点东西,然后把我叫进了书房。油灯的火苗跳跃着,将他清癯的身影投射在斑驳的墙壁上,像一个巨大的、即将远行的魂灵。
“静娴,”他轻声唤我,声音温和得让我心碎,“替我写封信吧。”
我心头猛地一沉,不祥的预感如同冰冷的潮水瞬间将我淹没。
“给明诚的。”他补充道。明诚,我们唯一的儿子,远在千里之外相对安全的重庆读书。他才十六岁。
我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模糊了视线。“不……文远……不要……”我摇着头,泣不成声。
他走到我身边,轻轻握住我冰冷颤抖的手,将一支笔塞进我手里。他的手依旧冰凉,却带着一种安抚人心的力量。“静娴,听话。”他的声音很轻,却有着不容拒绝的坚定,“告诉他,他的父亲,没有给他丢脸。告诉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告诉他……好好读书,将来,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一个再也不会任人欺凌的中国……一个能让他的子孙后代,挺直腰杆做人的中国……”
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钝刀,在我心上来回切割。我被他按在书案前,铺开信纸。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大颗大颗地砸落在洁白的宣纸上,晕开一片片绝望的湿痕。我握着笔,手抖得根本无法控制。墨汁滴落,污了纸面。我试图模仿他平日的字迹,可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像垂死之人的挣扎。
“别怕,慢慢写。”他站在我身后,一只手轻轻按在我的肩膀上,仿佛在传递他最后的力量和温度。
我咬着嘴唇,几乎要咬出血来。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仿佛在刻下他的墓志铭:“吾儿明诚,见字如晤。朔州危殆,日寇兵临城下……父为县长,守土有责,义无反顾……汝当勤奋向学,勿忘家国之恨……他日学成,当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父虽死,精神长存……勿悲,勿念,以父为荣……”
写到“以父为荣”四个字时,巨大的悲痛终于击垮了我。我再也握不住笔,伏在案上,失声痛哭。肩膀剧烈地颤抖,仿佛要把五脏六腑都哭出来。
文远没有劝我。他沉默地站着,任由我宣泄着这撕心裂肺的悲伤。过了许久,久到我以为眼泪已经流干,他才俯下身,轻轻地、极其短暂地抱了抱我。那个拥抱,轻得像一片羽毛落下,带着诀别的气息。
“静娴……对不住……”他的声音哽住了,后面的话,消散在浓重的夜色里。
他拿起那张被泪水浸染得字迹模糊的信纸,仔细地折好,放进一个信封,郑重地封上口,放在书案最显眼的位置。然后,他转过身,背对着我,望着窗外深沉的、没有一丝星光的夜空,久久沉默。
我知道,他已经做出了选择。不,是他从未有过第二个选择。那个曾经怀抱教育救国理想的青年,最终选择以最惨烈的方式,践行他对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的承诺——用生命。
那一夜,我抱着膝盖,蜷缩在冰冷的床角,睁着眼睛,看着窗外的黑暗一点点吞噬世界。那封被我藏在梳妆盒里的“投降书”,像一个巨大的讽刺,灼烧着我的灵魂。我悄悄将它取出来,在油灯上点燃。跳跃的火苗吞噬着那屈辱的字迹,也吞噬着我最后一点自私的幻想。灰烬落下,如同我死寂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