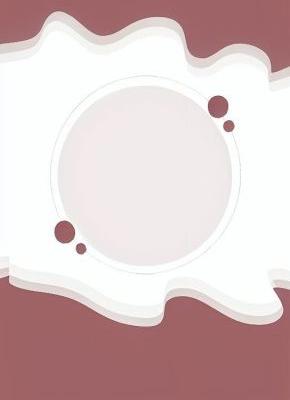
雨下得很大,铁皮屋顶被砸得咚咚响。
弟弟突然发高烧,咳血。我妈抱着他哭,我爸翻遍家里只找到几十块钱。
“送医院!快送医院!”我妈吼。
“送什么送?哪来的钱?”我爸也吼。
“我不管!你要是不送,我就抱着他从这楼上跳下去!”
我爸盯着她看了很久,狠狠踹了桌子一脚,拿起车钥匙:“走!”
医院里,医生检查后脸色凝重:“肺炎,要住院。先交三千押金。”
三千。
我爸和我妈面面相觑,最后我爸看向我:“今晚你去,找老张,问有没有急活,价格好说。”
我知道“急活”的意思——那些别人不愿意接的,有特殊要求的,下手没轻重的。
“好。”我说。
那晚的客人喝了酒,下手很重。结束后我几乎站不起来,但他给了两千。
“告诉老张,下次还找这丫头。”他醉醺醺地说。
我捏着钱,扶着墙走出房间。每一步,地上都留下血脚印。
我妈在车里看见我,冲过来,话没说完就看见我裙子上的血。
“钱。”我把钱递给她。
她接过钱,手指颤抖,抬头看我时眼里有什么闪了一下,但很快熄灭。
“上车。”声音嘶哑。
车上,她递来止痛药。我吞下药,闭上眼睛。
疼痛像潮水。
弟弟的医药费解决了,但我的身体垮了。高烧三天,伤口发炎流脓。第四天我能下床了,镜子里的脸苍白浮肿,眼睛深陷。
“今晚……”我妈在门口欲言又止。
“我去。”我说。
“你能行吗?”
“不行也得行。”我转身看她,“不是吗?”
她避开我的眼睛,转身走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突然笑起来,笑着笑着眼泪流下来。
那晚的客人身上有浓重烟味。结束后,他给了我一整块巧克力,不是糖。
“吃吧,补补。”他语气居然温和。
我握着巧克力回到家。我妈照例递给我一块糖,橙色的。
我把糖和巧克力放进口袋,回家后把橙色糖纸放进铁盒。
十三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