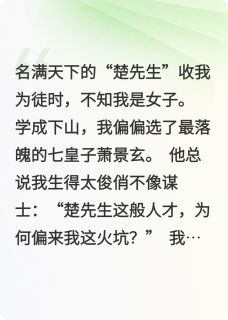
名满天下的“楚先生”收我为徒时,不知我是女子。学成下山,
我偏偏选了最落魄的七皇子萧景玄。他总说我生得太俊俏不像谋士:“楚先生这般人才,
为何偏来我这火坑?”我助他破粮草困局,解巫蛊之祸。他替我挡暗箭,
在寒夜里捂热我冻僵的手。直到那日刺客的剑刺穿我肩胛,他撕开我染血的衣襟。
满殿哗然中,他抖着手为我系好衣带:“管你是男是女...”“你都是我的楚先生。
”登基大典那日,他当众掀开我的官帽。青丝如瀑倾泻而下时,他笑着将凤印塞进我手里。
“女相还是帝后?选一个。”我反手扣住他手腕:“陛下,奏折批完了吗?
”建安十七年的秋雨,下得格外暴烈,像是天被捅穿了窟窿。
豆大的雨点砸在破庙腐朽的窗棂上,噼啪作响,震得屋顶的灰尘簌簌往下落。
风从四面八方灌进来,带着刺骨的湿寒,卷动着庙中央那堆将熄未熄的篝火,火苗挣扎着,
忽明忽暗,映着角落里一张年轻却过分沉静的脸。楚瑶裹紧了身上半旧的青布棉袍,
袍子宽大,越发衬得她身形单薄。她蜷在角落的干草堆上,尽量汲取着那一点微弱的暖意。
火光在她清俊的脸上跳跃,勾勒出挺直的鼻梁和紧抿的薄唇,
那双眼睛却沉静得如同古井深潭,映着跃动的火苗,也映不出太多波澜。只有她自己知道,
这看似平静的表象下,藏着多少初次踏入这纷乱棋局的紧张与谨慎。
师父“楚先生”的名头是她的敲门砖,也是悬顶的利剑,
女扮男装的身份更是稍有不慎便粉身碎骨的秘密。此行下山,每一步都如履薄冰。
破庙的门板被风猛地撞开,发出一声刺耳的**。一股裹挟着水汽和血腥味的冷风直灌而入,
瞬间压得篝火几乎熄灭。几个人影挟着风雨踉跄闯入,
沉重的脚步声和压抑的喘息打破了庙里的死寂。为首一人身材高大,即便浑身湿透,
肩臂处洇开一团深色,显然带着伤,也难掩那份骨子里的挺拔和迫人的气势。
雨水顺着他棱角分明的下颌不断滴落,打湿了鸦青色的劲装,更添几分狼狈中的桀骜。
他身后跟着两个同样狼狈却眼神精悍的护卫,警惕地扫视着庙内,目光如刀,
最终定在角落那个不起眼的青衫书生身上。楚瑶眼皮都没抬一下,
仿佛闯入的不过是一阵稍大的风。她只不动声色地将身体往阴影里又缩了缩,手拢在袖中,
悄然按住了藏于袖袋的冰冷短刃。篝火在冷风的侵袭下奄奄一息,几近熄灭。
那高大男子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目光锐利地扫过庙堂,最终落在角落里那堆将熄的火堆上。
他声音低沉,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生火。”两个护卫立刻应声,
其中一人走向角落的干草堆,打算扯些助燃。然而他刚伸出手,
一只脚便无声无息地踩在了那堆干草上。护卫动作一顿,愕然抬头。
只见那青衫书生不知何时已站在草堆旁,依旧是那副低眉顺眼的模样,声音却清清冷冷,
如同碎玉投珠:“兄台,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这草,是在下备下的。
”她说话时并未看那护卫,目光平静地投向篝火旁的高大男子——七皇子萧景玄。
空气瞬间凝滞。护卫的手按在了刀柄上,眼神凶狠。萧景玄眼中闪过一丝极淡的诧异,
随即化为审视的寒光,锐利地钉在楚瑶身上,似乎要将这不知天高地厚的穷酸书生看穿。
雨声和风声仿佛都远去了,只剩下篝火偶尔爆裂的噼啪声和无声的剑拔弩张。“哦?
”萧景玄缓缓开口,声音带着一丝疲惫的沙哑,却更显压迫,“若本王……偏要呢?
”他刻意顿了一下,点明身份,目光如鹰隼般锁定楚瑶的脸,不放过任何一丝细微的变化。
楚瑶脸上没有出现预想中的惊恐或谄媚。她甚至微微抬起了头,
火光终于清晰地照亮了她的眉眼。那是一张过分清俊、甚至堪称昳丽的脸,皮肤白皙,
眉眼如画,若非神情中那份超乎年龄的沉稳和眼底深藏的锐利,几乎会让人疑心是女子。
她迎上萧景玄审视的目光,嘴角竟勾起一个极浅、极淡的弧度,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
像是嘲讽,又像是洞悉一切的了然。“殿下,”她的声音依旧平静无波,
仿佛在陈述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您负了伤,血染衣袍。您的护卫,左肩微沉,
右手下意识护肋,步履滞涩,内腑震荡之象已显。另一位,气息粗重不稳,显是力竭。
这庙宇破败,门板腐朽,风急雨骤,追兵……”她顿了顿,目光扫过庙外浓墨般的雨夜,
“想必已近。您要这堆草生火取暖,照亮此间,是怕引不来追兵,还是怕他们找不着靶心?
”她每说一句,萧景玄和他护卫的脸色就沉下一分。她指出的伤势、状态,分毫不差!
尤其那句“引不来追兵”和“靶心”,像冰冷的针,精准地刺破了萧景玄此刻强撑的镇定,
直指他处境的核心——狼狈与危险。护卫的刀已半出鞘,寒光在昏暗的火光中一闪。
萧景玄却猛地抬手,制止了护卫的动作。他死死盯着楚瑶,眼中风暴翻涌,
震惊、警惕、一丝被戳破窘境的恼怒,还有更深沉的探究。“你是谁?”他声音低沉,
每一个字都像从齿缝里挤出。楚瑶轻轻拂了拂沾了灰尘的袍袖,动作从容不迫。“在下楚瑶,
”她微微躬身,行了一个标准的书生礼,姿态不卑不亢,“山野鄙人,蒙恩师不弃,
曾随‘楚先生’读过几卷书,略知世事。”“楚先生”三个字,被她平平淡淡地吐出,
却像一块巨石投入死水潭,瞬间在萧景玄心中激起千层浪!名动天下的隐士楚先生!
其门生故旧遍布朝野,得其指点一二者,无不视为莫大机缘。
眼前这个看似弱不禁风的年轻书生,竟是那等传奇人物的弟子?萧景玄眼中的风暴瞬间平息,
取而代之的是难以言喻的复杂光芒——难以置信、狂喜的灼热、巨大的疑虑。
一个楚先生的弟子,为何会出现在这荒郊野外的破庙?又为何如此精准地撞破自己的困境?
这究竟是上天送来的转机,还是一个精心布置、诱他入彀的陷阱?
这念头如毒藤般缠绕上心尖,让他后背无端生出一层寒意。“楚先生?”萧景玄重复了一遍,
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干涩,目光如炬,要将楚瑶的灵魂都烧穿,“如何证明?
”楚瑶没有直接回答。她从容地走到篝火旁,无视那两名护卫依旧警惕如狼的目光,蹲下身,
慢条斯理地拨弄起将熄的余烬。她的动作带着一种奇特的韵律感,专注而沉静。
几根枯枝被她巧妙地搭起,留出恰到好处的通风空隙。她并未用那堆干草,
而是从自己随身的包袱里摸出几片薄如蝉翼、似乎经过特殊处理的树皮,指尖一捻,
竟有微弱的火星溅出,精准地落入她搭好的柴枝空隙中。“蓬”一声轻响,
一点微弱的橘红色火苗顽强地跳了出来,贪婪地舔舐着枯枝。这手生火的本事,干净利落,
绝非寻常书生所能为。火苗渐起,照亮了楚瑶半边沉静的侧脸。她这才抬眼,看向萧景玄,
目光平静无波:“殿下今夜所遭伏击,东宫卫率所用箭簇,乃工部新制的三棱破甲锥。
此物打造费时,数量有限,唯太子亲卫及北境王帐精锐有配。
此地距北境千里之遥……”她话语点到即止,剩下的话不言而喻——伏击者,
必是东宫太子的人无疑!萧景玄瞳孔骤然收缩!这新制箭簇的机密,
连他也是在一次极其偶然的机会才窥知一二。眼前这个自称楚先生弟子的年轻人,
竟如此轻描淡写地道破!若非真得楚先生真传,洞悉天下兵事,如何能知?那点疑虑,
在这冰冷确凿的事实面前,如同薄冰般碎裂开来。他猛地向前一步,
高大的身影几乎将楚瑶笼罩,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紧:“先生何以教我?
”“先生”二字脱口而出,已带上了敬重与急切的期冀。
楚瑶看着眼前这双燃烧着求生与渴望火焰的眼睛,心中轻轻喟叹。这潭浑水,
终究是避无可避了。她目光投向庙外肆虐的风雨,声音不大,
却清晰地穿透雨幕:“雨急风骤,追兵善骑。此去东南三里,有洛水旧道,河道淤塞,
泥泞难行,人马皆陷。殿下此刻,当‘反其道而行之’。”她顿了顿,
指尖在冰冷的地面上迅速划过几道简略却清晰的线条:“不向北,不向西,掉头向南。
南面官道旁,有一处废弃的砖窑。追兵料定殿下急于北返或西遁,
必在洛水与西山隘口重兵设伏。那砖窑,此刻便是灯下之黑,最安全处。
”萧景玄听得心头剧震!这逆向而行的思路,大胆到近乎疯狂,
却又精准地切中了他和追兵的心理盲区!他脑中飞速权衡,楚瑶点出的“灯下之黑”,
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他眼前的迷雾。那废弃砖窑的位置,他依稀记得!“好!
”萧景玄猛地一握拳,眼中迸发出孤注一掷的决绝光芒,“就依先生之计!走!
”他再无半分犹豫,对两名护卫下令。“殿下!”一名护卫急道,眼神依旧警惕地扫过楚瑶,
“此人……”他话未说完,但意思昭然若揭。萧景玄抬手打断,目光灼灼地看向楚瑶,
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邀请,或者说,是一种强势的“绑票”:“楚先生高才,景玄身陷险境,
前途未卜,恐有负先生指点。先生若不弃,可否同行一程?景玄定以师礼相待,护先生周全!
”他语气诚挚,姿态放得极低,但那眼神深处,
却是不容置疑的强势——这送上门的“楚先生”,他绝不可能轻易放走。楚瑶心中了然。
这一步踏出,便再无回头路。她看着萧景玄眼中那混合着恳求与霸道的火焰,最终,
几不可察地点了点头。---王府书房,松烟墨的冷冽气息与古籍特有的陈旧纸香混合,
萦绕在略显压抑的空气里。窗外日光正好,却驱不散室内沉甸甸的凝重。
巨大的舆图铺展在紫檀木案上,山川河流、关隘城池历历在目,
而象征七皇子封地的那一小块区域,被朱砂残酷地圈了出来,
旁边一行小字触目惊心:粮道断绝,存粮不足半月。萧景玄一身玄色常服,负手立于案前,
眉头拧成一个深刻的“川”字。他身形依旧挺拔,但连日来的巨大压力,
在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上刻下了难以掩饰的疲惫。他修长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舆图边缘,
指节因用力而微微泛白。书房内侍立的心腹幕僚和将领们,个个屏息凝神,脸色灰败,
空气仿佛凝固的铅块。“北境军需催逼日急,太子那边扣着漕粮不放,
地方官仓推诿搪塞……”萧景玄的声音低沉,带着压抑的怒火和深深的无力,
“难道真要本王开仓放赈,坐等饿殍遍野,授人以柄?或者……”他猛地一拳砸在舆图上,
发出沉闷的声响,“强行征调?那与激起民变何异!”这几乎是个无解的死局。
无论选择哪条路,都是饮鸩止渴,将把柄亲手送到政敌面前。压抑的死寂中,
一个清越的声音平静地响起,打破了沉重的僵局:“殿下,何不‘借’粮?”众人循声望去。
只见楚瑶端坐在窗下的一张圈椅中,身姿清瘦,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靛蓝布袍,
越发显得气质疏淡。她手里捧着一卷摊开的书,目光却并未落在书页上,而是越过窗棂,
望着庭院里一株开得正盛的白玉兰,神情恬淡,仿佛刚才那句石破天惊的话并非出自她口。
“借?”萧景玄猛地转身,目光如电般射向楚瑶,带着一丝荒谬和不敢置信的急切,
“向谁借?太子?皇后?还是那些等着看本王笑话的藩王?他们巴不得本王立刻倒台!
”楚瑶这才缓缓将目光从窗外收回,落在萧景玄焦灼的脸上。她放下书卷,起身走到舆图前,
指尖轻轻点在朱砂圈出的区域之外,一个毫不起眼、甚至有些偏僻的小城标记上——平陶县。
“非是向虎狼借,”她指尖轻叩平陶县的位置,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是向‘死人’借。
”“死人?”萧景玄和众人都是一愣,不明所以。
楚瑶唇角似乎勾起一丝极淡、近乎狡黠的弧度:“平陶县令钱庸,贪婪成性,尤好囤积居奇。
去岁江南大水,他趁机低价购入大批陈粮,以次充好,堆满私仓,
只待今春青黄不接时高价抛出,牟取暴利。”她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惊疑不定的脸,
“此人,前日暴毙于外室宅中,死因……颇为不雅,家中正乱作一团,唯恐丑闻外泄,
极力遮掩。”萧景玄眼中精光一闪,
瞬间抓住了关键:“先生是说……趁他钱家慌乱遮掩丑事、无暇他顾之时,
以雷霆手段‘借’走他那批见不得光的黑心粮?”“正是。”楚瑶颔首,
指尖在舆图上迅速划出一条隐秘的路线,“钱家私仓位于平陶城外荒山,守卫松懈。
殿下可遣一队精锐,扮作流寇山匪,夤夜突袭,只取粮草,不伤人命,不留痕迹。同时,
在封地内,大张旗鼓,假意开仓放赈,做足姿态,吸引各方视线。”她抬起头,
目光沉静如水,迎向萧景玄灼热的视线:“此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钱家失粮,
必不敢声张,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自认倒霉。殿下得粮,解燃眉之急,赈济灾民,
稳住后方。至于北境军需……”她话锋一转,带着一丝冷峭,“太子既扣着漕粮,
殿下不妨将此事‘不经意’地漏给北境那位刚直不阿的王将军知晓。军粮乃国之命脉,
王将军震怒之下,自会向太子施压。此乃‘驱虎吞狼’,祸水东引。”书房内落针可闻。
所有人都被这环环相扣、胆大包天又精妙绝伦的计策震住了。借死人的粮,驱虎吞狼,
每一步都踩在刀尖上,却又每一步都精准地指向生机!
萧景玄死死盯着舆图上平陶那个小小的点,又看看楚瑶平静无波的脸,胸膛剧烈起伏。
震惊、狂喜、难以置信,最后化为一种近乎灼热的、带着强烈探究欲的光芒。
他猛地一拍桌案,震得笔架都跳了起来,声音因激动而嘶哑:“好!好一个‘向死人借粮’!
好一个‘驱虎吞狼’!楚先生……”他大步上前,一把攥住楚瑶略显单薄的肩膀,
力道大得惊人,眼中是毫不掩饰的激赏与某种更深沉难辨的情绪,
“你……你真是上天赐予本王的……良师!”那“良师”二字,似乎在他舌尖滚了滚,
带着异样的温度。楚瑶被他攥得肩膀生疼,对上他那双过于炽热的眼睛,心头猛地一跳,
一股难以言喻的慌乱悄然滋生。她下意识地微微偏头,避开那过于直接的视线,清咳一声,
不动声色地挣开他的手,垂下眼帘:“殿下过誉。事不宜迟,当速做决断。
”---寒冬腊月,滴水成冰。七皇子府邸后苑的练武场空旷寂寥,积雪被扫开一片,
露出冻得硬邦邦的青石板地。萧景玄只着一身单薄的玄色劲装,身姿挺拔如松,
手中一杆沉重的铁枪舞得虎虎生风。枪尖撕裂冰冷的空气,发出尖锐的呼啸,枪影翻飞,
时而如蛟龙出海,时而如灵蛇吐信,矫健的身影在空旷的场地上腾挪闪转,
挥洒着仿佛无穷无尽的精力。汗水早已浸湿了他额角的碎发,顺着棱角分明的下颌滚落,
砸在冰冷的石板上,瞬间凝结成细小的冰珠。每一次出枪都带着凌厉的破空声,
每一次步伐变换都沉稳有力,他仿佛不知疲倦,
要将心中积压的愤懑、焦虑、还有那日益滋长却难以言说的、对某个人的复杂心绪,
统统发泄在这枯燥而暴烈的枪法之中。楚瑶裹着一件厚厚的银狐裘,
远远地站在廊檐下避风处。寒风卷着细碎的雪沫刮过,吹得她脸颊生疼,鼻尖冻得通红。
她看着场中那个不知疲倦的身影,眉头微蹙。自从巫蛊案后,萧景玄就时常这样,
将自己逼到极限。那案子虽然最终凭借楚瑶的机变和一份伪造的“天象示警”密档,
险之又险地洗脱了萧景玄的嫌疑,将祸水引向了另一个倒霉的皇子,
但其中的凶险和步步杀机,显然在萧景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殿下,
”楚瑶终于忍不住开口,清冷的声音穿透寒风,“风雪甚大,寒气侵骨,如此练法,
恐伤经脉。”她的关心藏在劝诫之下,带着一贯的疏离。枪势猛地一收!
沉重的铁枪“锵”地一声顿在地上,枪杆兀自嗡嗡震颤。萧景玄倏然转身,
汗湿的脸颊在寒风中蒸腾着白气,一双眼睛却亮得惊人,直直地望向廊下的楚瑶。
那目光锐利、灼热,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穿透力,仿佛要将她整个人看透。
楚瑶被他看得心头一凛,下意识地紧了紧狐裘的领口,仿佛那目光能带来实质的寒意。
萧景玄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带着一身凛冽的寒气与蒸腾的热意,停在她面前几步远的地方。
他胸膛微微起伏,气息还未平复,目光却紧紧锁在楚瑶脸上,仿佛在研究一件稀世珍宝,
带着审视,带着探究,更带着一种让楚瑶心头发毛的专注。“楚先生,”他开口,
声音因剧烈运动而有些沙哑,却字字清晰,“本王一直很好奇。”他向前逼近一步,
高大的身影带来无形的压迫感,“以先生之才,天下何处不可去?
太子、三哥、五哥……哪个不比本王势大?哪个不比本王能许你泼天富贵、高官厚禄?
先生……”他微微倾身,目光如炬,直刺楚瑶眼底深处,
“为何偏偏选了本王这艘四处漏水、眼看就要沉底的破船?嗯?”他的语调低沉,
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近乎危险的玩味,
还有那毫不掩饰的、对楚瑶“过分俊秀”容貌的审视。那目光如有实质,
掠过楚瑶白皙得过分的脸颊,挺秀的鼻梁,
最后落在那双沉静却偶尔会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躲闪的眼睛上。楚瑶的心跳骤然漏了一拍,
袖中的手指猛地蜷紧,指甲几乎要掐进掌心。她强自镇定,迎上他审视的目光,
眼神坦荡无波,声音平稳:“殿下何必妄自菲薄?破船亦有龙骨,沉舟亦有艨艟之志。况且,
”她话锋一转,语气带上了一丝清冷的疏离,“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在下择主,
非看一时之势,而观其本心之韧、志向之远。
至于富贵高官……”她唇角勾起一抹极淡的、近乎嘲讽的弧度,“不过是过眼云烟,
岂是在下所求?”萧景玄定定地看着她,那双深邃的眼眸中风暴翻涌,探究、激赏、困惑,
还有一丝难以捕捉的、被这疏离态度隐隐刺伤的恼怒,
以及那越来越难以忽视的、对眼前人容貌的奇异感受。半晌,他忽然低低地笑了起来,
笑声中带着几分自嘲,几分释然,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好一个‘观其本心之韧、志向之远’!”他猛地伸手,在楚瑶毫无防备之下,
一把握住了她拢在狐裘袖子里的手!楚瑶浑身剧震,如同被火烫到一般,下意识地就要抽回!
然而萧景玄的手掌宽大、温暖、带着厚茧和练枪留下的微湿汗意,力道极大,不容她挣脱。
那滚烫的温度透过薄薄的衣袖,瞬间灼烧着她的肌肤,也灼烧着她紧绷的神经!
“手怎么这么冰?”萧景玄剑眉一拧,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强硬,
更带着一种自然而然的关切。他双手合拢,
将那冰凉纤细(他下意识觉得这个词贴切)的手完全包裹在自己滚烫的掌心之中,
用力地揉搓着,仿佛要将自己所有的热力都传递过去。
楚瑶只觉得一股强大的暖流从那交握的手掌汹涌而至,瞬间冲垮了她强装的镇定堡垒!
血液猛地涌上脸颊,烧得她耳根通红。她用力挣扎,声音都带上了无法抑制的微颤:“殿下!
放手!成何体统!”那羞恼和慌乱,几乎要冲破她竭力维持的“楚先生”外壳。
萧景玄却恍若未闻,他低着头,专注地用自己的手焐着那只冰冷的手,
感受着那奇异的、仿佛能沁入心脾的凉意,和那细腻得不可思议的触感。
这触感……这触感实在太过异样,与他握过的任何男子的手都截然不同!
一丝强烈的、近乎荒谬的疑惑,如同冰冷的毒蛇,悄然钻入他的脑海。他下意识地抬眸,
目光再次落在楚瑶因羞愤而涨红的脸上,那过分精致的眉眼,
那此刻因慌乱而显得格外生动的神情……就在这时,
一阵更加猛烈的寒风卷着雪粒子呼啸而过,狠狠扑打在两人身上。楚瑶被冻得一个激灵,
猛地咳嗽起来,单薄的肩膀微微颤抖。萧景玄瞬间从那危险的思绪中惊醒,
看着楚瑶冻得发白的脸和微红的鼻尖,心中那点疑惑被强烈的担忧取代。
他立刻松开楚瑶的手(那细腻冰凉的触感却仿佛烙印般留在了掌心),
毫不犹豫地解下自己身上那件尚带着他滚烫体温的玄色大氅。“披上!”他不由分说,
带着不容抗拒的强势,将带着浓烈男子气息和暖意的大氅裹在了楚瑶身上,动作近乎粗鲁,
却又带着一种笨拙的急切,仔细地将领口拢紧,确保寒风一丝也钻不进去。
厚重的皮毛瞬间隔绝了刺骨的寒冷,将楚瑶娇小的身躯完全包裹,
属于萧景玄的体温和气息霸道地侵袭着她的感官。楚瑶僵在原地,如同被施了定身咒。
大氅下的身体微微颤抖,不知是冷,还是别的什么。脸颊上的红晕非但未退,反而更深了,
一路蔓延到脖颈深处。她想拒绝,想立刻脱下这带着他气息的“枷锁”,
喉咙却像是被什么堵住,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只能低垂着头,盯着自己沾了雪沫的靴尖,
长长的睫毛剧烈地颤动着,掩盖着眸中翻江倒海的惊涛骇浪。
萧景玄看着她这副近乎“羞怯”的模样,包裹在自己大氅里显得异常单薄的身影,
心头那股异样的悸动和难以言喻的怜惜感再次汹涌而来,瞬间压倒了方才那一闪而过的疑虑。
他有些烦躁地搓了搓自己依旧滚烫的手掌,那上面似乎还残留着那冰肌玉骨的触感,
这感觉让他莫名地口干舌燥,心绪不宁。他别开脸,粗声粗气地道:“行了,回屋去!
冻病了,谁给本王出谋划策?”语气依旧强硬,却掩饰不住那丝不易察觉的狼狈和关切。
他率先转身,大步流星地朝着暖阁方向走去,背影带着一种近乎落荒而逃的意味,
不敢再看身后被自己大氅包裹住的、此刻显得无比“脆弱”的“楚先生”。
---初春的皇家猎场,旌旗猎猎,号角长鸣。一场盛大的春蒐,既是皇家仪典,
更是暗流汹涌的角力场。太子萧景瑞一身明黄骑装,高踞骏马之上,志得意满,
目光扫过全场,带着居高临下的睥睨,
最终落在七皇子萧景玄及其身后低调策马的楚瑶身上时,嘴角勾起一抹阴冷的笑意。“七弟,
”太子声音洪亮,带着刻意的关切,“听闻你府上新得了位‘楚先生’,智计百出,
连父皇都略有耳闻。今日春蒐,良辰美景,何不让这位先生也下场一试身手?
让我等也见识见识‘楚先生’门下高徒的风采?”他刻意加重了“先生”二字,
眼神中的恶意毫不掩饰。谁都知道楚瑶在七皇子府深居简出,从不习武,太子此举,
摆明了是要当众折辱萧景玄,更要让这碍眼的“楚先生”出个大丑。场中瞬间安静下来,
无数道目光齐刷刷地投向楚瑶,有幸灾乐祸,有好奇探究,也有担忧。萧景玄脸色一沉,
握着缰绳的手骤然收紧,指节发白。他正要开口回绝,
一个清冷平静的声音已在他身侧响起:“太子殿下有命,在下敢不从尔?
”楚瑶策马缓缓而出,依旧是那身半旧的靛蓝布袍,在满场华服贵胄中显得格格不入,
却又自有一股沉静如渊的气度。她面上无波无澜,仿佛只是答应去饮一杯茶般寻常。
萧景玄心头猛地一紧,急道:“先生!”他深知楚瑶底细,让她下场狩猎,
无异于羊入虎口!楚瑶却只是侧头,给了他一个极淡、却带着安抚意味的眼神,
随即轻夹马腹,缓缓行入场中。太子眼中闪过一丝得逞的狞笑,
挥手示意手下:“给楚先生备弓!挑最好的!
”一张沉重的硬弓和装满箭矢的箭囊被递到楚瑶马前。楚瑶接过弓,入手沉重冰凉。
她掂量了一下,并未尝试拉开,只将箭囊随意挂在马鞍旁,
对着太子微微颔首:“谢殿下赐弓。”那姿态,与其说是准备狩猎,
不如说是准备去踏青赏景。号角再起!狩猎正式开始。王公子弟们呼喝着,策动骏马,
如离弦之箭般冲入密林深处,马蹄声如雷滚过。唯有楚瑶,依旧不紧不慢,
任由座下那匹温顺的老马驮着,闲庭信步般沿着林间小径缓行,仿佛真是来游玩的。
萧景玄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目光死死追随着那抹蓝色的身影,再无心思狩猎。
他挥手示意自己的亲卫远远跟上保护,自己则策马缀在楚瑶后方不远处的林间,
焦灼地观察着四周的风吹草动。时间一点点流逝。密林深处,
呼喝声、野兽的嘶吼声、弓弦的铮鸣声此起彼伏。楚瑶这边却安静得诡异。
她甚至勒马停在了一处开满野花的向阳坡地,俯身摘了一朵淡紫色的小花,拿在指尖把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