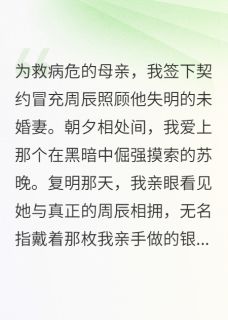
为救病危的母亲,我签下契约冒充周辰照顾他失明的未婚妻。朝夕相处间,
我爱上那个在黑暗中倔强摸索的苏晚。复明那天,我亲眼看见她与真正的周辰相拥,
无名指戴着那枚我亲手做的银戒。三年后重逢,她是非遗传承人,我是小记者。
发布会上她高调宣布:“我与周辰即将订婚。”目光却如利刃穿透人群,直直钉在我身上。
“唐记者,你似乎对我的过去很感兴趣?”周辰当众诬陷我偷窃机密,放出伪造的不雅照。
苏晚突然举起左手:“你送的戒指,不打算认了吗?”我苦笑:“是我拿了钱,骗了你两年。
”她一把抓住我手腕:“可你骗走的心,打算什么时候还?”---冰冷的雨点砸在脸上,
生疼。医院惨白的灯光从高处泼下来,将“ICU”三个字母映得如同索命的符咒。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催款单,指尖被劣质的纸张边缘割得发木。单子上那个不断膨胀的数字,
像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扼住了我的喉咙,每一次呼吸都带着铁锈般的血腥味。
母亲苍白虚弱的脸在眼前晃动,她枯瘦的手曾那么用力地抓紧我,
仿佛我是她沉没前唯一的浮木。“五十万。现金还是转账?
”一个裹挟着雨水泥腥气的男声在身侧响起,带着一种刻意压低的、不耐烦的傲慢。
我猛地扭过头。周辰。我那同父异母、锦衣玉食长大的哥哥。
他穿着一身剪裁完美的深色羊绒大衣,昂贵的皮革手套一尘不染,
与医院门口这混乱、潮湿、绝望的氛围格格不入。他脸上没什么表情,
只有嘴角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混合着轻蔑与施舍的弧度。他身后两步远,
站着一个沉默如铁塔的保镖,眼神锐利地扫视着周围。“签了它,钱马上到你账上。
”他从保镖手里接过一个厚厚的牛皮纸文件袋,随意地递过来,动作像是在打发路边的乞丐,
“照顾好她,别露馅。记住,你是‘周辰’,不是那个穷酸记者唐宇安。”文件袋沉甸甸的,
像一块烧红的烙铁。我几乎能闻到里面崭新钞票的油墨气味。五十万。
这是母亲从死神手里抢时间的唯一筹码。我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下,雨水顺着额发流进眼睛,
一片刺痛模糊。没有第二条路了。我伸出手,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颤抖,
接过了那个决定命运的袋子,也接过了“周辰”这个偷来的身份。“知道了。
”我的声音干涩得如同砂纸摩擦。周辰满意地勾了勾嘴角,仿佛完成了一桩微不足道的交易。
他转身钻进那辆停在雨幕里的黑色宾利,尾灯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拖出两道猩红的光轨,
迅速消失在城市的霓虹深处。保镖留了下来,
面无表情地递给我一把钥匙和一个地址:“苏**在等你。安分点。
”推开那扇沉重的雕花木门,一股混合着昂贵熏香和淡淡药味的空气扑面而来。
别墅内部空旷得惊人,昂贵的家具在昏暗的光线下如同沉默的巨兽。
巨大的落地窗被厚重的天鹅绒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一丝天光也透不进来。
一个纤细的身影蜷缩在客厅中央那张过分宽大的沙发里。听到声响,
她像受惊的小动物般猛地抬起头,空洞的眼神茫然地投向门口的方向。“周辰?
”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种长期缺乏安全感的沙哑,像羽毛刮过心尖,激起一片细密的涟漪。
我喉咙发紧,那个偷来的名字卡在嘴边,沉重得几乎无法吐露。深吸一口气,
我强迫自己用尽可能平稳的声线回应:“是我。苏晚?”她似乎松了口气,
紧绷的肩膀微微塌下一点,摸索着想要站起来:“嗯。你迟到了十七分钟。
”她的动作带着盲人特有的谨慎和试探,手指在空中虚虚地抓了一下,才扶住沙发的靠背。
那小心翼翼的姿态,像一根无形的刺,扎进了我心里某个刚刚开始变得柔软的地方。
最初的几天如同行走在布满荆棘的雷区。苏晚的脾气如同她此刻所处的黑暗世界一样,
阴晴不定,难以捉摸。她像一只竖起全身尖刺的刺猬,对所有靠近都充满敌意。“周辰,
收起你那套虚伪的关心!”她猛地挥手打翻了我递过去的温水杯,
玻璃碎裂的声音在空旷的客厅里显得格外刺耳。温热的水溅湿了她的睡袍下摆和我的裤脚。
她胸口起伏着,空洞的眼睛里燃烧着愤怒的火苗,
声音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周家,
不过是想拿我这个瞎子在爷爷面前装样子!你们心里早就巴不得我消失,对吧?
”我沉默地蹲下身,一片片捡拾着地上的碎玻璃。锋利的边缘轻易划破了指尖,渗出血珠。
疼痛反而让我混乱的思绪清晰了一瞬。我抬起头,看着她因为激动而微微泛红的脸颊,
看着那曾经明亮、如今却蒙着阴翳的眼睛深处藏着的巨大恐惧和孤独。
一股莫名的冲动瞬间压倒了所有理智。我猛地站起身,一步跨到她面前。
在她惊愕地张开嘴想要斥责的刹那,我低下头,带着一种近乎粗鲁的掠夺,
狠狠地吻住了她冰冷的唇瓣。那不是温柔的吻,更像是一种孤注一掷的证明。牙齿磕碰,
气息交缠,带着血腥的铁锈味和我自己也说不清的复杂情绪。苏晚整个人都僵住了,
像一尊骤然冻结的冰雕。几秒钟的死寂后,她猛地抬手想要推开我,指尖却颤抖得厉害。
我喘息着退开一点,双手依旧紧紧抓着她的肩膀,声音低沉而急促,
带着未平息的喘息和一丝狠意:“感受到了吗?还觉得我嫌弃你吗?
”客厅里只剩下我们两人粗重的呼吸声。苏晚的耳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染上一层绯红,
一直蔓延到脖颈。她嘴唇微微翕动,最终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只是茫然地睁着那双没有焦距的眼睛,仿佛被那个突如其来的吻彻底打懵了。
时间在黑暗中无声流淌,像一条浑浊的河。母亲的病情在昂贵的药物支撑下奇迹般稳定下来,
电话里她的声音渐渐有了生气。而我与苏晚之间,那层坚硬的冰壳,在那个失控的吻之后,
竟开始悄然融化。她依旧敏感,偶尔会发脾气,但不再像刺猬一样无差别地攻击。
她开始习惯我的脚步声,会在**近时微微侧过头倾听。
她会在我给她读一本关于古代漆器纹样的书籍时,安静地蜷在沙发角落,
手指无意识地捻着毛毯的边缘,偶尔会问几个问题。“唐…周辰,”有一次,她忽然开口,
声音很轻,带着一丝犹豫,“你说,书上写的‘剔犀云纹’,摸起来是什么感觉?
”她第一次主动问起一个“看”不到的东西。我愣了一下,
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放下书,我环顾四周,
目光落在茶几上一个硬木笔筒边缘的简单回纹上。我轻轻拉过她的手,
小心翼翼地引导她的指尖去触碰那微凉坚硬、带着清晰转折棱角的木纹。“就像这样,
”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放得更轻,“一圈一圈,连绵不断,很光滑,又带着清晰的边界感。
云纹……想象一下,就像把天上的云朵,用最柔和的刀,一层层刻在了木头深处。
”她的指尖顺着我的指引,在那细密的纹路上缓慢移动,神情专注得近乎虔诚。
长长的睫毛垂下来,在苍白的脸颊上投下小片阴影。那一刻,
她身上那种拒人千里的疏离感消失了,只剩下一种近乎脆弱的好奇和专注。
“原来是这样……”她喃喃自语,指尖恋恋不舍地停留在那木纹上,
嘴角微微弯起一个极淡的弧度,像初春冰雪消融时探出的一点嫩芽。
一种陌生的、温热的情绪在我胸腔里悄然滋生、蔓延。我看着她唇边那抹若有似无的浅笑,
看着她沉浸在指尖触感里的专注侧脸,忽然觉得这冰冷的、被谎言笼罩的囚笼里,
透进了一线微弱却真实的光。她的二十岁生日,在一个深秋的夜晚悄然而至。
窗外是城市遥远的、模糊的灯火,窗内只有一盏落地灯散发着昏黄的光晕。“生日快乐,
苏晚。”我把一个丝绒小盒子轻轻放在她摊开的手心。她的指尖带着微不可察的颤抖,
摸索着打开盒盖,触碰到里面冰凉的圆环。她将它拿了出来,
小心翼翼地套在自己左手的无名指上,尺寸竟意外地贴合。“是什么?”她明知故问,
声音里压着一丝极力掩饰的雀跃,耳尖又悄悄红了。
看着她珍而重之地抚摸着那枚粗糙的银戒,像个得到心爱糖果的孩子,
一股酸涩的暖流猛地冲上我的眼眶。我压下喉间的哽塞,
故意用轻松的语气逗她:“路边捡的,不知道谁丢的。苏大**别嫌弃啊。”“别这么叫我!
”她立刻反驳,语气却带着一丝罕见的娇嗔。她摸索着,
将戴着戒指的手轻轻按在自己心口的位置,仿佛要把它藏进最深处,“捡来的……我也喜欢。
”她停顿了一下,声音低了下去,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认真:“因为,是你送我的。
”灯光下,她微微仰起的脸,苍白却生动。无名指上那枚朴素的银戒,
在昏黄的光线下折射出一点微弱的星芒,照亮了她空洞的眼底,
也狠狠烫伤了我心底那块名为“谎言”的痂。那一刻,我无比清晰地认识到:我完了。
我爱上了这个被我欺骗、命运多舛的女孩。这份在黑暗中滋生的情愫,
沉重得让我几乎无法呼吸。希望像肥皂泡一样脆弱。母亲病情刚稳定不久,
一个深夜的紧急电话将我扯回冰冷的现实。母亲再次被推进了抢救室。
隔着ICU厚厚的玻璃,我看着她身上插满管子,监测仪发出单调而刺耳的滴答声,
每一次跳跃都像踩在我的心脏上。医生沉重的话语如同冰锥:“情况很不乐观,
需要尽快进行二次手术,费用……恐怕要翻倍。”**在冰冷的墙壁上,浑身力气被抽空。
五十万早已耗尽,新的天文数字像一座大山轰然压下。口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
是周辰发来的信息,只有一行字:“苏家老爷子快不行了,风声紧,别出岔子。钱的事,
自己想办法。”自己想办法?我能有什么办法?绝望如同冰冷的潮水,瞬间没顶。
我攥着手机,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仿佛那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也是勒紧我脖颈的绳索。
我闭上眼,苏晚戴着那枚银戒、仰着脸说“喜欢”的模样在黑暗中浮现,
与母亲苍白痛苦的脸重叠在一起,撕扯着我的灵魂。浑浑噩噩地回到别墅,已是后半夜。
客厅里一片狼藉,浓重的烟味和酒气混合着,呛得人喉咙发紧。苏晚蜷在沙发一角,
像一只被遗弃的猫。听到我的脚步声,她猛地抬起头,
那双空洞的眼睛里此刻却盛满了惊惶和一种濒临崩溃的愤怒。“你去哪了?!
”她的声音尖利得变了调,带着浓重的鼻音,“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是个累赘?
是不是也觉得我死了更好?!滚啊!都滚!我不需要你们假惺惺的可怜!
”她摸索着抓起手边一个靠枕,用力朝我声音的方向砸过来。靠枕软绵绵地落在地上,
毫无杀伤力,却像一把重锤砸在我心上。母亲在生死线上挣扎,而这里,
另一个被我卷入深渊的女孩,正因我的失约而痛苦嘶喊。
巨大的压力和愧疚瞬间冲垮了理智的堤坝。连日来的恐惧、疲惫、无能为力的愤怒,
如同岩浆般喷涌而出。我几步冲到她面前,一把抓住她挥舞的手臂,力道大得让她痛呼一声。
我不管不顾地俯身,带着一种近乎绝望的疯狂,再次狠狠吻住了她。
这个吻比上一次更加粗暴,带着血腥味和咸涩的泪水(不知是我的还是她的),
像是溺水者最后的挣扎。苏晚起初还在用力挣扎,指甲甚至抓破了我的脖子。但很快,
她的抵抗变得微弱,最终化成一声压抑的呜咽,融化在这个充满绝望气息的吻里。
滚烫的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滑落,滴在我的手背上,灼痛了我的皮肤。“苏晚……”我喘息着,
额头抵着她的额头,声音嘶哑得如同砂纸摩擦,“我没有晚饭吃了,你赔给我吧。”黑暗中,
她的身体猛地一颤。她似乎想说什么,话语却被我再次落下的吻堵了回去。这一次,
不再是掠夺,而是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沉沦和乞求。我吻去她眼角的泪水,尝到了苦涩的咸。
窗外是无边无际的浓重黑暗,窗内是昏黄灯光下两个紧紧相拥、彼此舔舐伤口的灵魂。
所有的伪装、谎言、身份带来的隔阂,都在这一刻被汹涌的情感冲垮。
我笨拙地解开她睡袍的系带,她纤细的手指颤抖着,摸索着攀上我的脊背,留下灼热的痕迹。
她的回应带着生涩的试探和一种不顾一切的决绝,像飞蛾扑向唯一的火光。
我们像两个在冰海中即将溺毙的人,只能死死抓住对方,
以此汲取一点点虚假的温暖和活着的证明。肌肤相亲的温度暂时驱散了绝望的寒意,
喘息和细碎的低吟交织,成了这无边黑暗里唯一的声响。
些沉重的现实——母亲的医药费、周辰的威胁、苏家未知的变局——都被短暂地抛在了身后。
此刻,只有怀中这具温热的、微微颤抖的身体是真实的,只有彼此纠缠的气息是真实的。
这一夜,世界颠倒错乱,只剩下我们。我们在绝望的悬崖边缘疯狂起舞,
用身体刻下最深刻的印记。当风暴终于平息,我紧紧抱着疲惫不堪、蜷缩在我怀里的苏晚,
听着她逐渐平稳的呼吸,感受到她温热的眼泪无声地洇湿了我的胸口。
一种沉甸甸的、混合着巨大满足和更深重负罪感的东西,沉甸甸地压在了心上。我知道,
有些东西,再也无法回头了。---苏晚重见光明的那一天,阳光好得刺眼。
我站在VIP病房门外,像一尊被钉在耻辱柱上的雕像,浑身冰冷。门是虚掩的,
里面传出的声音清晰地钻入耳膜,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针。“灵心,我在这里。
”是周辰刻意压低、模仿我声线的声音,带着虚伪的温柔,“我真的很担心你。”“你说过,
等我恢复视力后,你要做第一个被我看到的人。”苏晚的声音带着初愈的沙哑,
却有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近乎撒娇的埋怨,“你食言了。”“对不起宝贝,路上堵车了。
”周辰的声音腻得发齁,“现在,
让我好好看看你……”后面的话语被一阵衣物摩擦的窸窣声淹没。我僵硬地侧过头,
透过门缝的缝隙,清晰地看到病房内——苏晚坐在病床上,初愈的眼睛还有些微红,
却亮得惊人,清晰地倒映着周辰那张与我相似却更显油滑的脸。周辰俯下身,
一手捧着她的脸,嘴唇毫不犹豫地印了下去。苏晚没有抗拒,甚至微微闭上了眼睛,
长长的睫毛像蝶翼般轻轻颤动,脸上泛起淡淡的红晕。她的左手,正被周辰紧紧握着,
无名指上,那枚我亲手打磨、笨拙地刻下“S&W”缩写的银戒,
在阳光下反射着冰冷而刺眼的光芒。轰——!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脑子里炸开了。
所有的血液瞬间涌向头顶,又在下一秒被彻底抽干,只留下刺骨的寒冷和一片空白的轰鸣。
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疼得无法呼吸。眼前的一切——阳光,拥抱,亲吻,
戒指——都扭曲变形,化作最尖锐的嘲笑,狠狠刺穿了我最后一丝自欺欺人的幻想。原来,
从一开始,她眼里看到的、心里认定的、唇齿间呼唤的“周辰”,从来就不是我唐宇安。
我只是一个可悲的影子,一个用完即弃的替身。她所有的温柔,所有的依赖,
甚至那个绝望夜晚的缠绵,都只是透过我,投射给了那个叫“周辰”的身份标签。
我踉跄着后退一步,撞在冰冷的墙壁上,才勉强没有倒下。喉咙里涌上一股浓重的腥甜,
又被我死死咽了回去。一只手突然从后面用力地抓住了我的胳膊,是周辰那个保镖。
他面无表情,力气却大得惊人,像拖拽一件货物般将我粗暴地拽进了旁边的休息室。
门被关上,隔绝了外面那令人作呕的温情画面。没等我的眩晕感过去,
休息室的门再次被推开。周辰走了进来,脸上带着胜利者的笑容,志得意满,春风拂面。
他慢条斯理地整理了一下刚才可能被苏晚弄皱的昂贵衬衫袖口,目光扫过我苍白的脸,
嘴角勾起一抹毫不掩饰的恶意。“啧啧,瞧瞧你这副样子。”他嗤笑一声,走到我面前,
刻意抬起手,用指腹抹了一下自己下唇上一个新鲜的、细小的伤口,眼神充满挑衅,
“是苏晚亲的,她真的很爱我,很离不开我。”他顿了顿,欣赏着我痛苦的表情,
慢悠悠地补充道:“这两年,你把她照顾得很好。不过对她来说,这一切都是我做的。
”他凑近一步,声音压得更低,带着毒蛇吐信般的阴冷:“唐宇安,认清楚自己的位置。
你这样身份卑贱的人,永远、永远不可能和她扯上什么关系。拿着钱,滚得越远越好,
别让我再在国内看到你这张晦气的脸。否则……”他冷笑一声,未尽之意充满威胁。
保镖适时地将一张冰冷的支票拍在我旁边的茶几上。我看着那张轻飘飘的纸,
上面一串长长的零,像一张巨大的、嘲讽的鬼脸。它买走了我两年的时光,买走了我的真心,
买走了母亲的生命,也买走了我最后一点尊严。我猛地弯腰,剧烈的呕吐感翻江倒海而来,
却只吐出几口酸涩的苦水。我扶着茶几边缘,身体因为极度的愤怒和痛苦而剧烈颤抖。
指甲深深抠进坚硬的木质桌面,发出刺耳的刮擦声。
周辰轻蔑的冷笑和保镖冰冷的注视像两把钝刀,反复切割着我残存的理智。最终,我伸出手,
指尖颤抖着,却异常缓慢、异常用力地,将那张支票一点点攥紧在掌心。
薄薄的纸张被揉捏成一团废纸,发出不堪重负的**。我抬起头,
死死盯住周辰那张得意洋洋的脸,用尽全身力气,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
声音嘶哑如同破锣:“我、签、字。”三年时光,足以冲刷掉很多东西,
比如初入社会的棱角,比如对不公的愤怒嘶吼。但有些东西,却像沉入深海的锚,
只会随着时间沉淀得更加沉重、更加尖锐。我成了一名奔波在新闻第一线的记者。
镜头和话筒是我的武器,笔下的文字是我无声的呐喊。我选择这个职业,不仅仅是为了生存,
更是为了那个沉甸甸的、刻在骨髓里的名字——母亲。三年间,
我像猎犬一样追踪着周家的一切。周家表面光鲜,靠古董倒卖起家,
如今在周辰母亲周婧的掌控下,披着文化产业的外衣,实则干着不少见不得光的勾当。
我利用记者身份,辗转多地,抽丝剥茧,收集着他们当年构陷母亲的证据,
以及他们非法走私、洗钱的线索。每一次调查都如履薄冰,
每一次发现都让心底的恨意烧得更旺。这天,主编王哥兴冲冲地把我叫进办公室,
将一份烫金的邀请函拍在我桌上:“小唐!大活儿!苏氏集团那位新上任的掌门人,苏晚,
你知道吧?她主导的那个国家级非遗文化复兴项目发布会,点名要我们台去做专访!
你小子走运,上头点名让你去!”“苏晚”两个字像一道无声的惊雷,
猝不及防地劈进我的脑海。心脏骤然一缩,三年前病房外那刺眼的一幕——阳光下的亲吻,
无名指上的银戒,周辰挑衅的嘴脸——瞬间清晰无比地撞回眼前。
握着采访提纲的手指猛地收紧,纸张边缘深深勒进掌心。“怎么?傻了?
”王哥看我脸色不对,拍了我一下,“紧张了?别怂!这可是露脸的大好机会!
苏总现在可是风头正劲,听说她眼睛恢复后,靠着铁腕手段整合了苏家,
还弄出了这个国家级的大项目。她那个未婚夫周辰,
也沾光成了文化推广大使……”“周辰”两个字像淬了毒的针,狠狠扎进耳膜。
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压下翻涌的情绪,挤出一个职业化的笑容:“知道了,王哥,
我这就去准备。”发布会设在苏氏集团新落成的文化中心,恢弘大气,
处处彰显着深厚的底蕴与雄厚的财力。闪光灯如同密集的星群,聚焦在主席台上。
当苏晚在助理的簇拥下缓步走上台时,整个会场瞬间安静下来,仿佛连空气都凝滞了。
三年时间,足以将一个人彻底淬炼。
当年那个在黑暗中倔强摸索、偶尔流露出脆弱的女孩已经消失无踪。眼前的苏晚,
穿着一身剪裁利落的珍珠白色西装套裙,身姿挺拔如修竹,气场强大而凛冽。
长发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露出光洁饱满的额头和线条优美的天鹅颈。她的妆容精致却冷肃,
尤其那双眼睛,明亮锐利得如同淬了冰的寒星,目光所及之处,仿佛能穿透一切伪装。
她从容地落座,姿态优雅而疏离。那份久居上位的强大气场,
无声地宣告着她此刻的身份——苏家真正的掌权者。我的位置在媒体区前排角落。
在她目光扫过全场、即将掠过媒体区时,我下意识地低下了头,手指无意识地蜷缩起来,
仿佛这样就能躲开那目光的审视。“非常感谢各位莅临。”她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会场,
清冽、平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与记忆中那个沙哑、带着依赖的声音判若两人,
“苏氏集团致力于传统文化保护与创新多年,此次‘薪传’项目,
旨在将那些濒临失传的非遗技艺,重新带回公众视野……”她侃侃而谈,条理清晰,
对项目的规划、意义如数家珍。那份自信与掌控力,
让人很难将她与三年前那个失明的女孩联系起来。然而,
当有记者提问到关于项目启动的初衷,是否与她个人的经历有关时,
苏晚那完美无缺的表情面具,似乎出现了一丝极其细微的裂痕。
她端起水杯的动作停顿了半秒,目光似是不经意地,再次扫过媒体区,
准确无误地落在了我所在的位置。那目光锐利如刀,带着一种洞悉一切的穿透力,
仿佛在无声地质问:你看到了吗?我回来了。我的心跳骤然漏了一拍,
一股寒意顺着脊椎窜上。她……认出我了?就在这时,侧门被推开。
一身骚包浅咖色西装、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的周辰,挂着恰到好处的歉意笑容走了进来。
他径直走到苏晚身边,极其自然地俯身,在她耳边低语了几句,姿态亲昵无比。“抱歉,
亲爱的,片场那边有点事耽搁了。”他的声音不大,却足以让前排的记者听到。
苏晚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几不可察地点了下头,示意他在旁边的位置坐下。周辰落座后,
目光随意扫过台下,当看到角落里的我时,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