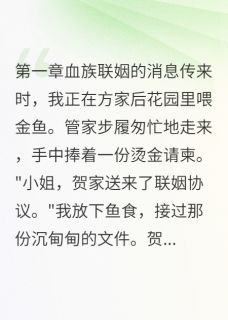
血族联姻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方家后花园里喂金鱼。
管家步履匆忙地走来,手中捧着一份烫金请柬。
"**,贺家送来了联姻协议。"
我放下鱼食,接过那份沉甸甸的文件。贺时琛,京城首富贺家的继承人,传闻中冷漠无情的商业天才。
协议条款很简单:我嫁给他,贺家帮助方家度过财务危机。
代价是我必须每月献血给他的白月光——慕清歌。
因为只有我这种稀有的银月血脉,才能维持她体内血族基因的稳定。
"**不必担心,贺先生承诺只是名义上的夫妻。"
我轻笑,名义夫妻?那就是说我连妻子都算不上,只是一个活体血库。
但方家已经走投无路,父母在车祸中去世后,留下的只有债务和年幼的弟弟方景行。
为了景行,我什么都愿意做。
"我同意。"
三天后的婚礼极其冷清,没有鲜花,没有祝福,只有必要的仪式。
贺时琛穿着黑色西装站在我面前,那张俊美得近乎完美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我只对慕清歌一个人有感情,你最好记住自己的身份。"
他的声音冷得像冰,字字都在提醒我,我只是一个工具。
婚礼结束后,我被安排住进贺家庄园的偏房。
主屋里住的是他和慕清歌。
那个被他捧在手心里的女人,有着这世上最纯净的血族血统,却因为基因缺陷需要我的血续命。
第一次献血是在结婚当晚。
医生抽了400毫升血液,装进特制的血袋里。
我看着那袋鲜红的液体被送往主屋,心中升起一种说不出的悲哀。
这就是我的新婚夜。
独自一人躺在冰冷的床上,听着远处传来的钢琴声。
那是贺时琛在为慕清歌弹奏她最爱的曲子。
月光透过窗棂洒在床上,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说过的话:"瑾年,你的血液很特殊,将来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
可是现在,我连保护自己的权利都没有。
第二天早上,我在餐厅见到了慕清歌。
她穿着白色长裙,肌肤苍白如雪,那双澄澈的眼睛里带着脆弱的美感。
"谢谢你,瑾年姐姐。"她轻声说道,"要不是你的血,我可能已经......"
我摆摆手,"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贺时琛坐在她身边,温柔地为她切着早餐,眼中的柔情如水。
从未有人用这样的眼神看过我。
"以后每周三次,医生会来为你抽血。"贺时琛头也不抬地说道,"记住按时补充营养。"
我点点头,就像应声虫一样乖顺。
慕清歌有些不好意思,"时琛,会不会太频繁了?瑾年姐姐的身体......"
"她的身体恢复能力很强,不会有问题。"贺时琛打断了她的话,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
我低头吃着面包,味同嚼蜡。
饭后,贺时琛搂着慕清歌离开,留下我一个人坐在偌大的餐厅里。
管家走过来,恭敬地说:"夫人,您的房间我已经重新布置过了,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夫人?
我苦笑,这个称呼真是讽刺。
我在这个家里,连佣人都不如。
下午,我去了一趟医院检查身体。
医生看着化验报告,眉头紧锁。
"方**,您的血红蛋白已经降到临界值了,必须减少献血频率,否则会危及生命。"
我接过报告,上面的数据触目惊心。
但我能怎么办呢?
慕清歌需要我的血维持生命,而我需要贺家的保护维持方家的存续。
这是一个无解的死循环。
回到庄园时,正好撞见贺时琛在花园里教慕清歌画画。
夕阳西下,他们的身影如此般配,仿佛童话里的王子和公主。
而我,只是这个童话里的配角,甚至连配角都算不上。
我绕过他们,回到自己的房间。
房间里确实重新布置过了,但依然冰冷得像个监牢。
我打开抽屉,里面放着母亲留给我的唯一遗物——一个银色的手镯。
手镯上刻着奇异的符文,母亲说这是我们家族的守护符。
可是现在,连守护符也保护不了我。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忽然听到隔壁传来慕清歌痛苦的**声。
我披上外套跑出去,看见贺时琛正焦急地抱着她往医务室走。
"快!叫医生!"他的声音里带着从未有过的慌乱。
医生匆忙赶来,检查后摇摇头:"慕**的基因又开始排斥了,需要立刻输血。"
贺时琛的目光瞬间锁定了我,那眼神如同饿狼看见猎物。
"现在就输。"
"可是方夫人今天刚刚......"医生欲言又止。
"我说现在就输!"贺时琛的声音冷得能结冰。
我静静地走向医疗椅,主动伸出手臂。
针头扎进血管的瞬间,我感到一阵眩晕。
400毫升,600毫升,800毫升......
"够了!"我终于忍不住出声。
贺时琛冷冷地看着我,"慕清歌的命比你重要一千倍,明白吗?"
我闭上眼睛,任由血液流淌。
直到彻底昏厥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