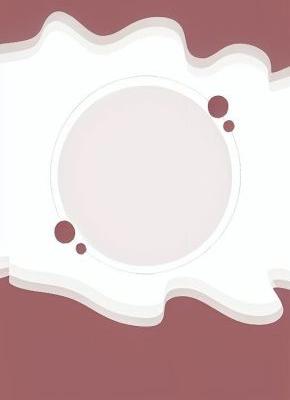
1.天是无情的。毒辣的日头悬在上面,炙烤着万物。地是无情的。无边无垠的黄沙,
刮着似乎永远不会停的风,发出各种怪声,细碎的沙砾被卷起来,打在脸上,不疼,却磨人。
我的客栈,就开在这片荒凉的沙漠边缘,那条已被风沙啃噬的模糊不清的古道旁。说是客栈,
不过是黄土夯成的两层,歪歪斜斜,随时可能被下一场沙暴揉碎埋掉。
楼下是大堂、厨房、和我睡觉的一个小间,楼上两间,每间一个大炕。
门口挑着个破旧的幡子,依稀可辨的四个字“黄沙客栈”,有气无力的晃荡着,
像块招魂的布。真正招魂的,是檐下挂的那一排风铃。灰白,粗糙,风一过就相互磕碰,
发出沉闷又刺耳的嗒嗒声,像是谁的牙齿在暗夜里咯咯打颤。有喝高了的客人眯眼瞅半天,
大着舌头问:“老板娘,你这铃铛,声儿可真怪,像、像骨头磨的...”我正低头斟酒,
劣质烧刀子的气味混着沙土味,熏得人眼睛发涩。“是风干的羊骨头。”我撒了谎,
声音不起一丝波澜。他们便哄笑,不再深究。在这条道上走的人,都知道规矩,有些东西,
看得,摸不得;有些话,问得,答不得。就像他们看我。一个看起来不该出现在这里的女人。
年纪不算大,眉眼间甚至还能看出几分江南水色,
却被塞外的风沙和日子熬煮得只剩下一副硬邦邦的骨架子。“老板娘,说真的,
”一个脸上带疤的汉子灌下大口酒,喉结滚动,目光却黏在我提壶的腕子上,
“你这般模样的娘们,守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卖这马尿一样的酒,图个啥?”“图个清静。
”我用布巾擦过粗陶碗沿。“清静?”另一个瘦猴似的男人嗤笑,
“这鬼地方的风嚎得像野鬼哭坟。”他挤眉弄眼,压低声音,“莫非是在等哪个负心汉?
”火塘里,干驼粪噼啪一响,爆起几点星火。我是在等一个人。一个我不认得脸,
却认得他魂魄里浸透了我家人鲜血的人。五年前,慕容家,江南莺飞草长、春雨杏花的地方,
一夜之间烧成焦土。五十一口,包括护院、仆役、借宿的表亲,都没能走出来。
我的幼弟冲儿,那时还不足三岁。除了我。我那夜恰好不在。仇人来得快,去得也干净,
像一阵妖风,刮过了,只留下死亡。但他们不是风,是人。是人,就有踪迹。
那块在父亲书房残骸里找到的已烧得变形的玄铁片。上面刻的字迹,鬼画符一般:黑玉至,
黄沙滚,五年期,烽烟漫。落款是一个火焰图腾。我翻烂了古籍,问遍了白道黑道,
用最烈的酒和所剩无几的银钱,终于找到了一个知情人,撬开了一点口风。那火焰图腾,
代表“流火”,是一个近十年才在江湖出现,行事诡秘、心狠手辣的杀手组织,总部在西域,
在这片沙漠的另一边。那块玄铁叫“流火令”,五年一发,是“流火”召集核心人物的令牌,
关乎巨大的利益和权力的重新划分。接到令的人,无论在天涯海角,都必须准时赴约,地点,
就在这片沙漠中的某一处。那晚带头的人,叫玄蝎,是“流火”江南分舵的舵主。
从江南进入这片沙漠,必定经过我的客栈。下一个五年期,就在今年,沙枣熟透的时节。
沙枣,已经熟透落尽了。所以,我等的那个人,他快要来了。檐下的骨铃又在风里撞响,
嗒……嗒……嗒……像是计数,催命。2.午后,一个身影掀帘而入。
带进一股干燥的风沙气息。他穿着普通的灰色布衣,风尘仆仆,头上的斗笠压得很低,
几乎遮住了整张脸,露出的下颌线干净利落。他选了最角落的一张桌子坐下,
用嘶哑的嗓子要了一壶普通的烧刀子和一碟花生豆,他喝酒很慢,一粒花生咀嚼很久,
彷佛在品味什么珍馐,像是再等什么人,或者在躲什么人。
这样的独行客在这条道上并不少见,他不是我等的人。直到黄昏,驼铃响起,
叮当……叮当……刺破了死寂。一个商队由远及近,轮廓逐渐清晰,十匹骆驼,十个人。
骆驼精悍,背上的人个个眼神锐利如鹰,带着经年累月刀头舐血磨出来的漠然和警惕,
簇拥着中间一个头目模样的黑衣男子。此人四十来岁,脸上有深深的纹路,一双眼,
深陷在眉骨阴影下,像两口枯井。风尘仆仆,遮不住他身上的剽悍冷厉。而我的全部心神,
瞬间被他腰间那把刀吸了过去。刀鞘暗沉,古朴无华,唯独刀柄末端,镶嵌着一小块白玉。
被精心雕琢成一弯月牙的形状,叶脉丝丝分明。轰的一声,血冲上我的头顶,
却又在刹那间冰冷彻骨,四肢百骸都冻僵了。那白玉,是我十岁那年,父亲握着我的手,
在江南温暖的阳光下,一刀一刀雕出来的。原有一对,一枚嵌在父亲最珍爱的端砚上,
另一枚……就嵌在我家祖传的宝刀——“挽月刀”的刀柄上。刀名挽月,刀出,清辉凝滞。
现在这把刀,正挂在他的腰侧。所以他就是玄蝎,我要等的人。耳边嗡嗡作响,
知情人带着酒意和炫耀的声音又一次响起:“你算是找对人了,
这事儿江湖中可没几个人知道,大家都当是慕容家得罪了谁,才被人找流火灭门的,
其实是蝎爷看上了慕容老头的宝刀,那老头不识时务死活不给,蝎爷干脆灭了他,
得了宝刀、还立了威,一举两得...”我的双眼一眨不眨的盯着挽月刀,
手已不自觉的摸向腰带,那里缠着一把软剑,五年来日夜不曾离身。但下一刻,便松开了手,
所有翻腾的情绪被强行摁了下去。我转过身,脚步稳得像生了根,
一步步走向那群刚刚落座、带来满室血腥与风沙气息的不速之客。“店家,上酒,切肉。
有什么好吃的都端上来。”一个随从粗声吆喝。我垂着眼,将酒菜一一放在他们面前。
玄蝎没看我,他似乎有些疲惫,又或是觉得根本不值得留意一个边陲客栈的老板娘。
他将那把“挽月刀”解下,“哐当”一声,随意扔在油腻的桌面上。
一个像是新来的、脸上还带着几分稚气的随从,眼睛盯着那把刀,
忍不住带着讨好问:“头儿,这刀看着真不凡,有啥来历不?”玄蝎抓起酒碗灌了一大口,
哈哈大笑两声,声音洪亮,带着残忍和不屑,还未开口,另一个随从已跑过来,
语气讨好的说:“那当然,这可是战利品,当年咱舵主可是一战成名。”玄蝎又灌了一口酒,
浑浊的酒液从他嘴角溢出,他毫不在意地用袖子抹去,大手啪的一声拍在刀上,
“那老鬼到死都攥着这把刀,掰都掰不开。”他话音落下的那一刻,
世界的声音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骤然掐灭。风吼,驼铃,火塘的噼啪,
甚至檐下骨铃那催命般的嗒嗒声,全都消失了。
我的耳中只反复回荡着那句:“掰都掰不开……”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
狠狠烙在我表面结痂的心口,烫得皮肉焦糊,露出底下五年未曾愈合、汩汩流血的伤口。
窗外,一阵狂风猛地扑上来,狠命摇撼着客栈。檐下那五十一颗骨铃,发了疯似的相互撞击。
嗒嗒嗒嗒嗒嗒——声音密集、沉闷、急促,像无数冤魂在同时尖啸。五十一具尸首。
五十一串骨铃。五十一笔血债。慕容挽月。我曾是慕容挽月。江南的烟雨杏花,
父亲的谆谆教诲、母亲的慈爱、弟弟蹒跚学步时软糯的笑声……这一切,
都在五年前那个夜里,被烧得干干净净。而现在,放这把火的人,就坐在我面前,
喝着我的酒,拿着我的刀,用最轻描淡写的口吻,谈论着我亲人的惨死。
指甲深深陷进掌心肌肤,刺痛感让我维持着最后一丝理智。不能动。现在还不能动。
他带来的那些随从,看似松散,实则每个人的手都离兵器不远,眼神像鹰隼一样扫视着四周,
包括我这个微不足道的老板娘。这些人都是老手,嗅得到危险的味道。玄蝎嗤笑一声,
大手一挥:“喝酒!这鬼地方,能有一口热乎酒就算老天开眼。”众人哄然应和,
气氛重新活络起来,粗鄙的笑骂声和灌酒声充斥了小小的客栈。我低下头,
用抹布慢慢擦拭柜台,眼角的余光却像蛛丝,死死缠绕在玄蝎身上,
缠绕在那把“挽月刀”上。他在喝酒,一口接一口。这里的酒烈,掺水再多,后劲也足。
他看起来心事重重,或许是为了那“黑玉之约”,或许是为了别的,酒喝得又急又猛。很好。
酒能乱性,也能降低警惕。一个随从凑近他,压低声音:“蝎爷,约期是明日巳时,
鬼泣谷那边……都安排妥当了。听说这次几个长老都想……”玄蝎猛地瞪了他一眼,
那眼神凶戾得像沙漠里饿极了的狼,护卫头目立刻噤声,冷汗涔涔而下。“不该你打听的,
把嘴闭上。”玄蝎的声音不高,却带着冰冷的杀意,“看好你的人,明日之前,
别给老子惹事。”“是,是。”那人连声应诺,不敢再多言一句。
鬼泣谷……明日巳时……我记下了这两个词。玄蝎不再说话,只是闷头喝酒。
他的脸在跳动的火光下显得格外阴郁。时间一点点流逝,窗外天色彻底黑透,
只剩下狂风卷着沙粒,永无止境地抽打着门窗。护卫们大多也有了醉意,有的趴在桌上打鼾,
有的还在划拳行令,声音含混不清。是时候了。我转身从身后的架子上,
取下一只看起来有些年头的黑陶酒坛。坛口用泥封着,上面落满了灰。这坛酒,
在这柜台最深处放了五年。和我的仇恨一样久。里面不是掺水的马尿,是真正窖藏的烈酒,
性极烈,入口如刀,后劲能放翻一头骆驼。最重要的是,里面还泡着几味来自西域的草药,
能让人醉得更快,睡得更沉,并且,再也不会醒来。这是我为贵客准备的。我抱着酒坛,
走到他们桌旁,声音依旧沙哑平淡:“各位爷,看你们是豪爽人,这坛是小店最好的酒,
叫‘忘忧’,算我请的。”玄蝎抬起醉眼朦胧的眼,看了看那坛酒,又看了看我,
咧嘴笑了笑,露出发黄的牙齿:“哦?老板娘倒是大方……这荒沙野地的,还有这等好货?
”“祖上传下来的法子,就剩这一坛了。”我小心地拍开泥封。
一股极其醇烈又带着奇异草木辛香的酒气弥漫开来,
让那几个还没醉死的随从都下意识抽了抽鼻子。“好酒!”一个随从赞道。玄蝎盯着那酒,
眼神浑浊,却忽然问了一句:“老板娘,在此地开店几年了?”我照实答:“五年了。
”五年。和慕容家灭门,一模一样的时间。他目光在我脸上停顿了一瞬,那眼神带着探究,
但很快就被更浓的酒意覆盖。他大概只是随口一问,一个边陲客栈的女老板,五年还是十年,
对他而言并无区别。他把碗中余酒一饮而尽,“好,就尝尝大漠的忘忧。
”我的手在坛子边握紧。酒碗已空。新酒就要续上。3.就在酒要入碗的刹那,
角落里那个一直沉默的彷佛不存在的灰衣男子,突然猛地一拍桌子大喊一声说:“好酒!
好酒啊!”带着浓重的醉意,摇摇晃晃的站起身,跌跌撞撞的朝这边撞过来。
我闪身想躲竟没有躲开,哐当一声,我手中的酒被他撞落,酒液混着瓷片溅了一地,
顿时满屋酒香。我心头一紧,他看似笨拙的步伐,竟藏着极高明的身法。“混账东西!
”一个随从怒喝一声,伸手就要去抓灰衣男子的衣领。看似醉醺醺的男子,
在护卫手掌即将触及他肩膀的瞬间,脚下轻轻一滑,身形以一个近乎不可能的角度扭开,
护卫势在必得的一抓竟然落空了。护卫一愣,玄蝎的眼神却骤然变得锐利,
如同发现了猎物的毒蛇。他抬手,阻止了手下进一步的行动。在这荒僻之地,
突然出现这样一个目的不明、深藏不露的高手,由不得玄蝎不心生警惕。
灰衣男子对这一切恍若未觉,打着酒嗝,身子一歪,似乎要跌倒,与我擦肩而过的瞬间,
我垂在身侧的手心里多了一个小布团。他像是耗尽了力气,扶住身边一张桌子,
对着我和玄蝎含糊的摆手,“对...对不住,
脚...滑...喝...喝多了...我赔...”说着,摸出了一锭银子扔在桌上,
随后踉踉跄跄的走到门口,掀开帘子,径直走了出去。玄蝎死死盯着灰衣男子的背影,
杀意在眼底闪现,但最终,被他压了下去。五年之约在即,鬼泣谷凶险未知,
此时不宜节外生枝。“扫兴。不喝了,睡觉。”玄蝎摆摆手,径直上楼,
一众随从立刻跟着也都走了。堂内恢复了死寂。我退回柜台后,
迅速而隐蔽的展开手心里的小布团。上边有五个模模模糊糊的字,
像是用小棍子划出来的:他有百解散。百解散?神医门独有的解毒灵药,据说可解任何毒。
此药配方只传给神医门历任掌门,传闻配方中有一味是生长在极北严寒之地山峰上的灵草,
极难采到,所以神医门每年也只能做出十颗,在江湖中千金难求。
又传闻神医门上任掌门赵大风在三年前一天夜里暴病而亡,死前没来得及传下配方,
所以此药如今剩的数更是屈指可数,多少银子都买不到。玄蝎竟有百解散。
“忘忧”毒不死玄蝎,还会让我暴露,而面对他们一行十人,我绝无胜算。
所以那灰衣男子是在帮我。可是他是谁,
他又是怎么知道酒里有毒、玄蝎有解药的?我把布条扔进炉子,带着疑问走到门外。
大漠的夜,气温骤降,夜风冰冷,和白天的炎热反差极大。天边挂着一个半圆的月亮,
到了这里,连月亮的光都变得不一样了,昏黄粗粝,不似江南的月光,永远温婉透彻。
四下早已没有了灰衣男子的影子,只有永远不会停的风,吹着沙子,吹着檐下的骨铃。
嗒嗒...嗒嗒...仇人就在眼前,我能忍住吗?不能。我深深的吸了一口冷冽的空气,
精神一振。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是什么目的,不管他知道多少,今日就是天塌了,
这仇也得报。我转身进去端了火盆送上楼,玄蝎一伙很高兴,这大漠的夜,正需要火盆。
回到大堂,熄灭烛火,我一动不动的坐在黑暗中,静静的听着楼上的动静。
火盆里我加了无色无味的药粉,没有毒,只是能让他们睡个好觉。4.不到一个时辰,
楼上已是鼾声如雷。我悄无声息的行动起来。屋外栓骆驼的棚子里,堆满了干草柴火,
我一捆一捆抱进来,铺满楼上走廊、楼梯、还有大堂。又从床下拖出几个沉甸甸的皮囊,
里面是满满的火油。我小心翼翼的将火油倒在铺好的甘草柴火上。做完这一切,我来到门外,
小心的将檐下的骨铃一一取下、包好,背在身上。最后取出火折子,轻轻一吹,
微弱的火苗在风中摇曳。陪了我五年的客栈,到谢幕的时间了。火折子飞了出去。
轰的一声火焰腾起,沿着火油轨迹飞快蔓延,几乎是瞬间,客栈已成火海。“走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