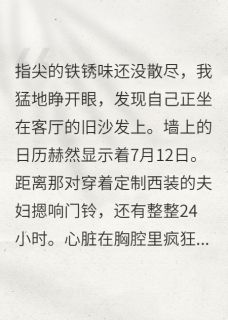
老槐树的叶子落了又绿,第三年春天时,枝桠已经够到二楼的窗台。窗台边的桌上,
放着薇薇的高中课本,一只布偶小熊被她摆在旁边,
耳朵上的补丁换了块新的蓝布是我用她穿小的校服改的。“妈!爸爸修的秋千好高!
”楼下传来她清脆的叫喊,混着林建国钉木板的“砰砰”声。我探头望去,
他正往树干上固定铁链,额角的汗珠滚进下巴的胡茬里,阳光下闪得像碎钻。
那之后我们搬回了老宅。老宅实际上离老城区不远。而老城区那套房子赶上拆迁,
我们用拿到的拆迁款将老宅重新修缮了一番。院门口的梧桐树是去年栽的,
现在已经能遮住半扇门。周记者送的扩音喇叭被改成了喂鸟器,挂在树杈上,
每天清晨都有麻雀来啄食,叽叽喳喳的像在开早会。“秀兰!取报纸不?
”蓝布衫大爷拎着油条走过,烟袋锅别在腰间,晃悠悠的,
“今天头版说顾宏远在里面又闹事,想绝食呢。”我接过报纸,
头版照片上的顾宏远瘦得脱了形,囚服套在身上像挂着的布袋。
报道说他挪用的农民工工资基本都被追回,
拿到工资的农民工总念叨“多亏了那对护闺女的夫妻”。“刘梅呢?”我翻到社会版,
上周说她在精神病院总抱着枕头喊“瑶瑶”。“还那样。”大爷咬着油条含糊道,
“听说她弟弟判了十五年,没人给她送钱了,护工都懒得理。”而顾瑶,
因为故意伤害高达十几人,且其中有百分之八十都是重伤,手段极其残忍,被判了无期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