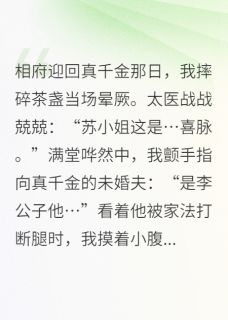
赵翠花如同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在嫁入陈府后,便彻底消失在了京城的视线里,连一丝涟漪都未曾再激起。
东南河工案的余威逐渐平息,朝堂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只是这平静之下,暗涌的潜流只有身处漩涡中心的人才能感知。东宫的威势在那一役后如日中天,依附者众,但暗中的窥伺与反扑,也从未停止。
清心观的日子,在表面上的诵经洒扫和暗地里的风起云涌中,缓慢流淌。萧彻的书信往来愈发频繁,内容已不仅限于东南案后续,开始涉及吏治、赋税、乃至边关军务。他像是在打磨一件趁手的兵器,不断将更复杂、更危险的议题抛给我,测试我的极限。
我如同行走在万丈悬崖边的钢丝上,殚精竭虑,不敢有丝毫懈怠。每一次呈上的策论都力求完美,每一次应对都如履薄冰。身体在深山的清寒和精神的极度紧绷下,日渐消瘦,唯有那双眼睛,在昏黄的油灯下,燃烧着越来越亮的火焰。
萧彻送来的东西也悄然变了。不再是枇杷、胭脂,而是上等的野山参、温补的阿胶,甚至有一次,是一小盒御医特制的安神丸。东西依旧通过云舒云卷的手递来,没有任何言语,却比任何言语都更清晰地传递着一个信息:他需要我活着,需要我保持清醒。
这种无声的豢养与掌控,让我在疲惫之余,心底也滋生出一种冰冷的警惕。我知道,自己陷得越来越深了。
直到那个冬日的傍晚。
寒风卷着细碎的雪沫,敲打着道观破旧的窗棂。我正伏案疾书,分析着北境粮草转运的弊端,一阵突如其来的、尖锐的恶心感毫无预兆地涌上喉咙!
“呕……”
我猛地捂住嘴,冲到墙角放着的铜盆边,剧烈地干呕起来。胃里翻江倒海,却什么也吐不出,只呛得眼泪直流。
“姑娘!”一旁的云舒云卷脸色骤变,立刻上前扶住我。
云舒的手迅速搭上我的腕脉。她的指尖带着常年习武的薄茧,按在我的脉搏上,凝神细察。片刻之后,她猛地抬起头,眼中充满了震惊和难以置信,看向云卷。
云卷立刻会意,转身快步走了出去。不多时,她带着一个须发皆白、背着药箱的老者走了进来。正是当初在相府诊出“喜脉”的王太医!他显然也是东宫的人,被云卷悄然带进了观中。
王太医看到我,浑浊的老眼里闪过一丝复杂,但很快被恭敬取代。他示意我坐下,伸出枯瘦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搭在我的腕脉上。
时间在压抑的寂静中流逝。只有窗外风雪的呜咽和炭盆里银霜炭燃烧的噼啪轻响。
许久。
王太医缓缓收回手,脸上神色变幻不定,震惊、了然、还有一丝如释重负的庆幸。他对着我,深深一揖,声音带着无法抑制的颤抖:
“恭喜……姑娘!是……喜脉!已近……两月!”
“轰——”
仿佛一道惊雷在脑中炸开!
我瞬间僵在原地,血液似乎都凝固了!指尖冰凉,下意识地抚上自己平坦的小腹。
喜脉?
近两月?
那正是……我与萧彻在书房中,无数次深夜密谈、心力交瘁之时……那几次,他批阅奏折至深夜,我侍立一旁研墨应对,困倦至极时,他曾命内侍端来参汤……有一次,他见我脸色苍白得厉害,甚至将他手边那碗未动的参汤推给了我……
是他!
竟然是他!
一股冰冷的寒意瞬间从脚底窜上头顶!原来那无声的“照拂”,那温补的参汤,从一开始就带着如此深沉的心机和算计!他早已算准了这一步!他要的,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幕僚,一个“眼睛”!
他要的,是一个绝对无法摆脱他掌控的、血脉相连的……筹码!
云舒和云卷也惊呆了,随即脸上都露出了凝重的神色。她们显然也想到了什么。
王太医跪在地上,额头渗出冷汗,大气不敢出。
我扶着冰冷的桌沿,缓缓坐下。最初的震惊和寒意退去后,一股难以言喻的疲惫和……认命般的冰冷,席卷了全身。
原来,从踏入这间书房的那一刻起,不,或许从我在相府晕倒、指认李逸的那一刻起,我的命运,就已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牢牢地钉在了通往他身侧的道路上。
孩子。
一个流着萧氏皇族血脉的孩子。
这才是他真正想要的“投名状”,一个我永远无法背叛、永远无法挣脱的……枷锁与阶梯。
我闭上眼,靠在冰冷的椅背上,良久。
再睁开眼时,眼底所有的情绪都已褪去,只剩下深潭般的平静。
“王太医,”我的声音有些沙哑,却异常平稳,“此事,除殿下外,不得泄露分毫。”
“是!是!老朽明白!”王太医如蒙大赦,连连叩首。
“云舒,云卷,”我看向她们,“往后,我的饮食起居,需更仔细了。”
“是,姑娘!”两人齐声应道,眼神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郑重。
窗外,风雪更大了。
我抚着小腹,感受着那里面悄然孕育的、微小却足以改变一切的生命。
前路是深不见底的漩涡,还是直上青云的天梯?
或许,从来都是同一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