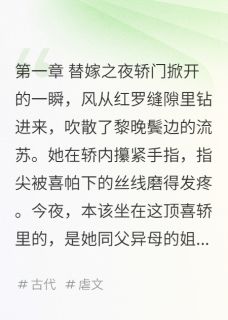
第一章替嫁之夜轿门掀开的一瞬,风从红罗缝隙里钻进来,吹散了黎晚鬓边的流苏。
她在轿内攥紧手指,指尖被喜帕下的丝线磨得发疼。今夜,本该坐在这顶喜轿里的,
是她同父异母的姐姐黎芷。可黎芷逃了。她逃走前留下一张纸条:“妹妹,世道艰难,
各安天命。”天命?黎晚喉间发涩。侯府为保和权相陆琛的联姻体面,
将她塞进了这场无路可退的婚事。锣鼓喧天,喜队沿着宣德街行进。
街边茶楼里有人压着嗓子说:“替嫁?啧,权相府可不是好惹的地方。陆相清冷心狠,
娶谁都只是添个名头,何况是个替身。”喜轿停在权相府门外。大红灯笼连成一片,
门匾如墨,沉沉压着夜色。黎晚被嬷嬷搀下轿,一路送入内院。喜房里烛火正旺,
鸳鸯蜡泪横流,桌上的合卺酒泛着琥珀光。“新娘稍坐,待相爷来行礼。
”管事妈妈笑容恭谨,目光却带着探究与淡淡不屑。门扉合上,屋中只剩她与燃烧的火光。
喜帕下的世界猩红而闷,她能听见自己心跳。脚步声在门外停住。门开,风声跟着进来,
烛影一晃。黎晚听见靴底踏地的声响清冷又克制,那样的节奏感让人不自觉地屏住呼吸。
喜帕被挑起,一截锋利的银光从她视野边缘划过,是根簪子。黎晚抬起头,终于看见他。
陆琛,朝中权相,年不过二十七,玉冠乌发,眉眼如削,清冷如霜雪。
他身上是黑绣暗纹的蟒袍,衣摆无声地拂过地毯。那双眼淡得像极寒之水,落在她脸上时,
没有一丝温度。他目光不动声色地停了半瞬,像在审视,像在衡量。
随后淡淡开口:“你不是黎芷。”四个字,像刀尖轻轻落在桌面,没溅起声响,
却逼得人呼吸发紧。黎晚指尖一颤,仍挺直背脊:“今夜拜堂之人,是陆相的妻。
”陆琛看着她,没有立刻发火。片刻后,他似笑非笑:“倒也会说。坐吧。”他没有伸手,
也没有靠近。只是绕过她,在桌边坐下,修长的手指捏起酒盏,像看一件无关紧要的陈设。
“合卺就免了,你不配。”他说。黎晚喉间那口气在胸腔打转,却硬生生咽了下去。
她不是来为自己出气的。她来,是为活路。侯府在她身上不肯投一分怜悯,她只有把背挺直,
走过这条刀锋。“相爷既不愿行礼,那我自去更衣。”她站起,声音平稳。她才走到屏风旁,
陆琛忽而道:“你的名字。”“黎晚。”她回身看他,黑白分明的眼里没有畏惧,
“迟来的晚。”“晚?”他重复一遍,指尖敲了敲杯沿,“迟不迟,无关紧要。
记住——你进了权相府,便是我的人。不许擅离,不许妄言,不许妄求。”黎晚没说好,
也没说不。她只是垂眸行礼,平静地把屏风拉合,把所有的脆弱藏在红色背后。
烛火跳了一下,像极了她心里那点倔强的小火星。这一夜无洞房,无合卺。
权相府的月亮冷冷挂在檐角,如一枚锋利的银钩。无人知晓,窗纸后,
那个被替嫁来的姑娘悄悄把手心掐出了血——那条细细的疼,让她记得:她来,
不是做谁的替身。她要活成她自己。——第二章初遇争锋次日一早,
权相府的仆从们都在打量新夫人。有人说她温顺,有人说她眼里一根铁。流言不重要,
重要的是规矩。黎晚被带去向长公主请安。长公主萧绾,陆琛的姑母,
皇族中最不好惹的一位。她不出声,屋里的温度就会低两分。“替嫁?
”萧绾把玩着一串血珀珠,“你可知自己在赌什么?”“赌一条活路。”黎晚跪拜,
清晰回答,“赌我能把这日子过下去。”萧绾看了她很久,忽地笑了笑:“倒不蠢。起来吧。
”她不再多问,只吩咐身边侍女把一方旧玉递过来:“权相府的门,出得去难,进得来也难。
你既进了,就别哭。拿着吧,算我见面礼。”玉不华美,却温润。黎晚谢过,安静收好。
出门时正撞上陆琛。他似乎也来请安,目光掠过她手里的玉,淡淡地“嗯”了一声,
像是在承认什么,又像无所谓。“相爷,”管事总管压着嗓子禀报,“三司那边来人,
说东市案有了新证。您看——”“进衙门。”陆琛一句话,人已迈步出去。黎晚侧身让开,
裙摆掠过他的衣角。两人无话,却像互为两道锋面,相交一瞬,彼此寒意都被打量了个遍。
午后,内院传来消息:主母不许出门。“相爷命的,”嬷嬷笑容温软,“新婚头三日,
夫人安心养神,别乱走。”黎晚抬眼:“我只是想去藏书阁找两本书。”“夫人想看书,
奴婢让小厮去取。”黎晚笑了笑,不再说话。她知道,这是软禁的另一种说法。夜里,
屋外风声更重。她点了烛,打开一个小包裹。
里面是她在侯府时偷偷收集的几张旧账单和一根细细的银针。银针不是用来绣花的,
是用来打开某些锁的。她把银针**妆匣暗扣,转了两下,“咔哒”,暗层弹起。
里面是一张小小的纸片,上面写着几个名字,倒映在烛火里,字字如刀。这些名字,
都指向一个人——当年的靖北将军府覆灭案。她的父亲,便死在那场案里。
黎晚把纸片重新藏好,抬起头时,窗外掠过一道黑影。她指尖一紧,袖中银针落入掌心。
门缝处,风声断了一下,有人轻轻落地。接着一只干净利落的手,从门后伸来,
像一只冷调的野兽探入他人地盘。“谁?”黎晚沉声。“自己人,”那人低笑了一下,
声音极轻,“夫人别怕,陆相派我来看看,有没有人趁夜造次。”门开,一名黑衣侍卫拱手,
脸上带着不甚恭敬的随意:“夫人胆子不小,银针握得不错。”“你叫什么。”黎晚问。
“阿黎。”“很好记。”侍卫挑眉:“夫人也挺好记。晚,是吧?迟来的晚。
”他把话说得轻佻,却在打量屋里的一切。目光在妆匣处停了一瞬,随即移开,
像什么也没看见。“相府规矩多,夫人最好乖些。”他笑笑,脚步一晃,
像来时一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月色里。黎晚轻吸一口气。她知道,陆琛并非毫不在意。
他在看,且看得极深。那么,好。她也让他看看——她不是一只待宰的小羊。
——第三章宅院生存第三日,内院女眷设宴,名为新妇洗尘。
京中权贵的夫人**来了不少,碎金流光,笑里藏刀。“听说黎家的大姑娘不见了?
”一位王妃笑吟吟,“这替嫁的小姑娘,倒也不易。”“说不定是攀了高枝,
”另一位夫人扇子轻摇,“有些人若不是运气好,哪轮得到进权相府门?”话没指明,
箭却直直射向黎晚。她稳稳饮了一口茶,笑得温婉:“夫人说得是。
只是我这个人运气向来不好,今日能在此,多半靠各位贵人的抬爱。”众人一愣,
随即有人“噗嗤”一声笑了——这不是软话,是软刀子。既不承认,也不谄媚,
偏偏把别人抬到了“抬爱”的位置,逼得人顺着台阶下。“黎夫人会说话,
”长公主萧绾看戏一般,慢悠悠扔下一句话,“会说话的人,不一定会做事。”“学着呢。
”黎晚起身行礼,落落大方。一曲未完,门外有小厮慌慌来报:“长公主,
外头宫里递了旨——圣上临时召相爷入宫议事。”屋里静了一瞬。萧绾接旨,眸色深了深。
她笑道:“都散了吧。京里不大太平,各位回去在自家院门口多放几盏灯。”她一开口,
众人收敛笑色。权相府与皇宫的风向,向来被人盯得紧。宴散时,侧门角落里,
有两个丫头悄声议论:“你看那黎夫人,真有意思……瞧那手,白,却有茧。还有她步子,
不像闺阁里养出来的——”“别说了,被人听去要挨打的!”黎晚站在回廊,
看着远处的廊灯被风吹得左右摇。她知道,府里有人开始扒她底。这不是坏事,
反而能乱人眼。她要做的,是在水里稳住身,同时把手悄悄伸到水下,把一张网撒开。
夜色深时,阿黎又出现了。他站在檐下投下的影子里,像一道线。“夫人,”他说,
“你今日收揽了两位管事嬷嬷的心。”“你看到了?”黎晚不意外。“我看到了,
相爷也看到了。”阿黎笑,“他让人别动你。”“为什么?”“说你会自己动。”黎晚失笑。
她转身回屋,把门关上,背靠着门板,心里某处微微松了点力。她做了三件事:一,
替库房账目加了两行“旧年未清”,二,命人把内院井边的青苔刮净,三,
给长公主送去一罐她亲手配的安神香。三件事看似无关,
却能掀动三重水波——账目会引来注目,井边会换走人心,安神香会换来庇护。她不急,
慢慢下饵。——第四章宴会惊艳半月后,宫中设菊宴。圣上好菊,文武列坐,
诸家贵女献诗投壶,热闹非凡。权相府新妇被点名入宴,名义是“慰劳贤相新婚”。
这是一场看人的宴。黎晚入场时,并不艳。她穿一身月白褙子,衬得人越发清冷。
与那些珠翠流霞比,她像一束被霜打过的兰,雅,却不张扬。“权相夫人也来献艺?
”右丞相之女顾筠挑眉,笑容里全是锋芒,“可敢同我一试?”顾筠有才名,京中女学魁首,
喜欢在宴上挑人。她以为一个替嫁来的新妇不过是土鸡,被她拔两根毛就能丢出场去。
黎晚看着她,淡淡一笑:“琴棋书画,我都不擅。若要献艺,愿以兵书论一段制敌之策。
若顾**不屑,我自罚三杯。”殿上静了静。许多人都看向高坐的陆琛。陆琛手执酒盏,
眼底并无赞许,也无阻止。他只把盏放下,指尖轻敲了一下案几。圣上来了兴趣:“兵书?
你如何解?”“今岁北境边卡有小股匪乱,扰民甚重。”黎晚行礼,“若臣妇为北境将领,
所布之策分三步——”她把“诈营引敌、断粮截水、夜袭拔寨”的三式拆解成浅显的话,
落于席间,连宫中侍卫都听得目光一亮。“言之有物。”萧绾笑着敲案,“不像闺阁。
”顾筠脸色僵了僵,勉强笑道:“夫人既通兵事,不若再作一首诗,以梅喻志,如何?
”“好。”黎晚不推,“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她接着翻出一首新作,
短短四句,气象清绝。殿中便有人低声赞叹。顾筠的扇子“啪”的一声合上。
权相府那位冷刀子的主人,眼底终于有了一丝非常细微的变化。他脊背微倾,
像是不经意地把目光停在她唇线的起伏上。“赐座。”圣上笑得开怀,“权相夫人不俗。
”人群中的另一个目光却冷了下去——靖北案余孽的名册里,
忽然多出一个不该出现的人名:黎晚。宴散之后,偏殿的影壁后,有一段低语。“她是谁?
”“权相夫人。”“查她。越快越好。”殿外风起,菊香被夜色撕开,
露出一道冷到骨里的味。——第五章暗潮涌动回府的马车里,黎晚的手心出了汗。
她不是因为献艺紧张,她是在回味殿中那道冷意——直觉告诉她,有人记起了靖北将军府。
“方才你和顾筠,收得漂亮。”阿黎掀帘,递来一杯温茶。“帮我盯着顾府。”黎晚接过,
“她背后,不止女学的先生。”阿黎“嗯”了一声,又低低道:“东市案翻得差不多了。
相爷今日入宫,怕是要给谁摘人头。”“谁的?”“刑部尚书。”黎晚的手指一顿。
刑部尚书邢源,正是当年审靖北案的主审之一。“今夜三更,刑狱司有一批旧卷要转仓,
”阿黎压低声音,“你若想看,只有一个时辰。”“相爷知道吗?”“他没说让你去,
”阿黎眨眼,“也没说不让。”夜深,京城风紧。刑狱司后院的墙不高,翻过去需要一根绳。
黎晚在屋里换了一身夜行衣,把小匣里的银针、蜡丸、火折、竹签一一收好。她站在镜前,
盯着自己半秒,嘴角勾起一点冷。她不是替身,她是猎人与饵。翻墙时,
手臂被檐角划了一道口子。疼意逼出冷汗,她却轻声落地,像一只适应夜的猫。
卷库在最里头,门上锁很新。黎晚端详片刻,取出银针,薄薄一转——“咔哒”。门开。
潮湿纸张的味扑面而来。她一卷一卷地翻,蜡丸贴在边角标记关键页,火折点得微小,
光线像蚊子一样抖。她很快找到了“靖北”二字。
“靖北将军府叛国私通案卷——”她手抖了一下,压住。
里记着她父亲的“罪证”:边境仓库少粮两成、军械账目不清、将军府与北夷使者私下往来。
每一条,都有证人证词。签名是——邢源、顾问之。顾问之,是顾筠的叔父。“脚步声。
”阿黎的声音像一阵风从窗缝钻进来,“有人来了。”黎晚飞快把卷宗塞回,蜡丸一抹,
留下不易察觉的灰痕。她与阿黎贴墙。外面两名狱卒走过,谈笑风生。
“听说明儿尚书大人要被问了?”“谁知道。朝堂风云哪,是我们两颗头能猜的?
”脚步远去,夜又沉下来。黎晚与阿黎对视一眼,心里同时闪过一个名字:顾家。
翻窗而出时,院墙外忽然一阵光影摇晃,有人举着灯笼拦在路口。“谁在那里!”一声厉喝,
紧跟着弩箭破空的“咻”!阿黎翻身将黎晚一把压倒,箭贴着她耳鬓过去,钉在石阶上,
震得她耳膜发痛。“走!”阿黎架起她,直直往巷内更深处窜。身后追兵拥出,
火光像溅落的金雨。他们绕过一条死胡同,前方突然是一堵墙——无路。“给我。
”黎晚从袖里抽出钩绳,抛向墙头,第一下没挂稳,第二下“嗒”地一声咬住。
她咬牙攀上去,手臂伤口被绷开,血顺着手心一路滴落。墙头上,忽地站着一个人。黑衣,
风里立着,像夜的骨头。是——陆琛。他手里拿着一支无羽黑箭,指尖漫不经心地弹了一下。
墙下追兵刚拐入小巷,黑箭已先他们一步扎进对面墙缝,“铮”的一声炸开一团火星,
惊得马匹乱嘶,追兵仓皇。陆琛垂眸,看着墙上抓绳而上的女人,眼底是一片深黑的静。
“下来。”他抬手,五指伸出,像给她递了一个台阶。黎晚盯着他半秒,把手放上去。
两人的掌心一合,汗与血交在一起,热得让人惊醒。落地时,
阿黎已经把巷子另一头的火头引走。陆琛不紧不慢转身,像他只是掌灯夜行。“你在做什么?
”他的声音很淡,却不容回避。“找一份答案。”黎晚迎着他,眼尾还挂着没擦干的汗,
“与我父亲有关。”“你父亲是谁?”“靖北将军,黎曜。”夜风像突然被扔进一块石头,
在两人之间荡出一圈一圈的波纹。陆琛很久没说话。他只垂眼,看着她指节边的一点血。
“回府。”他最终说,“你想要的,我——”他顿了半拍,“或许可以给。
”他说“或许”的时候,很轻。可就是这两个字,像在黎晚心里亮起一盏微弱却顽固的灯。
——第六章身份将启回府后,陆琛吩咐人把黎晚的院子重新整修,窗棂换了,门槛抬了,
摆件添了两件,不华不奢,都是耐看之物。“你在笼络我?”黎晚问。“我在安静。
”陆琛淡淡,“你太吵。”黎晚笑出声:“原来相爷也会说笑。”他不接话,
只命人递来一卷旧册:“东仓失粮案的副本。看完还我。”黎晚接过,指尖微凉。
她翻开第一页,血便“嘭”的一声撞在耳后。
纸上钉着一张旧旧的密札——“顾氏商号与北境粮行私通账目”。“顾家?”她抬头。
陆琛目光像刀背:“你在宴上踩了顾筠,她叔父会还礼。”“他若还礼,我也不怕。
”“你该怕。”他走近一步,低声道,“你现在的每一步,落在的都是别人的眼睛里。
你不是在替自家复仇,你是在借我的手。那就记着——借刀,先看刀锋向哪边。
”黎晚安静了片刻,忽然行了一礼:“多谢相爷。”陆琛看她,
神色终于缓了一分:“别谢我。我们只是暂时同路。”“同路也好。”他转身要走,
忽又回头:“你手臂伤口,叫医官来上药。”“我自己会缝。”他停住,
像是第一次真正重新打量她:“你会缝合?”“学过一点。”“嗯。”他“嗯”的这一声,
像不经意的认同,轻轻落在她肩上。夜很深。院外的风把桂花香吹得很碎。她坐在灯下,
解开袖子,看着血痕里翻卷的皮肉,捏住针线,一针一线在肉里穿过去。疼痛让她喘得轻,
眼里却很亮。门外有人影一晃,是萧绾。“手稳。”萧绾看了一眼,丢给她一瓶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