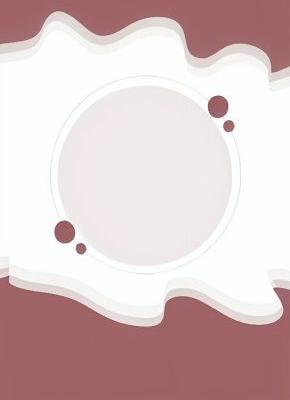
前导未婚妻头七,一个陌生男人上门退婚。他说那场夺走她性命的车祸,是她为了摆脱他,
精心策划的一场“自我了断”。而我,这个她用命也要嫁的人,却对她的过去一无所知。
1白菊和百合堆砌的灵堂,空气稠得像凝固的猪油,甜腥味挥之不去。我机械地握手、松开,
虎口已麻。定制黑色西装熨帖,却如铁皮勒进皮肉,每次呼吸都带着肺叶的刺痛。
黑白照片里,曾被誉为古典**神的林婉眉眼低垂,清冷如一捧抓不住的雪。还有三天,
本是我的婚期。门口骤起的嘈杂,像粗糙的锯子锯断了哀乐。
硬底皮鞋毫无顾忌地踩在大理石上,伴随陈特助急促的低阻。我皱眉望去,
一个灰扑扑的影子硬闯进来——是个穿着极不合身灰色西装的中年男人。
地摊货的西装肩宽得像挂在衣架上,袖口却短了一截,露出黑黄粗糙的手腕。头发油腻打绺,
指间夹着半截劣质香烟,一股陈年烟草混合酸腐汗臭的味道,如尖刀般捅破满室奢华香水。
宾客如避蛇蝎,嫌恶退散。赵铁柱对鄙夷目光视若无睹,径直走到供桌前,不鞠躬,不默哀,
抬头用一种近乎穿透的眼神,肆无忌惮地审视林婉的遗像。那眼里没有敬畏,
只有黏糊糊、令人作呕的审视。我胃里翻涌,刚抬手示意保镖,赵铁柱却动了。“啪!
”一声脆响,一张折得皱皱巴巴、边缘泛黄、满是污渍的纸,被重重拍在洁白的供桌布上,
震得一只青苹果滚落,砸在我的脚边。“徐老板是吧?”赵铁柱咧开嘴,
参差不齐的黄牙缝里卡着绿色残渣,音量足以让前排所有人听见,
“我是林婉那娘们的正牌男人。听说她死了,我来随个礼,顺便把五年前的这桩婚事退了。
”灵堂死寂。“把他扔出去。”我的声音冷得像冰渣。保镖上前扣住赵铁柱肩膀。他不挣扎,
反而怪笑,指着那纸:“怎么?心虚?不信?这上面有她按的红手印,有村的公章!
白纸黑字!”被拖着经过我身边时,赵铁柱猛地死死扒住我的胳膊,在昂贵面料上留下污痕,
凑近我的耳边,口臭直冲鼻腔,压低的语气带着狎昵的笃定:“林婉左大腿内侧,靠近根部,
有块指甲盖大的红色蝴蝶胎记。她脸皮薄,每次行房都要关灯,
还非得拿被子遮着……徐老板,那地方,你也没少摸吧?”轰!我脑中一根弦断了。
那极其私密的位置……这无赖怎会知道?我要推开他的手僵在半空,整个人如被液氮封冻。
赵铁柱趁机将一张脏污名片塞进我的口袋,
阴森地看了一眼遗像:“她欠老子的彩礼还没肉偿完。想让她在下面安生,
你就去翻翻她那豪宅卧室床底下,最里面那个鞋盒里的红鞋子。那是她这辈子都洗不掉的债。
”说完,他踢踏着沾满泥点的皮鞋,哼着下流小调,扬长而去。我站在原地,指甲深陷掌心,
细微的颤抖从身体深处传来。口袋里那张名片,像烧红的烙铁,灼烧着我的理智。
葬礼结束那晚,我没有回酒店。方向盘打得急促而疯狂,我的帕拉梅拉撕裂夜色,
直奔半山那座婚房。我必须知道,那双红鞋子,到底藏着什么。
2我的保时捷在婚房车库熄火,金属冷却的细微爆裂声在死寂中格外清晰。我没立刻下车。
车内弥漫着林婉留下的冷冽雪松香,此刻却刺得我鼻腔发痒。我没开灯,
借月光绕过施坦威钢琴,直闯主卧——那个林婉生前笑着称为“禁地”,
说床底藏了惊喜的地方。我跪下,西装裤摩擦地板发出沙沙声。深吸一口气,
我趴下将手伸进床底漆黑的虚空。灰尘的绒毛感激起我的鸡皮疙瘩。
摸索过几个装换季衣物的硬纸箱后,我的指尖终于在死角触到一个异样的硬纸壳。
不是林婉常用的光滑礼盒,而是受潮发软、起层的劣质瓦楞纸盒。我几乎狼狈地将盒子拽出。
是个印着“富贵花开”的生锈铁皮月饼盒。掀开盖子,陈年樟脑丸味呛人而出。盒内,
一双红得刺眼的布鞋静静躺着。艳俗的大红布鞋面,绣着鸳鸯戏水,针脚粗糙。
最刺目的是鞋尖几点早已干涸的暗红泥点,像凝固的血痂。这就是赵铁柱嘴里的“债”。
我喉咙干涩发痛,颤抖地将手伸进左脚鞋筒,指尖触到一层硬纸。
猛地一抽——一张泛黄的热敏纸飘落。B超单。姓名栏:林二妮。检查日期:五年前的十月。
宫内早孕,7周+。五年前十月……正是林婉说去维也纳进修的时候。原来所谓的封闭训练,
是她怀着别人的孩子?愤怒像高压蒸汽顶开我的理智阀门。半小时后,咖啡馆角落。
苏雯赶到时妆都没卸,眼底乌青。她刚端起咖啡,我已将B超单拍在玻璃桌上。
苏雯瞳孔骤缩,咖啡泼在手背却毫无知觉,声音发颤:“这……哪里来的?”“林二妮是谁?
”我死盯着她,“五年前她其实是去生孩子了,对吗?”“不是!她没生!”苏雯尖叫反驳,
意识到失态后慌乱擦桌子,“徐远,有些事你不知道更好!赵铁柱去找你了是不是?那是鬼!
吸血鬼!”“被逼着生孩子?”我指着B超单。“我说了那不是孩子!”苏雯彻底崩溃,
隔着桌子抓住我的手腕,指甲嵌进我的肉里,眼泪晕黑了她的眼妆,“那是她的买命钱!
那村子吃人!你别查了,求你别查了!
”她压低的声音每个字都从牙缝挤出:“知道赵铁柱为什么敢头七上门?
因为林婉没‘离婚’!在他们那儿,没离婚的女人死了,尸体得运回去入祖坟!
如果让他们知道你在查这孩子,林婉就算烧成灰,也会被他们挖出来配阴婚!”配阴婚。
三字如生锈的钉子,狠狠钉进我的耳膜。我看向单子最下角,
一行模糊小字:同川镇卫生院影像科。3我的保时捷底盘在土路上刮出刺耳的闷响。
导航早已失灵,只有黄泥路蜿蜒进被浓雾锁住的山坳。我把车停在枯死的老槐树下,
推开车门,牛粪和烧秸秆的焦糊味呛得我皱眉。村口立着两人高的青石碑。走近了我才看见,
斑驳的石碑背面密密麻麻刻满名字。有些被红漆粗暴涂抹,像刚结痂的伤口。
没被涂掉的名字旁,刻着一串串数字:李招娣,三千五。王秀琴,四千二。张桂兰,
两千八……我的手指在虚空中颤抖。这不是功德碑。是把活人明码标价的“价目表”。
我的视线在名字间疯狂搜索,直到在最下角的阴影里,
看到被红漆狠狠划了一道杠的名字——林二妮。红杠旁,
新刻着一行潦草狰狞的小字:“欠三百万,未清”。我扶着石碑干呕起来。
在这个现代文明触手可及的世界,这里竟还保留着把女性当牲**易的“贞节榜”。
村子里静得可怕,只有几声嘶哑的狗叫。焦糊味越来越重,混着塑料烧焦的刺鼻气味。
在村头摇摇欲坠的瓦房前,我找到了赵铁柱。他正蹲在废弃轮胎垒成的火盆前,
手里抓着一把卷成筒的纸,一张张往火里扔。火苗窜得老高,噼啪作响。
我看清了那是什么——林婉的海报。是她获“荷花奖”金奖的剧照,是她巡演的宣传单,
是被撕碎的杂志封面。画面里身姿曼妙、光芒万丈的她,在浑浊火舌中卷曲、发黑,
化作带着油墨味的灰烬。“你疯了吗?!”我冲上去,一脚踹翻火盆。
未烧尽的海报漫天飞舞,像黑色的雪。赵铁柱慢吞吞站起来,拍了拍裤腿的灰,
看着地上只剩半张脸的林婉海报,浑浊的眼珠里透出毛骨悚然的满足。“烧了好,干净。
”他咧开嘴,露出一口黄牙,“她在外面浪了这么多年,又是跳舞又是露大腿,脏了。
烧给祖宗验明正身,下辈子还得回来做我的婆娘。”“她是人!不是你的东西!”“人?
”赵铁柱往地上啐了口浓痰,黏稠的液体在我锃亮的皮鞋边炸开,“老板,做生意讲诚信。
当年买她花了我们全家凑的三万——五年前,那是巨款。”他伸出三根粗短的手指,
指甲缝里塞满黑泥:“她跑了五年,老子五年没婆娘睡,没人做饭。利滚利,三百万,
不过分吧?本来她说这周打钱,结果自己把车往护栏上撞。人死了,账得还。父债子偿,
妻债夫还,天经地义。”我的理智彻底崩断。我揪住赵铁柱油腻的衣领,
把他狠狠掼在土墙上,陈年灰尘扑簌簌往下掉。“那是意外!刹车失灵!
交警报告写得清清楚楚!”被抵在墙上的赵铁柱不反抗,反而发出夜枭般的怪笑。“意外?
”他从油污的枕头底下摸出个黑色物件,丢向我,“大明星车技那么好,开了十几年车,
怎么会把油门当刹车踩到底?你自己听。”我接住那支外壳磨掉漆的老式录音笔。
赵铁柱整理衣领,眼神阴毒:“她死前寄回来的,指名给我。这是她最后的‘还款凭证’。
”我手指颤抖着按下播放键。滋啦——电流声后,没有遗言,没有哭泣。是风声。
极速流动的风声。紧接着——吱嘎——!!!刺穿耳膜的金属摩擦声。
刹车片被外力强行抱死,因车速过快在地面剧烈拖拽的声音。持续整整十秒。我玩车多年,
太清楚这声音意味着什么——这不是刹车失灵。这是在高速行驶中,
死踩刹车的同时没松油门,并在最后一刻猛打方向盘。摩擦声即将断裂的刹那,
录音笔里爆出一声嘶吼。不是温柔婉转,不是恐惧尖叫。是林婉的声音,撕心裂肺,
绝望中带着狠劲:“赵铁柱!我把命还给你!这婚我退了!你敢动徐远一下,
我做鬼也不放过你——!”轰!!!巨响。死寂。风声、狗叫、怪笑,都从我的世界消失了。
我呆呆站着,手里冰冷的录音笔像烧红的烙铁,烫进我的心里。没有意外。
那场夺走她生命的车祸,是她为切断吸血鬼伸向我这爱人的黑手,
为彻底摆脱“未婚妻”身份,精心策划的以命换命的“退婚”。她用死堵住赵铁柱勒索的嘴,
用死把我隔绝在肮脏泥潭之外。如果不是今天找来,这秘密将永远随变形的跑车埋葬。
我喉咙涌上腥甜,死死攥着录音笔,指关节因过度用力发出脆响。眼前开始模糊。
那是极度的悲痛,正转化为我心中的滔天恨意。4刹车声像生锈的锯子,在我脑神经上拉扯。
视野瞬间充血猩红。我抄起供桌上沉甸甸的铜香炉,用尽全力砸向赵铁柱的脑袋。“去死!
”赵铁柱怪叫着翻滚躲开。香炉砸在水泥地上,“哐当”巨响,四分五裂。
陈年香灰炸成灰白烟雾,弥漫整个堂屋。我喘息着,胸膛剧烈起伏。尘埃渐落时,
我看见有个东西从香炉残骸里滚出来,撞在我的皮鞋边。灰白色,两指节长,两头磨得圆润。
是人的小指指骨。记忆如电流击穿脊背——林婉那双“会说话的手”,
总在跳舞后蜷起左手小指。她常年戴肉色硅胶指套,说是练功受伤,指甲长坏了。
原来不是长坏。是没了。她缺失的这截骨头,竟被装在这香炉里日夜烟熏。“那是我的!
别动!”墙角的赵铁柱像疯狗般扑来,脸上满是封建的恐惧:“那是镇物!不能见光!
见了光那娘们会回来索命!”就在他脏手要触到指骨的瞬间——警笛声撕裂夜空。
我进山前就给刑侦队的发小打了电话。对付这种无赖,法律才是最硬的拳头。“警察!
抱头蹲下!”木门被踹开,强光手电把堂屋照得雪亮。赵铁柱还没反应过来,
已被两名刑警按在香灰地上。“警官!城里人杀人啦!”他杀猪般嚎叫。
领头的张警官戴上白手套,小心翼翼捡起指骨,装入透明物证袋。拉链“滋啦”合上时,
赵铁柱像被抽走脊梁骨,瘫软在地。失去这“镇物”,比坐牢更让他恐惧。**在门框上,
死死攥着录音笔。赵铁柱被押出门外,即将塞进警车时,突然停住脚步。他慢慢转过头。
浑浊的眼珠死死钉在我身上,眼神里没有了恐惧,
只有扭曲恶毒的快意——像断脊毒蛇喷出最后一口毒液。“徐大少爷,你以为你赢了?
报警告我勒索伤人?”他咧开黄牙怪笑,“哈!真正的杀人犯是你啊!是你把她逼死的!
是你这‘救世主’亲手送她进地狱!”我冷冷看着他。“不信?”赵铁柱被警察推搡着,
仍拼命扭头,脸上肌肉因亢奋抽搐,“你现在就把送她那枚几百万的钻戒拆开看看!
看钻石托槽底下藏着什么好东西!”“那是你的眼,也是催她命的符!”车门重重关上,
隔绝了癫狂大笑。警笛声远去,山村重归死寂。我站在空荡院子里,夜风吹得脊背发凉。
我僵硬地把手伸进西装口袋,
摸到那个冰凉的丝绒盒子——清理林婉遗物时我特意带上的订婚戒。卡地亚定制款,
主钻五克拉,纯净度FL。百万造价,象征完美无瑕的爱情。月光下,钻石璀璨夺目。
赵铁柱最后那句话,像刺扎进我心里最柔软处。托槽底下……藏着东西?
手指无意识摩挲戒指底座,金属冰冷坚硬。没有犹豫。我拉开车门,发动机低沉轰鸣。
我的黑色帕拉梅拉如被激怒的野兽,调头朝市区狂奔。这个深夜,
只有一个地方能解开这个谜。5凌晨三点,鉴定室的松香和咖啡味混成一股酸苦。聚光灯下,
五克拉粉钻像颗跳动的心脏。老吴戴着寸镜,镊子悬在半空:“徐少,这一刀下去,
几百万的戒托就废了。真要拆?”我坐在阴影里,从烟盒磕出根烟,没点,手指把滤嘴捏扁。
沉默像铅板压着我的胸口。老吴叹了口气,换上钨钢撬刀。“咔哒”一声脆响,
爪镶底座崩开。钻石滚落黑丝绒布上。铂金凹槽里没有爱情誓言,嵌着米粒大的黑色方块。
高倍放大镜下,方块露出狰狞真容——精密电路,侧面一行微不可见的编号。
老吴镊子“当啷”掉在桌上:“操……军工级微型音频定位器?徐少,
你这是娶媳妇还是防特务?”我的肺像被冰手攥紧。这戒指是母亲给的。
那天她拉着林婉的手,慈眉善目:“这是徐家传家宝,只传长媳。”林婉感动得眼眶通红,
除了洗澡从未摘下。原来那不是认可,是项圈。是把人当牲口圈养的电子项圈。
我抓起黑色芯片,手指泛白。读卡器连接笔电,
屏幕弹出一张密密麻麻的轨迹图——令人窒息的网。
红色光点记录着林婉生前三年的所有行踪:医院妇产科、练功房、菜市场,
连便利店买水停留的三分钟都被精确标记。我胃里翻江倒海。我以为的自由恋爱,
在母亲眼里,是全程直播的楚门秀。鼠标滑动声刺耳。时间轴拉到车祸当天。
轨迹出现诡异折线——林婉的车没有驶向大剧院,而是在下午两点调头开往城西郊区。
红点在一片荒芜坐标上闪烁,停留两小时四十分钟。红星化工厂,废弃多年。我合上电脑,
抓起车钥匙冲出门。城西夜风带着铁锈和腐烂植物的腥气。废弃化工厂大门早已拆除,
杂草高过人头,风中如鬼手挥舞。车灯刺破黑暗,照亮满地锈化工桶和玻璃渣。我举着手机,
深一脚浅一脚踩进泥泞,走向定位最后停留处——三号车间后的堆料场。
空气残留刺鼻化学药剂味。坍塌的石棉瓦下,有块被刻意撬起的水泥板。我跪在地上,
不顾手指被粗糙边缘磨破,疯了一样掀开板子。底下塞着防雨布,
包着一部屏幕碎成蛛网的旧手机——十几年前的老款诺基亚。我跑回车里,
手哆嗦着插上车载充电器。漫长两分钟开机后,屏幕亮起幽蓝微光。没有通话记录,
没有APP。信箱草稿箱里,静静躺着唯一一条未发送短信。编辑时间:车祸前半小时。
收件人栏只有两个字,却像重锤砸碎我的脊梁:婆婆。手指在屏幕上方悬停很久,
我颤抖着点开。“妈,我答应您的所有条件。我会像五年前一样‘消失’,
也会把林二妮和那个孩子的秘密永远带进棺材,绝不让徐家的门楣蒙羞。
求您撤回对他公司上市的所有阻击,资金链断了他会疯的。也求您……别动他在乎的人。
这婚,我拿命退。”车厢死寂。只有充电器电流的细微滋滋声。我盯着那行字,
眼角干涩发痛,却流不出一滴泪。所有疑惑在此刻闭环。没有抑郁症,没有意外,没有背叛。
那个傻女人,被我的亲生母亲用我的前途做筹码,逼进了必死的绝路。而她到死,
都在用决绝的方式保护我那可笑的自尊和事业。五年前的消失是交易。五年后的死亡,
还是交易。我把碎屏手机揣进怀里,贴着胸口。冰凉的触感像刀子在剜我的肉。我慢慢抬头,
透过挡风玻璃看向远处山顶——灯火通明的富人区,住着滨海最有权势的人,
也住着那个吃斋念佛、慈眉善目的“好母亲”。我伸手挂挡,动作轻得像抚摸情人的脸。
脚下油门瞬间踩到底。我的帕拉梅拉如受伤发狂的黑豹,咆哮着撕裂夜幕,
朝那座象征权力与血统的半山庄园狂奔而去。6我的帕拉梅拉冲出废弃工厂,
如黑箭射向半山。凌晨四点,徐家老宅灯火通明。苏式园林在白墙黑瓦间透出清贵的冷。
我一脚踹开红木大门。檀香味让人窒息。母亲穿着素净真丝旗袍,
正修剪一盆价值学区房的黑松。她头也不抬,捻去剪刀上的松针:“这么晚,带着烂泥味,
这就是继承人的教养?”我大步走去,把包着防雨布的旧手机拍在红木案上,震得黑松颤抖。
“教养?”我的声音嘶哑,“妈,您的教养是用儿子的前途逼死一个女人?”母亲放下剪刀,
接过热毛巾擦手,淡漠地扫过手机:“既然知道了,就该明白我的苦心。林婉那种出身,
配不上徐家。”“因为她被拐卖过?因为她在地狱里挣扎过?”我盯着母亲的脸,
第一次觉得那妆容像画皮。“不止这些。”母亲眼神陡然锋利,“赵铁柱是无底洞。
五年前他能卖林婉,五年后就能拿着她生过野种的证据,把徐氏股价拉到跌停!徐远,
你是商人,该懂什么叫止损。”“所以你用孩子威胁她?”我的心脏被攥紧,
“你明知那是她的噩梦!”“不这样,她怎么会死心?”母亲冷笑,“我告诉她,
那个‘野种’还在赵铁柱手里。如果她不离开你,不把破事烂在肚子里,
我没法保证孩子能不能见到明天的太阳。”她顿了顿,
语气像在评价一件瑕疵品:“我给了她选择。拿着三百万远走高飞,
或者看着孩子和你一起身败名裂。没想到她选了第三条路——为了不让你背上污点,
她选了死。不过也好,死人最能保守秘密。”“那是命啊……”我后退一步,“在你眼里,
两条人命不如股价重要?”母亲重新拿起剪刀,对准黑松一根旁逸的枝条:“这棵树值钱,
就是因为不断修剪长歪的枝叶。那个女人,就是长在你身上的歪枝。”“咔嚓。
”翠绿松枝掉落在地毯上。我胃里翻江倒海。原来林婉活在两个恶魔的夹击中——一个要钱,
一个要命。而我像个傻子,享受着她用生命换来的“安稳”。我转身就走。“站住!你去哪?
”母亲厉喝。“去赎罪。”我没有回头,“找那个孩子。徐家欠她的,我还。”走出门时,
清晨阳光刺破黑暗,却照不进我心里。刚坐进车里,我的私人手机震动。
**阿K发来加密邮件。没有正文,
只有一个附件:【五年前·同川镇卫生院·绝密档案复印件】。进度条加载。
泛黄病历单出现在屏幕。
字迹像尖刀扎进我的眼球:【患者姓名:林二妮(林婉)】【入院诊断:重度营养不良,
腹部遭钝器击打致胎盘早剥。】【手术记录:孕28周,胎心停止。行引产术。
】【死胎处理意见:作为医疗废弃物焚烧处理。】时间戳:五年前冬天。
“轰——”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手机滑落,砸在换挡杆上。死胎?焚烧?
如果孩子五年前已死,骨灰都被当垃圾烧掉……那么母亲用来威胁林婉的“人质”是谁?
那个让林婉甘愿赴死也要保护的“孩子”,究竟是谁?还是说,林婉明知孩子早就不在,
却依然被某种更可怕的东西勒住咽喉,不得不走向死亡?这背后,不仅是交易,
还有一个被烧成灰烬后又被人重新捏造的弥天大谎。我抓起手机,油门踩到底。
我的帕拉梅拉如失控的野兽,冲向关押赵铁柱的方向。
第7章看守所会见室的冷气开得像停尸房,空气中弥漫着霉味和劣质消毒水的刺鼻气息。
隔着厚重的防爆玻璃,赵铁柱的脸显得更加扭曲。他被铐在特制铁椅上,双手虽被限制,
却依然神经质地抓挠脖子,指甲在垢腻的皮肤上划出血痕。我没有坐下,直直站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