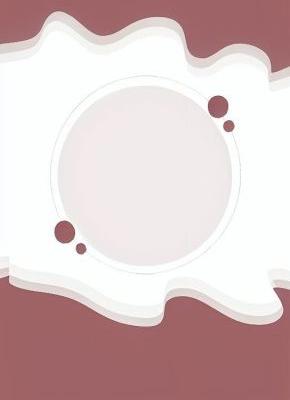
周启明把我堵在墙角,刚从外面回来的他,
衬衫领口还带着别的女人的香水味和一抹刺眼的口红印。“白露身体弱,闻不得油烟,
你搬去厂里宿舍住。”他一边说,一边往我手里塞了一沓厚厚的大团结,
语气是那种惯有的、高高在上的不耐烦。我捏着那沓钱,指尖在崭新的人民币上轻轻划过,
笑了。“周厂长,让她住进来可以。”我抬眼,对上他那双已经毫无爱意的眸子,
慢悠悠地开口:“但我们得谈谈价钱。”他愣住了,似乎没料到我会这么说。
我将钱扔回他怀里,一字一句,清晰无比:“羞辱我的价码,可不止这些。
”---01“你什么意思?”周启明皱起了眉头,
英俊的脸上写满了不解和一丝被冒犯的恼怒。“意思就是,从今天起,我姜禾,
不做你周启明的免费保姆了。”**在冰冷的墙壁上,第一次用这种平静到冷漠的眼神看他。
“白露要住进来,住我亲手刷的墙,用我亲手打的家具,睡我结婚时的婚床,可以。
但这是我的家,不是收容所。”我伸出一根手指:“主卧,一个月,三百块。
”周启明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姜禾,你疯了?你掉钱眼里了?”“是啊,被你逼的。
”我笑得更开了,“怎么?周大厂长财大气粗,连这点钱都舍不得为你娇弱的白月光花?
”“还是说,在你心里,她也就值这个价?”这句话显然刺痛了他。周启明最在意的,
就是在白露面前的体面和强大。他咬着牙,从皮夹里又抽出几张大团结,
狠狠拍在我手心:“给你!以后别再耍这种花样!”我捏着那几百块钱,心里一片冰凉。
钱货两讫,公平交易。想当年,他周启明还是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村小子,是我,
不顾家里反对,拿出我妈留给我傍身的金镯子,又低声下气地求遍了所有亲戚,才凑够了钱,
让他盘下了那个快要倒闭的街道小厂。工厂刚起步那两年,没钱请工人,我跟着他一起,
白天在车间里满身油污地修机器,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踩着缝纫机赶订单。有好几次,
累得直接趴在堆积如山的布料上就睡着了。他抱着我,红着眼眶发誓:“禾禾,
等我们有钱了,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这辈子,我周启明绝不负你!”誓言犹在耳边,
可说誓言的人,心已经变了。工厂步入正轨,成了市里的纳税大户,
他周启明也成了人人敬仰的周厂长。而我,这个陪他吃苦的糟糠之妻,却成了他眼里的污点。
他开始嫌我没文化,嫌我穿得土气,嫌我上不了台面,带不出去。直到半年前,
他在一次广交会上,重逢了他年少时求而不得的“白月光”——白露。
白露是城里长大的姑娘,读过大学,会说几句洋文,身上总有股淡淡的雪花膏香味。
她看我的眼神,总是带着一种不加掩饰的鄙夷,仿佛我就是地里的泥,而她是天上的云。
从那天起,周启明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他身上的香水味换了一款又一款,
衬衫上的口红印也越来越刺眼。我哭过,闹过,质问过。可换来的,
只有他越来越冷漠的脸和一句“你能不能懂点事”。心,就是在那一次次的争吵和失望中,
慢慢死掉的。现在,他要把白露正大光明地领回家。也好。既然他想要体面,想要两全其美,
那我就把我的尊严和感情,全都明码标价。白露搬进来的那天,开来了周启明新买的桑塔纳,
阵仗极大。她穿着一身时髦的连衣裙,站在院子里,像个女主人一样,
指挥着搬家工人把她的东西搬进主卧。街坊邻居都伸长了脖子看热闹,对着我指指点点。
“哎,那不是姜禾家吗?怎么又一个女的搬进去了?”“你还不知道?那是周厂长的相好,
城里来的大学生呢!”“啧啧,姜禾也太窝囊了,老公都把人领家来了,屁都不敢放一个。
”我充耳不闻,抱着一盆我妈留下的兰花,搬进了院子角落那间又小又暗的杂物间。
白露扭着腰肢走过来,涂着丹蔻的指甲尖轻蔑地划过我的兰花叶子,柔声细语,
话里却带着刀子:“姐姐,真是委屈你了。启明也是心疼我,说我身子弱,
住不得阴暗的房间。”我抬起头,冲她一笑:“不委屈。三百块一个月的房租,这地段,
你去哪儿找?再说,你们付的钱,可不止房租。”白-露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周启明从屋里走出来,搂住白露的腰,不悦地瞪着我:“姜禾,你又在胡说八道什么?
”“没什么,”我拍了拍手上的土,“提醒一下房客,别忘了交水电费。”说完,
我不再理会他们,关上了杂物间的门。门外,传来白露娇滴滴的抱怨和周启明不耐烦的安抚。
我坐在小床上,打开一个上了锁的木盒子。里面,是我这些年偷偷攒下的所有私房钱,
加上刚刚从周启明那里“赚”来的三百块,一共是三千六百七十二块。
我小心翼翼地把钱抚平,压在箱底。我的目标很明确,当年,我为他投入了五万块。如今,
我要连本带利,全部拿回来。这憋屈的厂长夫人,谁爱当谁当。02白露的到来,
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池塘,把这个家搅得天翻地覆。她是个很会“作”的女人。
今天说床板太硬,睡得腰疼,明天说窗帘颜色太深,影响心情。周启明对她有求必应,
立刻拉着我,让我去置办新的。我看着他递过来的钱,面无表情地开口:“换床可以,
席梦思的,进口货,要两千。窗帘,丝绒的,也要五百。”“你怎么不去抢?
”周启明瞪大了眼睛。“市场价就是这样。”我摊开手,“我一个家庭妇女,又没工资,
你总不能让我贴钱给你养别的女人吧?传出去,别人还以为你周大厂长破产了呢。”“你!
”他气得说不出话,但为了在白露面前维持他一掷千金的形象,还是咬牙把钱给了我。
我拿着钱,转身就去了百货大楼。席梦思我买了,但买的是最便宜处理的那款。
窗帘我也买了,但扯的是处理的的确良布头。剩下的钱,一分不差地进了我的小金库。
白露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开始变着法地挑衅我。她不肯叫我“嫂子”,在外面跟人介绍我时,
只说是“家里的保姆”。厂里开联欢会,每个干部家庭都有两张票。
周启明毫不犹豫地把票给了白露。那天,白露穿着一身大红色的连衣裙,挽着周启明的胳膊,
像个真正的厂长夫人一样,接受着所有人的恭维和羡慕。而我,被堵在家里,连门都出不去。
第二天,我直接找到了周启明的办公室。他正在和白露你侬我侬地喂水果。看到我,
他脸上闪过一丝不耐烦:“你来干什么?没看到我正忙吗?”我没理他,径直走到他面前,
摊开手。“什么?”“昨晚的事,该结账了。”我淡淡地说。“什么账?
”“对外宣称我是保姆,剥夺我参加联欢会的权利,这两项,
都严重损害了我的名誉和家庭地位。”我像个没有感情的账房先生,“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
给你打个折,一共两千块。现金还是转账?”周围的空气瞬间凝固。白露的脸涨成了猪肝色,
她没想到我敢这么直接地打上门来。周启明更是气得浑身发抖,他一把挥开我的手,
怒吼道:“姜禾!你还有完没完了!你除了钱还认什么!”“我认啊,”我看着他,
一字一顿地说,“我还认合同精神。当初你求我凑钱时,写的欠条上白纸黑字,
说盈利后给我百分之五十的分红。这些年,我见过一分钱吗?”“现在,你不给我分红,
践踏我的尊严,我收点精神损失费,过分吗?”周启明被我堵得哑口无言。当年的欠条,
早就被他哄着我烧掉了。可这事,是他心里的一根刺。他怕我闹大,影响他的声誉。最终,
他还是不情不愿地从抽屉里拿了两千块钱,摔在我面前。“拿着钱,赶紧滚!”我捡起钱,
仔细地数了数,然后冲他笑了笑:“合作愉快,周厂长。”转身离开办公室的那一刻,
我听到了身后白露尖利的哭声和东西被砸碎的声音。我的心,却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
拿着这笔钱,我没有存起来。我拐进了市里最大的律师事务所,
找到了一个叫沈维韦卡南的年轻律师。“沈律师,我想咨询一下,
如果我想创办一个自己的服装品牌,需要走哪些流程?商标注册又该怎么弄?”沈维韦卡南,
是我在一次法律援助的讲座上认识的。他年轻,有冲劲,更重要的是,他眼里有光,
有一种周启明早就失去了的东西——正义感。他看着我,有些惊讶,
但还是专业地解答了我的所有问题。临走时,他突然问我:“姜女士,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回头,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
轻声说:“因为我想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不只是钱,还有被偷走的人生。从那天起,
我的生活分成了两半。一半,是在周家那个压抑的牢笼里,
扮演一个斤斤计较、满身铜臭的“疯女人”,不断地从周启明身上榨取我的“启动资金”。
另一半,是在我的秘密基地里,画设计图,研究布料,联系代工厂。
我给我的品牌取名叫“涅槃”。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我要让所有看不起我的人都看到,
我姜禾,不是只能依附男人才能活的藤蔓。我是一棵树,即便被砍断,也能在春天发出新芽。
03白露大概是我见过最沉不住气的“小三”。她想要的不仅仅是周启明的钱和爱,
她更想要的是彻底取代我,抹去我在这个家里存在过的一切痕迹。
她看上了我妈留给我的那间向阳的小书房,说想改成她的画室。周启明来找我谈。
我正在我的杂物间里,借着昏暗的台灯画设计图。“那间书房,白露想用。”他站在门口,
居高临下地说道。我头也没抬:“可以。一千块,一个月。”“姜禾!
”他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那是我家的房子!”“那也是我妈留下的陪嫁房。”我放下笔,
冷冷地看着他,“里面有我妈所有的藏书和我从小到大的奖状。你觉得,一千块,贵吗?
”周启明噎住了。这栋房子,确实是我娘家的祖产。当年我们结婚,我爸妈疼我,
就把这栋位置最好的房子给了我当婚房,房产证上写的也是我的名字。这是我最后的底牌,
也是我敢于和他叫板的底气。他大概也想起了这一点,脸色变了又变,
最后还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千块钱。“钱给你,但你得把里面的东西都清走,
白露不喜欢看见别人的旧物。”“没问题。”我爽快地接过钱,“搬家费,另算。五百。
”周启明的拳头捏得咯咯作响,眼神凶狠得像是要吃人。我毫不畏惧地与他对视。最终,
他还是妥协了,又加了五百块。我用了一天的时间,把他付的“搬家费”花得明明白白。
我雇了城里最贵的搬家公司,让他们用最专业的态度,把我妈的书和我的旧物,
小心翼翼地打包,运到了我租在城郊的那个小仓库里。那个仓库,既是我的工作室,
也是我的避难所。白露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书房。她把我妈精心侍弄的书架拆了,
换上了她喜欢的欧式画架,墙上挂满了她画的那些不伦不类的油画。
她甚至还开了一个小型的“画展”,邀请了厂里有头有脸的人物来参观。那天,
家里热闹非-凡。白露穿着洁白的纱裙,像个骄傲的公主,在人群中穿梭,
接受着所有人的赞美。周启明满脸宠溺地跟在她身边,为她介绍着每一位“贵客”。
我一个人待在杂物间里,门缝里透出客厅的光,也传来了他们推杯换盏的笑声。突然,
门被敲响了。我打开门,是沈维韦卡南。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手里提着一个果篮,
站在门外,显得与这间破旧的杂物间格格不入。“沈律师?你怎么来了?”我有些惊讶。
“周厂长也邀请了我。”他笑了笑,目光越过我,看了一眼客厅里的景象,
然后又落回到我身上,“你的商标,已经注册下来了。这是文件。”他递给我一个牛皮纸袋。
我接过来,打开,看到“涅槃”两个字被印在正式的文件上,下面盖着鲜红的公章。那一刻,
我感觉心里有什么东西,破土而出。“谢谢你,沈律师。”“不用客气。”他看着我,
眼神里带着淡淡的关切,“姜女士,这样的日子,你打算过多久?”我沉默了片刻,
然后抬头,迎上他的目光,坚定地说:“快了。等我拿回我该拿的东西,我就离开。
”他点了点头,没再多问。就在这时,白露的声音尖锐地响了起来:“启明!
我的项链不见了!就是你上次从香港给我带回来的那条钻石项链!”客厅里瞬间安静了下来。
很快,周启明和白露就带着一群人,气势汹汹地冲到了我的杂物间门口。白露的眼睛红红的,
一看到我,就指着我,哭着说:“启明,家里就我们几个人,外人也进不来……一定是她!
她嫉妒你对我好,偷了我的项链!”所有人的目光,都像刀子一样,齐刷刷地射向我。
周启明看着我,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姜禾,是不是你拿的?把项链交出来,
我可以不追究。”我笑了,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周启明,在你心里,
我姜禾就是个会偷鸡摸狗的小偷吗?”“不然呢?”他冷哼一声,“你现在钻进钱眼里,
什么事做不出来?”好,真好。这就是我爱了十年,为他付出了一切的男人。我深吸一口气,
看着他们,一字一句地说道:“搜。你们可以搜。但是,如果搜不出来,又该怎么算?
”我目光直直地射向白露:“白**,你这条项链,值多少钱?”白露被我的气势镇住了,
下意识地回答:“五……五万!”“好。”我点了点头,“如果在我这里搜不出你的项链,
你就赔偿我名誉损失费,五万块。周厂长,各位领导,你们,都是见证人。”04“五万?
你抢钱啊!”白露尖叫起来,脸色煞白。她没想到我会反将一军,还把价码定得这么高。
“怎么?只许你污蔑我,不许我讨个公道?”我冷笑一声,环视了一圈看热闹的众人,
“还是说,白**你心里有鬼,根本就没丢项链,只是想找个由头来羞辱我?
”周围的人开始窃窃私语。“是啊,五万块,可不是小数目。”“这姜禾,
今天怎么这么硬气?”白露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求助似的看向周启明。
周启明此刻也有些骑虎难下。他知道我的脾气,如果今天真的搜不出东西,以我现在的性子,
绝对会闹得天翻地覆。可白露哭得梨花带雨,他又不能不管。他咬了咬牙,
对白露说:“别怕,有我呢。要是真没有,五万块我替你出!”然后,他转向我,
眼神阴鸷:“姜禾,这可是你自找的!搜!”两个厂里的保安走了进来,
开始在我的杂物间里翻箱倒柜。我的东西很少,几件旧衣服,几本书,
还有一个我用来画设计图的木箱子。他们把我的衣服扔了一地,把我的书翻得哗哗作响。
最后,一个保安打开了那个木箱子。里面,是我画的几百张设计图。白露的眼睛瞬间亮了,
她冲过去,一把抢过那些图纸,尖声叫道:“这是什么?你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土包子,
还会画画?这里面肯定藏着我的项链!”她疯狂地把图纸撒得到处都是,一张一张地抖着,
试图从里面找出那条根本不存在的项链。周启明也皱着眉,看着那些设计图。图纸上,
是各种款式新颖的连衣裙、衬衫、风衣,旁边还标注着详细的尺寸和面料说明。那画风,
那设计,完全不像是我这个“土包子”能画出来的。“姜禾,这些是……”他有些惊疑不定。
我没有回答他,只是冷冷地看着白露的表演。终于,所有的东西都被翻了个底朝天,
别说钻石项链,连根金项链的影子都没有。空气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焦在了脸色惨白的白露身上。“现在,可以赔钱了吗?”我走到白露面前,摊开手。
白露吓得连连后退,躲到周启明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