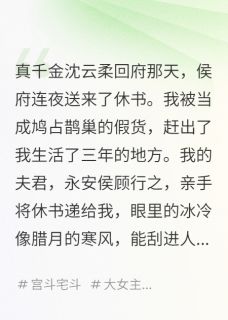
真千金沈云柔回府那天,侯府连夜送来了休书。我被当成鸠占鹊巢的假货,
赶出了我生活了三年的地方。我的夫君,永安侯顾行之,亲手将休书递给我,
眼里的冰冷像腊月的寒风,能刮进人的骨头里。他说:“沈知鸢,你既非沈家女,
便不再是我的妻。拿着这封休书,滚出侯府。”他身后,沈云柔穿着一身娇嫩的鹅黄,
怯怯地拉着他的衣袖,声音柔得能掐出水来:“侯爷,姐姐她……她也是无辜的,
不如就让她留在府里,做个偏房也好……”顾行之将她护在怀里,看我的眼神愈发厌恶,
仿佛我是什么脏东西:“她不配。云柔,你太善良了。”我握着那封薄薄的信纸,
指尖被纸张的棱角割得生疼。三年的夫妻情分,抵不过一句“血脉不正”。我没有哭,
只是平静地看着他,看着他当着我的面,宣布三日后,将以正妻之礼,迎娶沈云柔。
我被净身出户,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衣,在满府下人鄙夷的目光中,一步步走出侯府的大门。
那一刻,我觉得,我为顾行之而死的那颗心,终于凉透了。1“沈知鸢,你还在等什么?
难道要我亲自派人把你扔出去吗?”顾行之的声音里没有一丝温度。他曾用这把声音,
在我耳边低语过无数情话,说要与我一生一世一双人。如今,却成了催我离开的利刃。
我抬起头,目光越过他,落在他身后梨花带雨的沈云柔身上。她看起来是那么柔弱可怜,
一双眼睛哭得红肿,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可我知道,她那双看似无辜的眼睛里,
藏着的是怎样的得意与算计。“侯爷。”我开口,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我什么都不要,
只求带走我母亲留下的医箱。”那是我被抱错的养母,
一个温柔的乡野大夫留给我唯一的遗物。也是我从沈家,这个所谓的“家”里,
唯一想带走的东西。顾行之皱了皱眉,似乎对我的平静有些意外。在他看来,
我或许应该哭天抢地,死死抱住他的腿不放,求他垂怜。“医箱?”沈云柔怯生生地开口,
“姐姐,你一个大家闺秀,要那东西做什么?侯府什么金贵的药材没有,何必……”“闭嘴。
”我冷冷地打断她,“我与侯爷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吗?”沈云柔的脸色瞬间煞白,
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整个人摇摇欲坠,仿佛下一秒就要昏过去。“沈知鸢!
”顾行之果然勃然大怒,他一把将沈云柔搂得更紧,厉声呵斥我,“你放肆!
云柔是你的妹妹,更是未来的侯府主母,你敢对她不敬?”我笑了,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侯爷说笑了。我一个被扫地出门的弃妇,哪来的妹妹?更不敢高攀未来的侯爷夫人。
”我看着顾行之,一字一顿地说,“我只要我的医箱。给我,我立刻就走,
绝不再碍你们的眼。”三年的付出,嘘寒问暖,操持家业,为他挡下明枪暗箭。原来到头来,
只换来一句“你不配”。我的心,在那一刻,彻底死了。顾行之眼中的怒火几乎要将我吞噬,
但他终究还是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对身边的管家道:“把那个破箱子给她,让她快滚!
”2管家很快将那个落了灰的木箱子拿了出来,嫌恶地扔在我脚下。我弯下腰,
用袖子仔仔细细地擦去箱子上的灰尘,像是对待什么稀世珍宝。然后,我抱起箱子,
挺直了脊背,转身就走。没有回头,没有留恋。
身后传来沈云柔带着哭腔的、故作大度的声音:“侯爷,姐姐她一个人出去,会不会有危险?
要不要……派人送送她?”“不必。”顾行之的声音冷硬如铁,“她这样心如蛇蝎的女人,
死在外面也是活该。我们准备大婚要紧,别为这种不相干的人费心。”不相干的人。
这五个字,像五把尖刀,狠狠扎进我心里,将那最后一点残存的温情也绞得粉碎。
我抱着医箱,走出了侯府那扇朱漆大门。京城的晚风吹在身上,冷得刺骨。
我却觉得前所未有的轻松。从今往后,沈知鸢,只是沈知鸢。不是沈家的假千金,
也不是永安侯的弃妻。我凭着记忆,在城南一个偏僻的巷子里,租下了一个小小的院落。
院子很破旧,但很安静。我将医箱里的东西一一拿出来,那些熟悉的草药气味让我感到心安。
养母教我医术时曾说:“鸢儿,医者仁心,但也要懂得自保。这世上最难医的,是人心。
”那时候我不懂,如今,我懂了。我用身上仅有的一点碎银,
置办了些简单的家具和生活用品。第二天,我就在院门口挂上了一块木牌,
上面写着“知鸢医馆”。我不求名满京华,只求能在这乱世中,有个安身立命之所。
医馆开张的第一天,并没有病人。我也不急,只是安安静静地整理着药材,抄录着医书。
日子清贫,却安宁。侯府的一切,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3我以为我和顾行之的纠葛,
到此为止了。却没想到,从我离开侯府的第二天起,他开始做梦。这些,
都是后来我从别人口中听说的。据说,他做的第一个梦,是在他们定下婚期的那个晚上。
梦里,不是洞房花烛,而是刀光剑影。那是两年前,他奉命去边境剿匪,途中遭遇埋伏。
一支淬了毒的冷箭,从暗处呼啸而来,直指他的心口。是他以为早已面目模糊的前妻——我,
沈知鸢,在千钧一发之际,奋不顾身地扑到他身前,用自己的身体,
为他挡下了那致命的一箭。他记得清清楚楚,梦里的我,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素裙,
脸色苍白,唇边却带着一抹释然的笑。“顾行之,”我倒在他怀里,气若游丝,
“能为你死……我心甘情愿。”毒箭穿胸而过,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襟。他惊恐地抱着我,
一遍遍地喊着我的名字,可我却再也没有回应。顾行之是从这个噩梦中惊醒的。醒来时,
他浑身冷汗,心脏狂跳不止。窗外月色如水,身侧躺着的,是满面娇羞的沈云柔。
他看着沈云柔的脸,脑海里却不受控制地浮现出梦中我倒在他怀里,了无生息的模样。
那感觉太过真实,真实到让他分不清究竟是梦,还是曾经发生过的事。他烦躁地起身,
披衣走到窗前。两年前,确实有一次剿匪遇伏,他也确实差点中箭。但他记得,
是他的一个亲卫为他挡了箭,那个亲卫后来重伤不治,他还为此厚恤了其家人。
怎么会梦到是沈知鸢救了他?荒谬。他一定是最近太累了。为了迎娶云柔,
他确实耗费了不少心神。顾行之这样安慰着自己,强迫自己将那个诡异的梦抛之脑后。
4可是,噩梦并没有停止。第二个梦,发生在他与沈云柔大婚的前夜。这一次,
梦里没有血光,只有侯府深夜沉寂的书房。他因为一份重要的军报,在书房熬了三天三夜。
梦里的我,端着一碗热腾腾的参鸡汤,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侯爷,夜深了,
喝点汤暖暖身子吧。”我的声音温柔又带着一丝心疼。他记得梦里的自己,头也不抬,
语气很不耐烦:“放下吧,我没空。”我没有走,只是默默地站在一旁,为他研墨,
替他整理散乱的文书。夜很长,烛火摇曳,我陪着他,一站就是一夜。天快亮时,
我抑制不住地咳嗽起来,咳得那么厉害,仿佛要把心肺都咳出来。他终于抬头,
不悦地皱起眉:“吵死了,身子不好就滚回房去,别在这里碍事。”我苍白着脸,
对他歉意地笑了笑,转身默默离开。梦里的他,并没有看到我转身之后,用手帕捂住嘴,
那雪白的手帕上,瞬间被刺目的鲜血染红。这个梦,比上一个更让顾行之感到心悸。
因为这个场景,也真实发生过。那是去年冬天,他确实为了军务在书房熬了几个通宵。
他也确实记得,沈知鸢来送过汤,他也确实……呵斥过她。只是他不知道,
她那时候已经病得那么重了。他一直以为,她只是有些体弱。府医也说,是操劳过度,
需要静养。他给了她最好的药材,最好的补品,却从未真正关心过,她的病,到底因何而起。
原来,是为了他。为了他这个冷漠自私的丈夫,积劳成疾,耗尽了心血。顾行之从梦中醒来,
天光大亮。今天是他的大喜之日。满府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可他的心里,
却像是被一块巨石压着,沉闷得透不过气来。他起身,
鬼使神差地走到了我以前住的那个院子。院子已经被打扫干净,准备给沈云柔的陪嫁丫鬟住。
曾经我亲手种下的那些花草,早已被尽数拔除,光秃秃的一片。他忽然想起,我刚嫁给他时,
曾兴致勃勃地对他说:“夫君,我把院子打理一下,种上你最喜欢的兰花,好不好?
”他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他好像是说:“随你。”然后,他就再也没踏进过这个院子一步。
顾行之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心里第一次生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慌。5大婚当日,
顾行之整个人都有些心不在焉。拜堂的时候,他看着眼前披着红盖头的沈云柔,
脑海里闪过的,却是我三年前嫁给他时的模样。那时候的我,也是这样一身红嫁衣,
隔着盖头,他都能感觉到我的羞涩与欢喜。“礼成——”司仪高亢的声音将他拉回现实。
他掀开盖头,露出一张娇美如花的脸。沈云柔含羞带怯地看着他,柔声唤道:“侯爷。
”周围是宾客们的恭贺声,一切都是那么喜庆,那么圆满。可顾行之的心,却空落落的。
洞房花烛夜,他喝了很多酒。沈云柔温柔地为他宽衣,伺候他躺下。他看着她忙碌的身影,
又想起了我。以前,每当他喝醉了,都是我这样默默地照顾他。替他擦脸,喂他喝醒酒汤,
然后安安静静地守在一旁,等他睡熟。他从未觉得这有什么。身为他的妻子,
这不都是她该做的吗?可为什么,现在换了一个人,他却觉得哪哪都不对劲?“侯爷,
您是不是不高兴?”沈云柔小心翼翼地问。顾行之闭上眼,烦躁地挥挥手:“我累了,睡吧。
”那一夜,他又做梦了。梦里,是更久远之前的事。是他还是个不受宠的庶子时,
在冰天雪地里被罚跪祠堂。是我,当时还是沈家娇生惯养的大**,
偷偷给他送去了一件厚厚的冬衣,和两个热乎乎的包子。“快吃吧,别饿坏了。”梦里的我,
笑得眉眼弯弯,像冬日里最暖的太阳。他记得,现实中,确有其事。只是,他一直以为,
当初给他送东西的,是沈家的另一个丫鬟。他后来发达了,还特意将那个丫鬟寻来,
给了她一份丰厚的赏赐。难道……他一直都记错了?那个在他人生的寒冬里,
唯一给过他温暖的人,竟然是沈知鸢?这个认知,像一道惊雷,在顾行之的脑海里炸开。
他猛地从床上坐起,惊出了一身冷汗。身边的沈云柔被他惊醒,睡眼惺忪地问:“侯爷,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顾行之看着她,眼神复杂。他忽然开口问道:“云柔,
你小时候……有没有在冬天,给我送过吃的?”沈云柔愣了一下,随即眼眶一红,低下头,
委屈地说:“侯爷,您怎么……突然问这个?那时候,我还在乡下受苦,连饭都吃不饱,
哪里……哪里有机会见到您……”她的回答,像一把锤子,狠狠敲在顾行之的心上。
他一直以为,自己娶的,是年少时的那一点温暖。他一直以为,自己厌弃的,
是一个鸠占鹊巢的冒牌货。可梦境却在声嘶力竭地告诉他,他把一切都搞错了。
他亲手推开的,才是他生命里唯一的光。6从那天起,顾行之像是疯了一样,
开始派人满京城地找我。他想找到我,不是为了弥补,而是为了印证。他想亲眼看看,
那个被他赶出侯府的女人,是不是真的像他想的那样,过得穷困潦倒,凄惨无比。只有这样,
才能让他心里那种莫名的恐慌,稍微平息一些。然而,手下人带回来的消息,
却让他一次又一次地失望。“回侯爷,没找到。城里所有能落脚的破庙、道观都找过了,
没有沈氏的踪影。”“侯爷,问了城门口的守卫,最近并没有符合沈氏样貌的女子出城。
”“侯爷,沈家那边也派人问过了,他们说,自从沈氏被赶出侯府,就再也没跟家里联系过,
他们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一个大活人,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顾行之越来越烦躁。
那些关于我的梦,还在继续。他梦见我为了给他筹集军饷,偷偷当掉了我母亲留下的嫁妆。
他梦见我为了维护他在朝堂上的名声,亲自去求那些曾经看不起我的贵妇人们,
受尽了冷眼和嘲讽。他梦见我替他挡下政敌的毒酒,自己吐血昏迷了三天三夜。梦里的我,
为他付出了一切,无怨无悔。梦里的他,却对这一切,视若无睹,心安理得。梦境与现实,
尖锐地对立着。一边是我浓烈到化不开的爱意与牺牲。一边是他冷酷无情的厌弃与羞辱。
这种强烈的撕裂感,几乎要将顾行之逼疯。他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睁着眼,直到天亮。
他变得沉默寡言,喜怒无常。整个侯府,都笼罩在一片低气压之下。沈云柔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她用尽了浑身解数,想要讨好他,安慰他。她学着我以前的样子,为他熬汤,
为他打理书房。可她越是这样,顾行之就越是烦躁。“别碰我的东西!”有一次,
当沈云柔想要替他整理书案时,他猛地挥手,将她推倒在地。沈云柔摔在地上,
不敢置信地看着他。顾行之的眼里,是她从未见过的暴戾和厌恶。“滚出去!”他低吼道。
沈云柔哭着跑了出去。书房里,只剩下顾行之一人。他看着一室的狼藉,痛苦地抱住了头。
他到底……是怎么了?7在我开医馆的第二个月,我终于迎来了我的第一个病人。
是一个摔断了腿的大叔。我用养母教我的正骨手法,替他接好了骨头,
又开了些活血化瘀的草药。大叔千恩万谢地走了。第二天,他就给我介绍来了好几个病人。
我的医馆,渐渐有了些名气。来看病的人,大多是些穷苦的平民百姓。
他们付不起昂贵的诊金,我便只收些药材的成本钱。有时候遇到实在困难的,
我甚至分文不取。大家都很感激我,亲切地称我为“知鸢小神医”。巷子里的邻居们,
也渐渐和我熟络起来。东家的张大娘会给我送来自己做的点心,
西家的李大哥会帮我修葺漏雨的屋顶。我很久没有体会过这种朴素的善意了。在沈家,
在侯府,我活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我以为只要我做得足够好,
就能得到他们的认可和喜爱。现在我才知道,不爱你的人,你做什么都是错的。一天下午,
医馆里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他穿着一身青色的布衣,气质却温润如玉,
与这破旧的巷子格格不入。“姑娘,在下萧临安,路过此地,闻到一股极纯正的药香,
便冒昧前来,不知可否讨教一二?”他对我拱手作揖,态度谦和有礼。我请他坐下,
给他倒了杯茶。我们从药材的辨识,聊到疑难杂症的辩证。我惊讶地发现,
他在医道上的见解,竟比我还要精深。“萧公子师从何人?”我好奇地问。他笑了笑,
说:“家学渊源罢了。倒是姑娘你,年纪轻轻,这一身医术,着实不凡。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是我养母教的。”我们相谈甚欢,不知不觉,天色已晚。
萧临安起身告辞,临走前,他看着我,认真地说:“沈姑娘,你心有郁结,于身体有碍。
医者不自医,还需宽心才是。”我愣住了。他竟一眼就看穿了我深藏在心底的伤。
8自那日之后,萧临安便成了我医馆的常客。他时常会带来一些罕见的药材与我探讨,
或是拿着一本古旧的医书,与我争论某个方剂的用法。与他相处,是轻松而愉悦的。
他从不问我的过去,也从不探究我的身份。在他眼里,我只是一个同样热爱医术的同道中人。
我的生活,因为他的出现,多了一抹亮色。我的心情,也渐渐开朗起来。脸上的笑容,
也多了起来。而此时的顾行之,却陷入了更深的痛苦之中。他终于找到了我。
不是他派出去的那些眼线,而是他自己。那是一个黄昏,他处理完公务,
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鬼使神差地,就走进了城南那条偏僻的巷子。然后,他就看到了我。
我正坐在医馆的门槛上,和一个小女孩说话。夕阳的余晖洒在我身上,
为我镀上了一层温柔的光晕。我的脸上带着他许久未见的、发自内心的笑容。那一刻,
顾行之的呼吸都停滞了。他想象过无数次找到我时的场景。我想象过我衣衫褴褛,食不果腹,
在街角乞讨。我想象过我走投无路,为了生计,自甘堕落。他甚至想象过,
我或许已经不在人世了。他唯独没有想到,我会过得这么好。没有他,
我竟然……过得这么好。这个认知,比任何噩梦都让他感到痛苦和愤怒。
他以为我是依附他而生的藤蔓,离了他,便无法存活。可现实却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原来,
我不是藤蔓。我是一棵树,即便被移植到贫瘠的土地,也能靠自己的力量,扎根生长,
活出自己的姿态。他站在巷口,远远地看着我,心里五味杂陈。他看到我送走了那个小女孩,
然后一个温文尔雅的青衣男子,提着一篮子新鲜的水果,走进了我的医馆。我笑着迎了上去,
自然地接过他手里的篮子。两人并肩走进院子,身影消失在门后。那一幕,
刺痛了顾行之的眼。那个男人是谁?他们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我看到他,会笑得那么开心?
无数个问题,在顾行之的脑海里盘旋,几乎要将他吞噬。他攥紧了拳头,
指甲深深地嵌进肉里,却浑然不觉。9顾行之没有立刻冲进去。他像一个阴暗的偷窥者,
在巷口站了很久,直到天色完全黑透,那个叫萧临安的男人才从我的院子里出来。
萧临安走后,顾行之才迈着沉重的步子,朝我的医馆走去。他站在门口,
看着那块简陋的“知鸢医馆”的牌子,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怒火。知鸢。他有多久,
没有好好叫过我的名字了?他推开虚掩的院门,走了进去。我正在院子里收拾晾晒的药材。
听到脚步声,我以为是萧临安去而复返,便头也不抬地说道:“怎么又回来了?
落下什么东西了?”回应我的,是一片沉默。我疑惑地抬起头,然后,我看到了他。顾行之。
他就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穿着一身华贵的锦袍,与这破败的院子格格不入。
他定定地看着我,眼神复杂得让我看不懂。有愤怒,有不甘,
还有一丝……我从未见过的脆弱。我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侯爷。”我站起身,
疏离而客气地行了一礼,“不知侯爷大驾光临,有何贵干?”我的冷漠,显然激怒了他。
他往前一步,逼近我,声音里带着一丝咬牙切齿的味道:“沈知鸢,你倒是过得逍遥自在。
忘了自己是个被休弃的弃妇了吗?”我抬起眼,平静地看着他:“侯爷此言差矣。
我记得很清楚,是你亲手写的休书,将我赶出侯府。如今我自食其力,安分度日,
不知又碍着侯爷什么事了?”“你!”顾行之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他大概是没想到,
一向对他温顺恭敬的我,竟敢用这样带刺的语气跟他说话。“那个男人是谁?”他突然问道,
声音里带着浓浓的质问。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问的是萧临安。我忍不住笑了。
“侯爷是以什么身份在问我呢?前夫吗?”我看着他,眼神冰冷,“顾行之,
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我的事,轮不到你来管。”“没有关系?
”顾行之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
力气大得几乎要将我的骨头捏碎,“沈知鸢,你别忘了,你这条命都是我的!我让你生,
你才能生!我让你死,你就得死!”他的话,让我感到一阵恶心。我用力地挣扎,
想要甩开他的手:“放开我!顾行之,你疯了!”“我是疯了!”他低吼着,
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我就是被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逼疯的!
你是不是早就跟那个男人勾搭上了?所以被我赶出侯府,你才一点都不伤心,是不是?
”他的质问,荒谬又可笑。我看着他,忽然觉得很悲哀。为我自己,也为他。“顾行之,
”我放弃了挣扎,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噩梦,所以才跑来我这里发疯?
”我的话,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他心底最恐惧的闸门。他的脸色“唰”地一下变得惨白,
抓着我的手,也不由自主地松开了。“你……你怎么知道?”他声音颤抖地问。
10我怎么知道?我当然不知道。我只是随口一猜。看他最近憔悴的样子,
再加上他反常的举动,除了被噩梦折磨,我想不出别的理由。没想到,竟然被我猜中了。
我看着他失魂落魄的样子,心里没有一丝快意,只有无尽的疲惫。“侯爷,您病了。
”我淡淡地说,“心病还需心药医。我的医馆小,治不了您的病,您还是请回吧。
”我下了逐客令。顾行之却像是没有听到一样,他失神地看着我,
喃喃自语:“我梦见你……梦见你为我挡箭,为我咳血……那些梦,太真实了……”他的话,
让我心里猛地一沉。为他挡箭?为他咳血?这些……不都是上一世发生过的事情吗?
我上一世,痴恋顾行之,为了他,我确实做过这些事。我为他挡下刺客的毒箭,
最后毒发身亡。我为了替他打理家业,积劳成疾,最终在他怀里咳血而亡。我以为,
重生一世,这些惨痛的过往,只有我自己记得。为什么他也会梦到?
难道……一个荒唐的念头,在我脑海里闪过。我看着他,试探着问:“你还梦到了什么?
”顾行之抬起头,眼神痛苦而迷茫:“我还梦到,小时候,在沈家祠堂,
是你……给我送了冬衣和包子。”我的心,彻底沉了下去。如果说挡箭咳血,
还可以解释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么祠堂送衣这件事,除了当事人的我们,
不可能有第三个人知道。他梦到的,不是梦。而是真真切切,发生在我上一世的记忆。
这个认知,让我不寒而栗。老天爷到底在开什么玩笑?它让我重生,
是为了让我远离这个男人,过自己的生活。可为什么,又要将那些属于上一世的纠葛,
用这种方式,重新呈现在他面前?这是在帮我?还是在害我?11“沈知鸢,
”顾行之向我走近一步,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恳求,“你告诉我,
那些……到底是不是真的?”我该怎么回答?告诉他,是真的。
那些都是我上一世为你做过的傻事。你看到的,是你欠我的,一条命,满腔情。然后呢?
让他因为愧疚,重新将我纳入他的羽翼之下?让我回到那个金丝笼里,
继续做他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附属品?不。我不要。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我不想再回去了。
“侯爷,你真的病了。”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梦境虚幻,当不得真。
你之所以会做这些梦,大约是……对我的休弃,心有不安吧。”我故意将他的痛苦,
归结于廉价的愧疚。果然,顾行之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心有不安?”他冷笑一声,
“我有什么好不安的?你一个冒牌货,占了云柔十几年的富贵生活,
我只是让你回到你本该在的位置,何错之有?”“对,侯爷没有错。”我顺着他的话说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