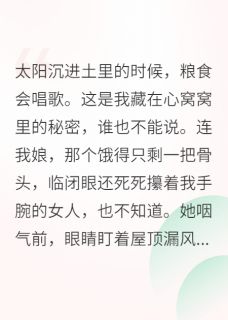
太阳沉进土里的时候,粮食会唱歌。这是我藏在心窝窝里的秘密,谁也不能说。连我娘,
那个饿得只剩一把骨头,临闭眼还死死攥着我手腕的女人,也不知道。她咽气前,
眼睛盯着屋顶漏风的茅草棚,哑着嗓子一遍遍说:“晚啊…活下去…别像娘…”我叫莫晚。
莫问前程的莫,晚来天欲雪的晚。这名字是我那据说读过几天私塾的爹起的,
可惜他走得比娘还早,名字里的那点墨水味儿,早被苞谷碴子和野菜汤冲得没影了。
1960年的冬天,刀子风刮得人脸生疼。生产队食堂的大锅里,清汤寡水,
能照见人影的玉米面糊糊,一人就一勺底。肚子里像揣了只永远喂不饱的耗子,
咕噜噜叫得人心慌。我缩在冰冷的土炕角落,破棉被硬得像铁板。手指头冻得发木,
悄悄伸进贴身的破棉袄里层,那里缝着一个小口袋。指尖触到一粒饱满滚圆的麦粒。冰凉,
坚硬。没人看见。意识沉下去,像掉进一口深井。再睁眼,眼前豁然开朗。
一片望不到边的金黄麦田。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腰,风一吹,麦浪翻滚,沙沙作响。
空气里弥漫着阳光烘烤麦粒的干燥香气,混着泥土的腥甜。田埂边,一小洼清泉,
水清得能看见底下圆润的鹅卵石。泉眼旁边,孤零零立着个半人高的土坯粮仓,仓门紧闭。
这就是我的地方。我管它叫“地头”。很小,只有不到一亩麦子,一小洼泉眼,
一个打不开的粮仓。但在这能把人活活饿死的年景,这就是我的命根子。每次进来,
心都跳得像揣了只兔子,又慌又怕,又忍不住地欢喜。我不敢多待,
生怕外面有人发现我不见了。赶紧蹲在泉眼边,撩起冰凉甘甜的水,狠狠灌了几大口。
那水一下肚,像一股暖流,瞬间驱散了四肢百骸的寒气,连咕咕叫的肚子都安静了片刻。
然后,我扑向离我最近的一株麦子。手指颤抖着,掐下几穗最饱满的。不敢多掐,
怕留下太明显的痕迹。麦芒扎手,有点疼,可这疼里带着让人心安的实感。意识再一动,
人已经回到了冰冷的土炕上。手里沉甸甸的,是那几穗带着新鲜麦芒的麦穗。
心还在咚咚狂跳。借着破窗户纸透进来的惨淡月光,我小心翼翼地把麦穗上的麦粒搓下来。
一把金黄的小颗粒,躺在手心,散发着生命的气息。我把大部分藏进炕洞里一个破瓦罐里,
只留下十几粒,塞进嘴里,慢慢嚼。麦粒粗糙,带着生涩的麦香,在齿间磨开,混着唾液,
变成糊糊,艰难地咽下去。一股微弱却真实的热量,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
靠着这点偷来的生机,我熬过了那个冬天。人虽然瘦得像根芦苇杆,风一吹就晃,
但眼睛里的光没灭。开春,队里组织挖野菜。我落在最后,趁没人注意,
手指飞快地在刚翻开的湿土里一点,几粒麦子悄无声息地落了进去,又被浮土盖住。
没过几天,那几处被我点过的地方,嫩绿的麦苗就悄悄钻了出来,
混在一片灰扑扑的野菜和荒草里,格外显眼。我每天下工都绕过去看两眼,
看着它们一点点窜高,绿得喜人。这天收工,我照例绕过去。远远地,
就看见那几簇格外精神的麦苗旁边,蹲着个人。心猛地一沉,手脚瞬间冰凉。
那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劳动布工装,袖口挽到胳膊肘,露出小臂。他背对着我,
正低头仔细看着那几株麦苗,手指轻轻拂过叶片。夕阳给他周身镀了层毛茸茸的金边。
我认识他。新来的研究员,姓顾,叫顾明远。队里人背后都叫他“眼镜”。
他是上头派下来的,说是研究什么土壤改良、提高产量的。人很安静,不太跟人说话,
整天拿着本子和笔在地头转悠,鼻梁上架着副掉了漆的黑框眼镜。他怎么会注意到这里?
我站在原地,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喉咙发干。脑子里嗡嗡响,只有一个念头:完了。
顾明远似乎察觉到了身后的动静,站起身,转了过来。镜片后的眼睛很平静,没什么波澜。
他个子高,我得微微仰头看他。“莫晚同志?”他准确无误地叫出了我的名字,声音不高,
带着点书卷气的清朗。我紧张地攥紧了衣角,指甲掐进掌心,勉强应了一声:“…嗯。
”他指了指脚下那几株明显长势过旺的麦苗:“这几株麦子,长得有点特别。
”我的血好像都涌到了脸上,又唰地一下退得干干净净。嘴唇动了动,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只能僵硬地点点头。他蹲下身,从随身挎着的帆布包里掏出个放大镜,
又仔细看了看麦苗的根部,还捻起一点土在指尖搓了搓。动作很专注,
像在研究什么稀世珍宝。时间一点点过去,每一秒都像在油锅里煎。终于,他收起放大镜,
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镜片后的目光落在我脸上,很平静,没什么探究,也没什么怀疑。
“土质好像有点不同。”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生命力很顽强。
”我悬到嗓子眼的心,咚地一声落回一半。他…他没发现什么?只是觉得土好?“是…是呢。
”**巴巴地挤出两个字,声音发飘,“这块地…向阳。”他没再追问,只是点了点头,
从帆布包里拿出个牛皮纸封面的本子,翻开,用铅笔在上面快速地记着什么。写完,
他合上本子,对我很客气地说:“打扰了,莫晚同志。你回吧。”我如蒙大赦,
含糊地应了一声,几乎是同手同脚地转身就走。走出老远,还能感觉到背后那道平静的目光,
像根细针,扎得我脊背发凉。他到底看到了什么?他记了什么?那平静的眼神底下,
藏着什么?这个疑问像块大石头,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
我开始刻意避开顾明远可能出现的地方,下工也绕开那片“自留地”。
每次远远看见他那身蓝工装的身影在地头晃动,我的心就揪成一团。
可“地头”里的麦子熟了。金黄一片,沉甸甸地压着枝头,再不去收,麦粒就要落进土里了。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队里活计重,白天根本没机会。晚上?晚上村里静得吓人,
一点动静都能传出老远。而且,顾明远就住在村尾废弃的队部小院里,离我家不算太远。
等了好几天,终于等到一个阴沉的夜晚。乌云遮了月亮,风也大,吹得树叶哗哗响,
正好能盖住点声音。我悄无声息地溜出家门,像只夜行的猫,贴着墙根的阴影,
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到村外那片荒地。确认四周无人,只有风声呜咽。我深吸一口气,
意识沉入“地头”。没有月光,但“地头”里却像蒙着一层柔和的微光,能看清。
麦浪在无形的风中起伏,沙沙声更响了。我不敢耽搁,冲到麦田边,
徒手抓住麦秆就往下撸麦穗。麦芒扎进手心,又刺又痒,也顾不上疼。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快点!一把,两把…刚撸了小半捧,塞进怀里破棉袄的内袋。突然,
一种强烈的、被窥视的感觉,像冰冷的蛇一样爬上我的后背!汗毛瞬间炸起!我猛地回头。
“地头”边缘,那层无形的屏障外,本该是浓稠的黑暗。可此刻,黑暗里,
静静地站着一个模糊的人影!看不清脸,但那身形,那轮廓…蓝工装!是顾明远!
他怎么会在这里?!他看到了什么?!巨大的恐惧瞬间攫住了我,
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停止了跳动。血液都冲到了头顶,
又在下一秒冻成了冰碴子。我僵在原地,连呼吸都忘了。他看到我凭空消失了吗?
他看到这片麦田了吗?他是不是一直在监视我?那人影一动不动,隔着那层无形的屏障,
沉默地“注视”着这边。时间仿佛凝固了。完了。彻底完了。我的秘密,保不住了。
下一个冬天,我大概真的要去陪我爹娘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绝望的嗡鸣。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只是一瞬,也许有一个世纪那么长。那个模糊的人影,缓缓地,
向后退了一步,融入了更深的黑暗里,消失了。他走了?他没进来?
巨大的恐慌之后是虚脱般的茫然。我瘫软在地上,怀里那点刚撸下来的麦穗硌得胸口生疼。
冷汗浸透了后背的破棉袄,风一吹,冷得我直哆嗦。他是谁?他到底看到了多少?
他为什么走了?一连串的问题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我再也顾不上收麦子,
几乎是连滚爬爬地离开了“地头”,意识回归冰冷现实的瞬间,身体还在不受控制地发抖。
怀里的麦穗像烫手的火炭。那一晚,我睁着眼睛躺在冰冷的炕上,听着外面呼啸的风声,
直到天亮。第二天上工,我故意磨蹭到最后才去**点。眼睛控制不住地往人群里瞟。
心提到了嗓子眼。顾明远果然在。他站在人群外围,依旧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蓝工装,
手里拿着他的本子和笔,正跟生产队长低声说着什么。神情专注,眉头微蹙,
鼻梁上的眼镜在晨光里反着光。他似乎完全没注意到我。或者说,他的目光扫过我时,
和扫过其他人一样,没有任何停留,平静得像一潭深水。难道…昨晚只是我的幻觉?
是我太紧张看花了眼?可那种被冰冷注视的感觉,太过真实,
真实得让我骨头缝里都冒着寒气。接下来的日子,成了煎熬。我像惊弓之鸟,
一点风吹草动都能吓出一身冷汗。顾明远的存在本身,就成了一种无声的威胁。
他在地头测量,在本子上写写画画,和社员们交谈(虽然很少),
甚至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看天,都让我坐立不安。他越是平静,
我越觉得那平静底下藏着深不可测的漩涡。我停止了从“地头”里拿任何东西出来。
连喝里面的泉水都不敢了。怀里的那点麦粒,省着吃,很快就见了底。
肚子里的饿虫又开始疯狂叫嚣,四肢又开始发软。日子又回到了那个冬天之前的灰暗。饿,
无尽的饿,像钝刀子割肉。这天傍晚,收工回来,饿得前胸贴后背。
刚推开吱呀作响的破院门,脚步就顿住了。院门口那块平时光秃秃的石墩子上,
放着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搪瓷碗。碗里,是半碗黄澄澄、颗粒分明的玉米碴子。
不是食堂里那种稀得能照见鬼影的糊糊,是实实在在、能立得住筷子的干饭!
我的眼睛死死盯着那碗饭,喉咙不受控制地滚动了一下。香味,实实在在的粮食香味,
钻进鼻孔,勾得胃里一阵痉挛。谁放的?我猛地抬头四顾。暮色四合,
家家户户烟囱里冒着稀薄的炊烟,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隔壁张婶家的狗,
懒洋洋地趴在门口。心咚咚直跳。一个名字,不受控制地蹦进脑海。顾明远。是他吗?
除了他,谁会给我送这么金贵的粮食?队里的人自己都饿得眼冒绿光。他什么意思?试探?
封口?还是…怜悯?饥饿和恐惧在脑子里激烈地打架。那碗饭的诱惑力太大了,
像沙漠里的一汪清泉。可理智告诉我,不能碰,这可能是裹着蜜糖的毒药。我盯着那碗饭,
足足站了有十分钟。最终,饥饿的魔鬼占了上风。我飞快地端起碗,闪身进屋,
紧紧关上了门。管不了那么多了!先填饱肚子再说!玉米碴子有点凉了,但嚼在嘴里,
是实实在在的粮食的甜香和满足感。我狼吞虎咽,几口就把半碗饭扒拉得干干净净,
连碗底都舔了一遍。胃里有了东西,暖烘烘的,身体也恢复了些力气。
可满足感只持续了一小会儿,更大的恐慌又攫住了我。吃了他的东西,
是不是就等于承认了什么?他会不会以此为把柄?接下来的几天,我活得像个影子,
尽量缩在人群里,避开任何可能和顾明远单独碰面的机会。他没再来找我,
也没再往我院门口放东西。就在我以为这事可能就这么过去了的时候,麻烦自己找上门了。
那天下午,我在玉米地里薅草。太阳毒辣,晒得人头晕眼花。地头那边,
顾明远带着两个戴红袖箍的人(后来知道是公社下来检查工作的),正在测量着什么,
比比划划。突然,村里的快嘴李婆子一阵风似的冲了过来,手指头差点戳到我鼻子上,
嗓门尖得刺耳:“莫晚!你个小蹄子!说!你给顾研究员灌了什么迷魂汤?
让他把那么金贵的玉米碴子偷偷塞给你?啊?大家都勒紧裤腰带,凭啥就你吃干的?!
”她的声音又尖又利,像破锣,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地里干活的人,地头测量的人,
全都齐刷刷地看了过来。那两个戴红袖箍的人,眉头立刻皱了起来,眼神锐利地扫向我。
嗡的一声,我的脑袋像是被重锤砸了一下。血液瞬间冲上头顶,又刷地退下去,手脚冰凉。
李婆子怎么知道的?!那晚明明没人看见!我下意识地看向顾明远。他站在地头,
脸色似乎白了一下,镜片后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紧紧盯着快嘴李婆子。“你…你胡说!
”我气得浑身发抖,声音发颤,“谁…谁拿他东西了!”“还狡辩!
”李婆子唾沫星子喷了我一脸,“我亲眼看见的!那天擦黑,顾研究员揣着个碗,
鬼鬼祟祟放你家门口石墩子上!不是给你的,难道是喂狗的?!
”她的话像一把淬了毒的刀子,狠狠扎过来。所有人的目光都变了,怀疑的,鄙夷的,
看热闹的。“李婶子,话不能乱说。”顾明远的声音响了起来,很沉,
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冷意。他大步走了过来,挡在了我和李婆子之间,
高大的身影遮住了毒辣的日头。“那玉米碴子,是我自己的口粮。”他面对着那两个红袖箍,
也面对着所有看过来的人,声音清晰平稳,“莫晚同志身体太虚弱,
前些天晕倒在我测量点附近,是我扶了一把。看她实在撑不住,才匀了点自己的口粮给她。
就这么简单。跟其他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有关系。”他顿了顿,
目光扫过李婆子那张因激动而扭曲的脸,语气更冷了几分:“倒是李婶子,跟踪窥探他人,
还无端造谣生事,这种行为,恐怕不太好吧?”李婆子被他看得一缩脖子,
但仗着有红袖箍在场,嘴硬道:“我…我亲眼看见的!她家成分本来就不好!
谁知道是不是她勾引你,想腐蚀革命同志!”“够了!”一个年纪稍长的红袖箍沉着脸喝止,
“李秀英同志!没有证据的事情不要乱扣帽子!顾研究员是上面派下来的专家,
他的作风问题,不是你一张嘴就能污蔑的!”他又转向顾明远,语气缓和了些,“顾研究员,
关心帮助贫下中农是好的,但也要注意方式方法,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顾明远点了点头:“是我考虑不周,下次注意。”红袖箍又严厉地训斥了李婆子几句,
警告她不许再无事生非,才带着人继续去别处检查了。一场风波,
看似被顾明远三言两语压了下去。人群也渐渐散了,只是看我的眼神,依旧复杂。
李婆子狠狠剜了我一眼,啐了一口,扭着腰走了。地里只剩下我和顾明远。烈日当头,
空气却像凝固了一样。我低着头,看着自己破草鞋里露出的脚趾,指甲缝里全是泥。
刚才的恐惧还没退去,又添了难堪和屈辱。浑身都在微微发抖。“没事了。
”他的声音在头顶响起,比刚才温和了许多。我没吭声,也不敢抬头看他。
“以后…”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自己小心点。东西…别再让人看见了。
”我猛地抬起头,撞进他镜片后的眼睛里。那里面没有鄙夷,没有探究,只有一种…了然?
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忧?他果然知道!他什么都知道!巨大的恐慌再次攫住了我。
他知道我的秘密!他会不会去告发我?他似乎看出了我眼中的惊惧,轻轻叹了口气,
声音轻得像耳语:“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别怕。”别怕?我怎么可能不怕?我的命门,
就攥在这个才认识没多久的男人手里!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没再多说,转身离开了。
我站在原地,烈日晒得皮肤发烫,心却像掉进了冰窟窿。他最后那句“别怕”,像根羽毛,
轻飘飘的,却在我混乱的心湖里,投下了一圈微澜。他…到底想干什么?
那碗玉米碴子的风波,表面上平息了。但村里关于我的闲话,像夏天粪坑里的苍蝇,
嗡嗡嗡地,赶都赶不走。说我“勾引”研究员的有,说我“偷东西”的有,
甚至还有人说顾明远是我爹以前的学生,特意来照顾我的(纯属瞎掰)。
我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走到哪儿都觉得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日子更难熬了。
我更加小心翼翼,像只受惊的兔子,窝在自己的小破屋里,非必要不出门。
“地头”里的麦子,我终究没敢再去收。眼睁睁看着它们熟透,麦粒一颗颗落进土里,
心疼得滴血。那洼清泉,也只能在实在渴得受不了,又确定绝对安全时,才敢进去喝上几口。
顾明远依旧在村里活动。他似乎在搞什么试验田,
经常带着几个年轻的社员在村东头那块贫瘠的坡地上忙活。偶尔,
我会在收工路上远远看见他。他有时会朝我这个方向看过来,目光平静。每当这时,
我就赶紧低下头,加快脚步离开。他再也没给我送过任何东西。直到深秋的一天傍晚。
天阴沉沉的,下着小雨。我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地里回来,浑身泥水。推开吱呀作响的院门,
又愣住了。门槛里面,放着一个油纸包。不大,方方正正的。心猛地一跳。又是他?
我飞快地捡起油纸包,闪身进屋。关上门,背靠着门板,心还在咚咚跳。外面雨声淅沥,
屋里光线昏暗。颤抖着手打开油纸包。里面不是粮食。是几本书。旧的,
封面都磨得起了毛边。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一本《常见中草药图谱》,
还有一本薄薄的《土壤与肥料简易常识》。书?他给我书干什么?我茫然地翻着。
手册和图谱里画着各种草药、人体穴位、治疗方法。土壤那本,讲的是怎么堆肥,
怎么辨别土质。在最底下,压着一张折叠的小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是用铅笔写的,
字迹清隽有力:“技多不压身。天冷,保重。顾。”没有落款。我捏着那张纸条,
翻来覆去地看,好像能从里面看出花来。冰冷的雨水顺着湿透的头发滴到纸条上,
晕开了一小团墨迹。技多不压身…他是在给我指路?让我学点东西,以后能靠这个活下去?
保重…是关心吗?心里乱糟糟的。恐惧似乎淡了一点,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像冬夜里突然看到一点微弱的烛光,
明知道它可能随时熄灭,却又忍不住想靠近那点温暖。他真的…没有恶意?那个冬天,
过得格外漫长。有了顾明远送的书,日子好像有了一点微弱的盼头。白天上工累得半死,
晚上就着豆大的油灯光,我囫囵吞枣地翻看那几本书。很多字不认识,就瞎蒙,或者看图画。
草药图谱记得最牢,因为我认得山里好些野草野花。开春后,队里组织妇女去山里采野菜。
我挎着篮子,眼睛却像探照灯一样,在草丛石缝里搜寻。“哎,莫晚,你挖这苦蒿蒿干啥?
又苦又不能吃!”同村的春妮儿看见我篮子里的几株开着小白花的草,好奇地问。“哦,
这个啊,”我努力回想图谱上的说明,“书上说…叫夏枯草?晒干了…好像能泡水喝?
治…治嗓子疼?”我说得磕磕巴巴,不太确定。“真的假的?”春妮儿半信半疑,
“你从哪儿看的书?”“就…捡的。”我含糊过去,心里有点虚。没想到过了几天,
春妮儿风风火火地跑来找我:“莫晚!莫晚!你上次说的那个夏枯草真神了!
我爹咳嗽得整宿睡不着,我按你说的,晒干了给他泡水喝,喝了几天,真不怎么咳了!
”她嗓门大,引得周围几个妇女都围了过来。“真的假的?莫晚你还懂这个?
”“那书还在不?给我也看看呗?”“我娘这两天也说心口闷,有啥草能治不?
”我一下子成了焦点,有点手足无措。赶紧拿出那本翻得卷了边的《常见中草药图谱》,
指着上面的图给她们看。她们大多不识字,但看图认草没问题。“这个是车前草,
煮水能利尿…”“这是蒲公英,叶子能当菜吃,根晒干了泡水能清火…”“这个是艾草,
端午挂门上的,熏蚊子挺好,捣烂了敷关节能去寒气…”我把自己记得的那点皮毛,
磕磕巴巴地倒了出来。她们听得认真,还七嘴八舌地补充着从老一辈那里听来的土方子。
慢慢地,村里人看我的眼神有点不一样了。不再是单纯的鄙夷或疏远,多了点好奇,
甚至是一点…信服?尤其是当我用蒲公英捣烂的汁水,
帮隔壁张婶家被马蜂蜇了的小孙子消肿止痛之后。“莫晚这丫头,别看闷不吭声,
肚子里有点墨水。”“那草药书没白看,挺灵光。”“以后头疼脑热的,不用跑公社了,
找她问问。”这些议论传到耳朵里,我心里有点小小的、隐秘的欢喜。
这是靠我自己(虽然起点是顾明远的书)挣来的一点认可,不是靠那个不能见光的“地头”。
顾明远也知道了。有一次在村口碰见,他推着辆自行车(大概是公社配给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