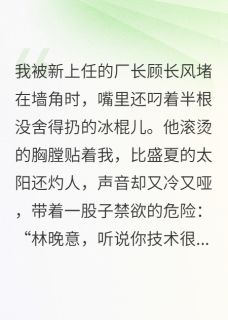
我被新上任的厂长顾长风堵在墙角时,嘴里还叼着半根没舍得扔的冰棍儿。
他滚烫的胸膛贴着我,比盛夏的太阳还灼人,声音却又冷又哑,
带着一股子禁欲的危险:“林晚意,听说你技术很好?”我心里一咯噔,坏了,
流言蜚语已经传得这么离谱了吗?下一秒,冰冷的铁铐“咔哒”一声锁上了我的手腕。
“跟我走一趟,”他面无表情,眼神却像要把我拆骨入腹,“厂里那台德国进口的宝贝机器,
也想请你‘治一治’。”01“林晚意,你还有什么话好说!”车间主任唾沫横飞,
指着我脚边散落的几个精密零件,痛心疾首的模样,好像我刨了他家祖坟。
我懒懒地靠在墙上,把最后一口冰棍儿咽下去,甜腻的滋味在舌尖化开,
冲淡了空气中机油和铁锈的混合气味。开口的瞬间,我看见了人群后面那个男人,顾长风。
白衬衫,黑西裤,身姿笔挺得像一棵白杨。他是空降来的新厂长,
据说是个上过战场的狠角色,来咱们这个半死不活的红星机械厂“技术扶贫”。上任三天,
就贴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整治摸鱼的、混日子的,搞得厂里鸡飞狗跳。而我,林晚意,
就是他要整治的典型。上班踩点,下班第一个冲,技术科那帮大学生看见我就头疼,
因为我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图纸上的毛病。他们说我没大没小,
我说他们是“理论的巨人,实践的矮子”。此刻,我成了众矢之的。
厂里最金贵、刚从德国进口的冲压机床坏了,耽误了给首都汽车厂的大订单,而我,
是最后一个离开车间的人,监控死角,人赃并获。“我能有什么话好说?王主任,
您这‘屈打成招’的戏码,是不是太老套了?”我瞥了一眼他因为激动而涨红的脸,
轻笑一声,“再说,就这几个破铜烂铁,值得我林晚意动手?
”我的话像一滴水溅进了热油锅。“你个小丫头片子!不知好歹!”“就是,
仗着自己有点三脚猫的功夫,目中无人!”“顾厂长,您可得为我们做主啊!这种害群之马,
必须严惩!”所有的矛头都指向我,而我,只看着顾长风。他穿过人群,皮鞋踩在水泥地上,
发出沉稳的闷响,一步一步,都像是踩在我的心上。他很高,站在我面前,
投下的阴影将我完全笼罩。然后,就发生了导语里那一幕。他那句“听说你技术很好”,
像一句淬了冰的调情,让周围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品出了其中的不对味,
眼神在我俩之间来回扫荡,暧昧又恶毒。我被他攥着手腕,一路拖进了厂长办公室。
门“砰”的一声关上,隔绝了外面所有的声音。他把我推到墙边,没有松开手铐,
另一只手撑在我耳侧的墙上,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包围圈。“说吧,怎么回事。
”他的声音里没有了刚才的冰冷,反而带着一丝探究。“报告厂长,我说我是冤枉的,
你信吗?”我抬起头,直视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很深,像藏着星辰的大海,
也像能吞噬一切的漩涡。他没说话,只是用那双深邃的眼睛盯着我,仿佛要看穿我的灵魂。
办公室里只有老旧风扇“吱呀”的转动声,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突然,他伸出手,
捏住了我的下巴。指腹上带着薄茧,摩挲着我的皮肤,带来一阵战栗。“林晚意,
你最好别耍花样。”他凑近我,呼吸喷在我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烟草味,“我的地盘,
我定规矩。给你一个晚上,找出证据证明你的清白。否则,明天全厂大会,
你就等着被送去农场改造吧。”他的话是威胁,可他的动作却像挑逗。
我甚至能从他漆黑的瞳孔里,看到自己惊慌失措的倒影。这个男人,比我想象的,
还要危险一万倍。02夜深了,我被关在工厂的档案室。这里比禁闭室强点,
至少有张桌子有把椅子,还能闻到旧纸张和墨水的味道。顾长风把我铐在这里,
美其名曰“冷静思考”,钥匙就在他自己身上。“想让我给你开后门,也得看你值不值得。
”他临走前,丢下这么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我坐在椅子上,晃荡着手腕上的铁铐,
心里把顾长风骂了八百遍。这个男人,做事滴水不漏。把我关起来,既能堵住悠悠众口,
又能给我这个“嫌疑人”施压。他就像个最高明的猎人,布下天罗地网,
就等我这个猎物自己露出破绽。但我林晚意是谁?我是在胡同里打架长大的野丫头,
最擅长的就是在绝境里给自己找条活路。我闭上眼,仔细回忆着下午在车间的情景。
那台德国机床,型号是DMG-80,我之前偷偷研究过它的说明书。
它的保险栓设计得非常精妙,除非用特定的工具,否则很难在不破坏零件的情况下取下来。
而我脚边那些零件,断口光滑,明显是专业工具拆卸的。这说明,对方是个行家。而且,
为什么要陷害我?我一个普通技术工,无权无势,挡了谁的道?除非……对方的目标不是我,
而是顾长风。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烧到了大动脉上,这批订单要是黄了,
他这个厂长也当到头了。想到这里,我心里有了个大概的轮廓。“吱呀”一声,门被推开了。
我警惕地抬起头,看到的却是顾长风那张没什么表情的脸。他手里提着一个铝制饭盒,
还有一个军用水壶。“先吃饭。”他把饭盒放在桌上,打开,是白米饭和红烧肉,
在这个年代,这可是招待贵客的伙食。“哟,断头饭还挺丰盛?”我没动筷子,
抱着胳膊看他,“顾厂长,这是怕我饿着肚子上路,到了阎王爷那儿告你的状?
”他没理我的阴阳怪气,自顾自地拧开水壶,倒了一杯水推到我面前。
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很专注,手指修长干净,骨节分明,不像个厂长,
倒像个摆弄精密仪器的工程师。“我查了你进厂的档案,”他突然开口,“初中毕业,
但三次获得市级青少年科技创新奖。进厂三年,提了七次技术改良建议,六次被驳回,
一次被你师傅王大海冒名顶替领了奖金。”我的心猛地一沉。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
连我自己都快忘了,他一个晚上就查得一清二楚。“所以呢?顾厂长是想说我怀恨在心,
报复工厂?”我冷笑。“不,”他摇了摇头,拿起桌上的一份文件递给我,“我是想说,
以你的脑子,不会用这么蠢的方法报复。”我低头一看,是一份机床的维修记录。
最近一个月,只有一个人有权限、也有技术接触到核心部件——副厂长,李卫东。
他是厂里的老资格,也是之前最有希望接任厂长的人。顾长风这是在……点我?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他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明天早上八点,全厂大会。
是龙是虫,看你自己的造化。”他转身要走,我鬼使神差地叫住了他:“顾长风!
”他脚步一顿,没有回头。“你为什么要帮我?”空气安静了几秒,我几乎以为他不会回答。
“我不是帮你,”他的声音从门缝里传来,有些飘忽,“我只是讨厌我的地盘上,
有藏头露尾的老鼠。”门再次关上,这一次,没有上锁。我看着桌上的红烧肉,突然觉得,
这个男人的侧影,和他敲桌子时总会习惯性地用食指和中指轻叩两下的动作,
似乎成了我灰暗世界里,一道独特又危险的风景。03天还没亮,我就着档案室昏暗的灯光,
把那份维修记录翻来覆去看了个遍。李卫东的名字像个烙印,频繁出现在上面。
他确实是最大的嫌疑人,可这同样说明不了什么,他是副厂长,主管生产,
关心设备再正常不过。顾长风给的不是证据,是一个方向。真正的证据,还得我自己去找。
我掂了掂手里的铁铐,另一头还锁在暖气管上。这玩意儿对我来说,跟玩具没什么区别。
我从发卡里抽出一根细钢丝,对着锁芯捅咕了几下,“咔”的一声轻响,手铐应声而开。
活动了一下发麻的手腕,我像只狸猫一样,悄无声息地溜出了档案室。凌晨四点的工厂,
万籁俱寂,只有远处锅炉房还冒着白烟。我得去两个地方,第一,
案发现场——冲压车间;第二,李卫东的办公室。车间已经被封条封了,但拦不住我。
我从后面一扇破了玻璃的窗户翻了进去,空气里还残留着那股紧张的气息。
我径直走向那台瘫痪的德国机床,它像一头沉默的钢铁巨兽,匍匐在黑暗中。我没有开灯,
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袖珍手电筒,这是我平时研究机器用的。
我仔细检查着机床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那个被拆下来的保险栓接口。果然,
在接口内壁一个极其隐蔽的凹槽里,我发现了一丝刮痕。非常新,是在拆卸过程中,
因为工具不匹配或者用力过猛留下的。DMG-80的原装工具是特种合金,
绝不会留下这种痕迹。这说明,对方用的是替代工具。我脑中灵光一闪。红星厂里,
能接触到这种特种设备的,除了几个老技术员,就只有工具库了。
而能从工具库里神不知鬼不觉借出替代工具,并销毁记录的,只有一个人能办到。李卫东!
我立刻赶往办公楼。副厂长办公室的锁,比档案室的结实不了多少。进去后,
我直奔他的办公桌。翻箱倒柜是下下策,我需要找到最直接的证据。他的桌上很整洁,
文件摆放得一丝不苟,茶杯也擦得锃亮。我扫视一圈,目光落在了他桌角的一个黄铜笔筒上。
那笔筒很重,看起来有些年头了,上面刻着“劳动模范”四个字。我心中一动,拿起了笔筒。
果然,在笔筒底座的毛毡下,我摸到了一串钥匙。这串钥匙里,有一把很特别,不是开门的,
更像……是开某种柜子的。我环顾四周,视线最终锁定在墙角那个不起眼的铁皮文件柜上。
我用钥匙打开了文件柜,里面没有文件,而是一些杂物。最下面,压着一个油布包。
我打开一看,心脏猛地一跳。里面是一套改装过的钳子和扳手,其中一把钳子的顶端,
有一个独特的缺口。我立刻想起了机床接口处的刮痕,形状,大小,完全吻合!人赃并获!
我正要把东西收好,走廊外突然传来了脚步声。很轻,但在这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我心里一紧,来不及多想,抓起油布包就近躲到了窗帘后面。门被推开,一个人影闪了进来,
他没有开灯,而是径直走向办公桌,似乎在找什么东西。借着窗外微弱的月光,
我看清了他的脸。是车间主任,王大海。那个在人前对我喊打喊杀,
恨不得扒我一层皮的男人。他来这儿干什么?只见他在李卫东的抽屉里翻找了一阵,
似乎没找到,嘴里不耐烦地“啧”了一声。然后,他的目光也投向了那个铁皮文件柜。
我屏住呼吸,心都提到了嗓子眼。04王大海显然是冲着那套工具来的。他掏出自己的钥匙,
却发现打不开文件柜,脸上的表情变得既困惑又焦急。他不知道,
锁芯已经被我用李卫东的钥匙打开了。就在他准备放弃,打算去撬锁的时候,走廊的另一头,
又传来一阵沉稳有力的脚步声。是顾长风!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下热闹了,
一出“捉奸”大戏,演员都到齐了。王大海也听到了脚步声,他脸色大变,
慌忙想找地方躲藏,可这小小的办公室一览无余,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啪嗒。
”办公室的灯被打开了,刺眼的白光瞬间充满了整个空间。顾长风站在门口,面沉如水,
目光像两把锋利的刀子,直直地射向屋里的王大海。“王主任,深夜拜访李副厂长的办公室,
是有什么重要的工作要汇报吗?”顾长风的声音不高,却带着千钧的压力。
王大海的冷汗“刷”地一下就下来了,他结结巴巴地解释:“我……我有点事,
想找李副厂长……对,工作上的事!”“是吗?”顾长风缓缓走进来,他每走一步,
王大海就往后缩一步。“可我怎么听说,你跟李副厂长,最近在倒腾厂里的废旧钢材,
赚了不少外快啊?”王大海的脸瞬间变得惨白,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顾长风不再看他,目光扫视了一圈,最后,定格在我藏身的窗帘上。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他发现我了。他没有声张,而是走到办公桌前,拿起那个黄铜笔筒,在手里掂了掂,
然后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我听:“有些人,总喜欢把重要的东西,藏在最显眼的地方。
自作聪明。”说完,他把笔筒重重地往桌上一放,发出“咚”的一声巨响,
吓得王大海一哆嗦。“王主任,跟我去保卫科走一趟吧。”顾长风转过身,
不容置疑地命令道。王大海腿一软,差点瘫在地上。他知道,这回是彻底栽了。
就在顾长风押着王大海走到门口的时候,他突然停下脚步,
头也不回地说道:“窗帘后面风大,别着凉了。”等他们走后,我才从窗帘后面出来,
后背已经惊出了一身冷汗。顾长风这个男人,心思缜密得可怕。
他显然早就怀疑李卫东和王大海勾结,今晚的一切,都是他设下的局。
他故意只告诉我李卫东是嫌疑人,就是想看看我能查到什么地步。而他自己,
则在暗中监视着另一个目标,王大海。我们俩,就像在进行一场没有言语的默契配合。
我看着手里的油布包,心里五味杂陈。现在证据确凿,只要等到天亮,
在全厂大会上把这些东西甩出来,李卫东就百口莫辩。但是,事情真的会这么顺利吗?
李卫东在厂里根基深厚,党羽众多,他会这么轻易地束手就擒吗?我走出办公楼,
清晨的微风吹在脸上,带着一丝凉意。我抬头看了看天,东方的天空已经泛起了鱼肚白。
决战的时刻,就要到了。05早上八点,红星机械厂的大礼堂座无虚席。所有工人,
无论当班还是休息,
都被要求参加这次“关于严肃处理工厂破坏分子林晚意”的全厂职工大会。
我被两名保卫科的人“押”在第一排,像个即将被游街示众的犯人。
李卫东坐在主席台的正中央,满面红光,官威十足。他旁边坐着几个厂里的老领导,
一个个表情严肃。唯独厂长的位置,是空的。顾长风还没来。李卫东清了清嗓子,
拿起麦克风,开始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先是痛斥了破坏工厂生产的恶劣行径,
然后话锋一转,矛头直指我。“……林晚意,年纪轻轻,思想却已经腐化!不思进取,
反而因为个人恩怨,蓄意破坏我们从德国引进的宝贵设备!这种行为,简直是令人发指!
今天,我们就要在这里,给她一个最严厉的处分!”台下响起一片附和声,
那些平时看我不顺眼的人,此刻叫得最大声。我冷眼看着台上表演的李卫东,
心里盘算着时间。顾长风为什么还没来?他不会是想让我一个人唱独角戏吧?
就在李卫东宣布要将我“开除厂籍,并移交公安机关”的时候,礼堂的后门,
“吱呀”一声被推开了。顾长风逆光而来,他没有穿那件标志性的白衬衫,
而是换上了一身笔挺的蓝色工装,更显得肩宽腿长。他手里没拿任何东西,就这么一步一步,
沉稳地走上主席台。他一来,整个会场的气氛瞬间就变了。“顾厂长,您来得正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