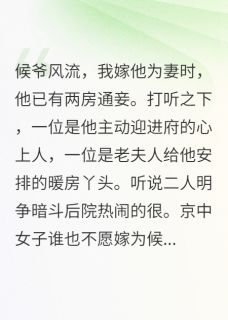
候爷风流,我嫁他为妻时,他已有两房通妾。打听之下,一位是他主动迎进府的心上人,
一位是老夫人给他安排的暖房丫头。听说二人明争暗斗后院热闹的很。
京中女子谁也不愿嫁为候府妻。就连母亲也劝我候府不是个好去处,
可嫁谁不都得看着他三妻四妾,更何况陛下赐婚。不从,许家满门如何活命。
1圣旨降下的那日我正在院中给花草浇水。母亲手中的茶盏碎了满地,
拉着我的手说:“妙竹那谢景已有两房妾室,你嫁过去……”她声音发颤,
指尖掐进我手腕:“侯府后院吃人不吐骨头的……”廊下石榴花开得正艳,
红得像宫里那道明黄的圣旨,黄绫上“钦赐良缘”四个大字烫得人眼眶生疼。
“母亲看这院子。”我指了指满架的葡萄藤,“这些藤蔓若攀着架子长,
能遮出半亩阴凉;若是拧成死结,不过烂在泥里罢了。”她抬起眼,
鬓边新添的白发在风里飘。我想起那年,也是这样的暮春,她蹲在我跟前擦去我膝头的血,
说“咱们妙竹最会化险为夷”。如今廊下的鹦鹉忽然开口,学舌般重复着“钦赐良缘”,
倒比母亲的哭声更刺耳。“我这便让你爹入宫!”她猛地起身,
裙角扫翻了矮几上的青瓷花盆,“称病、装疯……总能拖得一时是一时!
”碎瓷片划破了她的裙摆,我却没去扶。“母亲可记得,上月城西李娘子?
”我捡起半片完好的青花瓷,指尖摩挲着上面的缠枝纹,“她拒了太学博士的聘礼,
如今怎样了?”母亲身形一滞。李娘子的事闹得满城皆知。那姑娘以死抗婚,
最后被族长按在祠堂里浸了猪笼。昨夜我翻遍了《女戒》,
倒比任何时候都看得明白……这世道的女子,手里攥着的从来不是姻缘簿,而是生死簿。
“陛下赐的是‘金缕同心结’。”我将碎瓷片轻轻放下,“若许家抗旨……”不必说完,
母亲已跌坐在竹椅上。檐角鸽群掠过,投下细碎的影子在她脸上,像一道道无声的鞭痕。
安抚好母亲,我当即便让春桃去打听谢景那两房妾室的情况。春桃天黑透了才回来。
谢景那两房妾室。一位是他西征路上救回的孤女名唤绿芜,身娇体弱,
都传是他心尖尖上的人。另一位是老夫人给他安排的暖床丫头红袖,精明能干,
如今把中馈管得滴水不漏,账房的老管事都要让她三分。听闻两人在府中闹得不可开交,
倒是与传闻并无二致。春桃还说,不过短短半日京中早已传开圣上赐婚我与谢景。
京中贵女皆在看我的笑话,都说我这位才貌双绝的嫡**,竟要给风流侯爷做填房,
与病弱孤女、泼辣丫鬟共侍一夫。这倒也在意料之中。2婚期定下的红笺轻飘飘落在妆奁上,
像是一片催命符。母亲握着那纸婚书的手不住发颤,鬓边的银丝在晨光里晃得人眼疼,
不过一夜,她眼角的皱纹就深了几分,整个人仿佛被抽走了精气神。“妙竹,
再想想办法……”母亲的声音里带着哭腔,“那老夫人在京中出了名的难缠,手段狠辣,
你嫁过去……”我轻轻按住母亲颤抖的手,目光扫过窗外新抽芽的柳枝。“母亲,这京城里,
哪家贵公子后院不是莺莺燕燕?就算换个人家,就能高枕无忧了?”我扯出一抹苦笑,
“与其临阵慌乱,倒不如趁这一个月,把侯府底细摸清楚。”父亲在堂前负手踱步,
几次欲言又止。终于,他狠狠一跺脚,“我明日就进宫,求陛下收回成命!
就算拼上这把老骨头……”“父亲!”我急忙拦住他,“陛下赐婚,岂有收回之理?
您若去求,不是把许家满门往火坑里推吗?”我望着父亲苍老的面容,心里一阵酸涩,
“女儿既然要嫁,自然会做好准备。”送走父母后,我招来春桃。“这一个月,
你多去侯府附近走动,找那些婆子丫鬟打听消息。”我摩挲着手中的团扇,
“尤其是老夫人的喜好、脾气,还有府中的规矩,越详细越好。”这一个月,
我每日研读《内则》《女诫》,学习管家之道,也让父亲请来府中老嬷嬷,
传授应对后院纷争的法子,牢记于心。夜深人静时,我常对着铜镜练习微笑,
将所有不安藏进眼底。母亲看着我整日忙碌,心疼得直掉眼泪。大婚这日,
花轿碾过朱雀大街时,隔着红绸都能听见百姓的窃窃私语。
“许家姑娘可惜了”的叹息声顺着轿帘缝隙钻进来,混着媒婆撒的桂圆花生,
沉甸甸地压在膝头。三拜九叩时,谢景的手穿过盖头下的缝隙稳稳托住我。
他掌心的温度透过喜服渗过来,不似传言中浪荡子的轻佻。我余光瞥见他腰间悬着的玉佩,
羊脂玉上刻着“止戈”二字,倒与父亲那把匕首上的刻痕有几分相似。更漏敲过三下,
新房的门轴终于发出吱呀声响。喜烛爆开一朵灯花,将谢景的影子投在红纱帐上,
他立在门口顿了顿,才缓步走近:“委屈你了。”盖头被金簪挑起的瞬间,
烛火映得他眉目如画。传闻里整日眠花宿柳的侯府公子,此刻眼神澄澈清明,
嘴角挂着歉意的笑,倒像是被逼婚的良人。他身上萦绕着淡淡的松木香,混着喜烛的蜜蜡味,
竟让我想起儿时在后花园偷折的松枝。“若你不愿……”他忽然开口,喉结微微滚动,
“我今夜便歇在书房。”这话惊得我抬眼,正对上他泛红的耳尖。京中盛传他房中术精湛,
此刻却像个未经人事的少年。红烛燃尽时,我才惊觉传言与现实天差地别。
他的生涩不似作伪,连指尖抚过肌肤时都带着小心翼翼。帐幔低垂间,
我望着他后颈渗出的薄汗,忽然想起白日里绿芜倚在听松阁窗边的苍白面容,
还有红袖在二门处盯着花轿时凌厉的眼神。锦被下的玉镯硌得生疼,那是母亲偷偷塞给我的,
内侧刻着“平安”二字。谢景替我掖好被角时,我听见他低声呢喃:“往后有我在。
”3晨光刺破雕花窗棂时,春桃已将翡翠缠枝纹茶盏擦得发亮。
我对着铜镜调整鬓边的点翠步摇,镜中倒影映出身后攥紧衣角的丫鬟,倒比我更像临战的雀。
慈安院的鎏金屏风后飘来沉水香,老夫人斜倚在湘妃榻上,佛珠在指尖碾出细碎声响。
绿芜蜷在软凳上,藕荷色襦裙裹着单薄的肩,药碗腾起的热气模糊了她苍白的脸。
红袖捧着茶点立在一旁,嘴角噙着笑,眼神却像淬了毒的银针。“新妇敬茶。”我屈膝行礼,
茶盏稳稳落在青玉案上。老夫人垂着眼皮,
佛珠突然“啪”地打在案头:“听说许家姑娘擅画,可晓得这茶具上的缠枝纹有九种针法?
”茶汤在盏中泛起涟漪。我余光瞥见谢景向前半步,袖口的暗纹随着动作若隐若现。
指尖掐进掌心,将求助的目光化作一抹浅笑:“儿媳虽不擅女红,却记得《考工记》载,
缠枝纹取‘生生不息’之意,恰如婆母治家的恩泽绵长。”绿芜轻咳一声,帕子掩住唇色。
红袖手中的茶盘微微倾斜,杏仁酥滚落的声响在寂静中格外刺耳。老夫人终于抬眼,
浑浊的瞳孔里映出我挺直的脊梁,佛珠再次转动时,已换了慵懒的调子:“既如此,
便去抄二十遍《内则》,权当温书。”谢景的眉头皱成死结,我却抢先福身谢恩。转身时,
春桃慌乱中打翻了铜盆,水花溅湿我的裙裾。红袖捂嘴轻笑的瞬间,
我在水渍里瞧见自己的倒影……脊背笔直得如同侯府门前的石狮子。出了慈安院,
谢景攥住我的手腕:“为何拦我?”他掌心的温度灼人,
“你不必……”“侯爷可知藤蔓如何才能遮出阴凉?”我抽回手,望着远处飘飞的柳絮,
“若总攀着别人的架子,风一吹便断了。”日头爬上中天时,抄书的宣纸铺满了案头。
窗外传来绿芜的咳声,断断续续,倒像是催命的更鼓。我握紧狼毫,
墨汁在“妇德”二字上晕开,洇成一片深色的海。4宣德炉里的龙涎香正煨得袅袅,
我握着《齐民要术》的指尖突然顿住……雕花木门被叩响时,带着种刻意放轻的节奏。
谢景提着食盒跨进门槛,月白长衫沾着些许桂花香,倒不像平日里出入脂粉堆的模样。
“厨娘新做的杏仁酥。”他将食盒搁在案上,青瓷碗碰撞出清响,
“说是你前日提过……”“都传绿芜姑娘是侯爷的心上人。”我合上书卷,
墨香混着糕点甜腻的气息在屋内漫开。话一出口便觉荒唐,这侯府里的真心假意,
哪是三言两语能问清的?指尖无意识摩挲着书页折角,想起今早撞见他往听松阁去时,
怀里抱着的药匣子比昨日更沉。谢景倒茶的动作凝滞一瞬,茶汤险些溢出杯沿。
他望着杯中的涟漪轻笑出声,却未达眼底:“夫人也信那些坊间传言?”“不过随口一问。
”我抢在他开口前起身,广袖扫过案头的宣纸,抄录的《内则》墨迹未干,“侯爷不必解释,
圣上赐婚的旨意,总不能叫人说咱们夫妻失了和睦。”他凝视我片刻,
从袖中取出个锦盒推来。打开时,羊脂玉镯温润的光映得人心跳漏了一拍,
镯身刻着的缠枝纹与那日慈安院的茶具如出一辙。“你前日应对母亲时说的话,我记下了。
”他声音低沉,“藤蔓要自己攀,可这架子,总归能替你支得稳些。”话音未落,
院外突然传来瓷器碎裂声。春桃慌慌张张跑来,鬓发凌乱:“**!
红袖姨娘和绿芜姑娘在花园……”谢景起身时带起一阵风,锦盒在案上摇晃。
我望着他离去的背影,玉镯泛着冷光,忽然想起昨夜更漏声里,
隐约飘来的争执……“侯爷若真在意那许家女……”“住口!”我攥着玉镯至花园时,
满地狼藉。碎瓷片上还沾着胭脂红的汤药,绿芜瘫坐在太湖石旁,素白的裙摆洇着深色药渍,
模样说不出的狼狈。红袖捏着手绢站在三步开外,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
“这汤药本是给妹妹补身子的,谁知道妹妹竟发这么大脾气。”红袖声音婉转,
带着恰到好处的委屈,“妾不过说了句新夫人管家有方,妹妹就……”“住口!
”谢景脸色阴沉,弯腰要去扶绿芜,却被她偏头躲开。我站在廊下,看着他悬在半空的手,
突然想起方才他说要支稳架子的模样。绿芜剧烈咳嗽着,
指缝间渗出点点血丝:“侯爷既已娶了新夫人,又何必再来假惺惺……”她的目光越过谢景,
直直落在我身上,那眼神里的怨毒让我心头一颤。我缓步上前,
在满地碎片间寻了块干净的地方蹲下,掏出帕子替绿芜擦去嘴角的血渍。她身子猛地一僵,
显然没料到我会这般举动。“妹妹身子不好,汤药凉了喝着伤胃。”我轻声道,
“不如让厨房重新煎一服,再配上几样清淡的小菜。”谢景有些诧异地看向我,
红袖的脸色却瞬间变了。我转头吩咐春桃:“去请大夫来,再把厨房管事叫来,
就说我要过问每日膳食安排。”等众人散去,花园里只剩我和谢景。他望着满地狼藉,
自嘲般笑了笑:“让夫人见笑了。”“侯爷可知,”我弯腰捡起一片碎瓷,“藤蔓若想遮阴,
不仅要自己攀得高,更要学会化解旁的藤蔓纠缠。”将碎瓷片丢进竹篓,
我抬眼迎上他探究的目光,“今日这出戏,不过是个引子罢了。”谢景若有所思,正要开口,
远处传来老夫人院子里的传唤声。我福了福身:“侯爷先去忙吧,后院的事,
我自会处理妥当。”目送他离开,我转身走向听松阁。春桃小跑着跟上,
怀里抱着从厨房取来的新汤药:“**,您就这么放过红袖?”“不急。
”我望着手中重新煎好的汤药,热气氤氲间,仿佛看到了红袖眼中转瞬即逝的不甘,
“要想拔除毒瘤,总要等它自己露出破绽。”5归宁这日,八抬大轿停在许府门前时,
谢景亲自掀开轿帘,玄色蟒纹袖摆扫过朱漆门槛,惊起满地金箔般的银杏叶。
他伸手搀扶的姿态自然妥帖,引得门房小厮交头接耳……京中谁人不知,这素来浪荡的侯爷,
竟对新妇这般周到。母亲握着我的手不住摩挲,指腹的薄茧蹭得我腕间玉镯轻响。
她鬓角白发又添了几缕,眼底映着我身上的金线刺绣,
突然落下泪来:“苦了你了……在侯府万事小心,若能早些怀个孩子,
往后……”厢房暖阁里,父亲将一匣子银票推到我面前,
欲言又止:“若那谢景敢亏待你……”我按住父亲粗糙的手,瞥见窗外谢景正与兄长谈笑,
腰间玉佩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他应对得体,礼数周全,倒比在家中时更显沉稳。临别时,
母亲往我袖中塞了个锦囊,热气呵在我耳畔:“里面是求来的生子符,
贴身戴着……”话音未落,谢景已缓步而来,笑着接过我手中的锦盒:“岳父岳母放心,
妙竹在侯府一切安好。”回程的马车上,我捏着锦囊出神。车帘缝隙漏进的风掀起裙子下摆,
恍惚间又想起新婚夜。谢景局促的模样与白日里运筹帷幄的侯爷判若两人,
交合时生涩的动作……难道那些风流传言,竟是刻意为之?“在想什么?
”谢景忽然掀开暗格,取出一盏温茶。他身上的松木香混着茶香萦绕在狭小的车厢,
目光落在我攥紧的锦囊上,眸色微动,“母亲又给你塞了东西?”我将锦囊藏进袖中,
望着他棱角分明的侧脸:“不过是些家常话。”指尖无意识摩挲着杯沿,想起母亲的叮嘱,
“侯爷可知,后院安稳,子嗣……”“妙竹。”他突然打断我,声音低沉却坚定,
伸手轻轻拭去我鬓边碎发,“不必勉强自己。”马车颠簸间,他的手掌覆在我手背上,
温度透过锦缎传来,“我说过,这架子,我会替你支稳。”回到侯府时,
暮色已将听松阁染成青灰色。绿芜的咳嗽声隔着雕花窗棂传来,一声接一声,
像是要把心肺都咳出来。谢景脚步微顿,我却抢先开口:“侯爷去看看吧,我自己能回房。
”他深深看我一眼,转身往听松阁走去。春桃提着灯笼跟在我身后,小声嘀咕:“**,
您就这么让侯爷去?那绿芜姑娘……”“越是拦着,越显得心虚。
”我抚过回廊上斑驳的朱漆,想起母亲塞给我的生子符,“去把账房这个月的流水拿来,
再让人备些安神的药送去听松阁。”夜深人静时,我对着烛火翻看账本,
香料一项的支出高得离谱,可库房登记的数量却对不上。正皱眉间,窗外传来细微的脚步声。
“谁?”我吹灭烛火,抄起案头的剪刀。门轴轻响,谢景的身影出现在月光里,
手里端着一碗银耳羹。“看你房里灯还亮着。”他将碗放在桌上,“在查账?”我没回答,
借着月光打量他。他发间还沾着听松阁的药香,衣襟却有些凌乱,像是匆匆整理过。
“侯爷今夜在听松阁,可还顺心?”话一出口,才惊觉语气里带着自己都未察觉的酸涩。
谢景轻笑一声,伸手替我拨开额前碎发:“怎么,吃醋了?”见我别过脸,
他的声音突然沉下来,“绿芜……她的病没那么简单。”我猛地回头,正对上他凝重的目光。
还未及追问,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尖叫。春桃跌跌撞撞跑来:“**!
红袖姨娘房里……走水了!”谢景脸色骤变,抓起披风就往外冲。我紧随其后,心跳如擂鼓。
侯府后院火光冲天,红袖披头散发地跪在地上,身旁躺着昏迷的丫鬟,
地上散落着半截烧黑的蜡烛。“有人……有人要烧死我!”红袖抓住谢景的衣摆,眼神惊恐,
“侯爷,一定是绿芜!她嫉妒我……”“住口!”谢景甩开她的手,转身吩咐家丁救火。
我蹲下身查看丫鬟的伤势,指尖触到她后颈时,摸到一块凸起的胎记。火势扑灭时,
天边已泛起鱼肚白。谢景站在焦黑的废墟前,脸色阴沉得可怕。我走到他身边,
轻声道:“侯爷,这场火,烧得太巧了。”他侧头看我,眼中闪过一丝赞赏:“明日,
你接手府中大小事务吧。”话音未落,远处传来绿芜的咳声,在寂静的清晨格外刺耳。
6晨光刺破薄雾时,慈安院的紫檀木案上,红袖攥着账册的指节泛白,
芙蓉胭脂衬得她眼底的怨毒愈发鲜明:“夫人刚进门,许多规矩还不熟稔,
这中馈之事贸然交接,恐生疏漏。”老夫人转动着翡翠佛珠,
浑浊的目光在我与红袖之间逡巡:“妙竹啊,你虽聪慧,但到底是新妇,
再跟着红袖学上两月……”“婆母。”我福身打断她的话,
广袖扫过案上摊开的《内府规制》,“儿媳嫁入侯府前,
已将府中账目、人事细细梳理过三遍。”指尖划过账册上香料支出的异常数据,
“昨日红袖姨娘院中走水,恰是她掌管采买期间购入的劣质烛芯所致,这般疏漏,
儿媳实在不敢耽搁。”红袖猛地起身,裙摆扫翻了青铜香炉:“许妙竹!
你莫要血口喷人……”“够了。”谢景的声音突然从门外传来,他大步踏入厅堂,
玄色锦袍上还沾着晨露,目光如鹰隼般扫过众人,“妙竹为侯府主母,本该掌府中中馈。
”老夫人的佛珠“啪”地打在案头,正要开口,我却先一步屈膝:“婆母疼惜儿媳,
儿媳心中明白。”从袖中取出连夜整理的管家条陈,“但侯府诸事繁杂,
儿媳若因‘新妇’之名久居其位而不谋其政,才是真正辜负了婆母与侯爷的信任。
”谢景望着我手中的文书,唇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红袖脸色煞白,
突然捂住心口软倒在地:“侯爷……妾忽然心口绞痛……”“春桃,扶姨娘回房歇着。
”我淡淡吩咐,转而对老夫人道,“儿媳明日便着手清查库房,还请婆母派个得力嬷嬷监督,
免得落人口舌。”踏出慈安院时,谢景跟上来,压低声音道:“方才为何拦我?
”“侯爷可知鹰隼为何能擒狡兔?”我望着远处听松阁飘出的药烟,
“因它从不会在猎物面前展露爪牙。”转身时,瞥见绿芜倚在回廊尽头,
苍白的脸上浮起意味深长的笑。当夜,我在书房核对账册到三更。烛火忽明忽暗间,
春桃匆匆来报:“**!红袖姨娘房里的丫鬟,在后巷被人发现溺毙了。
”我握着狼毫的手顿住,墨迹在“香料”二字上晕开。我将狼毫搁在笔架上,
墨迹未干的宣纸在穿堂风里微微颤动。
溺毙的丫鬟与账房小厮有相似胎记的画面在脑海中重叠,这巧合背后定藏着见不得人的勾当。
春桃见我神色凝重,忙凑近一步:“**,要报官吗?”“且慢。
”我盯着案头被烛火映得忽明忽暗的账本,“先派人去查那丫鬟生前与何人来往密切,
尤其要留意采买相关的人。”第二日,我带着春桃和老夫人指派的周嬷嬷清查库房。
推开库房大门的瞬间,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清点香料时,
我发现账本上登记的数量比实际多出三成,而这些多出来的香料,
正是昨夜账册中异常支出的那批。“周嬷嬷,这批香料是什么时候入库的?
”我捏起一撮颜色暗红的香粉,指尖瞬间被染成诡异的紫色。周嬷嬷眯着眼凑近查看,
脸色突然变得煞白:“这……这是上个月红袖姨娘亲自验收的,说是西域进贡的珍品。
”正说着,门外传来一阵喧哗。红袖带着几个婆子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
她今日换了身鲜艳的大红色襦裙,脂粉涂得比往日更浓,
反倒衬得眼底的血丝愈发狰狞:“许妙竹!你三番五次针对我,到底安的什么心?
不过是查个库房,还要栽赃陷害不成?
”我不慌不忙地将染了色的帕子丢到她面前:“姨娘掌管采买期间,
购入的香料不仅数量不符,还暗**素,昨夜你房里丫鬟暴毙,莫不是与此有关?
”红袖的眼神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又镇定下来:“胡说!我那丫鬟是失足落水,与我何干?
倒是夫人,刚接手就查出这么多问题,谁知道是不是故意找茬?”“够了!
”谢景的声音从门外传来。他今日身着一身劲装,腰间佩剑泛着寒光,显然是刚从校场回来。
他扫了眼满地狼藉,目光最后落在我手中的毒香上:“把负责采买的人都叫来,
本侯要亲自审问。”就在这时,一个小厮慌慌张张地跑进来:“侯爷!不好了!
绿芜姑娘……她咳血昏迷了!”谢景脸色骤变,转身就要往听松阁跑,
却被我拦住:“侯爷且慢,绿芜姑娘的病来得蹊跷,昨夜丫鬟溺亡,今日她就昏迷,
这其中恐怕大有文章。”我压低声音,“或许,我们该先去看看她房里有没有这种香料。
”谢景的脚步顿住,眼中闪过一丝犹豫。最终,他点了点头。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往听松阁走去,长廊下的灯笼在风中摇晃,将众人的影子拉得又长又扭曲。
7听松阁的雕花门被推开时,药香混着若有似无的甜腻气息扑面而来。
绿芜苍白如纸的脸埋在锦被间,唇角还沾着斑驳血迹,剧烈的喘息声撕扯着寂静。
谢景大步上前探她脉搏,指尖触到她腕间时,我瞥见床头青瓷香炉里燃着半截香,
与库房中带毒的香料色泽如出一辙。“把香灭了!”我抢步上前打翻香炉,
火星溅落在青砖上迸出噼啪声响。春桃慌忙用铜盆扣住余烬,刺鼻的焦糊味瞬间盖过甜香。
谢景望着满地狼藉,喉结滚动:“这香……是红袖经手采买的?”话音未落,
门外突然传来老夫人的怒喝:“反了天了!在绿芜房里闹什么?”她拄着雕花拐杖闯入,
浑浊的眼睛扫过香炉碎片,“绿芜久病体虚,燃些安神香有何不妥?”“婆母请看。
”我展开被香粉染紫的帕子,“此香含西域曼陀罗,少量可助眠,燃久了却会侵蚀心肺,
绿芜姑娘咳血昏迷,怕是与此香脱不了干系。”老夫人的拐杖重重杵在地上,
佛珠撞出凌乱声响。红袖不知何时挤到人群前端,突然瘫坐在地哭嚎:“冤枉啊!
这批香料入库时我亲自查验过,绝无问题!定是有人偷梁换柱,想嫁祸给我!
”她泪眼婆娑地望向谢景,“侯爷明察,妾一心为侯府操持,怎会害绿芜妹妹?
”谢景剑眉紧蹙正要开口,老夫人却抢先打断:“够了!不过是府里些琐碎事,
闹得鸡飞狗跳成何体统!”她转动佛珠的速度愈发急促,“绿芜的病找太医好好治,
香料的事就此作罢,不许再查!”“母亲!
这分明是有人蓄意谋害......”谢景话音未落,就被老夫人严厉的眼神截断。
我望着老夫人不自然紧绷的嘴角,突然想起红袖耳后与溺亡丫鬟相似的印记,心中警铃大作。
红袖趁机爬起身,躲到老夫人身后时,投来一抹挑衅的冷笑。“婆母爱惜家人,儿媳明白。
”我福身行礼,袖中攥紧染毒的帕子,“只是侯府上下数百口人,
若再有类似疏漏......”“我说了不许再查!”老夫人的拐杖重重敲击地面,
震得青砖缝隙里的香灰簌簌扬起,“妙竹,你新掌家,莫要本末倒置!”夜色降临时,
听松阁的哭声渐歇。我站在廊下望着西厢房方向,那里还亮着点点烛火。
春桃捧着件披风过来,声音发颤:“**,就这样放过红袖?”风卷起满地香灰扑在脸上,
我望着掌心未褪的紫色痕迹,冷笑出声:“老夫人护得了她一时,护得了一世?
”8我将写满密信的素绢折成精巧的燕子形状,春桃跪在地上,把它塞进发间的银簪夹层。
“一定要亲手交到兄长手上。”我压低声音,望着丫鬟发颤的指尖,“不可让任何人知晓。
”春桃刚消失在月洞门,管家就捧着烫金请柬来报:“皇后娘娘邀夫人参加三日后的春日宴。
”春日宴那日,御花园的海棠开得如火如荼。我捧着鎏金酒盏,
听着贵女们娇笑谈论谢景新置的别院,余光瞥见女官对我使了个眼色。绕过九曲回廊,
在无人的凉亭里,我见到了身着常服的陛下。“许家丫头,可怨朕?”皇帝望着池中游鱼,
声音混着风声传来。我跪地时,膝盖硌在青砖上的疼痛让心跳漏了一拍:“陛下赐婚,
是许家的福分。”“福分?”他突然轻笑,转身时腰间玉佩撞出清响,“谢景那小子,
装疯卖傻倒瞒过不少人。”见我猛地抬头,他意味深长道,“看人,得用心。”话音未落,
远处传来皇后的传唤声,皇帝最后看我一眼,袍角扫过石凳,留下一缕若有似无的龙涎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