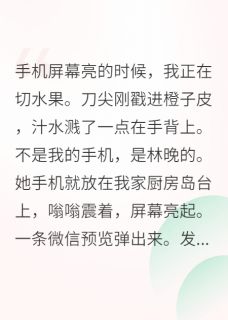
手机屏幕亮的时候,我正在切水果。刀尖刚戳进橙子皮,汁水溅了一点在手背上。
不是我的手机,是林晚的。她手机就放在我家厨房岛台上,嗡嗡震着,屏幕亮起。
一条微信预览弹出来。发信人:陈屿。内容:【昨晚的事,别让她知道。
】我的手指停在橙子上,凉凉的汁水顺着指缝往下淌。陈屿。我老公。昨晚?
昨晚他说公司加班,凌晨两点才回来,带着一身酒气倒头就睡。林晚从洗手间出来,
甩着手上的水珠,脸上还带着笑:“方蜓,你切个橙子也太慢了吧,我快渴死了。
”她伸手就要去拿手机。我比她快一步。抓起那块冰凉的金属和玻璃,屏幕还亮着,
那条信息像根刺,扎进我眼里。“谁的啊?给我看看。”林晚凑过来,
带着她常用的那款栀子花味香水的气息。这味道,昨天陈屿身上好像也沾了点?
我当时还以为是应酬场合里沾上的。我把手机屏幕转向她。林晚脸上的笑,像被按了暂停键。
就那么僵着。一丝慌乱,飞快地从她眼睛里掠过,快得几乎抓不住,但我看见了。
“哦……这个啊,”她声音有点飘,伸手想把手机拿回去,
“陈屿哥就是……就是问我点工作上的事。”“工作?”我盯着她,声音很平,
“陈屿做金融,你在出版社做童书编辑,你们有什么工作需要半夜聊?
昨晚什么事不能让我知道?”林晚舔了下嘴唇。这个小动作,只有她特别紧张的时候才会有。
大学时作弊被抓、向暗恋的学长表白前,都这样。“哎呀,你想哪去了!”她突然拔高声音,
带着点夸张的嗔怪,“就是……就是我们公司不是想搞个金融知识入门的儿童绘本嘛!
陈屿哥懂行,我就厚着脸皮请教了一下。昨晚正好微信上聊了几句,他怕你嫌我老是麻烦他,
才这么说的!你这醋劲儿也太大了!”她伸手戳我胳膊,试图用惯常的亲昵打破僵局。
我躲开了。心脏在肋骨后面咚咚地跳,又沉又重。林晚的解释,像一层薄薄的油,
浮在深不见底的水面上。不对劲。绝对不对劲。我和林晚认识十年了。
从大学挤一张床铺抢一包薯片,到毕业一起在这个城市打拼,租房子挤地铁,
分享每一任男友的八卦,吐槽各自奇葩的上司。她失恋,
我陪她喝到天亮;我生女儿悠悠时大出血,是她第一个冲进产房,手抖着签了字。
我们好得像一个人。陈屿?他是我相亲认识的。程序员,话不多,人踏实。恋爱两年,
结婚五年。日子像温吞的白开水,没什么波澜,但解渴。他对我好,对女儿悠悠更好。
我从来没想过,这杯白开水里,会掺进别的东西。更没想过,掺东西的人,会是林晚。
“行吧,工作。”我没再追问,把手机递还给她,转身继续切那个可怜的橙子。
刀锋划过果肉,汁水流了一砧板。林晚明显松了口气,拿起手机飞快地按了几下,
大概是在删记录。她凑过来,拿起一瓣橙子塞进嘴里,声音含混不清:“甜!还是你会挑。
对了,周末带悠悠去新开那个儿童乐园吧?听说有个超大的海洋球池……”我嗯了一声,
没看她。昨晚的事。别让她知道。这几个字,像鬼影,在我脑子里盘旋。
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看什么都像浇了水的苗。陈屿还是那个陈屿。下班回家,
陪女儿搭积木,笨手笨脚地给她扎小辫。饭桌上聊公司新项目的瓶颈,偶尔抱怨两句老板。
他看我的眼神,依旧温和,甚至有点……心不在焉?以前觉得是程序员木讷,
现在品出了点别的味道。林晚也还是那个林晚。三天两头往我家跑,给悠悠带玩具绘本,
跟我吐槽相亲遇到的奇葩男。她看陈屿的眼神呢?以前觉得是朋友间的熟稔,
现在……她给他递水果,指尖会不经意地擦过他的手背。她听他说话,会微微歪着头,
眼神专注得过分。她夸他给悠悠扎的小辫“真有创意”,语气里的崇拜,甜得发腻。
这些细节,过去像背景板上的噪点,自动被我忽略了。现在,每一个都被放大镜挑出来,
摆在眼前,刺眼得很。我开始留意陈屿的手机。他洗澡时,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屏幕朝下。
有密码。我知道他惯用的几个数字组合,试了,都不对。心往下沉了沉。一天晚上,
他应酬回来,醉得厉害。我扶他上床,他外套胡乱扔在椅子上。
一股淡淡的、熟悉的栀子花香,缠绕在衣领上。不是我的香水。我从来不用花香调。
是林晚的味道。我捏着那件外套,指尖发凉。陈屿在梦里咕哝了一句,翻了个身。
窗外城市的灯光照进来,在他脸上投下明明暗暗的影子,陌生得很。我需要证据。
实实在在的,能让我死心,或者让我清醒的东西。机会来得很快。林晚生日到了。
她嚷嚷着要请我和陈屿吃饭,感谢我们“收留”她这个单身狗蹭了这么多年饭。
地点定在一家新开的西餐厅,格调不错。出门前,我犹豫了几秒,
把那个很久不用的旧手机揣进了包里。充满电,调成静音。以前用它录过悠悠学说话的声音。
餐厅灯光幽暗,音乐舒缓。林晚特意打扮过,一条酒红色的丝绒连衣裙,衬得皮肤很白。
她坐在我和陈屿对面。“来,寿星,点菜!”我把菜单推给她。林晚笑着接过,
眼神却飘向陈屿:“陈屿哥,我记得你喜欢吃牛排?这家战斧好像评价不错。
”陈屿点点头:“行,你看着点。”点完菜,林晚起身去洗手间。她的包,
那个小巧的链条包,就随意地放在她椅子旁边的空位上。我的心跳得有点快。
陈屿在低头看手机,手指划拉着屏幕。我拿起面前的柠檬水喝了一口,冰凉的液体滑下去,
压不住那股往上冒的焦躁。趁着陈屿没抬头,我装作无意,身体微微前倾,
手肘“不小心”碰倒了林晚放在桌边的手机。手机掉在地上,屏幕朝下。“哎呀!
”我低呼一声,立刻弯腰去捡。陈屿抬起头:“怎么了?”“没事没事,林晚手机掉了。
”我捡起手机,屏幕没碎。借着桌布的遮挡,
我的手指飞快地划开屏幕——她一直用指纹解锁,但我知道她手机的图形密码,
一个简单的“Z”。大学时她告诉我的,说这样好记。屏幕解锁了。我心脏狂跳,手心冒汗。
动作必须快。我迅速点开微信,置顶的聊天框,除了几个工作群,就是……陈屿。
备注是“屿哥”。聊天记录是空的。干干净净。显然刚被清理过。我暗骂一声,手指有点抖。
时间不多。我点开陈屿的头像,进入聊天设置,往下拉。有一个选项:“查找聊天记录”。
我飞快地输入关键词“昨晚”。屏幕上转了个圈。几秒钟,漫长得像一个世纪。结果出来了。
只有一条。日期是前天晚上,十一点四十七分。林晚:【屿哥,睡了吗?
今天……谢谢你陪我聊那么久。听你说那些烦心事,感觉好多了。
就是……我有点担心蜓蜓会不会误会?她心思细。】陈屿:【她睡了。没事,别多想。
你也是好心。】对话到此为止。看起来……似乎没什么?正常的关心?朋友间的倾诉?不。
林晚那句“担心蜓蜓会不会误会”,像根针。她在试探。她在陈屿面前,
把我塑造成了一个“心思细”、容易误会、需要他们小心翼翼避嫌的人。一股冰冷的怒气,
顺着脊椎爬上来。就在这时,屏幕顶端突然弹出一条新消息预览。是陈屿发来的!就在此刻!
他本人就坐在我对面!我猛地抬头。陈屿正低头看着他的手机屏幕,手指在打字。
我手里的林晚手机,屏幕顶端,那条新消息预览清晰地显示:陈屿:【对了,
你上次说想看的那个艺术展,票我弄到了两张。周末?别告诉方蜓,她对这些不感兴趣,
省得她勉强陪我们去。】嗡的一声。我的脑子像被重锤砸中,一片空白。血液瞬间冲上头顶,
又在下一秒褪得干干净净,手脚冰凉。艺术展?两张票?别告诉我?他记得林晚想看展。
他费心去弄票。他计划着周末单独和她去。他体贴地“不想勉强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我死死攥着林晚的手机,指尖用力到发白,几乎要把那冰冷的屏幕捏碎。“蜓蜓?
”陈屿的声音响起,带着一丝疑惑,“你捡个手机怎么这么久?林晚回来了。
”我猛地回过神,手忙脚乱地把林晚手机屏幕锁上,扔回她座位旁边。抬起头时,
林晚已经站在桌边,正奇怪地看着我。“怎么了?脸这么白?”她问。“没事,
”我扯出一个极其僵硬的笑容,声音发紧,“可能……空调太低了。有点冷。”林晚坐下,
目光在我和陈屿之间扫了个来回。陈屿已经收起了手机,表情恢复如常。整顿饭,
我味同嚼蜡。盘子里的牛排像一块冰冷的橡胶。林晚的笑声,陈屿偶尔的附和,
都像是隔着厚厚的毛玻璃传过来,模糊又刺耳。他们谈论着那个该死的艺术展,
用着只有他们才懂的梗,默契十足。我看着他们。一个是我相交十年、视若亲姐妹的闺蜜。
一个是我同床共枕、育有一女的老公。两张熟悉的面孔,此刻陌生得令人心寒。
虚伪的笑容底下,藏着怎样的龌龊心思?那两张艺术展的票,是通往哪里的钥匙?
愤怒像烧红的烙铁,烫着我的五脏六腑。但更深的,是一种被掏空的冰冷和恶心。
被最信任的两个人,联手捅了一刀。不能就这样算了。我要亲耳听到。
听到他们亲口承认这背叛。我要撕开这层虚伪的皮,看看底下到底烂成了什么样。
那个旧手机,在我包里,沉甸甸的。机会,自己送上门来了。几天后,林晚给我打电话,
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和哭腔。“蜓蜓……呜……我完了……”我心里咯噔一下,
语气尽量平静:“怎么了晚晚?别哭,慢慢说。”“我……我那个项目,
就是跟陈屿哥请教过的金融绘本……黄了!主编把我骂得狗血淋头,说我的方案幼稚,
方向完全错误……呜呜……我熬了那么多夜……全白费了……”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是不是特别没用啊……”金融绘本?请教陈屿?方向错误?一个念头,
像毒蛇一样钻进我的脑子。冰冷,滑腻。“别哭别哭,”我放缓声音,带着安抚,“你在哪?
在家吗?我过去陪你。”“嗯……在家……我好难受……蜓蜓……”“等着,我马上到。
”挂了电话,我深吸一口气。飞快地拿出那个旧手机,检查电量,打开录音功能,
调成高灵敏度模式。然后塞进我日常用的托特包最内侧,一个带拉链的小口袋里。
麦克风口露在外面。出门前,我对着镜子,练习了一下表情。担忧,焦急,真诚。
开车去林晚公寓的路上,我手心一直在冒汗。车载空调开得很足,但后背却一阵阵发冷。
我在利用她的脆弱。我知道。但我停不下来。那两张艺术展的票,像两根烧红的铁签,
插在我心口。敲开林晚的门,她眼睛红肿,头发乱糟糟的,穿着皱巴巴的睡衣,
怀里还抱着半盒抽纸。屋子里弥漫着淡淡的酒气。“蜓蜓……”她一见我,眼泪又涌出来,
扑过来抱住我。我拍着她的背,像过去无数次安慰她那样。“好了好了,不哭了。
一个项目而已,不至于。”扶着她坐到沙发上,茶几上果然放着半瓶红酒和一个空杯子。
……说我不懂装懂……说我找的什么狗屁专家……害得整个项目方向都歪了……”她抽噎着,
又给自己倒了小半杯红酒,仰头灌下去,被呛得直咳嗽。“专家?”我顺着她的话问,
拿起酒瓶看了看牌子,是她平时舍不得喝的那种,“你说陈屿?
”“嗯……”林晚眼神有些涣散,酒精和情绪的双重作用让她防线脆弱,
“就是他……都怪他!
……说儿童金融启蒙就该这么切入……他说没问题的……我那么信他……”她捶了一下沙发,
又委屈又愤怒。我的血液似乎凝固了一瞬。陈屿?他故意误导林晚?为什么?
“他可能……也是好心吧?毕竟隔行如隔山。”我试探着,递给她一张纸巾。“好心?
”林晚嗤笑一声,带着浓重的鼻音和醉意,“他才不是好心!
他就是……就是……”她顿住了,眼神飘忽,似乎在挣扎。我屏住呼吸。包里的手机,
像个沉默的见证者。“他就是想看我出丑!”林晚突然爆发,声音尖利,“他怕我太能干!
怕我在你面前太耀眼!他根本不想我做好!他只想我依赖他!崇拜他!围着他转!
”我的心猛地一沉。这话……指向性太明显了。“晚晚,你喝多了。
”我按住她又要去拿酒瓶的手,“别胡说。”“我没胡说!”她甩开我的手,
酒精彻底冲垮了理智的堤坝,眼泪汹涌而出,“蜓蜓!我对不起你!我难受死了!
我憋得好辛苦!”来了!我全身的神经都绷紧了,指甲深深掐进掌心。林晚抬起头,
泪眼朦胧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痛苦和一种近乎崩溃的倾诉欲。
“我……我喜欢陈屿……我好喜欢他……”她终于说了出来,声音破碎不堪,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可能是那次悠悠发高烧,他半夜开车送我们去医院,
跑前跑后……可能是他听我抱怨工作,安静地给我分析……他那么稳重,
那么可靠……跟你说的那种木讷程序员一点都不一样……”她语无伦次,涕泪横流。
“我知道我不该!我知道他是你老公!是悠悠的爸爸!可我控制不住……每次看到他,
听到他说话,我就心跳得厉害……我嫉妒你!嫉妒得要死!凭什么你能拥有他!
凭什么他能对你那么好!”她捂着脸,肩膀剧烈地抖动。
的事……我知道他懂……我想听他的声音……想让他多看看我……昨晚……昨晚我心情不好,
……但我好开心……真的开心……我知道这样不对……我**……我恶心……”她泣不成声,
蜷缩在沙发里,像个破败的布娃娃。空气死寂。只有她压抑不住的抽泣声,
和我自己震耳欲聋的心跳声。包里的手机,忠实地记录着这一切。每一个字,
都像淬了毒的针,密密麻麻扎在我心上。十年友谊。五年婚姻。在这一刻,
被她的醉话撕得粉碎,露出底下血淋淋的背叛和丑陋的欲望。我看着她。这个我认识了十年,
分享过所有秘密和悲喜的女人。此刻只觉得无比陌生,无比……肮脏。
愤怒没有预想中那样排山倒海。反而是一种极致的冰冷和麻木,从脚底蔓延上来,
冻僵了四肢百骸。“所以,”我的声音干涩得厉害,像砂纸摩擦,“那两张艺术展的票,
也是你‘不小心’提了一句,他就巴巴地去弄来了?”林晚的哭声戛然而止。她猛地抬起头,
醉意朦胧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震惊和慌乱,随即被更深的羞愧淹没。她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这反应,就是最好的答案。够了。我站起身。腿有点软,但撑着没倒。“林晚,”我看着她,
声音平静得可怕,连我自己都惊讶,“我们完了。”说完,我没再看她惨白的脸,
转身离开了这间充满酒气和眼泪的公寓。门在身后关上,隔绝了里面崩溃的哭声。
走廊的声控灯应声而亮,惨白的光打下来。**在冰冷的墙壁上,掏出包里的旧手机。
指尖冰凉,按下了停止录音的按钮。屏幕暗下去。证据,拿到了。可心里那个巨大的窟窿,
呼呼地往里灌着冷风。开车回家。路灯的光晕在挡风玻璃上拉长又缩短,像一条条流动的河。
到家时,客厅灯亮着。陈屿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放着无聊的综艺,声音开得很小。
他心不在焉地看着,手里无意识地转着手机。听到开门声,他转过头:“回来了?
林晚怎么样?哭惨了吧?”语气如常。带着点对朋友遭遇的同情。我换鞋,没看他。
包里的手机像块烙铁,烫着我的神经。“嗯,哭得挺厉害。”我走到饮水机旁,倒了杯冰水,
一口气灌下去。冰冷的液体划过喉咙,稍微压下了那股灼烧感。“项目黄了,她肯定难受。
”陈屿叹了口气,拿起遥控器换了个台,“你也别太担心,她能力强,缓几天就好了。
”“能力?”我放下水杯,玻璃杯底磕在吧台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响。我转过身,
靠在吧台边,看着他,“她能力是不错。不过,这次方向搞错,也不能全怪她,对吧?毕竟,
是‘专家’给她指了条歪路。”陈屿换台的动作顿住了。他抬起头,看向我,
眼神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闪烁。“什么专家?”他故作轻松地问。“你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