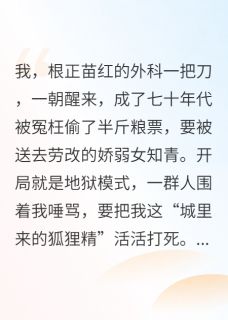
我,根正苗红的外科一把刀,一朝醒来,成了七十年代被冤枉偷了半斤粮票,
要被送去劳改的娇弱女知青。开局就是地狱模式,一群人围着我唾骂,
要把我这“城里来的狐狸精”活活打死。未婚夫更是当众退婚,搂着我继妹的腰,
骂我“破鞋”。我冷笑一声,破鞋?那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现代医学的铁拳!只是,
我没想到,我那刚退役回乡,据说是战场上杀敌不眨眼的冷面阎王邻居,
那个全村女人都想嫁的糙汉军官,会堵在我家门口,红着脸,支支吾吾地对我说:“同志,
我……我**上长了个东西,你能帮我看看不?”01“顾知夏,你个不要脸的,
偷东西还有理了?”尖利刻薄的女声在我耳边炸开,我被人用力推搡了一把,
后脑勺重重磕在土坯墙上,疼得我眼冒金星。我叫顾知夏,
上一秒我还是市中心医院最年轻的普外科副主任,正准备主刀一台复杂的直肠肿瘤切除术,
下一秒,我就被一群穿着的确良衬衫、满脸菜色的村民围在了中间。他们看我的眼神,
像是要活剐了我。“就是她!我亲眼看见她鬼鬼祟祟地从队长家出来,粮票肯定就是她偷的!
”一个瘦得像麻杆的男人指着我,唾沫星子横飞。“城里来的知青就是手脚不干净,
还长了一张狐媚子脸,不知要勾引谁呢!”“打死她!把她送去劳改!
”谩骂声和拳头一起向我涌来。我下意识地抬手格挡,脑子里却乱成一锅粥。
这不是我的身体!这双手纤细、白皙,指甲缝里却嵌着洗不掉的泥垢,
手腕上还有一道青紫色的掐痕。我猛地抬头,对上一双熟悉的眼睛。那是我名义上的未婚夫,
周建斌。此刻,他正一脸嫌恶地看着我,怀里还护着一个娇滴滴的姑娘。那姑娘,
是我同父异母的继妹,顾知秋。“顾知夏,我们完了。”周建斌的声音冷得像冰,
“我不能娶一个贼做老婆。”顾知秋躲在他怀里,怯生生地探出头,
声音里带着哭腔:“姐姐,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建斌哥的前途会受影响的……”我明白了。
这是一场早就设计好的陷害。原主是个单纯的城里姑娘,被继母哄骗着,
带着母亲留下的所有积蓄和工作名额,跟着继妹下乡。结果,工作名额被继妹抢了,
钱也被骗光了,最后还落得个偷盗的罪名,被活活打死。而我,就穿成了这个倒霉蛋。
“不是我。”我开口,声音沙哑得厉害,却异常平静,“我没有偷东西。”“还敢狡辩!
”村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手里拿着一杆旱烟枪,重重地磕在地上,“搜!给我仔细搜!
”两个膀大腰圆的妇女立刻冲上来,粗暴地在我身上摸索。我没有反抗,
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很快,她们从我贴身的口袋里,搜出了一叠崭新的粮票。
人群瞬间炸了。“人赃并获!还说不是你!”“不要脸的贼!”周建斌的眼神更冷了,
他搂紧了顾知秋,仿佛我是什么脏东西。顾知秋的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
我看着那叠粮票,忽然笑了。“村长,”我扬起头,目光直视着他,“这粮票上,
是不是应该有编号?”村长愣了一下,下意识地点头:“当然有。”“那好,
”我指了指粮票,“麻烦您对一对,这上面的编号,和你家丢的,对得上吗?
”我的话让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他们只顾着抓贼,却忘了最关键的证据。
村长的脸色变了变,他接过粮票,仔细看了起来。周围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脸上。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村长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终于,他抬起头,脸色难看地宣布:“编号……对不上。”02“什么?对不上?
”人群中发出一阵惊呼,所有人都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我。周建斌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顾知秋更是花容失色,死死地咬着嘴唇。我迎着他们的目光,缓缓地从地上站起来,
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既然编号对不上,就证明我不是小偷。”我的声音不大,
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朵里,“那么,是谁把这来路不明的粮票塞到我口袋里,
又是谁急着给我定罪呢?我想,大家心里应该有数了吧?”我的目光,
意有所指地扫过顾知秋苍白的脸。她浑身一颤,下意识地往周建斌怀里缩了缩。
村民们都不是傻子,前后一联系,立刻就品出味儿来了。“我就说嘛,
顾知青看着不像那种人。”“啧啧,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为了抢男知青,
连亲姐姐都陷害,这心也太黑了。”议论声像针一样扎在顾知秋身上,她再也装不下去,
哭着从周建斌怀里挣脱出来,指着我骂道:“顾知夏你胡说!你就是嫉妒我跟建斌哥好!
”“我嫉妒?”我像听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嫉妒你捡我不要的垃圾?”“你!
”周建斌被我一句话噎得满脸通红,气急败坏地吼道,“顾知夏,你别给脸不要脸!
”“脸是自己挣的,不是别人给的。”我整理了一下凌乱的衣领,
露出了手腕上那道刺目的掐痕,“周建斌,这道痕迹,是你留下的吧?就在半小时前,
你把我堵在墙角,说只要我肯把工作名额让给顾知秋,你就还认我这个未婚妻。我没同意,
你就想用强的,对吗?”我顿了顿,目光转向一脸惊慌的顾知秋:“至于这粮票,
恐怕是你趁乱塞进我口袋里的吧?真是好一招贼喊捉贼。”我的话像一颗炸雷,
在人群中炸开。所有人都用一种全新的,混杂着鄙夷和震惊的目光看着周建斌和顾知秋。
这个年代,作风问题可是天大的事。“你……你血口喷人!”周建斌彻底慌了。
“我是不是血口喷人,你心里清楚。”我上前一步,逼视着他,“周建斌,从今天起,
你我之间,婚约作废。从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说完,我不再看他,转身就走。
走出人群的那一刻,我感觉浑身都轻松了。原主的执念,似乎也随着我这番话烟消云散。
回到那个四面漏风的知青点,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烧了一大锅热水,
从头到脚洗了个干干净净。热水冲刷着身体,也让我混乱的思绪渐渐清晰起来。我,顾知夏,
回不去了。从今天起,我就是七十年代的顾知夏。既然老天让我再活一次,
我绝不会像原主那样窝囊。我正擦着头发,房门突然被人从外面“砰”的一声踹开。
周建斌和顾知秋一脸怒气地冲了进来。“顾知夏,你这个**,你敢毁我名声!
”周建斌双眼赤红,扬手就要打我。我眼神一冷,侧身躲过,同时手肘狠狠向后一顶,
正中他的软肋。周建斌闷哼一声,疼得弯下了腰。我学过几年的女子防身术,
对付他这种外强中干的草包,绰绰有余。“周建斌,嘴巴放干净点。”我甩了甩手,
活动着手腕,“再敢动手,我就让你尝尝什么叫‘脱臼’。”我的眼神太冷,
周建斌被我看得心里发毛,一时间竟然不敢再上前。顾知秋扶着他,
色厉内荏地叫道:“顾知夏,你别得意!你现在没钱没粮票,我看你怎么活下去!
”“这就不劳你们费心了。”我拉开门,做了个“请”的手势,“慢走,不送。”他们走后,
我看着空荡荡的屋子,确实感到了生存的压力。原主的所有积蓄都被骗光了,
现在我身无分文,唯一的财产就是这个破旧的铺盖卷。当务之急,是解决吃饭问题。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我以为又是周建斌他们,不耐烦地拉开门,
却看到一张陌生的,却异常英俊的脸。男人很高,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肩宽腰窄,
浑身都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冷冽气息。他的五官像刀刻一样,深邃立体,只是那双眼睛,
黑沉沉的,像古井,毫无波澜。“有事?”我问。男人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瞬,
然后递过来一个粗瓷碗。碗里,是半碗金黄的小米粥,上面还卧着一个白生生的荷包蛋。
“给我的?”我有些意外。男人“嗯”了一声,算是回答。他的声音,和他的人一样,
又冷又硬。我这才想起来,他是我邻居,叫陆时晏,是刚从部队退役回来的军官。听说,
他在战场上杀过人,性子孤僻,村里人都有些怕他。“为什么?”我问。
陆时晏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言简意赅地吐出两个字:“你饿。
”我确实饿了。从昨天到现在,我滴水未进。我没有矫情,接过了碗:“谢谢。
”就在我准备关门的时候,陆时晏突然又开口了。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别扭。
“那个……同志。”“嗯?”我回头。陆时晏的目光有些闪躲,
耳根也泛起了一层可疑的红色。他沉默了半天,才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压低了声音,
飞快地说道:“我……我**上长了个东西,**辣地疼,你能……帮我看看不?
”03我端着碗,愣在原地。**上……长了个东西?我上上下下打量着眼前这个男人。
一米八几的大高个,一身的正气,表情冷得像冰雕,耳根却红得能滴血。这反差,
有点……可爱?我清了清嗓子,努力让自己的表情显得专业一点:“什么症状?长在哪?
长了多久了?”作为一名专业的外科医生,职业病让我瞬间进入了问诊模式。
陆时晏被我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更窘迫了,眼神飘忽,就是不看我。“就……就那里,
”他含糊不清地说,“好几天了,又肿又疼,坐都坐不下。”我了然。根据他的描述,
十有八九是肛周脓肿。这在七十年代的农村很常见,卫生条件差,加上饮食辛辣,
很容易诱发。“我是医生。”我说。陆时晏的眼睛瞬间亮了一下,
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你……你真能治?”“能。”我点头,“不过我需要工具,
而且你这里……不方便。”我环顾了一下他家徒四壁的屋子,除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
什么都没有。陆时晏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沉默了片刻,说:“去我家。
”我跟着陆时晏来到他家。他家就在我隔壁,一个独立的泥坯小院,收拾得干干净净。
屋里的陈设也很简单,但比我那漏风的知青点强多了。“你等一下。”陆时晏说完,
就钻进了里屋。很快,他拿着一个木箱子出来,打开,里面竟然是一套崭新的手术器械。
虽然是最基础的几样,但在这种地方,已经算是顶级装备了。“部队发的。”他解释道。
我点点头,心里有了底。“去床上趴着,裤子脱了。”我一边用酒精给器械消毒,
一边头也不抬地吩咐。身后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半天没有动静。我回头,
就看见陆时晏僵硬地站在原地,脸已经红到了脖子根。我这才反应过来,我的要求,
对于一个思想保守的七十年代男人来说,确实有点……惊世骇俗。“我是医生。
”我再次强调,“在我眼里,没有性别之分,只有病人。”或许是我坦然的态度感染了他,
陆时晏终于咬了咬牙,转过身,磨磨蹭蹭地解开了裤腰带。我走过去,
戴上消过毒的橡胶手指套,轻轻分开他的臀部。情况比我想象的要严重。脓肿的范围很大,
已经出现了破溃的迹象,周围的皮肤红肿、发烫,显然感染不轻。“有点疼,你忍着点。
”我用食指在他的患处轻轻按压,探查脓腔的深度和范围。指尖传来的波动感,
让我确定了切开引流的最佳位置。陆时晏的身体绷得像一块石头,额头上青筋暴起,
却硬是咬着牙,一声没吭。检查完毕,我直起身,对他说:“是肛周脓肿,
需要立刻切开排脓,不然会越来越严重,甚至引发败血症。”“败血症?
”陆时晏显然没听过这个词。“简单来说,就是要命。”陆时晏的脸色白了白。
“你……你有把握吗?”他问。“百分之百。”我回答得毫不犹豫。这种小手术,对我来说,
比切白菜还简单。我的自信,给了他莫大的勇气。“好,我相信你。”他重新趴好,
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动手吧。”我不再废话,拿起手术刀,对准脓肿最薄弱的位置,
快、准、狠地划下。一股混杂着血和脓的液体,瞬间喷涌而出。陆时晏闷哼一声,
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我迅速用纱布吸干脓液,然后用探针深入脓腔,
探查并分离里面的间隔,确保引流通畅。整个过程,我做得干净利落,没有一丝拖泥带水。
处理完伤口,我用盐水纱布填塞引流,然后盖上干净的敷料,用胶布固定好。“好了。
”我摘下手套,长出了一口气,“这几天注意换药,不要吃辛辣的东西,很快就会好。
”我收拾着东西,准备离开,身后传来陆时晏沙哑的声音。“谢谢。”我回头,
看见他已经坐了起来,正定定地看着我。他的眼神很复杂,有感激,有震惊,
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情绪。“不用客气。”我说,“医药费……就当是你那碗粥的谢礼了。
”说完,我拿起我的东西,走出了他的家。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
第二天一早,我一开门,就看见陆时晏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只还在扑腾的老母鸡,
和一篮子鸡蛋。他看见我,脸又红了。“这个……给你补身体。”他把东西塞到我手里,
转身就想走。“等等。”我叫住他。我看着手里的鸡和蛋,有些哭笑不得。这个男人,
还真是实在得可爱。“陆时晏,”我看着他,“你是不是……喜欢我?
”04陆时晏的身体猛地一僵,像被人点了穴。他背对着我,我看不见他的表情,
但那瞬间绷直的背脊,已经暴露了他内心的不平静。空气仿佛凝固了。过了好半天,
他才缓缓转过身。他的脸,已经不能用“红”来形容了,简直像是被火烧过一样,
连脖子都变成了深红色。“我……我没有!”他几乎是吼出来的,声音又大又急,
像是在掩饰什么。“哦?”我挑了挑眉,故意逗他,“没有你脸红什么?
没有你大清早给我送鸡送蛋?”“我……我是为了感谢你!”他梗着脖子,
眼神却不敢跟我对视,“你治好了我的病,我给你送点东西,不是应该的吗?”“应该的。
”我点点头,煞有介事地说,“不过,我们村里,一般只有提亲的时候,才会送这么重的礼。
”陆时晏的脸,“腾”的一下,更红了。他张了张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最后只能憋出一句:“你……你一个女同志,怎么说话这么……这么不害臊!”说完,
他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转身落荒而逃。看着他仓皇的背影,我忍不住笑出了声。这个男人,
真是纯情得让人想欺负。我提着鸡和蛋回到屋里,心情大好。有了这些东西,
我短时间内的吃饭问题,总算是解决了。我把鸡圈在院子里,鸡蛋小心翼翼地放好。
做完这一切,我坐在桌边,开始认真思考未来的路。坐吃山空肯定不行,
我必须找到一个能长久挣钱的法子。我的专业是西医,但在缺医少药的七十年代,
西医的施展空间有限。反倒是中医,更受欢迎。好在,我大学时,因为兴趣,选修过中医,
还跟着一位老教授学过一段时间,虽然比不上专业的,但看一些常见的头疼脑热,
还是没问题的。最重要的是,我脑子里,有无数张经过现代医学验证过的,
行之有效的中药方剂。这就是我最大的金手指。打定主意,我准备第二天就上山去采些草药。
没想到,计划赶不上变化。当天下午,村里就出事了。村长的孙子,小石头,突然上吐下泻,
高烧不退,眼看着就要不行了。村里的赤脚医生看了,说是中邪了,要请神婆来跳大神。
村长急得团团转,正准备去请神婆,我找上了门。“村长,”我开门见山,“让我试试吧,
我能治好小石头。”村长看着我,一脸的不信任:“你?一个城里来的女娃娃,会看病?
”“顾知青,你就别添乱了!”旁边的人也跟着劝。我没有理会他们,只是看着村长,
一字一句地说:“如果我治不好,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如果我治好了,我只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我要在村里开一个卫生所。”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在村里开卫生所?她以为她是谁?村长也皱起了眉头,显然觉得我是在胡闹。“村长,
”我加重了语气,“小石头等不起了。”这句话,终于让村长动摇了。他看着我,
又看了看屋里气若游丝的孙子,最后咬了咬牙:“好!我就让你试试!你要是敢耍花样,
我扒了你的皮!”我走进屋,一股酸臭味扑面而来。小石头躺在床上,小脸烧得通红,
嘴唇干裂,已经陷入了半昏迷状态。我上前给他做了个简单的检查,听了心肺,按了腹部。
典型的急性肠胃炎,伴有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如果不及时处理,确实会有生命危险。“去,
给我准备一碗温水,加一勺盐,一勺糖。”我吩咐道。村长的儿媳妇,也就是小石头的娘,
将信将疑地照做了。我用勺子,一点一点地把自制的“口服补液盐”喂给小石头。然后,
我拿出随身携带的银针。这是我从陆时晏那里“借”来的,他那套器械里,正好有一包。
看到我拿出明晃晃的银针,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你……你要干什么?
”小石头的娘惊恐地护住儿子。“针灸。”我言简意赅,“放心,死不了。”说完,
我不顾她的阻拦,捏住小石头的手,找准合谷穴,快准狠地刺了下去。接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