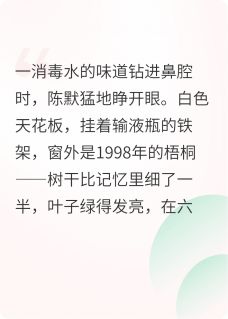
一消毒水的味道钻进鼻腔时,陈默猛地睁开眼。白色天花板,挂着输液瓶的铁架,
窗外是1998年的梧桐——树干比记忆里细了一半,叶子绿得发亮,
在六月的风里簌簌作响。他动了动手指,输液针头刺在手背的痛感清晰得不像话。
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掉漆的搪瓷缸,底下压着张纸条,是护士的字迹:302床陈默,
阑尾炎术后第二天,家属未联系上。家属。陈默的喉咙发紧,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他记得自己不是在医院,是在城郊的老房子里,守着林晚的遗像喝了半瓶农药。
她走的第三年,胃癌晚期,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最后弥留时拉着他的手说:“陈默,
要是有下辈子,别再遇见我了。”他当时哭得像个傻子,说不出话,只知道点头。
可真到了她走后,才发现活着比死更难。房贷没还完,她的病历本堆了半箱,
衣柜里还挂着她没来得及穿的羊绒衫,他怎么也过不去那个坎。没想到一睁眼,
竟然回到了24岁。这一年,他刚大学毕业,在设计院实习,住单位宿舍。
林晚是同系的师妹,比他小两届,还在念大三。他们是在系里的迎新晚会上认识的,
他弹吉他,她唱《后来》,眼睛亮得像装了星星。也是这一年夏天,他急性阑尾炎住院,
林晚每天下课就往医院跑,给他带食堂的小米粥,用保温桶装着,怕凉了揣在怀里。
就是那次住院,他跟她表了白,在病房外的梧桐树下,她红着脸点头,
发梢还沾着阳光的温度。前世的这个时候,他应该正盼着她来,心里像揣了只兔子。可现在,
陈默盯着输液管里缓缓滴落的药水,只觉得心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疼得喘不过气。
他想起林晚最后躺在病床上的样子,化疗掉光了头发,笑起来嘴角会扯动皱纹里的药渍。
她总说:“陈默,我不后悔跟你结婚,就是觉得累。”累。这个词像针一样扎进他心里。
是啊,她太累了。刚结婚时他们挤在15平米的出租屋,冬天没有暖气,她冻得手脚生冻疮,
却笑着说比宿舍暖和;他创业失败欠了债,她瞒着家里偷偷去做**,
晚上回来还要给他煮面条;后来日子好点了,他应酬喝得酩酊大醉,回家就对她发脾气,
嫌她菜做咸了,嫌她电话打得勤了……他总以为还有时间补偿,却忘了人是会被磋磨耗尽的。
“302床,该换药了。”护士推门进来,打断了他的思绪。陈默收回目光,
声音哑得厉害:“护士,我的手机能借我用一下吗?
”护士递过一个老式座机:“只能打内线,外线得去楼下。”他拨了宿舍的电话,
同屋的李哲接的:“默子?你醒了?我正想找你呢,林晚师妹刚才还来电话,
问你情况怎么样。”陈默握着听筒的手指收紧:“跟她说……我没事,不用来了。”“啊?
”李哲愣了一下,“人家特意问了好几次,你这……”“就说我家里人来了,不方便。
”陈默打断他,语气硬得像石头。挂了电话,他靠在床头,看着窗外的梧桐叶发呆。林晚,
这辈子,我听你的。别再遇见了。二出院那天,陈默特意绕开了去学校的路。
前世林晚是踩着下课铃来的,穿一条浅蓝色的连衣裙,手里拎着个布袋子,
里面装着她绣了一半的平安符。他记得自己当时还笑话她老土,
她却认真地说:“书上说这个能保平安。”现在想来,那些被他嗤之以鼻的笨拙心意,
都是她捧出来的滚烫真心。他回了宿舍,李哲正在收拾东西,
见他回来赶紧迎上来:“你可算回来了!林晚师妹昨天又来电话了,我按你说的搪塞过去了,
不过她好像不太高兴。”陈默点点头,没说话,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他向单位申请了外派,
去邻市的项目组,明天一早就走。“你疯了?”李哲瞪大眼睛,“那项目组在山沟里,
条件差得很,你实习刚转正,这时候走不是自毁前程吗?
”陈默叠着衣服的手顿了顿:“我想换个环境。”他没说的是,他必须走。
这座城市到处都是林晚的影子,图书馆靠窗的位置,食堂三号窗口,
操场边的看台……只要待在这里,他怕自己忍不住又要走向她。夜里,陈默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睡不着。手机突然响了,是个陌生号码,他犹豫了一下接起来。“喂,
是陈默师兄吗?”女孩的声音带着点怯生生的试探,像羽毛轻轻扫过心尖。
陈默的呼吸猛地一滞,握着手机的手开始发抖。是林晚。他记得这个号码,
是她用了四年的校园卡,后来工作了还一直留着,直到病重时才注销。“我是。
”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听说你出院了,没事了吧?”她的声音松了口气,
“我昨天去医院,护士说你家里人接你走了,我……”“我挺好的。”陈默打断她,
指尖冰凉,“还有事吗?没事我先挂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传来她低低的声音:“没事了,师兄你好好休息。”“嗯。”他几乎是立刻挂断了电话,
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像是要挣脱出来。他靠在墙上,大口喘着气,眼眶烫得厉害。
他好像能看到电话那头的林晚,肯定是皱着眉,有点委屈,又有点不知所措。
就像前世无数次被他冷落时那样,总是先低头的那个。对不起啊,林晚。这一世,
就让我做那个狠心的人吧。三邻市的项目组确实偏僻,在半山腰的工地上搭了几排板房,
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陈默把所有精力都扑在工作上,画图、跑现场、盯进度,
每天忙到倒头就睡,不给自己留一点胡思乱想的时间。李哲偶尔会给他打电话,说学校的事。
陈默总是小心翼翼地问:“林晚师妹最近怎么样?”“挺好的啊,拿了奖学金,
还参加了辩论赛,听说好多人追呢。”李哲的语气很轻松,“对了,她前段时间还问起你,
说你怎么突然走了,连个招呼都不打。”陈默握着电话,望着窗外的大山,
山风卷着尘土吹过板房,发出呜呜的声响。“我太忙了,忘了。”他说。挂了电话,
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照片。是去年系里的合影,他站在后排,林晚在前排,扎着马尾,
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他是后来才发现,她看镜头的时候,眼睛其实是往他这边瞟的。
他用指尖轻轻碰了碰照片上她的脸,低声说:“这样挺好的。”没有他,
她应该会有更轻松的人生吧。不用跟着他挤出租屋,不用为了柴米油盐精打细算,
不用在深夜等他回家,不用……最后落得一身病。项目做了两年,陈默成了技术骨干,
被调回了总公司。回去那天,他特意选了凌晨的火车,想避开早高峰的人群。走出火车站,
晨光熹微,街道上行人寥寥。他站在路边等出租车,忽然看到对面的公交站台上,
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林晚。她好像长高了些,头发留长了,扎成一个低马尾,
穿着简单的白T恤和牛仔裤,背着一个帆布包,手里拿着本考研词汇。她在等公交,
偶尔低头看看手表,阳光落在她脸上,绒毛都看得清清楚楚。陈默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
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躲到了一棵行道树后面。他看着她上了公交车,看着车子慢慢开走,
直到再也看不见,才缓缓直起身。胸口像是被掏空了一块,又酸又涩。原来真的可以,
像陌生人一样擦肩而过。四回总公司后,陈默搬进了单位分配的单身公寓。离学校很远,
离他们前世住过的出租屋也很远。他很少再听到林晚的消息,偶尔从以前的同学那里得知,
她考研成功了,还是本校的研究生,学的是她一直喜欢的现当代文学。有人组织同学聚会,
陈默找借口推脱了。他怕在聚会上遇见她,怕自己好不容易筑起的防线,
会在看到她眼睛的那一刻彻底崩塌。他开始学着自己做饭,学着整理房间,
学着在周末去爬山、去图书馆,像一个真正的独居者那样生活。
只是偶尔在超市看到打折的小米粥,会站在货架前愣很久。林晚以前总说,他胃不好,
要多喝小米粥养胃。2002年冬天,陈默去参加一个行业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