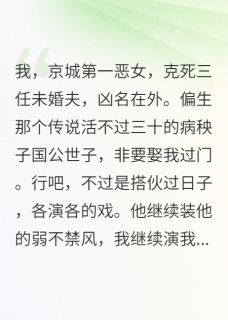
我,京城第一恶女,克死三任未婚夫,凶名在外。
偏生那个传说活不过三十的病秧子国公世子,非要娶我过门。行吧,不过是搭伙过日子,
各演各的戏。他继续装他的弱不禁风,我继续演我的嚣张跋扈。一年后拿钱和离,
他重获自由,我逍遥快活,两不相欠。谁知演着演着,他竟假戏真做,非要以身相许。
说好的逢场作戏,世子爷,你怎么能先动了心?1房门被人一脚踹开的时候,
我正被一个陌生的男人压在身下。他撕扯着我的嫁衣。布帛碎裂的声音,刺耳又清晰。门外,
我的婆母,当朝太夫人,领着乌泱泱一群人站在那里。她脸上是恰到好处的震惊,
眼底却藏着一丝得逞的精光。“孽障!”一声怒喝,响彻整个院子。
“我们侯府究竟是造了什么孽,竟娶了你这么个伤风败俗的东西!
”我身上的男人还在卖力地表演。他孔武有力,我被他禁锢着,动弹不得。
嫁衣被扯得七零八落,雪白的肩头暴露在微凉的空气里。真冷。我偏过头,目光越过人群,
落在了最后面那个姗姗来迟的身影上。我的新婚丈夫,卫国公府世子,京城第一药罐子,
卫谪。他披着一件单薄的外衣,面色苍白,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此刻,
他正用一种探究的眼神看着我,像是看一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戏。太夫人见他来了,
哭嚎得更起劲了。“我的儿啊,你看看,你看看你娶的好媳妇!”“这还没过头七,不,
这还没过洞房夜,就给你戴了这么大一顶绿帽子!”她一边说,一边向卫谪走去。
卫谪却没理她。他穿过人群,一步一步,走到了床边。屋子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
大家都在等着,等着看这位病秧子世子会如何处置我这个不贞的妻子。是休妻?还是沉塘?
他没有看地上那个还在演戏的男人。他的目光,自始至终,都落在我身上。
那双总是显得病气恹恹的眸子里,此刻竟像是燃着一团火。他俯下身。
冰凉的指尖轻轻划过我**的肩头。我浑身一僵。那触感,像是电流,
从他指尖窜遍我的四肢百骸。他的手指很凉,带着常年不散的药香,清苦又凛冽。他缓缓地,
一寸一寸地,拂过我的皮肤,像是在欣赏一件瓷器上的裂纹。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疼吗?”他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
我愣住了。他却笑了,那笑容苍白又脆弱,却带着一种惊心动魄的美感。
他拉起我凌乱的衣襟,慢条斯理地替我拢好。他的动作很慢,指腹有意无意地擦过我的锁骨。
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指尖的薄茧,和他身上传来的,令人心安的药香。暧昧的痒意,
从他触碰的每一寸肌肤蔓延开来。我的心跳,漏了一拍。他做完这一切,
才终于将目光转向地上那个男人。“演完了?”他淡淡地问。那男人浑身一抖,
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卫谪直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眼神冷得像冰。“我的人,
你也敢碰?”2我和卫谪的婚事,是全京城的笑话。一个,是克死三任未婚夫,
把亲爹气到中风,声名狼藉的相府嫡女。一个,是传闻中活不过三十岁,终日与汤药为伍,
病入膏肓的国公府世子。大家都说,我们是“恶锅配烂盖”,天造地设的一对。
我名声有多臭,我自己清楚。三岁那年,我将继母最爱的波斯猫扔进荷花池,
美其名曰“教它游泳”。十岁,我在御花园里,当着满朝文武的面,
扒了太傅家小公子的裤子。十五岁,我最后一任未婚夫,大理寺卿的宝贝儿子,
在与我郊游后,想不开,出家了。从此,京城再无人敢上门提亲。我爹看着我,
就像看着一个烫手山芋。直到太夫人亲自登门。她拉着我的手,情真意切。“好孩子,
我知道你受了委屈。”“实不相瞒,我家那个不成器的,顽劣得很,也就你这样的性子,
才能治得了他。”她态度诚恳,不像作假。继母在一旁帮腔,“眠儿的那些事,
太夫人想必都听说了?”“都知道。”太夫人点了点头,看向我的眼神,越发满意,
“我就喜欢眠儿这又虎又野的性子,和我年轻时一模一样。”我爹和我继母,
当场就想把我打包送走。他们不知道,太夫人来之前,卫谪就已偷偷找过我。
就在城外那间破庙。他穿着最普通的布衣,脸上带着病态的苍白,手里捏着个泥人,
一点点地打磨。“嫁给我。”他开门见山。“我需要一个名声足够差的女人,
帮我挡住府里那些牛鬼蛇神。”“作为回报,一年之后,我们和离。
我保你和**妹一生顺遂,万贯家财,任你挥霍。”“为什么是我?”“因为你够狠,
也够聪明。”他抬起眼,眸子黑得像墨,“最重要的是,你和我一样,
都想从这个牢笼里逃出去。”他把那个捏好的泥人递给我。那是个穿着铠甲,
英姿飒爽的女将军。是我妹妹,江月。她此时,正在千里之外的边关,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
我爹嫌她丢人,早已与她断绝关系。只有我,每个月都会偷偷给她送去银两和物资。这件事,
除了我的贴身丫鬟,无人知晓。卫谪却知道了。我看着他,他也在看着我。四目相对,
我们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同类的气息。孤独,隐忍,以及不甘。“成交。”于是,
我风风光光地嫁入了国公府。新婚之夜,我坐在婚床上,等来的不是我的新郎,
而是一个被下了药的陌生男人。还有一群“捉奸”的观众。领头的,
便是我那位“喜欢我喜欢得不得了”的婆母。她想用这种最恶毒的方式,毁了我,
也毁了卫谪。只可惜,她算错了一步。卫谪,他不是我的敌人。他是我,唯一的盟友。此刻,
我的盟友正慢条斯理地整理着自己的衣袖。他甚至还抽空咳嗽了两声,
仿佛刚才那句狠话耗尽了他所有力气。“来人。”他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喙的威严。
“把这个奸夫,拖出去乱棍打死。”“尸体,扔到我表妹芸**的院子里。
”3太夫人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芸**,是她的亲侄女,也是从小养在她身边的表**。
更是整个国公府里,最想嫁给卫谪的女人。“卫谪!你疯了!”太夫人尖叫起来。
“这……这事与芸儿有何关系!”卫谪抬起眼皮,淡淡地瞥了她一眼。“母亲,您年纪大了,
记性不好,儿子提醒您一句。”“这男人身上的迷情香,是西域贡品,整个京城,
只有皇商‘陈记’有售。”“而‘陈记’的东家,恰好是芸表妹的亲舅舅。”“您说,
巧不巧?”他每说一句,太夫人的脸色就白一分。那个被按在地上的男人,也开始拼命磕头。
“世子饶命!世子饶命啊!”“是芸**!是芸**指使我这么做的!”“她说事成之后,
就给我一千两银子,让我远走高飞!”“我再也不敢了!”人证物证俱在。太夫人一张老脸,
青白交加,像是开了个染坊。她想反驳,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男人,
被两个高大的家丁拖了出去。很快,隔壁院子就传来了芸**撕心裂肺的哭喊,
以及家丁行刑时,棍棒落肉的闷响。一声又一声,敲在每个人的心上。看热闹的人群,
此刻早已噤若寒蝉。他们看着卫谪的眼神,充满了恐惧和敬畏。
仿佛第一次认识这位传说中手无缚鸡之力的病世子。**在床头,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切。
卫谪这一手“杀鸡儆猴”,玩得可真漂亮。他不仅洗脱了我的嫌疑,
还顺手拔掉了太夫人安插在府里的一颗重要棋子。最重要的是,他立了威。从今往后,
这国公府的后院,怕是没人再敢轻易招惹我们这对“病秧子夫妻”了。风波平息,人群散去。
屋子里只剩下我和卫谪。还有满地的狼藉。他走到我面前,又咳嗽了起来。这一次,
咳得撕心裂肺,仿佛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我皱了皱眉,从床上下来,倒了杯温水递给他。
“谢了。”他接过水杯,一饮而尽。温热的液体滑过喉咙,似乎让他舒服了不少。他抬起头,
看向我。烛光下,他的脸比刚才更白了,唇上却带着一丝不正常的红。像雪地里开出的红梅,
脆弱又妖异。“我刚才,是不是很吓人?”他问。我摇了摇头。“不,你刚才,帅呆了。
”他愣了一下,随即低低地笑了起来。笑声牵动了伤口,他又开始咳。我走上前,
轻轻拍着他的背,帮他顺气。他的身体很瘦,隔着薄薄的衣料,
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背上凸起的蝴蝶骨。像一只折翼的蝴蝶,挣扎着想要飞翔。我的心,
莫名地软了一下。他的咳嗽渐渐平息。屋子里很安静,只剩下彼此的呼吸声。
我闻到他身上那股清苦的药香,比任何熏香都好闻。我的手还搭在他的背上。他的身体,
微微有些发烫。气氛,在这一刻,变得有些微妙。“江眠。”他忽然开口,声音有些喑哑。
“嗯?”“你的嫁衣,破了。”4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确实,胸前被撕开一道大口子,
春光乍泄。刚才只顾着看戏,竟没发现。真是丢人。我的脸颊,瞬间有些发烫。
“你……”我刚想说点什么,卫谪却忽然伸出手,将我揽入怀中。他的怀抱,并不温暖,
甚至有些冰凉。但却出奇地让人安心。他身上那股清冽的药香,将我整个人包裹。
我听见他有力的心跳,一下,又一下,敲在我的耳膜上。我的脸,贴着他微凉的胸膛。
他的下巴,轻轻抵在我的发顶。“别怕。”他低声说。“有我在,没人能欺负你。
”他的声音很轻,却像一颗石子,在我心湖里投下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我不是个轻易会感动的人。这些年,我听过太多虚情假意的甜言蜜语。
也见过太多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可这一刻,我却有些信了。信眼前这个看似弱不禁风,
实则心思缜密的男人。我抬起手,轻轻环住他的腰。他身体一僵,随即放松下来。
他抱得更紧了。我们就像两只在寒冬里互相取暖的刺猬。小心翼翼地靠近,
又害怕伤害到对方。许久,他才松开我。他脱下自己的外衣,披在我身上。宽大的衣袍,
带着他的体温和药香,将我整个人笼罩。“夜深了,早点睡吧。”他说完,转身就要走。
“你去哪?”我下意识地拉住他的衣袖。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有些复杂。“我去书房。
”“新婚之夜,你睡书房?”“不然呢?”他挑了挑眉,“难道你想让我留下来?
”他的语气,带着一丝调侃。我的脸,又红了。“我……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他步步紧逼。我被他问得哑口无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迈着虚浮的脚步,消失在夜色里。这个男人,真是个妖孽。时而脆弱得像一碰就碎的瓷器。
时而又强大得让人心惊。他总能轻易地撩拨我的心弦,又在我快要沉沦时,抽身而去。
我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和床上那一片狼藉。心里,却不像刚开始那么慌乱了。我知道,
从今天起,我的生活将翻开新的一页。而这一页的开篇,写着两个字。卫谪。第二天,
我是在一阵喧闹声中醒来的。芸**的院子里,依旧鬼哭狼嚎。听说,那个奸夫,
昨晚被活活打死了。尸体,就扔在她闺房门口。芸**受了**,疯了。
太夫人一大早就请了京城所有名医,却都束手无策。整个国公府,都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中。
而我这个始作俑者,却优哉游哉地坐在梳妆台前,任由丫鬟替我梳妆。“少夫人,
您今天可真美。”丫鬟春桃一边替我描眉,一边由衷地赞叹。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眉如远山,眼若秋水。褪去了少女的青涩,多了一丝妇人的妩媚。确实,比以前更好看了。
“对了,世子呢?”“世子一早就去给太夫人请安了,现在应该在书房。”我点了点头,
心里有了盘算。5我端着一碗刚炖好的燕窝,去了书房。卫谪正坐在窗边看书。
晨光透过窗棂,在他身上镀上一层金色的光晕。他看得入神,连我进来都没发现。
我走到他面前,将燕窝放在桌上。“世子殿下,该喝药了。”我学着丫鬟的口气,故意逗他。
他这才抬起头。看到是我,他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你怎么来了?”“来看看你死了没有。
”“让你失望了,还活着。”他端起燕窝,喝了一口。“味道不错。”“那是自然,
我亲手炖的。”我一边说,一边打量着他的书房。很大,很空。除了书,还是书。
从经史子集,到兵法谋略,应有尽有。真难想象,一个传闻中“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病秧子,竟会看这些书。“你在看什么?”我凑过去,想看看他手里的书。
他却不动声色地将书合上,藏在身后。“没什么,一本闲书罢了。”他越是这样,
我越是好奇。我绕到他身后,伸手去抢。他侧身一躲,我扑了个空,整个人重心不稳,
朝他倒去。“小心!”他惊呼一声,伸手揽住我的腰。我一头撞进他怀里。鼻尖,
是他身上熟悉的药香。我的手,不偏不倚,正好按在他胸口。隔着衣料,
我能感受到他结实的肌肉和有力的心跳。他的脸,近在咫尺。
我甚至能看清他脸上细小的绒毛。他的皮肤,比女人还好。我的脸,又开始发烫。
“你……你放开我。”我的声音,有些发颤。他却没有动,只是低头看着我,眼神幽深。
“江眠,你是不是故意的?”“我……我才没有!”“那你脸红什么?”“我……我热的!
”我死不承认。他低低地笑了,胸腔微微震动。“是吗?”“那为什么,你的心跳这么快?
”他的手,覆上我按在他胸口的手。他的掌心,很热。烫得我一个激灵,猛地抽回手。
我从他怀里挣脱出来,后退了好几步,与他保持安全距离。“登徒子!”我瞪着他,
恶狠狠地说。他却笑得更欢了。“我们是夫妻,做点亲密的事情,不叫登徒子,叫情趣。
”“谁……谁跟你讲情趣!”我被他气得说不出话。这个男人,脸皮怎么这么厚!“好了,
不逗你了。”他收起笑容,从身后拿出那本书,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封面竟是空白的。
我疑惑地看着他。他示意我打开。我翻开第一页,瞳孔猛地一缩。那不是什么闲书。
那是一本账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国公府这些年来,所有灰色收入的来源和去向。
每一笔,都触目惊心。而其中最大的一笔,指向的,就是当朝太后——太夫人的亲姐姐。
“你……”我震惊地看着他,说不出话来。“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要娶你了吗?
”他看着我,眼神前所未有的认真。“江眠,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6“扳倒太后?
”我合上账本,觉得有些荒谬。“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可是太后。皇帝的亲娘。
权倾朝野,一手遮天。扳倒她,谈何容易?“我知道。”卫谪的表情,依旧平静。“所以,
我需要你的帮助。”“我能帮你什么?”“你的名声。”“我的名声?”我自嘲地笑了笑,
“我的名声,早就臭不可闻了。”“没错。”卫谪点了点头,“我需要的,
就是你这‘臭不可闻’的名声。”“国公府这潭水,太深了。”“我需要一条鲶鱼,
把它搅浑。”“而你,江眠,就是最好的人选。”“你够恶,够狠,够不按常理出牌。
”“只有你,才能在这后院里,掀起一场真正的风暴。”“只有把水搅浑了,
我才有机会找到他们的破绽。”我沉默了。我不得不承认,卫谪说得有道理。我的“恶名”,
确实是我最好的保护色。也是我最锋利的武器。“事成之后,你想要什么?”他问。
“我妹妹。”我看着他,一字一顿地说,“我要我妹妹,能光明正大地活在阳光下。
”“不再被人指指点点,不再被家族视为耻辱。”“我要她,封侯拜将,光宗耀祖。
”卫谪看着我,许久,才缓缓点头。“好。”“我答应你。”我们再次达成了交易。
只不过这一次,赌注更大,也更危险。一旦输了,就是万劫不复。接下来的日子,
我开始正式接管国公府的后院。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规矩。我将所有下人召集到院子里,
当着所有人的面,将几个手脚不干净,阳奉阴违的老嬷嬷,狠狠地打了一顿板子。杀鸡儆猴。
效果显著。从那以后,府里的下人,看到我就像老鼠看到猫。我让他们往东,
他们绝不敢往西。府里的风气,为之一清。太夫人气得卧床不起,却也拿我没办法。
因为卫谪,始终站在我这边。他虽然不管事,但只要我开口,他都会无条件地支持我。
我们就像一对配合默契的搭档。我负责在台前唱黑脸,搅动风云。他负责在幕后坐镇,
稳固后方。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直到那天,我那个出家当和尚的前未婚夫,
忽然还俗了。不仅还俗了,还摇身一变,成了皇帝身边最得宠的红人,锦衣卫指挥使。
穆容熙。他回京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国公府“拜访”我。彼时,
我正在院子里教训一个新来的,不知天高地厚的丫鬟。穆容熙就那么穿着一身飞鱼服,
带着一群锦衣卫,浩浩荡荡地走了进来。他看着我,笑了。那笑容,阴森又怨毒。“江眠。
”“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啊?”7我看着穆容熙那张写满“小人得志”的脸,
差点没忍住笑出声。“哟,这不是穆公子吗?”“怎么,佛祖面前的青灯不够亮,
还是木鱼敲得不够响?”“怎么有空,来我这凡尘俗地了?”我说话向来不留情面。
尤其对这种,我亲手送上西天的“故人”。穆容熙的脸,果然黑了。他身后的锦衣卫,
也都齐刷刷地拔出了绣春刀。气氛,瞬间剑拔弩张。我却一点也不怕。我慢悠悠地拿起剪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