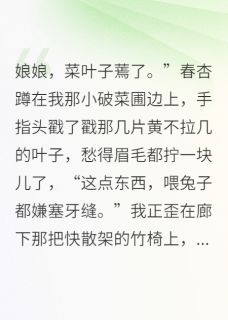
果然,消停日子没过两天。
这天下午,我正琢磨着要不要把墙角那几颗野蘑菇采了炖汤,破门又一次被推开。这次来的阵仗更大。
领头的是个穿着深紫色宫装的老嬷嬷,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绷得像块棺材板,眼神锐利得像刀子。她身后跟着四个膀大腰圆的粗使宫女,还有两个端着托盘的太监。托盘上盖着明黄色的绸布,看不清下面是什么。
这架势,来者不善。
老嬷嬷径直走到我面前,目光如电,在我身上扫了几个来回,那眼神,像是在评估一件待处理的物品。她没行礼,声音平板无波,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欧阳宝林,皇后娘娘懿旨。”
我心里咯噔一下。皇后?她找**嘛?我这冷宫咸鱼,碍着她什么眼了?
我赶紧拉着春杏跪下。春杏吓得直哆嗦。
“宝林欧阳氏,性情温顺,然体弱多病,久居清辉阁,恐非长久之计。”老嬷嬷的声音在空旷的院子里回荡,冷冰冰的,“为宝林玉体康泰计,皇后娘娘特赐‘福泽深厚’之地静养,望宝林好自为之。”
说完,她一挥手。后面一个太监掀开了托盘上的明黄绸布。
托盘上,赫然放着一卷厚厚的、颜色灰扑扑的经书。书皮上三个大字:《地藏经》。
另一个托盘上,是一串乌沉沉、油光发亮的紫檀木佛珠。
轰隆!我感觉又是一个炸雷劈在头顶!
赐《地藏经》和佛珠?还“福泽深厚”之地静养?这什么意思?这是明晃晃地告诉我:你这人晦气,不吉利,离皇上远点,去念经吧,别出来祸害人了!
皇后这招,比皇帝侍寝还狠!侍寝好歹是暂时的,这直接给我定性了!贴上“晦气”、“需静养”的标签,等于彻底把我钉死在冷宫,甚至可能……下一步就是暗示我去庙里当尼姑了!
“宝林,谢恩吧。”老嬷嬷的声音毫无起伏。
春杏已经吓得快瘫软在地了。我跪在地上,脑子里一片空白,手心冰凉。怎么办?谢恩?接了这经书和佛珠,就等于认了这顶“晦气”的帽子,这辈子别想翻身了!不接?那就是抗旨不遵,皇后立刻就能捏死我!
冷汗顺着我的鬓角流下来。我盯着那卷厚厚的《地藏经》,乌木佛珠在阳光下泛着冰冷的光泽。
时间仿佛凝固了。老嬷嬷的眼神像冰锥子一样扎在我身上。那四个粗使宫女往前挪了半步,无声地施加着压力。
清辉阁的风似乎都停了,只剩下我擂鼓般的心跳声。
“奴婢……”我深吸一口气,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把头深深埋下去,额头几乎碰到冰冷的、带着泥土味的地面,声音带着无法抑制的颤抖,听起来可怜又卑微,“奴婢……谢皇后娘娘恩典!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老嬷嬷鼻腔里发出一声极轻的哼,像是预料之中。她示意太监把托盘递到春杏面前。春杏抖着手接过了那沉重的经书和冰凉的佛珠。
“宝林好生诵经祈福,静心休养。”老嬷嬷丢下这句话,带着她那群人,如来时一般,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破门再次合上,隔绝了外面的一切。
我瘫坐在冰冷的地上,半天没爬起来。春杏抱着那卷《地藏经》和佛珠,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娘娘……这可怎么办啊……皇后娘娘这是……这是要把咱们往死路上逼啊!”
我望着头顶那片四四方方、灰蒙蒙的天空,第一次觉得这冷宫的院墙,高得让人窒息。咸鱼?呵呵,咸鱼在绝对的力量面前,连被煎的资格都没有,人家直接把你扔进咸菜缸里腌着,永世不得翻身!
“哭什么?”我抹了把脸,声音有点哑,但异常平静,“收起来吧。”
“收……收起来?”春杏抽噎着,不解地看着我。
“嗯,收起来。”我扶着旁边的柱子,慢慢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土,“皇后娘娘‘赐’的,是福气,得供着。”
我走到春杏面前,拿起那串沉甸甸的紫檀木佛珠,入手冰凉刺骨。我掂了掂,嘴角扯出一个没什么温度的弧度:“这珠子不错,够硬。哪天要是饿极了,磨成粉冲水喝,兴许能顶饿。”
春杏被我这话吓得忘了哭,眼睛瞪得溜圆。
“至于这本……”我拿起那卷厚厚的《地藏经》,随意地翻了翻,密密麻麻的梵文看得我眼晕,“留着。冬天冷的时候,撕两页下来引火,应该比干柴好使。”
春杏彻底傻了,张着嘴,看看佛珠,又看看经书,再看看我,仿佛不认识我了。
我把佛珠套回她手腕上,把经书塞回她怀里。“收好。记住,这是皇后娘娘的‘恩典’。”我加重了“恩典”两个字,语气平淡得可怕。
皇后这一手,是警告,也是绝杀。她成功地在所有人心里,给我欧阳茶打上了“晦气”、“不祥”、“需要诵经祈福”的烙印。以后别说侍寝,恐怕这清辉阁,真的要成为我的活死人墓了。
行,你们都觉得我晦气是吧?那我就把这“晦气”坐实了!我不仅要晦气,我还要晦气得名正言顺,晦气得理直气壮!
日子似乎又回到了原点,甚至更糟。
皇后娘娘“赐经赐珠”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整个后宫。原本就无人问津的清辉阁,这下彻底成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神之地。连御膳房那点本就不多的份例,也越发敷衍,送来的东西越来越不像样。
这天,送来的米粮里掺的沙子,多得快能筛出半碗来。几根蔫黄的菜叶子,几块硬得像石头的黑面馍馍,还有一小碟咸得齁死人的酱菜。
春杏气得脸通红,跟送膳的小太监理论:“这米都发霉了!还有这么多沙子!这叫人怎么吃?”
那小太监翻了个白眼,尖着嗓子:“有的吃就不错了!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晦气冲天,没断了你们的嚼用,那是皇后娘娘慈悲!爱吃不吃!”说完,把食盒往地上一撂,拍拍**走了。
春杏气得直跺脚,眼圈又红了:“娘娘!他们欺人太甚!”
我正坐在门槛上,就着最后一点天光,试图把一件旧衣服的破洞补上,针脚歪歪扭扭。闻言,头也没抬:“捡起来,洗洗还能吃。沙子筛掉,米多淘几遍。馍馍掰碎了泡水。酱菜省着点,齁咸,一点点就够下饭了。”
“娘娘!”春杏不可置信地看着我,“您就由着他们这么作践咱们?”
“不然呢?”我放下针线,揉了揉发酸的眼睛,看向她,“冲出去跟他们打一架?还是跪在皇后宫门口哭诉?有用吗?”
春杏噎住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省点力气吧。”我站起身,拍拍**上的灰,“去,把米筛了,多淘几遍水。我去看看那点野菜,还能不能摘点嫩的。”
日子再难,饭总得吃。咸鱼也得活着不是?
只是,这“晦气”的标签,算是彻底焊死在我脑门上了。连带着,清辉阁也成了宫里的一个笑话,一个禁忌。偶尔有宫女太监远远路过,都会指指点点,然后快步绕开。
我成了名副其实的“瘟神”。
也好。瘟神就瘟神吧。至少,清净。
时间就在这种近乎凝固的“清净”中,不紧不慢地滑过。外面宫墙里的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争奇斗艳,热闹非凡,仿佛与我隔着一个世界。
我在这方小小的、破败的院子里,种我那几棵永远长不好的菜,补我那永远补不完的破衣服,饿了就啃两口硬馍馍,渴了就喝点井水,困了就躺竹椅上晒太阳发呆。春杏从一开始的气愤、不甘、偷偷抹眼泪,到后来也渐渐麻木了,只是更加沉默地操持着这清苦的日子。
皇后娘娘的“恩典”被我束之高阁。那本《地藏经》垫在柜子腿底下,刚好能稳住那个总是摇晃的破柜子。那串紫檀佛珠,则被我挂在窗棂上,风吹过时,偶尔会发出沉闷的碰撞声,权当个风铃听。
晦气?不祥?我欧阳茶不在乎。我只想在这**棺材里,安安稳稳地躺平,熬到油尽灯枯的那一天。最好无声无息,像一粒尘埃。
然而,命运这玩意儿,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在你以为尘埃落定的时候,给你来个惊天大逆转。
那是一个跟往常没什么不同的午后。太阳懒洋洋地挂在天上,晒得人昏昏欲睡。我正歪在竹椅上打盹,春杏在院子里吭哧吭哧地洗那几件补丁摞补丁的衣服。
突然,清辉阁那扇破门,第三次,被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近乎粗暴的方式撞开了!
“哐当!”一声巨响,震得门框上的灰簌簌往下掉。
我吓得一个激灵,差点从椅子上滚下来。春杏手里的棒槌“啪嗒”掉进洗衣盆里,溅起一片水花。
冲进来的不是太监,也不是宫女,而是几个穿着禁卫军甲胄、手持长矛的士兵!他们面色冷峻,眼神锐利如鹰,迅速占据了院子里的几个角落,一股肃杀之气瞬间弥漫开来。
紧接着,一个穿着总管太监服饰、面白无须、眼神却极其精明的老太监,在几个小太监的簇拥下,快步走了进来。他目光如电,扫视一圈,最后精准地落在我身上。
我心脏狂跳,手脚冰凉。这阵仗……不对劲!太不对劲了!出大事了!
“欧阳宝林?”总管太监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压。
我扶着椅子站起来,腿有点软,强作镇定:“是……是我。公公有何吩咐?”声音干涩得厉害。
总管太监面无表情地看着我,那眼神复杂极了,像是在看一件极其棘手、却又不得不处理的东西。他深吸一口气,用一种平板无波、却足以掀起惊涛骇浪的语调宣布:
“圣上驾崩了。”
轰——!!!
我脑子里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一片空白!
皇帝……死了?那个老皇帝,死了?
春杏“扑通”一声直接瘫软在地,面无人色。
总管太监的目光依旧牢牢锁着我,继续用那种毫无起伏的调子,扔下了第二颗、威力更大的炸弹:
“国不可一日无君。太子殿下已于灵前即位。”
哦,太子登基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还在巨大的震惊中没缓过神。
然后,我听到了我这辈子听过最荒谬、最离奇、最匪夷所思的话:
“新帝年幼,尚需长辈辅佐。先帝后宫,唯宝林欧阳氏,诞育之功……呃,”他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用词,眼神飘忽了一下,“福泽深厚,品性端方。经宗室大臣合议,太后娘娘(指先帝的皇后)懿旨,尊奉宝林欧阳氏为太后,移居慈宁宫,即刻启程!”
时间,空间,声音……所有的一切,仿佛都在这一刻凝固了。
我张着嘴,像个傻子一样,呆呆地看着总管太监那张一开一合的嘴。他后面好像还说了些什么“新帝仁孝”、“太后福泽庇佑”、“国朝之幸”之类的冠冕堂皇的话。
但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我的脑子里,只剩下那几个字在疯狂盘旋、轰鸣,如同魔音灌耳:
太后?
欧阳氏?
我?!
咸鱼……太后?!
“扑通!”这次,是我自己腿一软,结结实实地一**坐回了我的破竹椅上。竹椅不堪重负,发出“嘎吱”一声刺耳的**。
慈宁宫?太后?移居?启程?
我茫然地环顾四周:院子里半死不活的老槐树,墙角稀稀拉拉的野菜,廊下缺了口的粗瓷碗,还有春杏那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旧衣服泡在盆里……
再看看眼前:明晃晃的铠甲,寒光闪闪的长矛,总管太监那张严肃得能刮下霜的脸……
荒谬!太荒谬了!这比皇帝召我侍寝、皇后赐我佛经还要荒谬一万倍!
诞育之功?我连皇帝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过!福泽深厚?我脑门上还贴着皇后钦赐的“晦气”标签呢!品性端方?我这冷宫咸鱼,唯一的品性就是躺平!
这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错?他们是不是找错人了?清辉阁还有第二个姓欧阳的吗?
“太……太后娘娘?”总管太监见我半天没反应,只是傻愣愣地坐着,眼神空洞,忍不住提高了点音量,试探着提醒,“请娘娘……移驾?”
这一声“太后娘娘”,像一根针,猛地扎破了那层包裹着我的、名为“荒谬”的膜。一股极其复杂、难以言喻的情绪瞬间冲上我的天灵盖!
不是惊喜,不是惶恐,不是激动。
是愤怒!是巨大的、几乎要喷薄而出的荒谬感和……憋屈!
凭什么?!
凭什么把我扔冷宫自生自灭的时候,没人问过我一句?凭什么给我贴“晦气”标签、恨不得我烂死在这里的时候,没人管我死活?现在皇帝死了,太子太小,需要个吉祥物一样的太后摆在前面挡风遮雨、平衡势力了,就想起来我这个“福泽深厚”的咸鱼了?!
哦,因为我“晦气”?因为我“不祥”?所以正好用来克死那些不安分的?还是因为我家世低微、无依无靠,在朝中没有任何根基,最好拿捏?或者干脆就是抓阄抓出来的?!
一股邪火直冲脑门!我这咸鱼躺了两年,泥人也有三分土性!
我猛地从破竹椅上弹了起来!动作快得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总管太监和他身后那些禁卫军,显然也没料到我这“弱不禁风”的前冷宫弃妃能有这爆发力,都下意识地绷紧了身体,手按上了刀柄。
“太后娘娘?”总管太监的声音带着明显的警惕和疑惑。
